

興安:阿霞和她的草原
阿霞,我們內蒙古人很少用這樣的名字。問了本人才知道,“阿霞”源自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我也非常喜歡這個有蒙古血統的老頭兒)著名的中篇小說《阿霞》。后來人們叫得忘記了她的真名——賈翠霞。
第一次見阿霞是在內蒙古文化圈的大聚會上,應該是十年前,她與一個舞者表演了一支圓舞曲,驚艷了在場的人。我問身旁的好友路遠,美女何人?他目不轉睛地答我是《草原》的編輯,我由此記住了她。
差不多一年后,我來呼和浩特給魯迅文學院作家班內蒙班學員講課。下課后,阿霞主動找我,說她正在做一組國內作家的訪談,要我推薦幾位著名的作家。那時她已是編輯部主任,態度誠懇,容貌又姣好,我當然義不容辭。之后她來北京,在魯迅文學院高級研修班學習,我又經常去呼和浩特開會、講課,這樣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2016年,我受她之邀參加了《草原》的“鄂托克筆會”,她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隨和熱情的待人方式,讓我記憶深刻。那次會,她請來了好幾個文壇大腕——小說家王祥夫,詩人閻安、雷平陽,三個都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還有散文家鮑爾吉·原野(他不久也成了魯獎的贏家)。
那真是一次愉快之旅。有一個場景頗具象征意義,我們與會的所有人,在一條寬闊的草原公路上,兩邊是一簇簇高揚的芨芨草。我們時而坐在地上背靠背,時而大踏步地往前行走,沒有長幼之序,沒有編輯與作家之分,也沒有名家與新人之別,只朝著一個方向,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天真與喜悅。至于前方是什么,我們誰都不去想。這便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聚會,讓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上世紀80年代。那時候的阿霞可能只有七八歲,而此刻,我們這些老家伙已經被她以文學的名義撒在這片空曠的草原上,變得和她一樣年輕。
說起阿霞,還得聊聊“十閨蜜”,這是呼和浩特文學圈的一道風景。十個人平時不易湊齊,一旦全體出動,那肯定是遇上大日子了。所以,我與他們聚過多次,幾乎沒有一次全乎的時候。但是阿霞永遠都在,她也逐漸成為她們的核心之一。
十閨蜜的身份多與文學相關,有寫小說的,有寫散文的,有詩人,有記者,有編輯,有大學教授,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年齡從六零后到八零后,民族有漢、蒙古、鄂溫克。在這座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青色之城,他們彼此幫襯,互為綠葉,民主而平等,組合成了一叢讓人艷羨的草原姊妹之花。
如果認識了全部的十閨蜜,再單獨約見其中的某個人是要犯眾怒的。這句話不是她們告誡我的,而是我給自己定的規矩。但我還是被單獨接見了一次,對方就是阿霞。她那時已經是《草原》的副主編,主持工作。她知道我在《北京文學》當了15年編輯,做了4年副主編,后來一直做文學出版,并且還算個過得去的文學評論家。
我們在一家布里亞特蒙古餐廳專心地聊天。我當然毫無保留地給她建議和主意,因為我知道一個文學雜志的主編,他(她)對文學的影響和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地方的文學雜志,它會影響這一地方的文學趣味和質量。有多少年輕的寫作者需要被它發現和正視,又有多少初學寫作的人因為被疏離被遮蔽而放棄文學夢想。我隱隱地感覺《草原》的好日子要來了。她卻說出了她的顧慮:“我們《草原》的歷任主編都是著名的詩人和作家,而我寫過的文章不多,這會不會影響我的感召力?”我告訴她,很多大刊的主編都不是作家,這絲毫不影響他們辦好雜志,并受到作家的尊敬。
我以為主編應該是一個好的管理者和謀劃者,要有犧牲精神,他(她)的工作是組織和激發手下的編輯,并依靠和信任他們去做好各自的工作,而作家型的主編,反倒比較難以客觀地對待一部稿子,個人喜好、審美趣味和所謂立場都會影響他(她)的判斷和選擇。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阿霞應該是最合適的一個主編。常有人問,一個文學雜志的主編,他(她)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我覺得,當然是眼光,但這遠遠不夠,還要沒有私心,沒有了私心,他(她)才會做到公允和客觀。還有就是熱情,這些年,我觀文學雜志,感覺真的少了熱情,辦刊人沒了激情,雜志缺少生氣、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十年如一日。
我一直以為主編的崗位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事業和責任。他(她)不應只是文壇的風向標,而應該是文學走向的策動者和推手。通過這么多年與阿霞的接觸,我在她的身上,發現了這些品質:眼光、熱情、寬容,沒有私心,很強的責任感。
可是,不久她就生了二胎,隱居于家中。我聽聞后有些困惑,此時正是她大顯身手的時候,卻為孩子所絆。但是,半年后,她又出山了,并正式出任主編。仿佛就是因了這半年的能量積蓄,她的熱情和干勁如火山般噴發。她上任后首要面臨的工作就是《草原》70周年大慶。
70年是一個人進入老年的門檻,而對一個雜志,它可能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節點。70歲的《草原》迎來了40歲出頭的年輕女主編,它注定有不凡的意義。我在想,紀念是什么,不就是向歷史致敬,向前輩致敬,然后尋找和摸索出一條未來之路?今年很多雜志都在紀念70年,這或許也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在走過70年后,需要總結,需要重振旗鼓,再次出發,再創輝煌。
此時的阿霞忙壞了,她要組建紀錄片攝制團隊,記錄作家們的聲音和影像;她要收集自創刊以來所有的《草原》雜志,梳理《草原》的歷史和發展;她要舉辦兩年一屆的《草原》文學獎;她要籌備盛大的《草原》70周年紀念慶典等等。最近幾個月來,她帶領她的團隊每天都要工作至晚上八九點。而回到家她還要安撫兩個孩子入睡。她說:“我為什么要再生一個?我希望我的兒子有一個妹妹或者弟弟,這樣他們就會在我不在身邊的時候,互為陪伴。”沉吟片刻,“現在好了,我可以更專心地做好《草原》了”。一邊是家庭、孩子;一邊是工作和《草原》,兩者全不含糊。我終于明白,她是一個母親,和普通人一樣,她要讓她的孩子健康成長;她還是主編,這是她上任時對領導和作家們的承諾。一小一大,一里一外,構成了她完整的多彩人生。她能把兩者井然有序地融合到一起,互不影響,互為動力,哪怕自己多受些累,也是值得。
《草原》這幾年的變化有目共睹,散發著一種清新之氣。首先是封面,郭沫若先生為《草原》題寫的刊名依然醒目,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從2020年開始,雜志將之前的印刷體蒙古文刊名改成了蒙古文書法,由著名蒙古族書法家藝如樂圖先生題寫。在欄目的設置上,在保留“北中國詩卷”這個傳統品牌的同時,又更新了“草原騎手”這個欄目,傾力扶持和展示80后、90后、00后的年輕作家的作品。比如阿塔爾、蘇熱,還有后來的渡瀾等都先后亮相于這個欄目。阿塔爾就是我推薦給《草原》的。
2017年初,我偶然見到了這位和我女兒一般年齡,還在上大三的蒙古族小伙子。他幾乎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漢語,卻令人吃驚地用標準的漢語完成了一篇小說《蕾奧納的壁爐節》,而且寫得有特點有想法。我當時很興奮,馬上轉給阿霞,沒想到她第三天就給我回話,她也非常興奮,說要在第四期馬上刊用,并囑我寫一篇評論。由此,我對阿霞和新《草原》的效率和編輯眼光更加刮目相看。小說發表后,馬上被《小說選刊》轉載,由此,阿塔爾還獲得了《草原》文學獎的新人獎。
其實讓我對阿霞最感動的是另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都說患難見真情,而對一個離世者的態度,更能說明生者的境界和善心。2019年初,內蒙古籍作家荊永鳴因心臟病突發故去。周圍的朋友既意外又感到可惜和悲傷。這兩三年我經歷了多個朋友的突然離去。作家紅柯、那耘,老友鮑洪飛……都是特別近的朋友,我的心緒一直處于既悲傷又恐懼的狀態中。
我甚至開始抵觸告別儀式,我已經承受不了那種場面和氛圍,但是永鳴的告別儀式我必須參加,這不僅是因為這么多年,我常去他所在的房山良鄉的家喝酒暢談,更多的是因為他的為人與為文。永鳴是中國煤礦作協的副主席,內蒙古赤峰市作協主席,又是北京作家協會的理事,身在三個作協,我常說他腳踩三只船。后來我才理解他。他的文學成績和影響已經可以不必依附于哪個組織,借此提升自己的名氣和地位。他是個善良的人,內蒙的赤峰是他的故鄉,是他文學起步的初點和依托;北京是他現在的居住地,也是給他創作最多榮譽的地方;而煤礦又是他最熱愛的工作,三個地方他都不好取舍,因為在他創作的各個時期,彼此之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他需要他們,難道他們不也更需要他嗎?永鳴是個重感情的人,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阿霞作為內蒙古唯一的省級漢語文學雜志的主持者,也作為好朋友,從五六百公里外的呼和浩特趕來與他做最后的告別。她可以不來,但是她毫不猶豫地來了。那天,據說她乘坐的飛機是晚上九點多的班次,因為延誤,凌晨四點才飛臨北京。早上六點又奔赴幾十公里外的良鄉,她幾乎一夜沒有合眼。儀式結束,我和她打招呼,見她面色倦怠,眼睛由于悲傷而濕潤泛紅。我想請她吃飯,她卻說要趕到國家圖書館,查閱《草原》雜志的創刊號以及早年的樣刊,為《草原》七十周年大慶采集資料。于是我們匆匆而別。
我有時候感覺,參加一個死者的告別或葬禮,很多時候是給生者看的,但阿霞不是,她是對文學人的一種本能的敬重與感激,以及對好兄長的情義與不舍。在當今這個時代,一個人的離去就意味著一切的終結,我們傳統的對逝者的尊重已經簡化到令人傷懷的地步。在今年的《草原》文學獎評獎中,阿霞力主將“特別獎”頒給永鳴,并邀請他的女兒專程來領獎,這一建議得到了評委們的一致支持。永鳴兄應該安慰,因為,在我的心里,它比他曾經渴望的“魯獎”更有意義。
關于阿霞的業績,我已經寫在《我愿與〈草原〉為伍》這篇文章里了,就不再贅述。總之,阿霞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樂于助人,尊敬長輩,關心后人,勤于工作,敢于創新。這些就足以讓我向她表達敬意,并抱以期待。愿《草原》越辦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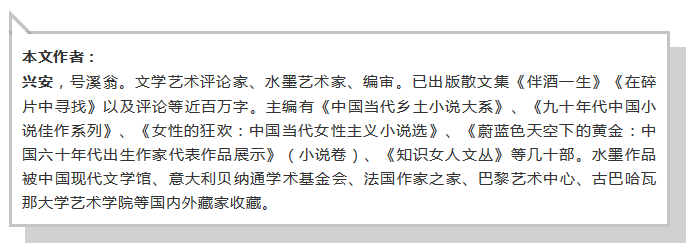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