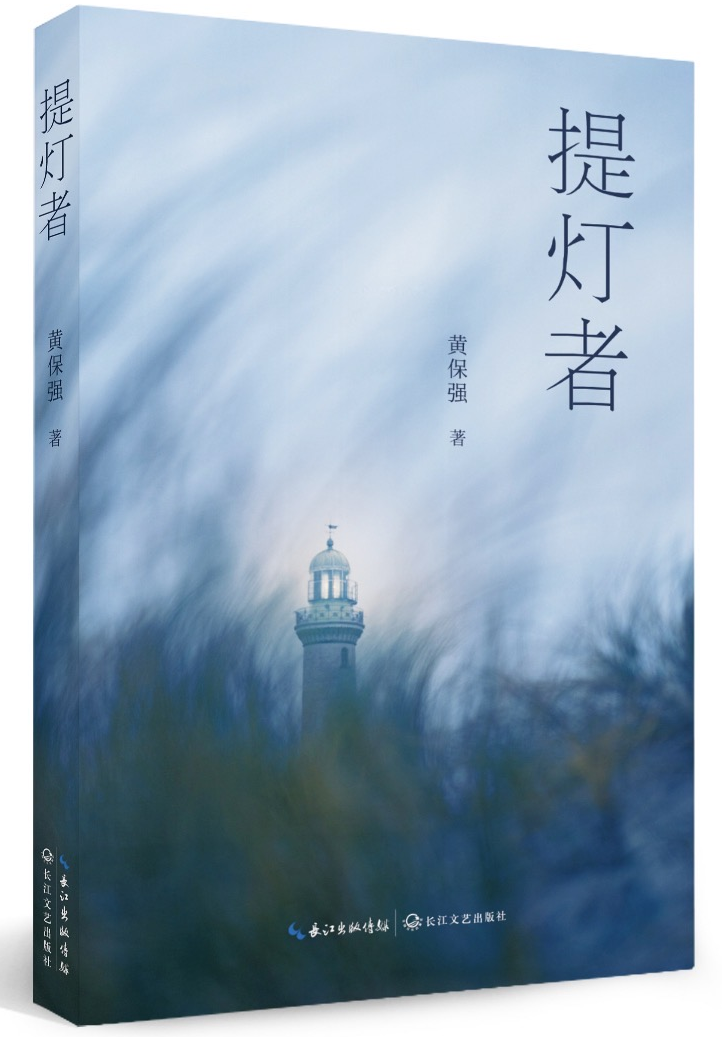
黃保強著詩集《提燈者》立體圖
青年詩人黃保強詩集《提燈者》出版發行
近日,青年詩人黃保強的最新詩集《提燈者》于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黃保強是一個敢于在詩歌世界探索嶄新詩意的詩人。他有能力在一個幾乎被所有詩人都引用過的鄉情、鄉愁、人文主題里,去做一次更加深刻的詩歌寫作。他在用詩歌檢閱靈魂的同時,也在用他不滅的心燈去檢閱詩歌。他把我們引入了一個用沙漠、風、雪、羊等元素包裹的靈魂世界。那里其實是他永遠不能忘卻也永遠無法揭開的靈魂密碼。(評論家苗洪)
本詩集之所以定名為《提燈者》,是因為作者堅持以詩“引路”的初心。其分為上編時間里的光譜和下編如泥土的愛,有抒情詩、敘事詩,有短詩,還有組詩。
湖北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詩人高曉暉在序言中評價道:“黃保強是一位年輕的‘80后’詩作者,一位創作勤奮的詩作者,一位立志以寫詩為專攻的詩作者,當然他已經是一位有自己獨到的、成熟的詩歌理念的詩作者。”詩人陳啊妮評論道:“黃保強的詩,皆與他日常生活和思考有關,依托故土獨特的地域性(甘肅),便有了寬厚,冷靜而硬朗的氣質。他慣用密集的意象,隱喻,立體感很強的筆觸,虛實結合的敘述來體悟生命的存在,俯身或者仰視都以個人方式承擔人類命運和詩歌追求,不斷再造精神落腳點,在詩歌空間和時間秩序中交叉真摯的情感,以極具巧妙的構思,采用最接近現實的詞語搭建詩歌之美。”
 詩人黃保強
詩人黃保強
黃保強簡介,黃保強,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詩文散見《詩刊》《山東文學》《散文詩》《長江叢刊》等報刊,獲選多種作品集。曾獲 “青年之聲”青少年詩歌創作征集活動銅獎(詩刊社主辦)、第十屆湖北產(行)業文藝楚天獎(展覽、文學類)入圍獎、湖北省職工主題征文活動一等獎、“美在荊楚”詩文征集大賽三等獎等獎項。已于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詩集《夕陽下這土地》。
黃保強曾說,既然選擇了文學、寫作這條不歸之路,讓我們相互喝彩,用個人的氣魄和胸襟鼓舞他人,用個人的燈火點亮遠方的燈塔,用虔誠,相遇更多同伴,留下腳印和車轍,留下一團攜手前行的影子,告訴這個世界,我們來過,并且還將共同抵達更美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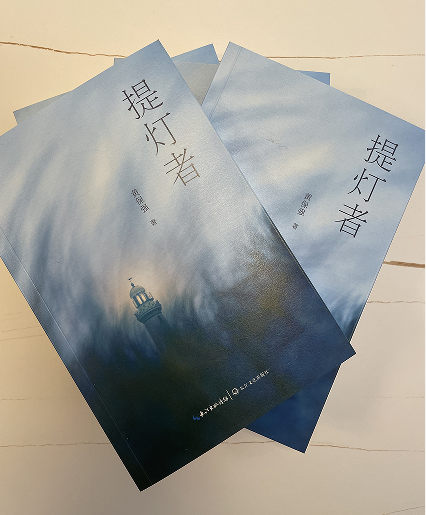
黃保強著詩集《提燈者》實體書
附:黃保強詩歌精選
黃 河
正午,那些劃羊皮筏子的人
仍攪動腳下之水
他們嘴里的“尕妹妹”在冗長的歌詞中開始含糊
他們應該在贖罪
草方格沙障也不能抵擋
五十多歲,黃河浪中起伏
他們曾手刃乳羊,剝皮制衣
從河東到河西
如同黑色的鐘槌
在騰格里脖子上敲敲打打
豁口上掉落下來
天地之間,這最小的沙才是歸根
華燈初上
像取暖挨近,一點點把火種消弭在夜海中
風卷著黃葉
夕陽,炊煙,千家萬戶的燈火如同約定
如同省略,三點連成一線
可溯流而上——
宋代官軍的火把閃爍
圍著的院子角門逃離的腳步匆匆
付之一炬,女子的朱砂痣和書中方字
輝映深閨,風和吶喊
都升騰成史
換了河山,溫暖從你的后腦勺
降落旋即升起,分野并不顯著
假以外力的孤單被光和水慢慢填補
大雪壓境
無關冷空氣
我的第一場雪來自史書
馬蹄輕輕,一條河川鱗次櫛比
不要驚動即將見到的炊煙
我有十萬雄兵枕戈待旦
嚴寒中點起篝火溫起酒
北方,戰前需要煽動,需要熱血沸騰
用兵如神
從天而降,三千里江山
一一裝點
北方,每個人都需要練習擁抱長劍,竹簡
和一片片厚積卻始終溫柔的雪
石 刻
一座碑石生生地斷開一個朝代
見字如面
匠心好比占卜師
錘子和鑿子,敲敲打打
不如一筆一畫
或羅織罪名,或歌功頌德
驢子自遙遠的地方來
每一次的蹄動
都仿佛吵醒那沉睡的碑刻
鐵索是慣用的樂器,多少紅顏墜入凡塵
一片廢墟猶如內心旁白
公元后假假真真,松樹長情陪伴
發青的石料,更愿意成為先賢仁人的頭骨
歷史是一個假面
我們微笑它冷峻
不然,一千多年前,匠人總會遇到熟悉的人和話
荒原上的寺廟
和干枯的野草同根
所以少香火和桐油
突兀地在一道沙梁上
偶爾的過路者在這里歇腳續水吃干糧
他們和菩薩一樣質樸
幾個修復塑像的匠人正描摹眼睛和耳朵
希望畫得大一點
讓慈悲看得更遠,聽得更遠
此刻
兩歲半的兒子對著荒蕪大喊
你好
回聲中,似乎木魚和金缽也響了一聲
致故鄉
我用所有的辦法熱愛
悲哀的,高尚的,卑鄙的
如同一株隸屬于百合科的植物
讓所有遇見都幸運地發生在春天
你所不知道的,彎曲的路
荒蕪的鹽堿地,映天的沙濤
低矮的老屋,陳舊的九宮格窗
都是我在一封介紹信中欺瞞外界的字符
十九歲那年,你把所有心事搖落
卻沒有眼見為實的豐收
多年后,我和你都習慣聽“回來了”招呼語
聽說下雨的異鄉會飄灑童年的味道
即使心中供養僧道
也數不過來究竟哪天該讓信鴿送信
當傍晚倦鳥歸林
當提起故鄉,我們仿佛水手
這一年年受風受潮的傷疤
又開始隱隱作痛
我且畫一柱高過屋頂的煙囪吧
再給一道熟悉的菜命上陌生的名字
盜火者
風再次吹干海水浸潤的巖石
如同烹飪
從最簡素的角度尋找靈感
這古老的記憶和你的反抗格格不入
一副鐐銬就是鋪灑在你身上的藤蔓
天生的書畫家啊
你迷戀火的色彩重于宮廷的尊嚴
你偷了薪火相傳的希望
偷了酒和整個春天
任你的帽子變成老鷹駐進心臟
你用手紋交織成網
先收納落日,劍和盾
還有美和智慧
這個夜晚,你只想和無數淺草沉醉一場
和黑暗中的低矮眼神在一起
等一聲又一聲號子響起
桐木和楠木尚在沉睡
你從十天埋伏中突圍
長成整個煙火人間一株不聞外事的高粱
一座城就是一個春天
曼陀羅花照樣盛開
一座城,甘做一世樵夫
以一座廊橋畫舫
垂涎所有白墻灰瓦后的暗角
我以莫大的同情
向只開花不結果的臘梅
索要過冬的糧食
我也學會在這陌生的水鄉
播撒火種,噓寒問暖
雨水的節氣
多像一個逃逸者隱藏了關于水所有的秘密
我不會吐露我對一座城,園林,林中的花式不一的窗
一覽無余的愛或恨
陽光下,即使一萬年
他們也在走向死亡
我只是委婉地讓你知道
所有辯解春天后的借口
包括水上漁火,是我無法拜月后留下的印信
 黃保強著詩集《提燈者》
黃保強著詩集《提燈者》
附:黃保強詩集《提燈者》序言
引譬連類之法,沉郁頓挫之風
文/高曉暉
有幸為黃保強的詩集寫序,得感謝劉麗君大姐。幾年前,劉姐主辦湖北汽車界的文學骨干培訓班,我和保強受邀參加,因此有了初見之緣。老實說,在湖北汽車界,優秀的詩歌寫作者為數不少,但保強應該是詩歌辨識度較高的一位。尤其難得的是,他還是一位年輕的“80后”詩作者,一位創作勤奮的詩作者,一位立志以寫詩為專攻的詩作者,當然他已經是一位有自己獨到的、成熟的詩歌理念的詩作者。我不否認,與保強初識,會眼睛一亮,有一種情不自禁的欣喜。不久前,劉姐把保強的新詩集《提燈者》推到了我的案頭,囑我為之作序。劉姐對汽車界的文學愛好者,當然不只是對保強一人,真的是呵護備至,盡其所能給予扶持、推介。正是感動于劉姐的熱心腸,她囑咐的事,還真不敢馬虎。
2018年10月,保強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夕陽下這土地》,博得廣泛好評。而此前,他所著詩集已有《黑燈長卷》《金色麥城》《灰煤告白》《叮咚叮咚》等多部,并著有三幕詩劇《夢蝕》。《提燈者》應該是他最新的一部詩集。本來,這部詩集,篇幅會更大,包容會更多。有抒情詩、敘事詩,有短詩、組詩,還有詩劇。這樣,詩集就顯得有些龐雜,我建議保強自己做一次精選,突出自己的創作特色。于是,《提燈者》篇幅變小了,當然也就相對精粹了。這一變,遺憾也跟來了。迄今為止,保強寫詩已有十數年,粗略統計,保強的詩作,應該不下千首,詩之所涉,如王輝斌先生在《夕陽下這土地》“序”中所指出的那樣,有鄉戀詩、愛情詩、詠史詩等。當然不止于此,比如他寫汽車題材的詩,還有一些游歷詩、唱和詩等等。僅就汽車題材,保強的詩作也當有百余首吧。保強的詩友黃承林評價《夕陽下這土地》,說他“嗅到詩人作品里濃郁的鄉土味道、親情味道、歷史味道、人文味道”,但就是少了“汽車的味道、汽柴油的味道、流水線的味道、東風的味道,以及在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國有企業詩人所應該品嘗和調配的味道”。承林的評價自然是中肯的。如《提燈者》面世,“汽車的味道”還是嗅不到的。這倒不是保強不寫“汽車的味道”,而是為了《提燈者》“味道”更純粹些,諸如“汽車的味道”之類詩作,被保強暫且擱置了,或者,下一部詩集中“汽車的味道”就變成“硬菜”了。
保強說他把一部詩集定名為《灰煤告白》,是“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那塊煤,我還需要詩歌這盞燈,為我點燃,為我引路”!這次他把詩集定名為《提燈者》,自有他的講究,他是否還是在堅持以詩“點燃”、以詩“引路”的初心,我不得而知。“提燈者”幾乎是十九世紀英國那位偉大護士長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專屬稱號,她是無可替代的“提燈天使”。保強是有意弘揚護士精神么?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首倡舉辦“提燈會”,寄希望于北京大學學子,立志驅逐黑暗,追求光明。保強是有意從蔡元培先生那里獲取精神營養么?詩集中,有兩首詩提及“提燈者”,一首是《彌生》:“八千里河山/倒春寒如同一種冒犯/提燈者結束結繩記事,向東相遇更早的陽光。”《彌生》中的“提燈者”,與拓疆者更接近。另一首是《燈火》:“今天,我們在最近的酒肆/聽撫琴或鐘聲,曾經的飛花字句架成琉璃/落雪的黃鶴,等到白頭/1700多年,提燈者互道兄弟/隱去名姓/至今仍在繡像中掐著歸期/任浪花,任浪花沖刷腳踝。”《燈火》中的“提燈者”,又好像是登樓詩人的影子。兩處“提燈者”,字面一致,所指之意卻相去甚遠。但內在的關聯,也并非毫無關涉,“提燈者”自帶光芒。
保強的詩作,數量最多也最動人的部分,還是他對故鄉的回望。故鄉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在保強筆下,總是那么令人回味悠長。鄧炎清先生在《詩人的天職是返鄉》中評價說,保強詩有情感之深厚、語言之敦厚、風格之渾厚,當是行家之言。關于故鄉,保強有更多的悲憫、更多的眷念。保強說,“人在異鄉,格外懷念故鄉”,“通過我的詩歌,我依舊可以回溯到騰格里沙漠,回憶起我已逝去的祖父和他生前放牧的那100多只羊,想象蒼鷹捕捉小羊俯沖下來的情景,回望過年時舞龍舞獅、劃旱船等民俗表演……”(《詩歌,點亮我眼前黑暗的一盞燈》)不難看出,保強對故鄉的回望,實際上是對關于故鄉的點點滴滴的記憶的找尋,或者說是對故鄉所有情感的反芻。組詩《味道系列》《如泥土的愛》,是集中書寫故鄉的兩組詩。關于土地、關于童年、關于祖父祖母、關于父親母親……故鄉的風沙、麥垛、圓場、羊和祖母的故事裝點的童年的溫馨記憶,當然還有貧瘠和苦難。總之是游子對故鄉的衷腸。這是因為:
沙漠邊緣的小村莊
是一條鱷魚
貪婪地順著陽光,河道
漂浮了幾代人
祖父在這里安家
父親在這里老去
時光的流逝,是保強心靈深處最深切的一種痛:
“下雨的異鄉會飄灑童年的味道”
“當提起故鄉,我們仿佛水手
這一年年受風受潮的傷疤
又開始隱隱作痛”(《致故鄉》)
所以,他在心里期希著:
“讓祖母的剪刀,時光和夢
慢一點”。(《衰老的祖母》)
寫記憶中的故鄉,刻進記憶深處的,當然是親人,比如祖父。保強在詩作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書寫祖父,當然可以理解為保強與祖父有更深的感情。或許,在保強的詩中,祖父不僅只是書寫對象,更多的時候,祖父會成為一種意象,祖父與故鄉,很容易互為表征,互為標記。對于祖父而言,騰格里沙漠、風、雪、羊,等等,這是祖父的人生舞臺布景,而羊皮襖子、背上的氈包,當然還有他的羊群,幾乎是祖父出場的標配。對于故鄉而言,祖父的形象,自然也應該視為故鄉最醒目的符號。《一只鳥在雪地散步》是最真切的故鄉風情紀實,而畫面的主角,就是祖父:
紅爪,白地
只有鳥,丈量得準
從家到墓地的距離
起初是一對,再到形只影單
雪霧廣袤
我的祖父偶爾攏著羊皮襖子打火點煙
偶爾被嗆咳嗽
像唯一一個蠕動著的黑點
一陣風來
誰都看不清
是那只鳥還是他的帽子
在飛
詩歌勾勒的畫面,鏡頭感很強,有長鏡頭:那是廣袤的雪原。有近景特寫:鳥的紅爪、攏著羊皮襖子打火點煙的祖父以及祖父的咳嗽。有遠景:祖父被拉伸為雪原上一個黑點,他的帽子飛動如鳥……
還有《羊皮襖子》《背包》等,關于祖父的記憶,情感濃厚,好像蘸在筆尖上濃墨,滯重、深沉,化也化不開。
除了親人,保強當然還有關于鄉親的記憶,像《歸來你還是少年》中的麥客,他們拼命地收割,不會顧及手上的傷疤,“一海碗臊子面后/他們扯著嗓子吼一曲蘇武牧羊”。再比如《手藝》中木匠,這位“斷了兩根手指的木匠在昏黃的燈下/除了劃線,還要唱一段秦腔”“他知道和一段木頭相互戰栗的所有真實”。帶著傷疤的麥客要吼《蘇武牧羊》,而斷指的木匠也要唱一段秦腔。保強記憶中的鄉親,就是這樣一種生存狀態,有傷,有戰栗,也有吼和唱。
關于家鄉風物的記憶,也是保強詩歌重要的書寫對象。保強的詠物詩,一種是以物擬人,是物的人格化。一種是以物寫人,物成為人的參照。保強“以物擬人”的詩作相對較多,比如《樹蔭》:“每一片葉子獨立經受太陽的箭陣及風的鼓動/受害又無辜,左右搖擺如同禪修/一棵老樹足夠撐開歲月和委屈”。一棵樹,因為老,難免會“經受”,也因老,才有了足夠的“撐開”,歲月與委屈,好像是一種“禪修”。《泥土》其實寫的是蚯蚓:“它活在泥土里/它吃泥土/它吐泥土/不停下來不問前程/”“它就在這樣的塵世/走過名人墓,也走過草民墳/”寫的是蚯蚓,而意之所指卻在“塵世”,保強從蚯蚓柔弱的路徑中發現了塵世的法則:名人墓、草民墳。墓與墳,看上去有天壤之別,而本質上卻高度統一,同一于泥土而已。“以物寫人”的詩作,我以為是保強詩的一個亮點。《羊皮襖子》的書寫對象,并非羊皮襖子,而是寫給祖父哀歌。《麥子》也并非關于麥子的抒情,而是寫給父親的贊詞:
在春寒中復蘇的村莊
父親喂養的色彩初來乍到
根芽,在觸摸溫度中,有的枯萎
有的倔強,抽穗,染上陽光
染上俗世發作的鬢白
《石頭》雖然被保強賦予了書寫對象的意義,但是,保強要表達的,是他發現了一顆石頭那如觀音一般的慈悲,這“足以讓我病重的小姨渡過難關”。石頭無情人有情。詩人把希望寄予一顆石頭,這里有多少的無奈,多少的絕望。小姨重病的難關,其實已經成為了壓在親人心頭的大山!
《提燈者》凡百余首,內容所涉,當然不限于寫故鄉,也有關于人在異鄉的見聞與思考。如《利川紅》《曾侯乙》《后官湖的候鳥》《四月,游子的虔誠——致周中》《夢回鼓浪嶼》等。這些詩作,當然也彰顯著保強創作的才情,但相較于寫故鄉的詩作,或多或少還是存在離地三尺的輕飄,惟有寫到故鄉,保強的詩情更有對土地的依附,情感的根系深深扎進故鄉的土里,厚重而深沉。
我是很強烈地感覺到保強詩的辨識度的。或者說,保強的詩有他獨具一格的質感。這種質感,當然有他地域書寫的獨特性,比如騰格里沙漠,以及大西北的蒼茫樸拙,這里蘊藏著豐富的美感。而保強詩作之所以使他地域書寫的美感得以凸顯,我以為主要得益于他的引譬連類之法和沉郁頓挫之風。“引譬連類”,實為傳統的比興之法。唐人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己意志,皆興辭也。”唐代皎然《詩式》說:“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皆入比興。”詩性思維的特點,正在于萬物有靈,天人合一,自然物象,即可隨意為詩人驅遣,所謂“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保強為詩,聯類之力尤盛。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足夠寬闊的時空背景下,他的聯想力是如此地收放自如,與李商隱“獺祭”之法,很有些類似。《將要去遠方》,可以理解為一次旅途的玄思,但一首詩的意象,并沒有明確的時空結構,隱隱約約,列車在呼嘯,而詩人的思緒則飛逝得更為邈遠。《山陰》感悟的是山的姿態,作為實體的山,在意象的紛亂中虛化,而作為理念的陰與陽,反而更明晰更動人:
以石碑為界,向陽的地方安葬靈魂
他們孤獨而怕冷
背陰的地方種上柿子
終究會發亮,也會溫暖一座經歷風雨的山頭
《又將春天》把春天的萌動寫得如此細微而又大氣磅礴,還是引譬連類,意象生發,虛與實,交相輝映,不同的聲部,構成繽紛而又和諧的混響。
保強作詩,思維發散,聯想奇崛。以致他的詩作總是有一個遼遠恢弘的時空結構,由此,也成就了他沉郁頓挫的美學風格。“沉郁頓挫”本是對杜甫詩風的贊詞,用來形容對保強詩風的閱讀感覺,可能有偏愛之嫌,但保強詩作中流露出的悲憫與雄健、凝重與蒼涼,借用“沉郁頓挫”一詞,還算貼切。《時間里的光譜》里,列舉出種種的“故鄉之重”,字里行間,充溢著啜泣般的沉痛。《泡菜漸漸老去》中那種細膩的腌制之痛,真真切切成了人生酸澀的某種隱喻。還有《石刻》,一方石刻,雖見字如面,但“歷史是一個假面/我們微笑它冷峻”的現象未必不是常見。“歷史”“時間”是保強詩中的高頻語詞,不難看出,保強總是習慣于“用典”“證史”,以此將現實的感悟與歷史的機緣作有機的貫通,或許,“沉郁頓挫”之風也就是在時光隧道的貫通之中積集而生成。
不用諱言,解讀保強的詩是有難度的。就我個人而言,對于保強的詩歌文本,大約是好像讀懂、沒有讀懂、根本讀不懂三類情形。關于詩歌,懂與不懂,從來就是聚訟紛紜的,但白居易的淺白曉暢、李商隱的晦澀朦朧,并沒有妨礙他們成就為一代大家。從根本上說,沒有一個人能夠洞穿他者的靈魂,“詩無達詁”本來就是常態,一千個讀者眼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保強詩作,取象紛繁而意蘊宏闊,閱讀的難度可想而知。看這首《大雪壓境》:
無關冷空氣
我的第一場雪來自史書
馬蹄輕輕,一條河川鱗次櫛比
不要驚動即將見到的炊煙
我有十萬雄兵枕戈待旦
嚴寒中點起篝火溫起酒
北方,戰前需要煽動,需要熱血沸騰
用兵如神
從天而降,三千里江山
一一裝點
北方,每個人都需要練習擁抱長劍,竹簡
和一片片厚積卻始終溫柔的雪
這壓境之雪,雪為何物,境在何處?不得而知。如是自然之雪,不可以與冷空氣無關。如是史載之雪,卻未見這場雪所生之域、所止之時。“十萬雄兵”緣何而起,神兵天降,意在何為?保強以一連串的謎團,推進詩作,引發閱讀障礙自是必然。但詩句營造的美感卻是可以感知的。詩人希尼說:“詩歌可以創造一個秩序,其忠實于外部現實的沖擊、敏感于詩人生命的內部規律。一種我們終于可以朝著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儲備的東西長大成熟的秩序。一種滿足一切智力中的饑渴和情感中的求索的秩序。”我以為保強的詩歌,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內在“秩序”的, 他在“智力饑渴”和“情感求索”方面能夠獲得“自我滿足”,只是作為閱讀者,要順利進入他的“秩序”中,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即便如此,那又何妨?大學問家梁啟超先生不也坦言,“理會不著”李商隱《錦瑟》等詩作講的什么事,但他感覺到了詩的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
喜歡保強的詩,大約是與我體會到他詩中葆有的那種“新鮮的愉快”有關。
是為序。
作者簡介:高曉暉,湖南臨澧人。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一級巡視員。著有長篇人物評傳《呼喚》 (作家出版社)及文學理論批評論文百余篇。完成“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文學組”國家級課題、中國作協2004年重點扶持項目《新世紀中國文學現狀調查報告》之子課題:《中國網絡文學現狀》和《中國文學期刊困境及解困思路》。有散文、詩歌、紀實文學、電視專題片腳本等作品。主編文學叢書、作品集多種。
(本文由作者授權作家網發布,供稿:見詩如面)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