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了二十年的祝福
——懷念我的兒時老師張冠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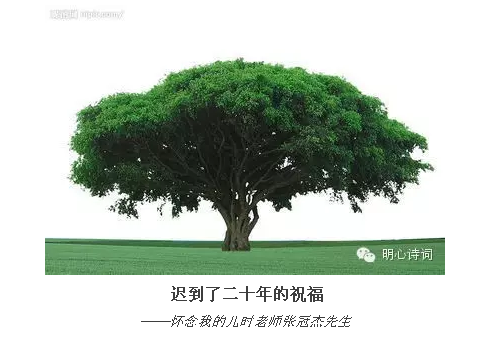
首先肯定我寫作的老師是兒時的老師張冠杰先生,他曾讓我在全校的師生大會上朗讀我寫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信心,使我在青少年時期閱讀了許多書籍,如《青春之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野火春風斗古城》《呂梁英雄傳》《草原風火》《革命的一家》《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詩集》《我的母親》《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白蛇傳》《小姑賢》《西廂記》《家》《春》《秋》《寫給小讀者的心》《醒世恒言》《警示名言》《聊齋》等等,有的書名今天回想起來不一定準確,但它們是我整個青少年時期的知心朋友,是我思想的家。那時我會和書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痛苦、一起興奮。我家有一本四角號碼字典,為了快速查出書中的生字我練就了一種本事,猜四角的準確率相當高,估計在90%以上。現在人們有了拼音字典很好查生字,但當時我家只有這一本“四角號碼字典”,后來都被我翻掉了頁碼。
兒時的閱讀奠定了我的文學基礎,使我在不知不覺中不僅愛上了中文,還愛上了英文。因為我不記得在哪個閱讀資料中見過一句引用詩“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書中說這句詩的作者是英國詩人雪萊。于是我除了知道有個國家叫蘇聯(現在的俄羅斯)外,我還知道有一個國家叫英國,可我一直沒有讀到任何關于英國的書。當初中開設英語課時,我充滿了好奇,心想是否可以在英語課上讀到英國的書?就這樣我對英語的積極性超過了其它科目,每一個單詞我都認真背認真記,直到后來真正考入英語專業,真正讀到雪萊的詩集,還真正踏上英國的土地。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追溯到兒時的老師張冠杰先生,是他的諄諄教導和以身作則給我播下了種子,我得以在隨后的歲月里經過一批一批老師的精心呵護開花結果。而就是這樣一位恩師我卻有30多年毫無他的音信,并不是老師去了遠方,而是我一直沒有停下腳步回望他,只顧風雨兼程朝前走。前幾日和高中班主任陳先攀老師微信聊天時,回憶起當時陳老師向學校推薦了我的一篇文章,學校拿毛筆抄出來貼在墻上給全校學生看的事情,給我鼓勵很大,同時我又提到了張冠杰老師(我曾在很多場合提到過他)。陳老師說不記得推薦我文章這件事了,并給我發一個笑臉。停頓一陣之后他發來一條信息:“實際上張冠杰老師已經去世了,而且已去世約20年。”我頓時對著手機屏幕驚訝的半晌沒有回過神來,他今年才70出頭,20年前他才多大,怎么會那么早就離開了他摯愛的講臺及疼愛他的家人。我獨自禁不住哭了,我兩眼模糊看不清屏幕的鍵。接著陳老師又告訴我“實際他和張冠杰老師是同學,只是張冠杰老師沒有考上大學。”怎么會這么巧,我此前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是同學,只是覺得他們如兄如父地關心我。我用心發了三個祝福標記,心里默默喊著張老師,請他原諒他不懂事的學生,接受這一聲遲到了20年的祝福。
可這三聲祝福張老師怎么聽得見?“張老師!”我心里用力喊著,如煙往事一件件清晰地出現在我眼前,我仿佛回到了當年的教室看到了張老師漂亮的板書,站到了他當年的辦公桌旁聆聽他的逐字逐句的講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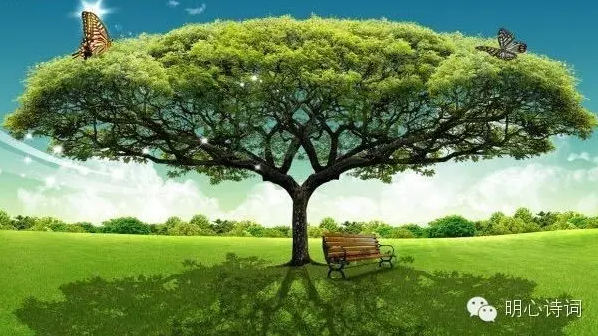
我第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小學四年級。他中上等個頭,胖瘦適中,肩膀平整,服飾總是干凈整潔,風紀扣經常扣著,臉型略圓,眼睛一眨一眨,嘴唇稍稍張開,總是帶一點點笑意,但又不是在笑。第一節上語文課,張老師聲音不高不低,先講課文的生字和詞語,具體課文內容我忘了,但我記得課文中有一個詞“終于”,張老師在黑板上寫了“終于”和“忠于”,板書太工整了,我為之驚訝,“太棒了!”我心中說。張老師問我們這兩個詞有什么區別?我不敢舉手,但我用眼神告訴張老師我知道。他于是指著我說“你知道嗎?”我的回答張老師很滿意,我不僅回答了有什么不同,還各造了一個句子。我喜歡張老師的講課方式,非常有條理;喜歡張老師的板書,每一個字就像刻在黑板上,盡管那塊黑板坑坑洼洼。下課了,我不知道是因為遇到了張老師而高興,還是因為我課堂的表現高興。下課幾分鐘我一直沉浸在語文課的情境中。
敲鈴了,那時的鈴聲是房檐邊掛著一尺長的一小截鐵軌,一個老爺爺手拿一根鐵棍有節奏地敲,好像是“一上二下三預備”,就是說一下一下地敲是上課,兩下兩下地敲是下課,三下三下地敲是預備鈴。這節是算術課,可走進來的老師還是張老師。他望一眼好奇的我,說“數學課也是我來教”。頭幾節數學課講分數,純分數和帶分數,同分母加減、異分母加減。張老師講得清清楚楚,如若還有聽不明白的同學,張老師會耐心地重復講。我從那時起真的很喜歡張老師,張老師講什么都能講得透徹,而且還很平易近人,于是我便敢大著膽子找張老師問問題。我記得當時有一次講到關于珍寶島事件的內容,張老師講到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還講了很多關于地理的知識,我便好奇,蘇聯是什么?東北是什么?黑龍江是什么?對于那時候只知道最大的地方就是太原的我來說,這要比會造句和會計算吸引力大得多。于是我就開始了解珍寶島事件,我把當時能找到的報紙、傳單都讀了,后來老師布置寫關于珍寶島事件的作文,之前的閱讀正好派上用場,寫得棒棒的,張老師讓我在全班讀我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在新同學面前讀自己寫的文章,心砰砰地跳,但非常自豪。
人們很容易對成功進行復制,從此我養成習慣讀報、讀傳單、讀任何我能讀到的東西。那時候我們經常有任務要給老人們讀什么什么公報,或什么什么社論,我可以中間不打啃地讀完,而且不會出錯。我明顯感覺我的詞匯量在增加,寫作文造句一點都不愁。后來記得有一次,學校布置任務對某件什么事表決心,具體事情不記得了,但是我沒有辜負張老師,我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張老師都吃驚了,怎么能寫那么多?我問“多了?那就刪掉一些。”張老師說“不,寫得非常好。”他先讓我在班里給同學們讀一遍,然后又在全校大會上代表全年級學生讀一遍。當時的確驚著了許多老師,實際我自己知道,那篇文章是我讀了一本當時關于表決心的書,我把上面的好詞語都抄下來,用在了這篇文章里。從那時起,我養成一個抄寫好詞語的習慣,而且我從讀報紙轉向讀大部頭的書,我覺得書里的東西更多。
偶然的一個機會我看到一本書《普希金詩集》還是《普希金故事》,書名記不清了,封面有一個頭像,頭發是卷曲的。光封面對我就產生了極大吸引力,頭發怎么是卷的?書中人物是蘇聯的,還提到俄羅斯,這對我來說都是天書。當時我們只讀到毛澤東的詩詞,印象中張老師講過關于梅花的那首,張老師很投入地講解,尤其講到后面幾句時,他充滿一種期待,進入一種幻想,目光似乎穿過教室的墻看到了遙遠的地方:
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這首詩被譜曲成了歌,我們還學會了唱。按照我們的方言“卜算”讀音和“剝蒜”的一個發音,這引起我很大好奇,我問張老師“什么是卜算子?”張老師說“詞牌名”,“那什么是詞牌名?”“為什么要用詞牌名?”“我怎么學習詞牌名?”等等,我就像一個“問題”女孩,經常問的張老師看著我直眨眼,但張老師沒有一次呵斥我,而每次都耐心地盡可能地告訴我。當我看到普希金的詩時,我發現根本沒有詞牌名,我當時真是暈了。我記得抄寫了普希金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騙了你》,我很好奇生活怎么欺騙人?那本書里還講了決斗的故事,我記得那個描述是,兩人背對背向前走,數到幾時突然轉身開槍,誰快就先打死對方,但我不記得是因為普希金慢呢還是因為對手耍奸。這件事困擾我很久,想不明白為什么要決斗,那個時候的教育是人要和敵人斗爭,去戰場殺敵人。我有幾次想問張老師,但都沒有問出口。一是不敢確定這個問題該不該問,二是因為張老師很忙,他的辦公桌就在一進門的左手,那間辦公室是里外兩間,里間我好像沒有記憶,外間好像有三個辦公桌,張老師的辦公桌最靠外,我經常站在門口,一只腳在里一只腳在外就可以說話。張老師當時有一個“任務”是要筆錄廣播里的重要新聞,那時沒有任何工具,只有一個收音機,在播放新聞時張老師就坐在那里,邊聽邊記錄。我不知道是學校派的任務還是張老師自己的要求,我后來也跟著試過,當大喇叭播什么內容時,我也開始記,但根本記不下來,第一句還沒來得及寫,第三句已經說完了。我很崇拜張老師,他懂得那么多,什么都知道,而且寫得那么好,那么快,那么整齊。我記得后來我們開一門課叫“農業課”,張老師仍然講得頭頭是道,24個節令我至今可以熟背:
春雨驚春清谷天,
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是六廿一,
下半年是八廿三,
每月兩節不變更,
最多相差一兩天。”

后來有一次,學校要選積極分子,忘了是什么積極分子,張老師和學校推薦了我,我參加了我們那個地區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會議,基本都是大人,我不知怎么會有我這樣一個小孩。他們說著我根本不懂的話,還要不時出去參觀,我跟著他們坐大卡車,那也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坐大卡車,走很遠的路,去了哪里我都不知道,只記得有一位叔叔一直照顧我,因為上下車我都夠不見,得有人抱著我上去再抱著我下來。而且那位叔叔怕我走丟一直拉著我。我什么也沒有弄明白會議精神,但是開了我的眼界,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回到學校我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講述會議精神,張老師和校長他們看著我都樂了,后來就不了了之了。
再后來,張老師不教我們了,換了別的幾位老師,對我的幫助也很大,但是終究沒有張老師在我的記憶里深刻。這可能還因為另一層關系,我和張老師還做了兩年的同學,他在物理班,我在英語班,那兩年是在我離開張老師大約7年后的重逢,如果算上張老師不教我們的時間應該是在8年后。當張老師和我同時走進同一個校門成為校友、同學時,我不知道張老師怎么想,但我還是那樣崇拜他,盡管我的專業完全跳出了張老師的范圍(他好像學的是俄語),但是中午在食堂吃飯時,或者下午下課后有時我還是要和張老師在一起,我們并不探討問題,就是隨便坐一起,張老師還是那樣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我,似乎我還是8年前的那個小小孩。他依然用關心的神情看我,但是我聽說張老師家里很需要他努力養家,至于具體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而我當時的小野心是要考研,所以那兩年我除了正常的課程外,我自學了全部的英美文學課程所要求的內容,還拜一位日語老師學習日語。
畢業時,我們幾個老鄉合了一個影,我和張老師以同學身份同坐一起,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我的老師,直到今日。畢業后張老師回到了原崗位,我又再次參加考試,考到北京。后來聽說張老師調離了原來那個學校,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去北京讀書的前幾天,我正在車站等車,張老師騎車從我身邊經過,我只顧看車來沒來,竟然沒有看到張老師過來,聽到喊聲,我很驚訝這時候竟然能遇到張老師。當時等車時還碰巧碰到我的一位高中男同學,他站在我身邊,張老師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看我看看那位同學,那種神情你應該懂得。我把我考學的事告訴張老師,他為我高興得真是合不攏嘴,我看到他從未有過的開懷而笑。他具體囑咐我什么我都忘了,但是我能記得我上車后他向我招手,而且還不時回頭看我那位男同學。那輛車是要繞個環島,等車繞回到出發地時張老師還在那里注視著這輛公交車。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張老師,他扶著車子的形象定格在我的記憶里。
之后我開始了新的征程,風雨兼程,一路向前,好像只有在夢里偶然會夢到小時候上課或玩的情景,張老師也偶然會出現在我的夢里,我還是像小時候那樣,輕輕地吐吐舌頭,跐溜就跑掉了。他真是如父如兄地關心我。說他如父是中國有句俗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其次我的父親那些年很忙,幾乎每天都周旋在運動中,我們一大家老老少少十來口人都指著父親,父親必須平平安安才行,所以父親對自己非常嚴格,他認為不妥的事情堅決不沾邊,即使在文革期間兩派中,父親是少有的無派人士。因此父親對我們的學業幾乎顧不上過問,張老師可能替代了一部分。我說如兄,是因為張老師一點都不兇,如果是父親會有害怕,但是張老師沒有讓我害怕,反而有時我還反駁他。記得有一次,我沒把字寫好,張老師批評我。我當時就不高興,反駁說“你是看內容還是看字?內容好了不就行了嘛,如果內容不行字好有什么用?”張老師看著我竟然沒話了,我好像很得意,張老師什么也沒多說就轉身走了。可是那天我越來越不得意,回家后,我把那個作業認真地抄了10遍,和新作業一起交上去。張老師一定看到了,但他仍然什么也沒說,也沒給我批語。
這幾日我腦子里不停地閃現張老師的影子,我找那張照片但沒有找到,不知道放到哪個家里了。我去年寫了一首詩《老師》,其中我有三個老師的形象在我的腦海里,第一個就是張老師。
老師
兒時見了老師會吐舌頭,
老師摸摸腦袋勝過五月玫瑰。
長大後見了老師會款款注目,
老師微微笑容猶如七月瓜果。
成人後見了老師會侃侃而談,
老師頻頻點頭像是九月醇酒。
無論世人贈了多少桂冠,
掛了多少光環,
改變不了老師在我心中
就是一盞路燈,
一段橋梁,
一個臺階,
一隻熒火蟲。
那盞路燈見證了我與書結緣,
那段橋梁送我奔向他鄉,
那個臺階扶我走上人生舞臺,
那只熒火蟲照明我曾陷入的黑暗。
老師是我的前世情人,
來完成他前世未盡的心。
默默付出不索回報。
只要我進步,
他就陽光燦爛。
我以為我馳騁了天下,
驀然回首,
老師站在身後依然那樣謙恭。
我以為我已長成了大樹,
駐目仰望,
老師還在幫我修枝剪叉。
走多遠走不出老師的眼,
長多大大不過老師的心。

我有時候想等我退休了去看老師們,也只是想一下,隨后就拋到腦后了。工作和家庭經常不給我多余的時間去想,總覺得老師是不會老的,應該還是那么年輕結實地站在那里,不相信歲月會對他們無情,他們對我那么好,歲月有情應該感知,應該對我的老師網開一面。但我忘了“天若有情天亦老”,等真正聽到說老師老了,老師等不了我了,我才意識到我錯了。我不知道老師走的時候是否想到過我,我不知道如果老師能聽見我的講述時他是否還記得這些事情,我不知道老師在他20年前離開時是否知道我已經走出國門去到雪萊的故鄉,我不知道老師是否會想到我今天會如此懷念他。我很想專門為他寫一首詩,但是所有的回憶都擠在我的筆端,都要出來表達對張老師的思念。實際張老師不是什么大人物,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位中小學老師,而且聽說那個年代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所以可以想象他當時是多么的無足輕重,但在我的眼里,他卻一直是高大的、偉岸的、挺拔的、睿智的,他的骨子里有一種東西讓我敬佩。他的教風一直影響著我,講課要有條理,要對學生友善,要多鼓勵學生。
親愛的張老師,如果我說“老師,對不起,這些年沒有回來看您,”您一定會眨著眼睛看看我,微微笑笑,什么都不說。如果我說“老師,對不起,在您最需要的時候,我沒有回來幫您,也許我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大夫減輕您的一點痛苦,也許我能求助到一個合適的療法能延長您的生命,讓您再多看看這個奇妙的世界。”您一定還是會眨著眼睛看看我,微微笑笑,什么都不說。您不多言語,然而一切盡在不言中。您走了已經20年了,對于別人已經習以為常了,可是對于我卻是久久不能平靜,我需要一天天地告訴我您走了,讓我接受這個事實。如果按照俗語“18年后又是一條漢子”,您應該又回到了這個世界,但是我不知道您在哪里。我這遲到了20年的祝福不知是該祝福您離開時一路走好,還是祝福您從此獲得新生。我相信這個世界有緣存在,您我有濃濃的師生緣,所以無論你在哪里,您都應該能聽到我的祝福。實際我一直都在默默祝福您,默默地祝福我的老師們,只是沒有像今天這樣讓我不平靜,非要把這份緣寫出來,才能讓心頭的波濤趨于平緩。張老師,我愛您;張老師,我懷念您;張老師,如果時間老人能安排好我倆的出場順序,我還愿意再做您的學生,聽您講課,看您寫板書……

雲水音(Gloria),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比較文化學者,詩人,散文作者,翻譯家。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作者與出處。
作者:云水音(Gloria)
來源:明心詩詞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