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笛的手掌和《手掌集》

詩人辛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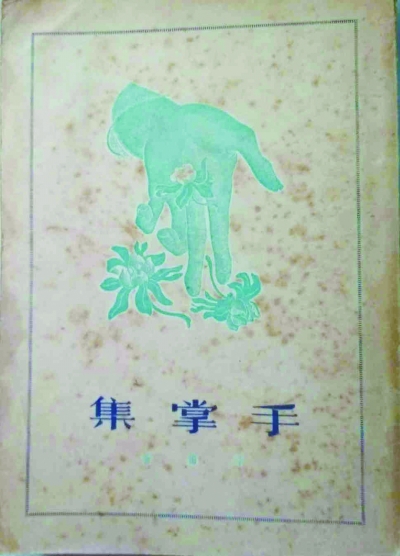
詩人辛笛的代表作
20年前我曾寫過辛笛訪問記,文章第一句這樣寫:“和辛笛先生握手!他的手掌,涼涼地。”
訪問辛笛的那一次,他送了我一本詩集,是1986年版的《印象·花束》,簽了名、蓋了章。現(xiàn)在舍下的一本1948年版的《手掌集》應該是后得的,不然,當時也一定會請他簽名留念。
辛笛說自己寫得最好的詩,在《手掌集》中。《手掌集》是辛笛的代表作,也得到詩歌史的公認。這本《手掌集》,1948年1月由星群出版社出版。印數(shù)1050冊,其中用西報紙印了1000冊,道林紙本50冊。是年8月,該書再版。出版者改為森林出版社。內(nèi)容沒變,與星群版不同處,一是封面做了改動,原由辛笛親書的“手掌集”和“辛笛”五字,改成了美術體。二是在版權頁上,增加了發(fā)行人辛白宇。就如同印刷者是子虛烏有的森林印刷廠一樣,至今仍未有人揭秘這個在一批以森林出版社出版物上赫然在目的發(fā)行人是為何人。是曹辛之?是辛笛?抑或誰都不是,只是障眼法而已。再版印數(shù)不載,想來不會多過初版的數(shù)量。如今,初版、再版均不易尋見。品相上佳的,更珍稀如鳳毛矣。
詩集由辛笛本人在1947年底編成,根據(jù)創(chuàng)作年代分“珠貝篇”、“異域篇”和“手掌篇”三輯。每一段的引首,都有一小節(jié)英文詩歌,分別來自霍普金斯、艾略特和奧登。所引詩歌,想來都是作者所喜愛的。這是一個漢語詩人用詩人的方式在向英語詩界的前輩作遙遠的致敬。
1948年的元月,辛笛隨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前往美國考察,隨身只帶了一本《手掌集》樣書。在舊金山,辛笛喜遇清華時代的同窗好友唐寶心,遂將這身邊僅有的一冊詩集題詞贈予。唐寶心歸國時,攜回此書。在后來的生活跌宕中,所有書籍被無奈散盡,此書自未例外。在流浪了若干年后,這本《手掌集》被愛書人姜德明(著名新文學版本藏書家)慧眼收藏。他在以后終于云淡風輕的日子里,分別找到了作者和受贈人。于是,這一本曾經(jīng)珍重相贈、認真庋藏、又流離冷攤的詩集,有了“回家”的幸運。
1931年辛笛從天津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yè)未幾,負笈英倫,回國后進入上海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是辛笛的父執(zhí)和同鄉(xiāng)。在海外和回國之后,他一直沒有放棄詩歌。直到他與星群出版社的詩友們猝然相遇。
最初成立的星群出版公司(星群出版社)醞釀于重慶,由同道朋友集資所辦。參加的人有曹辛之、郝天航、林宏、解子玉,臧克家未出股金,但以《罪惡的黑手》和《泥土的歌》兩本詩集的版權作為投入。故此,此5人應該是星群出版社的原始出資人。到了《詩創(chuàng)造》創(chuàng)刊,在曹辛之的敘述中,增加了沈明,減少了解子玉。前期的《詩創(chuàng)造》沒有名義上的主編,詩稿由大家分看,曹辛之負責編務,最后匯總征詢一下臧克家的意見。雖然可能他們都視臧克家為精神上的“帶路的人”,但也為后來該詩刊在編輯方向走向上的紛爭埋下了伏筆。
星群出版社出版的書和《詩創(chuàng)造》得到了讀者的擁護,但由于出版印刷和銷售回籠資金之間有較大的時間差,加上物價飛漲,出版社很快就捉襟見肘。這時,臧克家介紹曹辛之認識了辛笛。曹辛之晚年稱:當時出版社“經(jīng)濟壓力很大,主要經(jīng)濟來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務的銀行借支。辛笛在這方面幫了大忙,如沒有他的支援,出版社早就停業(yè)了。”
出生同一母體——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的《詩創(chuàng)造》和《中國新詩》,或許在政治(反蔣和親近共產(chǎn)黨)上并無太大的分歧,促使他們分野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在詩歌創(chuàng)作觀上的迥異。劉嵐山在1948年6月對臧克家的訪問記中,寫到臧的詩歌觀:“他覺得現(xiàn)在的詩,應該樸素有力,適宜于朗誦,而富于人民精神。對于空喊‘藝術性,永久性’以掩護自我中心的落后意識與情感的詩作品,則猛烈抨擊。”劉嵐山本人也是詩人,他認為,《中國新詩》“這本詩刊從發(fā)刊詞到作品,都比較隱晦,顯然有現(xiàn)代派意味……”有著現(xiàn)實主義詩歌觀的他,當年曾用化名著文批評《中國新詩》。他感到內(nèi)疚的,是從未向好友曹辛之坦誠說明此事。
《中國新詩》的提議者為辛笛,經(jīng)費問題也由辛笛所工作的金城銀行貸款解決。子虛烏有的森林出版社因為沒有實際地址,最后請在郵局工作的唐弢申請了一個郵箱代替,郵箱號碼為六四五號。但發(fā)行者仍為星群出版社。《中國新詩》每月一期,一共出了五期,便和星群出版社和《詩創(chuàng)造》一起被當局查封了。
1948年底,星群出版社被查封時,臧克家一度東躲西藏,也曾以“北方朋友”匿名被辛笛帶回中南新邨的家中躲避數(shù)日,還曾躲到李健吾家中,后來實在無法,找到黨組織的聯(lián)系人陳白塵(之前的聯(lián)系人先后為以群、蔣天佐,此時均已去了香港),陳寫了條子,讓臧去某銀行找某人可取700元“金圓券”,以為路費,囑可去香港找以群。辛笛知道臧克家要逃難遠避,再一次伸以援手,慷慨贈予2000元。雖然當年金圓券的實際價值俟考,但700和2000的對比,也可以確信辛笛此舉,無疑于“萬人叢中一握手”,臧克家由此感念了很多年。
黃裳為南開中學的同學好友黃宗江編了一本散文集,但出書卻很不容易。某日跟辛笛說了后,此書很快就印出了。這就是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的《賣藝人家》。封面題簽黃裳,裝幀設計曹辛之。道林紙印、毛邊。發(fā)行人,照樣是面貌不詳?shù)男涟子睢l轫撋希≈S宗江的題詞:“紀念亡友郭元同——藝名藝方”。這位郭元同,是黃宗江在燕京大學的同學,也是他妹妹黃宗英第一次婚姻的對象。這一冊小書,給朋友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作者而言,“垂老難忘”(黃宗江語)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年后,老資格的出版家范用還建議,稱這個版本應該原封不動地再印一次。可見此版給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辛笛在中南新邨的住所,曾給諸多文化人留下深刻印象。施蟄存的記憶里,辛笛家的栗子粉蛋糕極好、極好。黃裳的評價是:辛笛是好客的,文綺夫人燒得一手好咖啡。錢鐘書的“雪壓吳淞憶舉杯”詩中,記錄了第一次登門,和徐森玉(辛笛岳丈)、李玄伯、鄭西諦、陳麟瑞(柳亞子女婿)等人一起享用火鍋的舊事。
解放之初,此處房子賣出,辛笛一家搬進南京西路曹禺原來租住的房子。和辛笛在“更正朔”之后,與文學界雖然且行且珍惜,但在離開銀行界后卻一踅走進工業(yè)界直至退休一樣,辛笛當年的選擇,回頭看,屬明智之舉。
在李健吾的文字回憶中,曾寫過“辛笛家的揚州菜,特別是揚州湯包,到現(xiàn)在想起來,舌根還有留香之味。”當年,辛笛有自備車代步,家里還請有一位淮揚菜廚師。以淮安為代表的淮菜跟以揚州為標志的揚菜固然同屬一類,但細究起來,還是小有差異的。辛笛原籍淮安,雖然自小長在天津,但口味還是最鄉(xiāng)愁的。當年他家那一位大師傅推測應是烹淮菜小鮮的好手。告別中南新邨后,這位淮揚廚師也就散去,惜乎背影隱然,不傳其名。另,辛笛饗客,每以佳肴待之。其本人未必是老饕,但應是行家,惜乎在他留下的文字中,關于美食,終于不著一文。
辛笛是典型的讀書人,但待人處事有豪邁之氣。鼎革之年的7月,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辛笛請一批文化人吃飯,吃得高興,于是第二天又請了一次。方令孺稱辛笛是“慷慨好客”的“小孟嘗”。1983年新疆舉辦詩會,當?shù)弥械那嗄暝娙艘蚵焚M無著時,他又解囊相助,不計回報。
黃宗江在辛笛去世后曾著文回憶,文字還是一如既往地旁逸斜出。其中精彩的一節(jié),直可入當代《世說》:
“文革”后,我來滬,黃裳興高采烈地說:“辛笛又可以請客了”。當然要請!辛笛問我去哪兒?我說上海有一家可吃東坡肉比杭州的不差。結果卻是食興大敗,只因那時百廢待興,又百業(yè)難興。掃興之余,辛笛擊案曰:“重請!”
1997年歲末,我登門拜訪辛笛先生。他的家,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西路上。房子是老式的,略有些美人遲暮的味道,但立面挺括、建筑細部一絲不茍,終使這所老房子保有著自尊和雅的品位。我和辛笛先生相對而坐,當我說出對這房子喟嘆時,坐在遠處沙發(fā)上的辛笛夫人徐文綺清晰地告訴我:房子是維多利亞式的。
那一次,我曾認真地請教辛笛:詩歌還有希望否?剛剛過了87歲生日的辛笛老人,行動不便、嗓音嘶啞的他,很果斷、很堅定地一揮手說:新詩肯定有希望!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吳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1020/c404064-29599233.html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