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詩人的城市詩寫

詩人安琪(劉不偉/攝)
“城市詩”在中國當代詩歌語境里并非一個陌生的概念,1980年代,宋琳、張小波等人出版了《城市人》并先后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展》和《中國當代文學思潮》雜志上提出了鮮明的“城市詩”詩學主張,他們也因此被學者稱為中國“城市詩”派。有意思的是,30多年來,“城市詩”一直不溫不火,并未獲得足夠的重視,城市詩的書寫者也相對稀缺。“中國古代長期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和格局中,古人與土地河川交往甚密”(張德明),古人們寫起田園詩、農事詩堪稱游刃有余,由此形成一系列相對穩定的美學詞匯和象征指向一直影響到今日的新詩詩人。現今很多詩人的寫作其實是舊體詩的白話譯本,所寫的事物、所抒發的情感、所向往的人生,就像活在當代的古人。但這類詩依舊擁有強大的作者群和讀者群,刊物也中意這類詩作,畢竟每個中國人血液里流動著的依舊是傳統的血,教育所輸入、環境所熏陶,很難改變。所謂的“詩意”在中國當代,就是小橋流水、就是春暖花開,詩人們處理起農業文明的題材身手不凡,面對工業文明就不免捉襟見肘了。
“上海是中國首個現代化的城市,城市生活豐富多彩,許多生活內容與形式已經在根本上超越農業文明、田園隱逸范疇,對包括詩歌在內的藝術提出了挑戰”,批評家許道軍教授“挑戰”一詞道出了城市詩寫與鄉村詩寫的關系,它不是繼承而是另辟蹊徑,城市詩寫要尋找自己的意象、自己的表達方式,要打破習見的“詩意”,重新創造“詩意”,這是一個艱難的歷程。經常見到的是,詩人們一面享受著工業文明、現代文明帶給他們的便捷和舒適,譬如飛機、空調、電腦,乃至抽水馬桶,一寫詩就歌頌農業文明、咒罵工業文明,這里面有心態問題和寫作能力問題,他們寫不了城市詩歌,只能抱著農業詩歌粗壯的大腿不放,相比于城市詩,農業詩的大腿確實還很粗壯。真讓這些詩人定居到農村去耕田種地,保證他們個個叫苦,迫不及待要回到城市。這就是當下我們的詩歌寫作現狀之一。
北京跟上海不同,有極其現代先鋒的氣息,中國各界最高端的人才幾乎都匯聚到此,北京也有極其腐朽的封建王朝的遺存,故宮、紫禁城、頤和園,都是帝制時代的產物,北京周邊的農村也并未全部城市化,像宋莊這一個舉世聞名的藝術區,藝術家所租住的依舊是農民的房子。這一個混雜的復合型城市有一個龐大的群體稱之為“北漂”,北漂這個詞興起于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歷經30年而不衰,迄今已成為一個固定詞匯。北漂詩人群體的寫作和北京這個城市一樣,也是混雜而豐富,各類題材都有,本文我想分析的是北漂詩人的城市詩寫作。
北漂詩人因著各種原因離開自己的家鄉來到北京,對北京這座城市有何感受,認同還是拒絕?構成了北漂詩人城市書寫的一個主題。詩人許多直接說,“北京就是我的家”,小海賦予北京一個新名詞,“夢想之都”,于丹用“這是一個巨型城堡”來形容北京,郭福來“走在北京的路上”,身子雖然縮小成螞蟻,心卻拔得很高,這些青春與激情尚在的詩人,對北京充滿著勃勃旺盛的想象,他們有行動力,有干勁,北京對他們而言,有未來,有奔頭。詩寫北京更多的是這么一種,從北京風物入手,寫北京地理、北京風俗,李肇慶的“潭柘寺”、周瑟瑟的“動物園”、安琪的“菜戶營橋西”、花語的“北京地鐵”、張小云的“臥佛寺”、姜博瀚的“新街口”,角度獨特令人過目難忘的還有楊北城的《散落在北京的朋友》,寫了33個北京地名,每個地名又分別對照著與此地名構成反差或對應的朋友的體征,他讓青光眼住在燈市口、弱聽者住在鑼鼓巷、左撇子住在右安門,等等,楊北城此詩可以列入城市詩寫的典范。北漂詩人就這樣用詩歌的形式把北京這座城市搬運到紙上,每一處地理都蘊涵著寫作者的生命體溫和語言嘗試。詩寫北京還有這么一種,回向自己內心,體察自己與北京的關系,閉上眼睛對北京這個城市做冥想式的追問,對自己選擇北漂做刨根問底的反思:楊拓在小寒日的京城街頭,看見一絲不掛的乞丐,只能無奈地一聲嘆息;張后因為“你”不在了,就把北京當作“一座荒城”;蔡誠在北漂的宿舍里一遍一遍問自己,你“幸福了嗎”?讀之心酸;老巢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之后終于明白,“和家一樣可靠的名字是我租用的”,哀莫大于心死啊,連名字都不屬于自己。安琪的《極地之境》則觸及了這樣一個永恒的悖論和內心的掙扎,“一個/出走異鄉的人到達過/極地,摸到過太陽也被/它的光芒刺痛”。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是北漂隊伍不斷壯大的一個原因,農田被征用蓋房,耕田的成本和所得的回報不相抵,迫使青壯年農民出外打工謀生,北京成為他們的選擇之一。打工遇到欠薪怎么辦,讀讀孫恒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團結一心討工錢》,一輩子穩穩地躲在體制的飯碗里的人當能從此詩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光怪陸離的人,沈浩波詩中的那個已婚女“馬麗”,被老板一句“我愛你”哄住,死心塌地為他賣命,這樣的人自然不僅北京這座城市有,此詩的現實意義也因而不僅局限于北京。
宋莊作為藝術家的集散地早已聞名世界,它自成一個小世界,頹廢、奮進、快樂、悲傷、一夜暴富、落荒而逃,這里每天都在上演著生活的悲喜劇,居住在這里的詩人群體自然是這個小世界最有力的觀察者和書寫者,沈亦然《活得簡直就像一件藝術品》以自嘲的方式,寫出了北漂者與家人的矛盾沖突;阿琪阿鈺用“飄在宋莊的毛”來形容宋莊形形色色的藝術家無 根的狀態,特別有畫面感;牧野則用文字記錄下了一個反叛者的行為藝術(《關于冬天的回憶》);潘漠子的“808路巴士”宋莊人都不陌生,這是通往宋莊的最著名的一趟巴士,在這趟巴士上,一切皆有可能……宋莊是一個真正“相逢何必曾相似”之地,在這里,你可以盡情釋放你內心的魔鬼,宋莊當然也是需要你去掙養家活命的口糧,區別只在,在他處用體力,在此處用藝術、用腦力。我特別羨慕宋莊的藝術家們,羨慕他們時時行走在空氣中都是藝術氣味的宋莊。
2017年,我和師力斌博士聯合編選了一部《北漂詩篇》,由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這是北漂詩人的第一次詩歌集結,在編選過程中我發現,北漂詩人寫鄉村寫田園的反而不多,這讓我很有一種欣喜,仔細想想也正常,如果詩人們迷戀鄉村、迷戀土地,他們自然不會選擇北漂。北京是一個鍛煉人的地方,詩人們投身于此,被各種不可測的遭遇擊打所迸發的創作靈感,自然以北京這座城市所提供的生活種種為主,這是我認為的北漂詩人城市詩寫的理由。而此時,居住在自己的城市安穩過日子的詩人們正閉門造他們的田園詩和鄉村詩,那些詩,古典詩詞里可以淘得出的。
研究城市詩不可繞過北漂詩人。當然,北漂詩人所有的,滬漂詩人也有,粵漂詩人也有……北漂之北,可替換為任何一座城市,如果你選擇了漂。
2018-5-15,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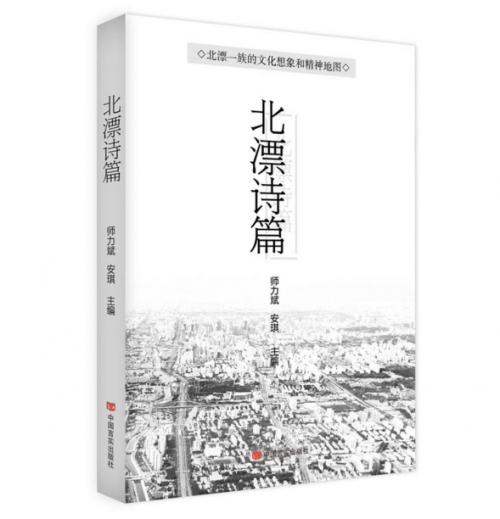
作者:安琪
來源:安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57e20102xr31.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