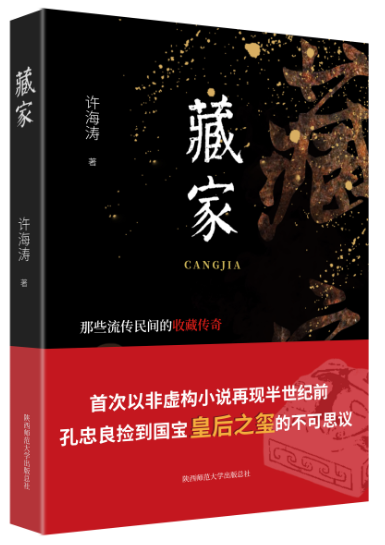
窺望
——《藏家》自序
作者:許海濤
馬家窯村旁的大陵,是我的瞭望之地。
馬家窯村東半里,蹲踞大陵。南一箭遠,“藏掖”殯儀館——半坡上,崖勢和樹木掩著,真像藏著掖著呢;老早時候是亂葬墳,雜亂擁擠,像大雜院。北二里,與王車村連畔種地。王車村,乃“王”曾駐輦之地。哪一尊“王”?沒人說得清白。西,隔公路,與黃家窯村相望。跟馬家窯一樣,老早時候,黃家窯也是亂葬墳。
馬家窯咋這樣憋屈,讓鬼魂圍了?
大陵下,亂葬墳中,殯儀館里,都是鬼魂啊!
先有大陵,后有亂葬墳,再后有馬家窯,最后才有殯儀館。
有位姓黃的洛南長工,扛活安了身,依二道原旋窯安家,遂有黃家窯。姓黃長工的同村鄉黨,姓馬的,扛活也安了身,平地鑿穴,穴內旋窯——這樣的窯叫地坑窯——便有了馬家窯。黃家窯坡勢陡,可旋窯;馬家窯坡勢緩,旋不得。咋不蓋房呢?
原上有的是黃土,長工有的是力氣啊。
活人與鬼魂睡在一搭,怕不?
洛南遭大災,逃不出來,死;逃出來,生!死里逃生了,還怕啥?窯里容了身,往前推日子。
我爺為啥在亂葬墳置地安家?
我爸說道:“做買賣不穩當。先人說,原上黃土厚,莊稼旺,日子穩當些。”
在地里做得直不起腰,我爸怨道:“穩穩當當下笨苦啊。”我跟在我爸后頭,也做得直不起腰,想去問我爺:“放著城里的舒坦日子不過,咋讓后人受這個罪?”
往哪兒問我爺?我降生馬家窯的時候,我爺已經睡在黃土深處的黑堂里了。我爺花了多少錢,買誰的幾畝旱地,我爸不知道。我爸說道:“你爺說,往東北方向走四百里,過黃河,進山西,那兒是咱的根。”
山西啥地方?
我爸答不上來。
我爸只記得他生在河南街;只記得他長在谷家巷,在窄窄的巷子里滾鐵環;只記得我爺的買賣是租賃花車,像如今的豪華婚車,卻鮮有“發斯”;只記得我爺給他吃豬尾巴,一手油,一嘴油,再沒有那樣的香了……我爺賣了花車,做起了鹵肉的營生;只記得他在果子市上小學,果子市有果子鋪,棉花鋪,糧食鋪,油鋪……
我們的根在哪里,我爸記不得了。
我長大了,不知道我們的根在哪里。
我兒子降生了,更不知道我們的根在哪里。
天色清朗空明,爬上覆斗頂——大陵像巨大的覆斗——我四面瞭望。南面,長長的、大大的山像挪移了,云霧繚繞,就在眼前,縱身跳,能跳到云彩上。云彩一朵又一朵,馱得了馬家窯村七十七口人。挖地坑窯的馬爺,佝僂腰,吭哧吭哧也爬上了覆斗頂,捋一捋被風吹亂的白胡子,指點著白云,對我說道:“東南那一大坨白云底下,就是洛南,我屋在柴峪溝,溝里的野毛栗子,又面又甜……”我沒有被野毛栗子誘惑,還是專心找河南街。正南,河的南岸,數不清的村莊,我難以確認哪一座村莊是河南街。我又找谷家巷。谷家巷在河的北岸,咸陽城里,街巷縱橫,房屋鱗次櫛比,我難以確認哪一條巷子是谷家巷。我朝東面瞭望,想看見黃河,更想看見黃河對岸的山西,卻看見一疙瘩又一疙瘩大陵。我瞭望西面,又看見兩疙瘩大陵。大陵間,散落大大小小的村莊。我爸說道:“刨到根兒上,馬家窯只有七戶人家。”這個根兒,指馬爺挖地坑窯后的十年間,之后,實行集體化,再沒有人家遷徙來。再之后,一九七六年,遷移了些半坡的亂葬墳,有了殯儀館。
之前呢?
七戶人家落戶馬家窯之前的根呢?
除馬爺記得清他出生在柴峪溝外,其他人,說得清的只是遙遠的縣名。村名呢?像離離原上草,被野火燒光了。
我迷茫。
我爸說道:“活下來的就是根!”
我不這樣想。我想,根在深處,在黑暗里,像草的根,樹的根,莊稼的根。
朝北面瞭望,還是山,與南面的山一樣,我不知道山的名字,像旁人一樣,叫南面的山南山,叫北面的山北山。北山的山梁,朝一個方向攢著勁兒,那勁兒似乎把控了每一塊山石,每一棵樹,每一株草,甚至每一朵云,從四方,朝中央一浪一浪奔,猛然間,拔高,凸起,直直向上,像高高擎起的火炬,直插云天。
一回又一回,一年又一年,我爬上覆斗頂瞭望,瞭望……瞭望到了什么?河南街從沒有得到過確認。谷家巷也從沒有找見過。從未望見過黃河。從未望見過黃河對岸的山西。只看見一疙瘩又一疙瘩的大陵,大陵間散落的村莊,不變樣子的咸陽城……
西北風吹著,東南風吹著,我一天天長大了。
到了該知道的年齡,我知道了南面的山叫秦嶺,河南街和谷家巷之間的河叫渭河。我知道了大陵叫作延陵,趙飛燕、趙合德姊妹倆侍奉的漢成帝劉驁埋在覆斗下。我知道東北方向一疙瘩又一疙瘩的大陵,是康陵、渭陵、義陵、安陵、長陵、陽陵,西面的兩個大陵是平陵、茂陵。這些陵下,埋的都是劉驁家的人。有他的長輩,也有他的晚輩。我知道了二道原叫作五陵原。南山和北山間,東西八百里,叫作關中。我知道了北面的山是九嵕山。“火炬”頂端,是昭陵,埋葬著李世民。我知道了昭陵西北方有乾陵,埋藏武則天和他的丈夫李治。昭陵東,綿延二百多里的山勢間,有獻、定、橋、泰、建、元、崇、豐、景、光、莊、章、端、貞、簡、靖十六座唐陵。陵下,埋的都是李世民一家人,有他的長輩,有他的晚輩。
有人說,劉家的陵下,是劉家的根;李家的陵下,是李家的根,都像大樹的根,深深扎在黑暗里,看不見。還有人說,那不僅僅是劉家的根、李家的根,還是更多人的根,民族的根。
他們說的似乎不錯。
九十三歲的馬爺死了。他唯一的愿望是把他埋在洛南的柴峪溝……馬爺的兒子、孫子、重孫子都無法滿足他的愿望。馬家窯一百二十二口人也無法滿足他的愿望。這時候,馬家窯已經一百二十二口人了。即使埋在火葬場東墻外的亂葬墳,為他堆起一疙瘩黃土,立一方青石的墓碑,這樣的想法也實現不了。亂葬墳早已不準許土葬,最后,終于……馬爺被推進了火化爐,高高的煙囪冒出濃煙,向東南方飄去,飄向秦嶺……我望著飄游的白云,默默禱念:“馬爺,風長眼呢,你會回到柴峪溝!”
馬爺的根在柴峪溝嗎?
像草的根、樹的根、莊稼的根,柴峪溝地下的黑暗里,有馬爺的根嗎?
在河南街,在谷家巷,在黃河,在黃河對岸的山西,在土地深處,黑暗里,像草的根、樹的根、莊稼的根,有我爸、我、我兒子的根嗎?
我想看見!就像我爬上覆斗頂瞭望,想看見與從前有關的一切。
王車村北二十里,一院幸存的老宅里,我看見了上千幅 “容”,色彩鮮艷,神情端莊。“容”是先人像,老早時候,懸掛在中堂,或是祠堂。
在轆轤把巷的一家老房里,我看見了三百多枚印章,銅的、骨的、玉的、壽山石的、象牙的、黃楊木的……從戰漢到民國,跨度三千年。轆轤把巷與谷家巷隔一條大街。爬上谷家巷口的樓頂,我望見了馬家窯,望見了漢成帝延陵。馬家窯像一枚草葉。漢成帝延陵像一粒土坷垃。
在渭河南岸一個叫做六村堡的村子,我看見了上萬枚瓦當,有云紋的、水渦紋的、樹葉紋的,有刻“漢并天下”的,刻“長樂未央”的,有刻“上林”的……我問主兒家咋有這么多,他笑道:“這兒是漢城遺址,這些瓦當都是咱先人房檐上的呀。”還有陶的豬、牛、羊、雞,陶的糧倉、灶、釜、盆、甕……他說道:“這些都是咱先人的家當啊!”
在秦嶺北麓,一個叫做南五臺的地方,我看見了近萬根拴馬樁,有輩輩封侯的,有太獅少獅的,有胡人馴獸的……五六百年、三四百年流傳下來,挺立曠野,像兵馬俑巍巍方陣一般震撼人心!主兒家說道“拴馬樁不光用來拴馬,還是咱莊戶人家的華表呢!”
在黃河岸邊,距離鯉魚跳龍門不遠,一個普通的莊戶人家,我看見了五萬多本老書。早的到明代,晚的到“文革”,堆壘滿屋,難以插足。主兒家不善言語,見我驚詫地喊叫,只咧嘴憨憨地笑……
在五陵原,在關中,在山西,我還看見了五千多份老契約、三千多幅老繡品、兩千多套老皮影、一千多本老課本、八百多本老日記、五百多幀老照片、三百多張老條案……
哎呀,數不清的老器古物,在數不清的人手上。
他們在干什么?
尋根!
尋得到嗎?
能!
他們說,尋到了先人的一幅畫,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當,就尋到了根。
這,這算尋到了根嗎?
他們說,算啊!一幅畫,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當,像根須,傳到如今,還活著,意味著根還活著啊!
根還活著嗎?
一葉窺秋,窺斑見豹,一幅畫,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當,就是葉,就是斑!
于是,我成為他們的徒弟。
他們被喚作“跑家”,深潛鄉下,挨門進戶搜羅先人的遺存,早的,更早的,老早的,更老早的先人遺存,越早越歡喜,越老越珍愛。跑得久了,跑下了規模,便被尊為“藏家”。
一絲絲根須在藏家手里聚攏,滋養起一條龐大的根系,滋養我的干渴和迷茫。
我不再爬上覆斗頂瞭望。瞭望給我的,只是迷茫和嘆息。
我開始窺望。窺望一幅畫、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當,像透過孔隙,窺望我爸、我、我兒子的根,馬爺的根,馬家窯的根,黃家窯的根,王車村的根,劉家的根,李家的根,亂葬墳下的根,或許,一個民族的根……
作者簡介:
許海濤,1969年生,陜西咸陽周陵人,著有短篇小說集《跑家:那些埋藏民間的古董傳奇》、長篇小說《殘缺的成全》等。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