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山
作者:王磊斌
1
那頭,家人們還在跟大姨媽大姨夫一家子告別,而我獨自一人悄悄地走向能看見那山的地方,那也是外婆家的方向,是外婆與外公安葬的地方,我輕輕地念叨:外婆,我走了。
那座白日里青蔥油綠的山,此刻是那么的灰暗,那山的正上方,月兒只要稍微關照下繚繞的云霧,便襯得那山更是漆黑,我甚至開始害怕起這樣的色調。
那山呀,我從不識它的名,但打我記事起,溫暖鮮亮是那山給我的獨特感覺。我猶記得去山中外公墓地的路上栽種著漫山遍野的橘樹,隨手一摘,剝開的橘肉是那么的甜美甘爽;猶記得山上有多條緩緩流淌的溪河,水里頭有游曳躍動的河蝦,我的母親在山腳下那塊溪水流經的大青石上搗浣過衣物;也猶記得山上的野蔥、竹筍、芋艿隨處可見,山風只要一經過,竹林沙沙作響,陽光忽閃忽現,是那般舒服且愜意。
可如今,曾那么溫暖的那山,在我心里確實暗淡了下來,并不由于此刻入夜的緣故,而是那度曾經的暖意漸漸涼卻甚至于在某一刻已然冰冷地凍結。要去溯源所謂的“某一刻”,是感懷且痛楚的,但只要看到那山,即便是再刻意的避閃,回憶也還是會不禁迸發出來。
茅畬鄉東邊村153號的一樓堂廳,我的外婆躺在冰棺中,大悲咒循環播放著,白色的蠟燭搖搖晃晃。我就站在冰棺的一側,看著棺內外婆慈祥的臉龐,突然覺曉至此我成了一個“沒有外婆”的孩子。母親、舅舅、姨媽們輪番為外婆守夜,好幾次半夜里母親回到三樓休息,我都被鬧醒便再也無法入睡。因為是夏天,外婆的老屋也沒有裝空調,故而電扇打著,窗也敞著,我躺在臨時架起的一張床上,面對著的就是那扇窗,而窗外便是那山。
2
那山,在這深夜里是烏黑一片,像是一塊巨大的陰影橫亙在眼前,冷峻的月光下云霧浮沉繚繞,似一縷萬般留戀世間的幽魂四處飄蕩,風來散開,風去又慢慢聚攏。夏里的悶雷忽閃,那山愈加顯得陰沉。
我極遺憾沒能見到外婆最后一面。最后一次見面是外婆住院時,她就躺在病床上,插滿了管子,我們幾個小輩陪了她幾日,看著外婆氣色漸好,便又匆匆返程上班。返程前,我依偎著外婆,她看著我,用半臺州話半舟山話用力說道:“斌斌,你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外婆就像看穿我那幾日的心思一般,那時我已被組織安排下社區主持工作,對于剛工作兩年的我來說承載的壓力還是巨大的。外婆的這一句叮囑,既是鼓勵也是讓我安心放手去干的寬慰。
只是沒想到,相別一個月不到,外婆便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和陽子表妹趕到茅畬的時候,我們那么愛的外婆就靜靜地躺在冰棺里,閉著眼睛,露著慈祥的笑,卻再也無法一見到我倆便欣喜地叫我們“祖宗外孫寶貝”了。
這月的11日晚,臺州黃巖的馬路上,舅舅家,姨媽家,還有我家飯后散步消食,我和陽子兩人走到黃巖中醫院的門口,一起望向了住院部,我說:“走到這里,我好想外婆啊。”陽子說:“我們與外婆的最后一面就在這里,那時我們所有人都在附近住著賓館夜以繼日地陪著外婆,雖然艱苦但因為是為了外婆,所以那時也感覺很幸福。”我又說:“每次來臺州黃巖,都是我人生歷經變故的時候,但每次來過這里,看到過外婆,我就充滿了力量,無懼即將面對的任何未知挑戰。有外婆的這里就像是我的加油站。”
隨后,大人們也踱步到了醫院附近,也都不知不覺地駐足了一會兒,他們沉默著沒有說話,想來也肯定是念到外婆了。
3
雨季里的夏日,幾道電光閃過,悶雷陣陣。
“媽,外婆走前,你在嗎?”我看著窗外那塊漆黑的陰影,突然問向還在整理床鋪的母親。
母親沒有因為我還未入眠感到驚訝,而是沉默了好一會兒,我以為是她太疲憊了,所以不愿再說起。
“我在,你外婆走前的那夜,是我守在她的身旁。她說肚子餓了,我便熬了一碗粥給你外婆吃,那碗粥你外婆吃下了大半。我本以為你外婆能吃下那么多是因為病情好轉了,可誰承想這卻是她這輩子最后的一頓飯,吃完這頓飯,沒過幾個時辰,你外婆自己悄悄地走了。”
那山的霧此刻正慢慢散開,一邊散開一邊努力地向山坡攏去。
伴著突襲來的涼風,我分明聽得見母親的抽泣聲。
“我該知道,這是你外婆臨行前的最后一餐,是你外婆想飽飽地上路,讓大家安心,不存遺憾。你外婆,就是在人生最后一刻,也還在為子女們作考慮。我只是后悔,那最后一餐太匆忙了,太匆忙了……”
人與人生與死的離別,都是匆忙的,哪怕有預知,也會故意掩藏下繁雜的心思。外婆就只是說了一句餓了,沒有說一定要吃一口心心念念的什么,而母親也只是很自然地熬了一碗適宜外婆入口的甜粥。母親后知后覺的這點遺憾,反而是我們任何人都極羨慕的幸福:至少,外婆的最后一餐是母親做的;至少,外婆在這人世間的最后一刻是母親守候的。
4
那山孤寂地聳立在蜜橘之鄉黃巖茅畬,這個聽名字就很鄉土的小鎮,但于我的人生而言,它的分量不亞于生我養我的泗礁小島。我就是從這些個不起眼的小地方而來,所以對小地方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即便它們再沒落再破敗,但那種早已植入生命基因序列的各種感覺永遠無法抹去了。
午前到了大姨媽大姨夫家,當地的大個橘子、堅果早已鋪滿桌面,大姨夫更是在灶臺前翻炒著我最愛的什錦米面,大姨媽則忙著包裹清明前浙人必吃的糯米青餅。這兩樣,都曾是外婆最愛為我烹制的吃食。說實話,小時候我總是嫌大姨媽大姨夫的做飯手藝不如舅媽,每次去大姨媽大姨夫家吃飯,雖是一桌子的好菜但總是寥寥幾口。而現在,看著這些本鄉本土的特色小食,那種饞意真是空前絕后了。或許,人的味蕾也會懷鄉念人吧。
長輩們在廚房在院內忙前忙后,而我獨自一人去了鄉里閑逛。鄉里的中心大街,那些店鋪還是我小時候的樣子從未改變,零食店里還有我小時候吃的五分錢一顆的牛奶糖,還是塑料罐子裝的;雜貨店前還是會擺出一排可論斤賣的書籍,我還記得我小學在外婆家過暑假,在這家店鋪買了本拼音標注的《三國演義》,然后一個暑假就光捧著這本書一遍遍看,一段時期我的作文里都充斥著《三國演義》的元素。我隨意穿梭著,然后也拿起手機不停地拍著照片,老式的民國建筑,頹棄坍塌的老屋,成堆晾曬的薺菜,街邊屋外三五成群的老人們,甚至于一只打著瞌睡的老狗,都存入了我的相冊。
就在這樣放空的狀態中,我已繞了大半個鄉里,也不知不覺走到了外婆的老屋前,因為沒有老屋的鑰匙,便就在屋外隔著窗向里張望了下。隔壁屋的一個老婆婆正好在院內串著小鈴鐺,她看了看我,問道:“你是誰啊?”
“您好哈,阿婆,這是我外婆的家,親外婆的家。”我回答道。
“這屋里已沒人住了。”老婆婆特意補充了一句。
“嗯嗯,我的外婆走了有幾個年頭了。”我邊回應著邊向后撤了幾步,拍下了老屋的全貌。轉身離開的一霎,晴好的天里,那湛藍的天空與閑逸的白云下是那山。
我想外婆要是還在,這難得一家團聚的幾天她老人家該有多么開心與幸福啊。
5
午飯過后,全員按照約定的計劃,上那山掃墓。
大姨媽拎著一籃祭品,姨媽與母親攜著紙錢香燭,大姨夫扛著把鋤頭,一大家子人浩浩蕩蕩地穿過東邊村一路向著那山行進。
瓦片堆砌的屋檐、宅門前的石敢當、淙淙流經的溪水、大棚里新培育的橘樹苗、田埂上散落了一片又一片的作肥的橘子皮,撥開一簇又一簇的竹林,終于來到了外公外婆的墓前。
男人們開始清理周邊的雜草樹木,女人們開始擺置祭供的物品。
除草的間隙,我無意間的幾次轉身看到了表妹翠翠在一旁悄悄地抹著眼淚。
這一幕,唰地一下,把我拉回了外婆出葬的那天。
雨下得極大,一切都是濕漉漉的,包括身上的喪服。雨混淆了淚水,風淹沒了哭聲,一路都是陰郁的,舅舅捧著外婆的遺像,斜風密雨嗒嗒地拍打在外婆的臉上,走過泥濘的山路,來到墓冢前,舅舅把外婆的骨灰放進墓里,墓里也是濕漉漉的,接下來外婆生前的遺物一件件放進墓穴中,外婆那些生前常穿的衣物濕透了,外婆那些平日常用的物件也滴著雨水。水汽一次次模糊了我的鏡片,我一遍接著一遍用力地擦拭著,心底里就一個念頭:再多看一眼外婆吧,再多記一些關于外婆的回憶吧。然后轉頭一看,外婆唯一的親孫女,我的表妹翠翠就呆站在一旁傷心地抹著眼淚,那眼淚流得是那么絕望且哀苦。
外婆最疼愛的翠,就是被外婆從小一手帶大的。后來外婆一直住在舅舅家,每次家庭出游或吃飯,翠都要帶上外婆,不愿讓外婆孤單一人留守在家;每次有好吃的或新鮮的東西,翠一定要給外婆留藏一些;甚至于讀了中學大學還時不時要跟外婆擠在一張床上睡。
翠,對外婆是那般孝愛。外婆走后,她整個人像是忽然長大一般,有時關于外婆所考慮的事或談論的感受讓我這個做哥哥的也嘆為不及。
外婆的墓清爽明凈了許多,然后我們一家接著一家輪流上香祭拜,母親和姨媽在兩邊燒著紙錢,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上墳的儀式全都落定了。大家一一跟外婆與外公告別,翠是最后一個,她跟大伙說,你們先下山吧,我跟小彭倆人再待一會兒。
小彭與翠的婚期就在明年,論起來應該是我的準妹夫了。這幾天,他特意跟單位請假,陪著我們走東訪西,但無論去哪里,他的手都始終牽著翠,一個小小的細節便看得出,他和翠感情很甜也很暖。
我跟長輩們說,我們先下山吧,讓翠跟外婆說些悄悄話。
下那山的途中,小姨媽感慨了一句:“翠,重感情,對外婆的感情是真的不一般。”
舅舅補充了一句:“是啊,咱媽一直隨身帶著的皮包證件,翠一直放在自己房間的枕頭下,想奶奶了,便時不時拿出來看看。前不久,我做夢夢到媽,媽開心地跟我說,翠的男朋友長得干凈精壯,是個好小伙。這個夢我也跟翠提起了。”
“那看樣子,翠現在正跟外婆外公介紹著小彭,讓外婆好好看看這個好小伙,好孫女婿呢!”我的話音未落,大家輕盈的笑聲便漾蕩在了那山的林間與溪頭。
6
下山后,午后的辰光還早,我在手機上無意刷到附近有個叫“天空之城”的地方,趁著如此晴好的天,我便建議一道驅車去看看,長輩們也都同意了。
“天空之城”是坐落于平田鄉最高峰的一處正在開發的茶園景觀,平田緊挨著茅畬,在“天空之城”亦可以望見那山。
崎嶇的山路,一彎接著一彎,不斷攀升的高度,加上30邁不到的速度,足足40分鐘的膽顫心驚,抵達“天空之城”的那刻,緊繃的神經一下子松弛了下來,腿也麻了,踩到地面的一瞬猶如航天員登月。
穿過漫山翠綠的茶園,在山頂的風車長廊處,我看到了這一生最美的景致。遠眺,一輪金光四射的柔陽,觸手可及,第一層是綠油油的茶園,五彩的風車還有透明的蘑菇屋,第二層是倒映著湛藍天空的如鏡湖面,第三層是錯落有致的蒼郁的島渚,再回到第四層輪廓尤明顯的藍天白云,四散的金光灑下,風搖著祈福的木牌,偶爾入景的風箏增添了不少夢幻與童趣。
這樣的景,我夢里似曾相識,但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夢境了。
我跟舅舅萬分欣喜地說道:這山上得雖然艱辛,但看到這景,覺得太值得了,一切都太值得了。
家人們有拍照的,有喊山的,有做著深呼吸的,也有就靜靜地看著遠處的景,雀躍的,安然的,夢幻的,惜時的。
我環拍著眼前的美景,鏡頭里突然闖入了一處熟悉的身影,是那山,應該是那山,就是那山了。
那山包裹在陽光里,曾經的灰暗瞬間褪散,青蔥油綠的明亮,在那山上熠熠生輝。
這偶得的“天空之城”像是外婆特意邀我們齊聚的地方,外婆在告訴我們她在天上和外公很好很好,也慰藉著我們她與外公一直在我們身邊,不曾離去,永遠護佑著我們,愛著我們。
那山,在粼粼的漾著波紋的水面上搖啊搖,搖啊搖,搖到了外婆橋,外婆好,外婆好,外婆對我嘻嘻笑;那山,在我與外婆那些珍貴的回憶中搖啊搖,搖啊搖,搖到了外婆橋,外婆說,好寶寶,外婆給寶一塊糕……
——刊于《草原》2022年第11期

作者簡介:王磊斌,1991年生,供職于山東省泰山學院。曾在《散文》《中國報告文學》《讀者》《中國青年》《中國青年作家報》《中國教師報》《上海故事》《海中洲》等雜志報刊發表小說散文百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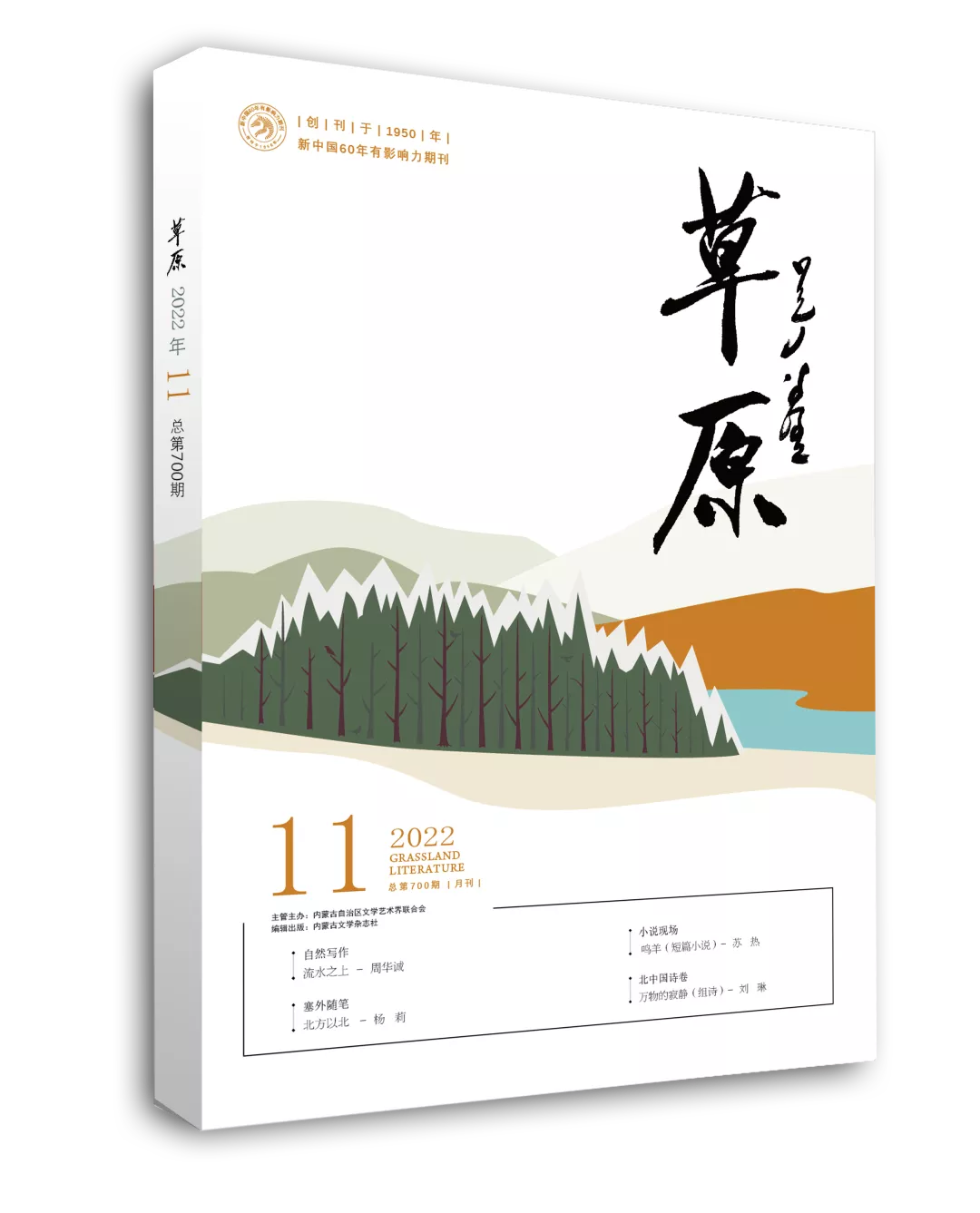
編 輯 | 塔 娜
初 審 | 高 陽
復 審 | 蔣雨含
終 審 | 阿 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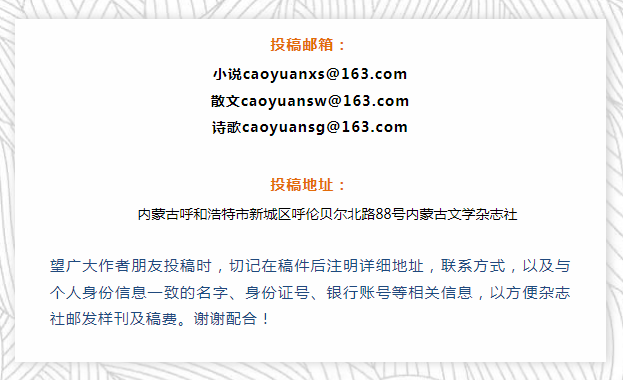

來源:草原
https://mp.weixin.qq.com/s/qwbK-d0dmLOzxry5eMw5xw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