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表弟羅上林
作者:楊遠新
一般來講,表兄表弟之間,從年幼到年輕階段,相互都很親近,甚至很密切,那是因為互為玩伴,互為依靠,彼此需要對方。隨著年齡的增長,特別是結婚成家后,各自有了新的玩伴和依靠,表兄表弟就漸漸疏淡了。這似乎是規律,也符合人之常情。但我與表弟羅上林則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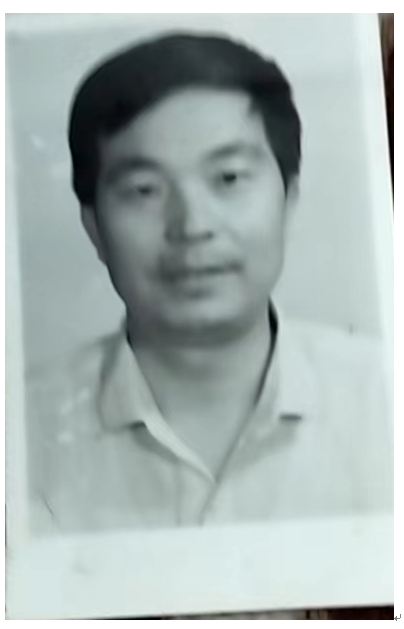
羅上林年輕時留影
這與我的母親與他的母親有著極大的內在關系。我母親李清鳳是姊妹中的老大,他母親李清枝是姊妹中的老二,姐妹倆年齡懸殊不大,僅僅兩歲之差。姐妹倆從小就相依為命。我母親是柔中有剛,他母親則是剛中有柔,往往相得益彰。
記得自我稍稍明白事理開始,就常聽外祖母以驕傲的口吻說起她的兩個女兒上曹家湖挖藕,為她臉上爭得光彩的事。
洞庭湖區挖藕,這本是男人干的活,從古至今皆無變化。我外祖父輩、曾外祖父輩及以上,家里男丁多,都是這樣傳承的。可到了我母親我大姨這一輩,家里缺少的就是男丁。這是因為我舅舅李少清,族名李承載,比我大姨晚出生十年,尚處在年幼階段,但凡男人干的農活,我母親我大姨都要干,挑起男人的重擔,為我外祖父外祖母分憂。
那是一個無大風,有陽光的冬日,離過年只有幾步遠了,洞庭湖人家都在準備各種各樣的過年貨,其中湖藕是必不可少的,到了過年那天,將藕放進臘肉一鍋燉煮,白生生的藕便變得烏油油,用筷子從中挑取一節,送到嘴邊,香氣撲鼻,順勢一口咬下去,會情不自禁地發出感嘆:“哎呀!粉坨噠!好吃得狠!”燉藕咬斷處,牽出縷縷藕絲,比蠶絲還要細,還要密,長度你想拉多長都可以。燉藕切片、切丁,切絲,放上綠蔥紅椒和白色的姜絲燴炒,是除夕那天的團年飯,和進入正月里宴請春客的一道主菜。
我母我姨看中那天是挖藕的好時機,姐妹倆各挑了一擔竹制的專門用來挑藕的夾子,各持一把專門用來挖藕的鐵鍬,從皇城村陽鋪崗李家大朝門出發,跨越架在碧蓮河上的那座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的老渡口青石板古橋,往北穿越一片布滿稻樁的農田,經過幾棟木板瓦屋之間一道樹竹掩映的百米長廊,再走幾段田間小路,就到了藕場曹家湖。
這里早在南宋末年,便是農民起義領袖鐘相、楊幺操練水軍的絕佳場所。后來因沅水卷來武陵山的泥沙,在此駐足生根,湖底逐漸升高,便演變成了湖灘,枯水時節,悠悠沅水繞湖灘而去。一代又一代湖區人抓住時機,筑起巍巍沅南大堤,使得這里成了內陸。內陸中間又夾有大大小小許多的湖泊,像從天上撒落的無數顆珍珠,熠熠生輝。曹家湖就是這其中的一顆。像其他湖泊一樣,他本無名,只因曹姓人氏最早從北方遷徙來到這里,看中了獨特的風水,便收住流浪的腳步,在湖的兩岸,搭起蘆葦棚子,安家落戶,繁衍子孫,曹姓人丁多了,這里便自然而然成了曹家湖。由于曹姓人向官府繳稅從不講價錢,官方也予以了認可,無論朗州、武陵,還是常德府志中,便有了曹家湖的名字。
曹家湖的藕,以其品質優良,味道獨特,享譽洞庭湖。每到冬臘兩月,四周漢壽、常德、安鄉,以至桃源的農民,都會從四面八方涌來曹家湖挖藕。
此時,我母我姨眼前的曹家湖,滿湖的玉臂藕,不再撐開綠傘般的荷葉,也不再舉起碗狀般的蓮蓬,而是彎下與風雨搏斗了春夏秋三季的傲然身軀,進入了冬眠時期。
我母我姨走進洋溢歡聲笑語的湖場,尋覓到一片好藕凼,便揮起手中的藕鍬,掀開烏黑的淤泥,接連不斷地從泥底掏出一支支白花花的玉臂藕。這除了需要力氣,更需要嫻熟的技術,藕鍬入泥,不輕不重,輕了,見不到一支完整的藕,重了,會把整支藕挖斷成多節。濱湖人對挖出的藕有極其嚴格的講究,那就是整支一丈多長的藕身不能有一絲藕鍬劃的傷?。專用名叫“傷鍬”。如果傷鍬的玉臂藕,出售,沒有好價錢,送人,也拿不出手,因為他失出了原汁原味。
我母我姨揮汗如雨,身旁的藕夾里,一支支玉臂藕整齊地往上加高。
一旁有個挖藕的男子名叫龍金虎,卻半天挖不出一支藕,向來欺善怕惡的他,眼紅我母我姨不停地從漆黑的泥巴里抽出一支又一支白花花的玉臂藕,便擠占我母我姨的地盤。
我母親與之理論,龍金虎平時作惡慣了,根本不把我母放在眼里。明明是我母親手中的藕鍬掀開泥巴,一支手臂粗,扁擔長的玉臂藕才得以從泥底露面見天,龍金虎則撞開我母親,強行把那支藕奪了過去,據為已有。
我大姨見此情形,火冒三丈,一步沖上去,揮起手中的藕鍬,朝龍金虎腳前猛地一插。
龍金虎吼道:“好你個小女子,敢與老子動武不成?”
我大姨二話不說,朝龍金虎臉上甩出一巴掌,說:“你欺老子不敢動武?老子是李祖軍的女兒,你有種就跟老子過招!”
我外祖父是出了名的“打匠”,即武功高強的人。他34歲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當挑夫,從皇城港行至常德的半途,他看準來水廟至蘇家渡之間那片有利地形,憑借一根齊眉棍,橫掃7個日本鬼子,得以死里逃生。這事傳遍了西洞庭湖一帶。
此時龍金虎聽了我大姨的話,兩眼有點發呆,兩腿也微微發抖。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我外祖父的對手。
“男不與婦斗。龍金虎你搶奪李家姐妹的藕,把你的臉用襠襠小衣(內褲)裝起來!”
“你那不是兩塊臉,是兩塊屁股!”
湖里挖藕的人一片吶喊聲,都出于抱不平,為我大姨助威。
我大姨一手插腰,一手指著龍金虎的鼻子,大聲說:“你不把這支藕還給我姐,老子就一鍬請你見閻王!”
“清枝姐姐,你把他夾到胯里打!”
“看他龍金虎還要臉啵?!”
藕湖里的喝彩聲一陣高過一陣。
這時,我母親對龍金虎曉之以理地說:“你看這湖里,到處都有藕挖,你偏要搶奪我們的藕凼,你沒有打到一滴滴男人的氣!”
我大姨對龍金虎下了驅逐令:“你滾開,這是我們的藕凼。你還不滾,老子就動手了!”
在眾人的一片助威聲中,龍金虎不敢與我大姨交手,只得提了藕鍬,連那支藕也沒有要,灰頭土臉的溜到一旁去了。
從這件事,也可見我母親與我大姨這對患難姐妹從小關系是何等的密切。這種基因遺傳給了我和上林。上林的性格頗像我母親,而我的性格則頗像我大姨。
1945年,我母親嫁進了何婆橋的楊家,一年之后,我大姨嫁進了金鵝嘴的羅家。我父親楊先德,我姨父羅廷貴,都是窮苦人家出身,都是忠厚本分人,都是農忙插田,農閑捕魚。因而兩家來往頻繁。這奠定了我與上林從小互相親近,結婚后照樣親近的堅實基礎。
同一年,我母親生育了我,大姨生育了上林,彼此相隔三個月。我是哥,上林是弟。他稱我母親姨媽,我稱他母親大姨。
小時候,我與上林,還有我表姨劉春秀的兒子萬龍武,三個結伴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家,因為我的外婆與萬龍武的外婆是親姐妹。萬龍武出生5月25日,小我11天,小名取其出生月日的諧音叫愛武。

母親李清鳳(前排左)、大姨李清枝(前排右)、小姨李圓清(后排右)、三姨李清純(后排中)、表姨劉春秀(后排左)合影
一次我們三個都爭著放牛,弄得那頭牯牛不知往左走還是往右走,結果直接跳進了水塘里。外婆自然對三人中的老大提出了批評。我覺得外婆偏向上林,氣呼呼扭頭就走,直接沖回了位于老渡口的家。上林則領著愛武,緊追三四里路,一直追到我家里。他滿臉微笑地勸說我回外婆家。他說:“哥哥你不回去,外婆就會不高興,不高興就會生病。難道你不害怕外婆生病?”我聽了他的話,兄弟三人又一路追趕著,回到了外婆家。
上 林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小名叫陽婆,我是母親生的第四個孩子,小名叫四婆,因為算命先生王子涵說,我倆都不好養,只有男孩女養,前世的父母找不到,才能長大成人。于是他是婆,我也是婆。
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一致認為,我倆躲避前世父母尋找的最佳辦法,就是上學讀書。
1965年,我考進漢壽縣二中,上林為我高興。1966年,上林考進漢壽縣一中,我為他高興。
1966年9月1日那天,我辦好入學手續,便立即從縣城東郊外的鎮龍閣,步行三四里,趕到縣城南側的漢壽縣一中,兄弟倆第一次遠離家門見面,都顯得格外興奮,也倍加親熱。
1968年12月,我被推薦上聶家橋中學高一班就讀。1969年12月,上林被推薦上聶家橋中學高二班就讀。兩個班的教室只隔一面墻,課間休息的鈴聲一響,我倆就會聚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那時都是走讀,每天早晨,他從金鵝嘴到達頂崗鋪三叉路口,如果沒有見到我,他就會在那里等候我的出現。如果我從老渡口先到達頂崗鋪三叉路口,沒有見到他,我也會在那里等候他的到來。我倆見面,一起有說有笑地踩著青石板鋪成的古老的聶家橋,跨一片滄浪水,穿幾坵農田,越幾塊旱地,肩并肩進入學校。放學后,我倆會一起奔跑在學校的籃球場,打完一場球,然后抹掉汗珠,踏上回家的路。抵達頂崗鋪三叉路口,他向東,順清泥湖回家。我向北,朝碧蓮河而歸。相互邊走邊揮手,直到何家灣里和彬樹王家的樹竹掩映了我倆的身子,彼此才不再揮手,一心往家里奔。
我倆同校一年的高中時光是愉快的。可接下來,是難舍難分地各奔一方。1970年冬季大征兵,他體檢合格,穿上綠軍裝,走向軍營。我則因有人從中作梗,未能實現當兵的愿望。我送他啟程時,他一再鼓勵我不要放棄,他在部隊等我。
上林入伍后,我大姨特別想念他,經常獨自站在門前那株如傘狀的桂花樹下,面對悠悠的清泥湖水,望著他向北流向滄浪河,仿佛看見她北去的兒子的英姿。這是她思念最濃的時刻。每當思念不能自拔,而深陷極度痛苦時,她就會到金鵝大隊部來看看我,或是托我姨父帶口信,要我上她家吃飯。
當時的金鵝大隊,民兵工作做得好,被樹立為全國的一面先進紅旗。漢壽縣委為了及時總結這里的民兵工作經驗,從縣里和公社抽調筆桿子,組成一個專門的駐隊寫作組,將這里創造的先進經驗和做法予以總結,不適時機地向全國報道推廣。縣里領頭的是宣傳組的干部劉平政,武漢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公社派出的是本身就在金鵝大隊長期蹲點的黨委委員張鐵成,聶家橋公社黨委書記兼武裝部長郭志才把我從熊家鋪大隊抽調出來,有幸成為這個寫作組的一員。

羅上林(左)任職中共武陵區委副書記期間與原聶家橋公社黨委書記、漢壽縣政法委書記郭志才合影
我姨父擔任金鵝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排位二把手,我便有機會經常與他一起開會,聽他介紹情況。他每次與我見面都會悄悄地說:“你大姨想上林都想病了,她說看見你,就像看到了上林。散會后,你就去我家,讓大姨好好地看看你吧!”我大姨家距大隊部近兩華里路,屬金鵝大隊第九隊。我每次去都是撲田跑(即抄近路),恨不能一步跨進她家門。大姨見到我,第一個舉動就是拉著我的手說:“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上林。太想他了,想得心里疼。”我如果隔兩天沒去,她就會上大隊部來找我。劉平政、張鐵成看到了,馬上會中斷我們的工作,囑咐我好好陪大姨說說話。他倆善解人意的舉動,令我終生難忘。劉平政溫文爾雅,給我的印象特別親切。張鐵成則不一樣,他身材武墩,皮膚漆黑,不是開會,很少說話,就像個黑包公。當地干部和群眾,對他說的話都是不打折扣地照做不誤。郭志才書記對他也是特別的倚重和信任。我開始報到時,就無形中對他有幾分懼怕感。他對我大姨的態度,不僅讓我消除了對他的懼怕,還格外增加了幾分親切感。正因為他倆能力強,水平高,為人好,不斷得到組織的提拔重用,劉平政官至常德市人事局局長、市政協副主席,張鐵成官至漢壽縣圍堤湖鄉黨委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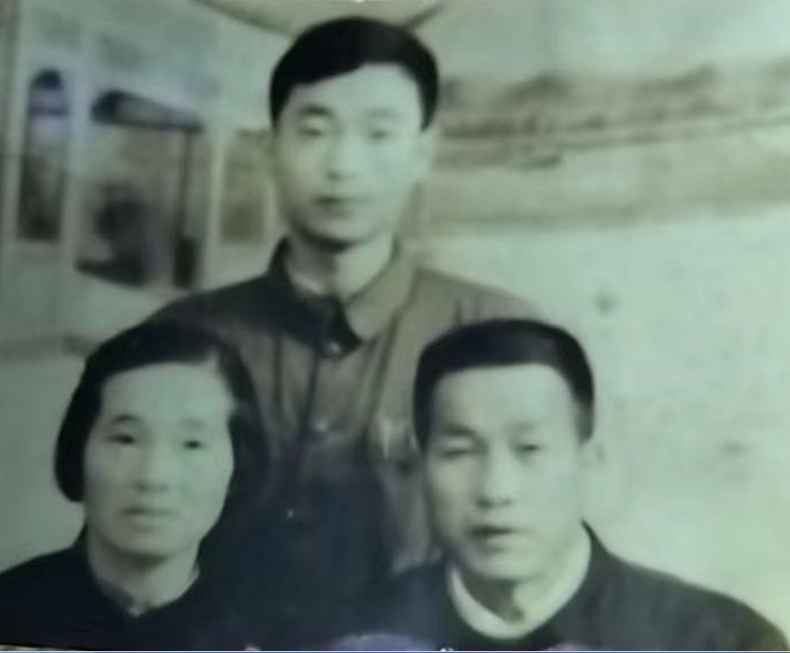
楊遠新與大姨李清枝、大姨父羅廷貴1973年春在漢壽縣照相館合影
1971年11月,我被錄用為國家干部,走進了漢壽縣城工作。從此,距金鵝大隊遠了,距大姨遠了。大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上縣城看看我,有時是她獨自一人,有時是和姨父一起。大姨見到我,第一個舉動依然是拉著我的手說:“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上林。太想他了,想得心里疼。”
我理解大姨的心。我便想方設法,接通遠在河北邯鄲市的上林所在部隊駐地的電話,讓他與母親說上幾句話。放下話筒,大姨抹著眼淚對我說:“要是從電話里能看到他,那就好了。”遺憾的是那時的通信不像現在這樣發達,我大姨的這一憧憬和愿望未能得到滿足。當可以視頻通話了,她已離開了人間。
1974年初夏,上林經部隊首長批準,回鄉探親。兄弟離別四年,終于盼來了重逢的機會,我當然抓住不放。我連夜兼程,天明趕到金鵝嘴,與他見面的第一時間,他向我遞上了從部隊帶回的珍貴禮物。一套全新的長篇名著《紅與黑》。那時要得到這樣一套外國名著,十分不易。我如獲至寶。幾十年過去,這套《紅與黑》一直隨我南征北戰,如今仍然完好的挺立在我的書柜最顯眼的位置。見書如見人,我在書房的時光里,總會情不自禁地朝《紅與黑》多看幾眼,這種時候,眼前就會浮現上林那英俊的身影。他那張微笑的臉,在我腦海里永存,揮之不去。
他這次探家,我給他物色了對象,但由于他尚未提干,加之家在農村,我第一次當紅娘,結果失敗了。我感到很歉疚,他則很大度,滿臉微笑地對我說:“哥哥,我們都還沒有老,還不到討不到堂客的那一步。面包會有的,堂客也會有的。”
接下來的一次探家,他給我帶回了一件嶄新的軍裝和一頂嶄新的軍帽。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崇尚軍人,實現不了當兵的愿望,也想有一件軍裝身上穿,有一頂軍帽頭上戴。那樣也覺得無尚的光榮。我打開軍裝一看,竟然是四個口袋的干部服。此時的他,已經提升為排長兼連隊副指導員。他還向我報告了一個好消息:他已經在常德市里找到了稱心如意的對象,道地的常德城里人,擔任基層團委書記,名叫馬先春。我也帶去了自己的女朋友,他和我大姨看了,都表示滿意。可他回部隊不久,我的女朋友和我吹了,他則與馬先春發展得很順利。也許愛情給了他動力,他很快被提升為某部營長。于是向部隊首長遞交結婚報告,順利得到批準,領了結婚證。他倆在部隊舉行了儉樸的婚禮。那種婚后相親相愛,美滿幸福的生活,既令我羨慕,也給了我動力。我急起直追,在總結前面七次戀愛失敗的教訓之后,我終于與第八個戀愛對象走進漢壽縣城關派出所,領取了結婚執照,繼而有了自己的小家。
接下來,上林轉業到常德市委組織部,即現在的武陵區委組織部工作。每年的春節,我倆都會攜妻,不約而同的在正月初二這天,給外祖父外祖母拜年,兄弟相聚甚歡。外祖父稱我遠新,稱他上林。而外祖母則一直沒有改口,依然呼我四婆,喚他陽婆。我倆總是樂呵呵地回應,而且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甜蜜的稱呼。
外祖父未能等到我倆的孩子降落人世,因病去世,享年71歲。外祖母則多活了11年,于1990年8月去世,享年84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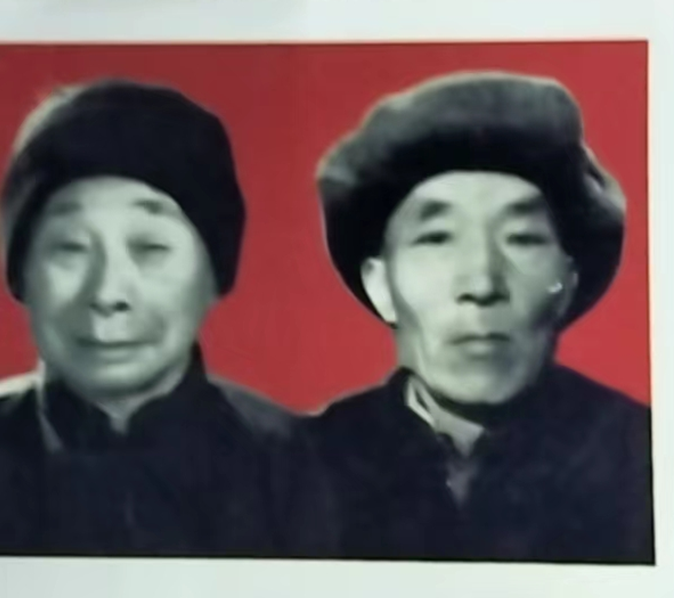
外祖父李祖軍外祖母鄧冬梅合影
直到始終堅持稱陽婆、四婆的那個最疼愛我倆的人去了另一個世界,才沒有人稱陽婆、四婆了。前世的父母也不來找我們了。我倆恢復了由婆到公的本來身份和面目。
外祖母去世時,她心心念念的陽婆已是常德市武陵區委組織部秘書,她心心念念的四婆已是湖南省公安廳《當代警察》編輯部副主任。外祖母安詳地合上那雙曾經美麗、曾經深邃、曾經憂患、曾經矍鑠的眼睛那一刻,我和編輯部另一位副主任熊劍先生正在隆回釆訪金庫失盜案。我連夜千里迢迢,幾經轉火車、轉客車、轉貨車,風塵仆仆趕到皇城之南的陽鋪崗李家大朝門時,陽婆和妻子馬先春、女兒羅欣欣已先我到達。他迎上前,拉著我的手,我倆都難過得張不開嘴,把千言萬語委托給了各自眼里涌流的兩條小溪。我倆并排走到外祖母靈前,同時屈下雙膝,同時伸出雙手,同時叩下頭,長拜不起。
此時此刻,外祖母為我們做的樁樁件件,化成沅水的波濤,澎湃涌來。外祖母離去后,漸漸地我倆這種相聚的時刻減少了。而在工作中相聚的時刻則增多了。
上 林不久出任武陵區民政局長,我倆同屬政法口。相互工作上有了交集。我最難忘的是我委托他給我堂弟楊遠忠從部隊復員后安排接收單位。他根據其魁梧英俊、酷愛運動的特點,竭盡全力,向市電業局推薦。正好該局籃球隊需要一名主力中鋒,便樂意地接收了。
此后不久,上林升任武陵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這在全省乃至全國而言,由民政局長提升政法委書記的他是首例。就客觀條件而言,民政局在政法口,與公檢法司比較,算是弱勢部門,政法委書記多數從公安局長位置上挑選。單從這點可見,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組織的高度認可。
提拔縣處級領導干部的前奏,是派到省委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習。常徳市政法委率隊的是副書記盧子成,一個人品和酒品堪贊的人。我接到上林的電話,立即采購了一件高度白酒,驅車省委黨校,就近選擇一家土菜館,與盧子成率領參訓的9位青年干部酣暢淋漓的碰杯。
上林結業后回常德,走馬上任武陵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1999年,他升任中共武陵區委副書記,依然分管政法口的工作。2000年9月1日,常德發生匪徒張君團伙搶劫銀行案。我從人口管理角度去作調研。他與常德市委宣傳部第一副部長周國忠一起接待我。我們三人是同鄉,是同學,他倆同屬高二班,在校時關系就很密切。這種特殊關系,所產生的特殊感情,凝聚于工作中,令我們都感到十分愉快。
那一夜,案情談完,幾瓶酒喝完。臨別時,三雙手緊握在一起,遲遲不肯松開。我們又走到沅水北岸,沿常德詩墻從西向東參觀品味,他以主人身份,介紹詩墻的產生和上榜吉尼斯世界紀錄的情況。那一夜,是我們三人走出聶家橋中學后,相聚時間最長、也是最難忘的一次。
接下來,上林改任常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在一位副市長與農林水系統幾大家之間擔當聯絡協調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好評。沒想到臨退休之前,一向樂觀開朗,微笑面對人生的他,卻突然患上了重病。開始,他并沒當回事。他盡管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多年,但他一直像在部隊時那樣堅持早晨鍛煉,身體一直結實硬朗,連頭痛腦熱,感冒發燒都未曾有過。直到他短時間內連續幾次昏倒在了辦公室,這才不得不引起重視。市政府派人派車護送他到長沙,入住湘雅二醫院治療。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表現得很樂觀,無論對醫護人員,還是對同病室的病友,都是以滿臉微笑相待。三個月時間里,醫院多次組織權威專家會診,中西醫配合治療,其妻馬先春沒日沒夜不離左右的精心護理,上林的病情得以好轉。臨出院時,主治大夫向他反復強調:休息為主,工作為輔。他卻恰恰相反,工作為主,休息為輔。我得知這一情況,是在我母親病逝期間,他帶領弟弟妹妹前往我老家吊唁,其妻馬先春背著他告訴我的,希望我能勸勸他。我勸他嚴遵醫囑,細水長流。他對我說:“哥哥!你我明年都要退休了,在有限的在崗時間,多做一點工作,退休后就可以一門心思把身體搞好。”我覺得他講的很在理,引起我的共鳴,便不再多勸。萬萬沒有想到,幾個月后,他的病情再次復發,并有所加重。他再次入住湘雅二醫院,院方則向家屬建議:速轉北京治療。其妻馬先春毫不猶豫,果斷決定,護送他進京,選擇部隊一家名牌醫院,經檢查確診,專家很快拿出了治療方案。
上林在京入院的第二天,我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已經買好了機票,4月25日飛抵北京,直接從機場到醫院,去看望他。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正在進手術室。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不等我進京去看望他,2013年4月19日10時,他不幸病逝于北京,享年60歲。我得知這一噩耗,心如刀削,悲痛萬分。
我和表弟李永勝,還有他在部隊的一位張姓戰友,從長沙驅車趕往常德,車過謝家鋪時,周國忠已經在常長高速第11個出口等候。我倆見面,相互眼眶潮濕。首先想到的是我們三人曾經的約定,退休后都回到老家聶家橋鄉,上林在清泥湖北岸,我在老渡口古橋南岸,國忠在武峰山東側,各自整修祖傳下來的老屋,一起過解甲歸田的詩意生活。三方約定再也難以兌現了。頓時淚水沖決大壩,沿鼻溝嘩拉而下,重重地砸到腳上。
走進追悼會現場,我小姨李圓清一步沖上來,雙手扶住我的肩,放聲痛哭。上林生前,每逢過年,都會攜妻女,到清泥湖水注入滄浪水一側的高凡村,給小姨一家拜年。小姨家每遇困難,只要他得知,都會盡全力相幫。這怎不令小姨痛心。
在上林的追悼會上,我看見一位50多歲的婦女,大聲痛哭地走進靈堂,撲到靈柩上,一雙淚眼端詳著棺內上林的遺容,撕心裂肺般地哭喊道:“羅書記呀!你是個大好人呀!你為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可老天爺不公,不給你長壽!老天爺真是瞎了眼啦!”接著她雙膝跪在馬先春面前,痛悔不迭地說:“羅書記住醫院我不曉得,我沒有去看望他這位大恩人,我這一輩子都后悔不完。”
常德市政府為上林舉行的追悼會上,一位市領導致悼詞,滿含深情地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績和高尚人品。尤其對他任武陵區委副書記期間,把下屬單位和個人吊唁其父母贈送的禮品禮金,頂著壓力,毫不動搖地全部如數退回的廉潔行為,給予了充分肯定。
常德市委督辦專員周國忠,代表親友,回顧了上林奮斗的一生。
家鄉金鵝村的村支兩委全體成員,和村民委派的代表,一起趕到追悼會上,送別上林最后一程。他們流淚數說建設村級路網和村級電網的過程中,遇到資金困難,是上林自掏腰包,并四處籌資,幫助渡過難關,成為全鄉第一個所有村民小組通水泥路、通民用電的先進村。鄉親們說到這些,不禁放聲悲哭。
上林去世后的這十年里,我從未將他忘懷,他那張微笑待人的臉,總是浮現在我眼前,多少回夢里與他相聚,醒來淚流滿面。
2014年4月29日、5月15日,我乘車過邯鄲,聯想起上林所在部隊曾經駐扎在此地的情景,難以抑制對他的思念之情,寫下了一首小詩:
車過邯鄲憶表弟羅上林
一
應征入伍駐邯鄲,
劈嶺開山筑路難。
軍營最苦工程兵,
卻在信中盡道甜。
姨母思兒難抑時,
視我為弟摟胸前。
千里探家載譽歸,
英武豪邁已軍官。
二
正當盛年轉地方,
半生武陵作奉獻。
局長書記秘書長,
民政政法主全盤。
除暴安良護百姓,
尊師愛友孝堂前。
可恨病魔突纏身,
華佗無奈手足斷。
我特別將此詩收入了《楊遠新文集》,以留作永恒的紀念。
(感謝羅榮建提供文中圖片)
2023年1月3日草稿于柯克蘭德18195號
2023年2月26日二稿于里加奧德211號
2023年4月13日定稿于里加奧德211號

作者楊遠新近照
【作者簡介】:楊遠新,湖南漢壽縣人,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作家協會第五、六、七屆理事,湖南省首屆公安文學藝術協會秘書長、湖南省公安文聯理事。迄今已發表出版文學作品1800余萬字,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春柳湖(全四部)》(與楊一萌、陳雙娥合著)《百變神探》《愛海恨涯》《東追西捕》《擬任廳長》《紅顏貪官》《春涌洞庭》,中篇偵探小說《特區警官》《驚天牛案》;中篇紀實小說集《中國刑警大掃黑》《中國刑警在邊關》,長篇兒童小說《歡笑的碧蓮河》《小甲魚的阿姨》《牛蛙大王》《險走洞庭湖》(與陳雙娥合著)《霧過洞庭湖》《孤膽邱克》,中短篇兒童小說集《落空的晚宴》《今夜,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長篇報告文學《內地刑警與香港警方聯合大行動》《創造奇跡的人們》《奇人帥孟奇》《縣委書記的十五個日日夜夜》《走進福山福水》《天有巧云》等,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8卷本880萬字《楊遠新文集》。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公安部金盾文學獎首屆一等獎、二屆二等獎、三屆三等獎、四屆二等獎,文化部和全國婦聯等七部委聯合頒發的編輯獎、湖南首屆文藝創作獎、湖南首屆兒童文學獎等各類獎項58次。散文《我的祖母》被編入大學教材,分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