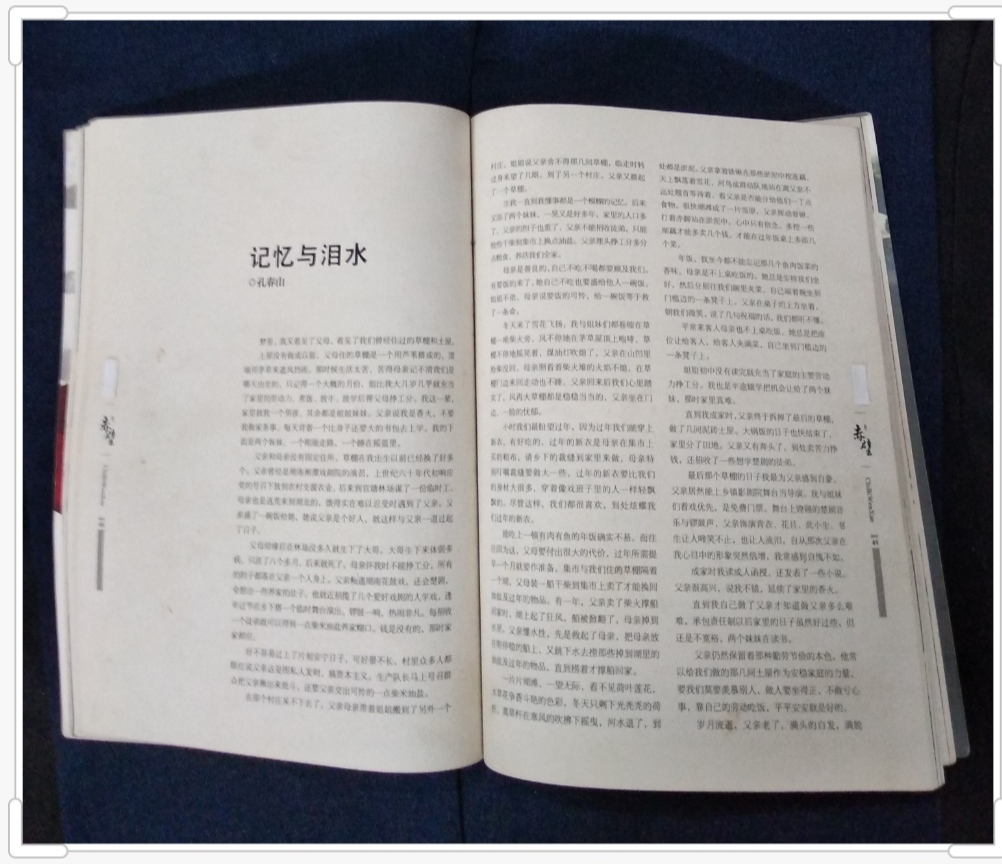
記憶與淚水
作者:孔春山
夢里,我又看見了父母,看見了我們曾經住過的草棚和土屋。
土屋沒有做成以前,父母住的草棚是一個用蘆葦搭成的,頂端用茅草來遮風擋雨。那時候生活太苦,苦得母親記不清我們是哪天出生的,只記得一個大概的月份,姐比我大幾歲幾乎就充當了家里的勞動力,煮飯、放牛、洗衣、放學后幫父母干農活掙工分。我這一輩,家里就我一個男孩,其余都是姐姐妹妹。父親說我是香火,不要我做家務事,每天背著一個比身子還要大的書包去上學。我的下面是兩個妹妹,一個剛能走路,一個睡在搖籃里。
父親和母親沒有固定住所。草棚在我岀生以前已經換了好多個。父親曾經是湖南湘潭國家戲劇院的演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響應黨的號召下放到農村支援農業,后來到原蒲圻縣官塘林場謀了一份臨時工。母親也是逃荒來到湖北的,餓得實在難以忍受時遇到了父親。父親盛了一碗飯給她,她說父親是個好人,就這樣與父親一道過起了日子。
父母結緣后在林場沒住多久就搬到了鄉下農村,沒多久就生下大哥。大哥生下來體弱多病,只活了八個多月,后來就病死了。后來母親又生下大姐。母親懷我時不能掙工分,所有的擔子都落在父親一個人身上。父親精通湖南花鼓戲,還會楚劇、越劇、京劇……會想一些養家的法子。他就近招攬了幾個、一群愛好戲劇的人學唱戲,逢年過節在鄉下搭一個臨時舞臺演出。鑼鼓一響,熱鬧非凡。每招收一個徒弟就可以得到一點柴米油鹽養家糊口。錢是沒有的,那時家家都窮。
好不容易過上了片刻安寧日子,可好景不長,村里眾多人都眼紅說父親這是圖私人發財,圖私人掙錢。生產隊長馬上號召群眾把父親揪出來批斗,還要父親交出可憐的一點柴米油鹽。
在那個村莊呆不下去了,父親、母親帶著姐姐搬到了另外一個村莊。姐姐說父親舍不得那幾間草棚,臨走時還轉過身望了幾眼。母親一臉淚水。到了另一個村莊,父親又搭起了一個草棚。
生我到我懂事一直都是一個模糊的記憶。后來又添了兩個妹妹,父母有我和姐妹四個孩,一晃又是好多年,家里這多人口了。父親的擔子也重了,父親不能招收學戲的徒弟,只能撿些干柴到集市上換點油鹽。父親埋頭做事掙工分才能多分點糧食,養活我們全家。
母親是善良的,自己不吃不喝都要顧及我們不挨餓,有要飯的來了,她自己不吃也要盛給要飯的一碗飯。姐姐不依,母親說要飯的可憐,給一碗飯等于救了一條命。
冬天來了雪花飛揚,我與姐妹們都蜷縮在草棚一堆柴火旁,風不停地在茅草屋頂上咆哮,草棚不停地搖晃著,煤油燈吹熄了,父親在山凹里撿柴沒回。母親照看著柴火堆的火焰不熄,在草棚門邊來回走動也不睡,時時用身子檔住草棚的門、擋住風。父親回來后我們心里都踏實了,風再大草棚都是穩穩當當的,父親坐在草棚門邊,一臉的憂郁。
小時我們最盼望過年,因為過年我們能穿上新衣,有好吃的。過年的新衣是母親在集市上買的粗布,請鄉下的裁縫到家里來做,母親特別叮囑裁縫衣要做大一些能多穿些日子。過年的新衣要比我們的身材大很多,穿著像戲班子里的人一樣輕飄飄的。盡管這樣,我們都很喜歡,到處炫耀我們的過年新衣。
能吃上一頓有肉有魚的年飯確實不易。而往往因為這,父母要付出很大的操勞代價,過年所需提早一個月就要作準備。集市離我們住的草棚隔著一個一望無邊湖,父母裝一船干柴到集市上賣了才能換回油鹽及過年的物品。有一年,父親賣了柴火撐船回家時,湖面上起了狂風,木船被狂風掀翻了,母親坐不穩掉到水里。父親懂水性,先是救起了母親,把母親放在剛停穩的船上,又跳下水去撈那些掉在湖里的油鹽及過年的物品,有些物品要從湖底一件件撈上來,直到撈著才撐船回家。
一片片湖灘,一望無際,看不見荷葉蓮花、水草花爭香斗艷的色彩,冬天只剩下光禿禿的荷桿,蒿草桿在寒風飛雪的吹拂下搖曳,河水退了,到處都是淤泥。父親拿著鐵鍬在那些淤泥中挖蓮藕,天上飄落著雪花,河鳥成群結隊地站在離父親不遠處翹首等待著,看父親是否能分給它們一丁點食物。很快湖灘成了一片雪原,父親揮動著鍬,打著赤腳站在淤泥中,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多挖一些蓮藕才能多掙幾個錢,才能在過年飯桌上多添幾個菜。
年飯,我至今都不能忘記那幾個魚肉飯菜的香味。母親是不上桌吃飯的,她總是安排我們幾個圍著桌子坐好,然后分別往我們碗里夾菜,自己端著碗坐到門檻邊的一條凳子上。父親在桌子的上方坐著,朝著我們微笑,說了幾句祝福的話,我們都聽不懂。
平常家里來客人母親也不上桌吃飯,她總是把座位讓給客人,給客人挾滿菜,自己坐到門檻邊的一條凳子上。
姐姐初中沒讀完就充當家庭主要勞動力掙工分。后來我也是半途輟學把機會讓給兩個妹妹,家里只有兩個妹妹還在讀書,那時家里真難。
直到我快成家時,父親終于拆掉了最后的草棚,做了幾間泥磚土屋。大鍋飯的日子也快結束了,家里分了田地。父親又有奔頭了,到處賣苦力掙錢,還招收了一些想學戲劇的徒弟經常搭臺唱戲。
最后那個草棚的日子,我最為父親感到自豪,父親居然能上鄉鎮影劇院舞臺當導演。我與姐妹們看戲優先,是免費門票。舞臺上咚咚咚當當震耳的楚劇、越劇、湖南花劇戲、京劇音樂與鑼鼓聲,悠揚的二胡伴奏聲。父親飾演青衣、花旦、武小生、書生、讓人啼笑不止,演到傷心處,也讓人流淚。自那次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倍增,我常感到自愧不如。
那時候父親閑時教我與妹妹們學湖南花鼓戲、楚劇、越劇、京劇的唱腔,還教我們學《轅門射戟》、《空城計》、《花木蘭》、《穆桂英掛帥》等等戲劇里的武小生,小生、旦角等表演走路的步法,可我們走也走不像,高著嗓門唱也沒父親唱的好。
成家時我讀成人函授,還發表了一些詩歌、小說,父親很高興,說我不錯,延續了家里的文化香火。
直到我自己做了父親才知道做父親多么艱難,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以后家里的日子雖然好過些,但還是不寬裕,兩個妹妹在讀書。
父親仍然保留著那種勤勞節儉的本色,他常以給我們做的那幾間土屋作為安穩家庭的力量,要我們莫要羨慕別人,做人要坐得正,不做虧心事,靠自己的勞動吃飯,平平安安就是好的。
人間世事多變,在我小孩六歲時,我自己婚姻破裂離婚。父母雖然焦慮,也只是安慰我堅強努力保重,我經常外出打工,父母幫我照顧小孩(他們的孫子)讀書。
歲月流逝,父親蒼老了,滿頭的白發,滿臉的白胡子,太陽落山時父親坐階沿上拉起二胡,唱上幾句《轅門射戟》或《霸王別姬》選段。家里那幾丘田地成了他的命根子,經常在田埂上走走瞧瞧。
父親的離去是猝不及防的,也成了我一生的遺憾。他是在一天早晨突發腦溢血倒地,我抱起他飛快地往醫院跑。彌留之際,父親握住我的手淚流不止,我也是泣不成聲。父親想說什么又沒說出來,或許他還想招收幾個戲劇徒弟,或許還想把莊稼種好,或許還想給我們做一頓豐盛的年飯。一切都挽救不了父親的生命,父親還是走了。
令我感到突然的是母親的離世比父親還要快。母親是因心臟病離世的,臨走時只說了幾句交待的話:“你一定要供小孩讀好書,家里那幾間土房子有危險不能再住了……”母親的離世讓我欲哭無淚。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我都是個不孝的兒子,父母生養了我,我今生還沒有回報父母恩情,父母走了,父母生前對我的關愛,我永遠都沒有機會報答了。
母親逝去的那年,我就開始籌建房屋。由于我的努力及各方面的人緣關心幫助,各方面的幫扶,一幢普通小樓房很快完美竣工。也是那年,家里那幾間土屋也在寒風暴雪中倒塌了。
土屋倒塌巨大的響聲讓我們的心震動。父親走了,母親也走了,現在留給我的是什么?是揮之不去的記憶與淚水,也有愧疚,如果我的房屋早建起來一年,母親就能住上新房屋了。
茅草屋告別了我,土屋子告別了我,父母親告別了我,一年一載,告別不了我心中永遠的思念。
注:《記憶與淚水》散文,曾刊載于東北作家網、北國網(遼寧日報網)、中國公安文學精選網、中國公安文學精選網吉林頻道、作家網、《赤壁文學》、咸寧新聞網等。

作者簡介:孔春山,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2016年被湖北省作家協會吸納為會員),媒體撰稿人。曾修文學與新聞專業。湖北省咸寧市赤壁市官塘驛鎮人,祖籍湖南長沙市望城縣,宗祖籍山東省。在全國省、地、市報刊雜志,文藝、新聞媒體平臺發表文學作品和紀實文學作品(迄今已發表中短篇紀實文學作品數十篇),長篇連載作品。有作品選于集,有小說作品《尋找失落的愛》選入《午夜夢》小說散文詩歌集一九九一年由時代出版社出版(臺北)。紀實文學散文《平凡的印象》2018年榮獲第五屆中外詩歌散文邀請賽一等獎。小說《明天》1993年榮獲安徽省雜志社,(合肥)文學院、文化周報等聯合舉辦的全國征文大賽優秀作品獎,有多篇作品榮獲全國性文學競賽獎。發表中篇小說《苦澀的夢》等。曾在《文化周報》、《希望》文學月刊、《青年周刊報》、《中國散文報》、《善天下》雜志、《九頭鳥》雜志、《赤壁文學》雜志及報刊雜志發表文學作品及參加征文大賽。在作家網(北京)、華語作家網(北京)、中國公安文學精選網(北京)、中國公安文學精選網吉林頻道(吉林)、北國網(遼寧日報網)、東北作家網(遼寧)、中國散文網,善天下傳媒網(陜西省西安)、故事屋閱讀網(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北咸寧網、咸寧新聞網等文藝、新聞媒體發表作品。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