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糧食
作者:牛銀萬
父親一生很愛惜糧食,作為一個農民,他不知道糧食中有多少蛋白質、脂肪和維生素,只知道糧食是關乎人生存的重要食物。他也不知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憫農》詩,只知道糧食的來之不易。
每年麥收后,他都要一個人反復在地里撿那些遺失的麥穗,撿起后捆成一小把一小把背回家。撿麥穗的時候,如果碰到老鼠洞,他就用鐵鍬深挖,掏出被老鼠盜進洞里的麥粒。麥子拉進打麥場后,在晾曬時,他反復用木叉翻動,讓麥子盡快晾干。碾壓的時候,因村里只有一副碌碡,常常需要排隊。輪到他時,他拉著韁繩站在麥場中央,唱著山曲兒,不停地揮著鞭,馬兒在跑,碌碡飛轉,飛起漫天的塵土。碾下的麥子揚干凈裝袋子,他蹲在麥場上,再一顆一顆摳那些壓在土里的麥粒,裝回來在院中曬干,用簸箕簸出土一并歸倉。摳過的打麥場,還有很多壓得較深的麥粒,父親摳不出來,就把家里的雞趕到打麥場,讓雞來啄。家里養的三十多個雞,趕到打麥場上,雞低著頭一陣狂啄。雞啄的時候,父親坐在麥秸堆旁,手里拿著一根長長的樹枝,如果有鳥來啄,他就站起來揮動樹枝,把鳥嚇跑。碾過麥的秸稈,除了春天和泥抹房外,大部分用來燒火。燒火前,父親覺得秸稈上可能有沒碾凈的麥穗,因此他背回來把秸稈在院中攤開,讓雞再來啄一遍。秋天,玉米成熟后,掰下棒子,割倒秸稈碼放在一起,父親翻開秸稈,要一棵棵檢查,看看秸稈上有沒有還沒掰下的玉米棒,哪怕是小的,他也不放過。掰下的玉米棒,父親趕著馬車拉在院中,整齊地碼放在土墻邊的木架上,風干得差不多時,就搬下來,和我們坐在院中用手往下搓籽,父親搓得特別快,我們搓一個他就能搓兩個,而且搓得很干凈,不剩一粒。
吃飯時,他從來不剩,把碗扒拉得干干凈凈,對不小心掉在炕上或桌子上的米粒,他常常用粗壯而結滿厚繭的手指,慢慢捻起來,一粒一粒送進嘴里。為此,我們很不理解,經常開玩笑數落他:“咱們家再缺糧也不缺這一點兒,讓院里的雞和狗也吃上點吧。”他卻邊撿邊笑著說:“浪費了真可惜,遭了年景你們就知道了,你們不記得小時候了?”
由于小麥糜子谷子產量低,后來,父親就不種了,種上產量高的玉米。吃米面時,就只能去買。可買回的米,沒有香氣,燜出的米飯色澤灰暗,吃起來很粗糙;白面不筋道,包不成餃子,幹不成面條,只能蒸饅頭吃。
于是,父親騰出一塊地,又種起麥子糜子和谷子來。
每次回去,在吃自產的米面時,他不停地夸耀,我們走時,他總要大袋小袋給我們帶一些。
父親除了愛吃米面,還愛吃莜面、蕎面,他想試種,我們說膠泥地不適合,種出來不好吃,他就放棄了。
父親生病時,最愛吃面條、喝小米粥。做面條的小麥和喝小米粥的谷子,都是他親手種的。母親搟的面條筋道細長,澆上腌豬肉和土豆塊熬的臊子,味道絕佳,父親低著頭吃得很香。喝小米粥時,就上爛腌菜,他能喝三四碗。每當吃了面條,或喝了小米粥,父親仰面躺在炕上,心情很是舒暢,臉上常常露出滿足的笑容,身體也很快恢復。
平時的早飯,他特別愛吃酸粥。一年四季,他讓母親在鍋頭的罐子里漿著自產的小米。吃酸粥時,就上爛腌菜或胡麻鹽,坐在炕上能吃兩三碗。在做酸粥時,母親有時放入土豆塊,吃的時候,把土豆塊搗爛,酸粥的粘性更大,父親吃起來更爽口,有時吃完酸粥,父親常常連鍋巴也鏟出來,在碗里泡著酸米湯吃,不浪費一點兒。
夏天,父親最愛吃燜酸米飯,故鄉叫酸撈飯。吃酸撈飯時,有菜時就菜,沒菜時就紅腌菜。午睡起來,他不忘用塑料瓶裝一瓶酸米湯,下地慢慢喝,又解渴又解暑。
那時,村里不少人家因缺錢賣多余的小麥,父親為了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從不賣一粒。他在院中靠墻的地方,挖了幾個地窖,鋪上麥殼和麥秸,把多余的小麥儲進去,并每隔一段時間,在晴天時取出來晾曬兩天,以防發霉。實在儲存不下,他就把小麥磨成面才賣,因故鄉的小麥品質好,磨的面又白又筋道,遠近聞名,買的人很多。
父親管理莊稼特別精心,他把田間的雜草清理得干干凈凈,別人鋤一遍他鋤二遍,別人鋤二遍他鋤三遍。為了不錯過澆地的日子,他披星戴月,半夜就起來,到地里蹲在渠邊等水。因買不起化肥,除了家養的牲口積糞外,閑下的時候,他還挎著籮筐到野外拾糞,拾回的糞和牲口積的糞,經過一冬發酵,是很好的農家肥,施到地里即沒污染又有后勁。
為了增加產量,父親在麥田中套種上黃豆。小麥收割后,給黃豆灌一次透水,黃豆苗馬上一片蔥綠。為了不浪費土地,父親在田壟上點上蠶豆,黃豆成熟了,蠶豆也成熟了。黃豆用來喂羊生豆芽,蠶豆數量少,逢年過節炒著吃。
有時外出,父親最放心不下的是地里的莊稼,走的時候,一再安頓家里人按時鋤地澆水。回來時,他首先到地里看看,然后才回家。
因一年四季只吃酸菜,沒有其它菜,買又舍不得,于是,我們勸他種些菜,他卻理直氣壯地說:“地就那么點地,種了菜就不能種糧了,人不吃菜不咋,不吃糧可不行。”
在那困難的年代,村里種的糜子谷子小麥大部分交了公糧,返銷糧都是清一色的玉米面,早晨玉米糊,中午玉米窩頭,晚上玉米拿糕,幾乎天天這樣。那時我們還小,吃得膩了難以下咽,父親卻大口大口吃的很來勁。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有了自主權,父親每年都要種上大幾畝小麥。即使這樣,過年時,家里除了篜足夠的饅頭外,還要篜一大盆玉米面發糕,篜的時候,放入糖精,篜出來特別香甜。父親這樣做,一是讓我們不要忘了本,二是換換口味。每年產下的玉米,大部分人家賣了,父親卻留一部分,除了做飼料,其余的都食用。
如遇災年,父親時不時到糧房查看,站在糧倉前,他默默計算著糧還能吃多久。如糧少時,他反復安頓母親,盡量把飯做得稀一些,吃飽就行。當在電視里看到有的地方受災,莊稼被淹糧食減產時,他憂心忡忡,不停地嘆氣,好像自家受了災似的。
一次,他在電視里看到國家倡導“光盤行動”,猛地坐起來,激動地說:“早就該這樣了,大吃大喝不心疼,不知道浪費掉多少了!”冬天,當看到大雪紛飛時,他常坐在窗前,一邊抽旱煙,一邊望著窗外,高興得合不攏嘴,不停地自言自語:“瑞雪兆豐年,下哇,好好下,明年又是豐收年了!”
他經常勸我們多吃糧食少吃肉。當得知我們晚飯喝玉米糊時,他特別高興,一下磨了一大袋玉米面,讓我們帶回來喝。
每逢祭日上墳時,父親帶得最多的是饅頭。在墳地,他把又白又大的饅頭擺在墓碑前,燒完紙,他把饅頭掰成小塊,一塊一塊認真地潑散在墳上。這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讓故去的親人,吃到又白又新鮮的饅頭。
父親生前最放心不下的是心愛的土地,一再安頓,他走后不要把地包出去,包出去沒幾個錢,自己種,錢少花不咋,沒飯吃就麻煩了。
父親一生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他是千千萬萬中國農民的縮影。在他逝去的日子,我經常想起“民以食為天”這句話,我想,這里的食應該主要指糧食。這句話,在父親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驗證。這時,我真正理解了國家給予農民糧食補貼大力發展糧食生產的重大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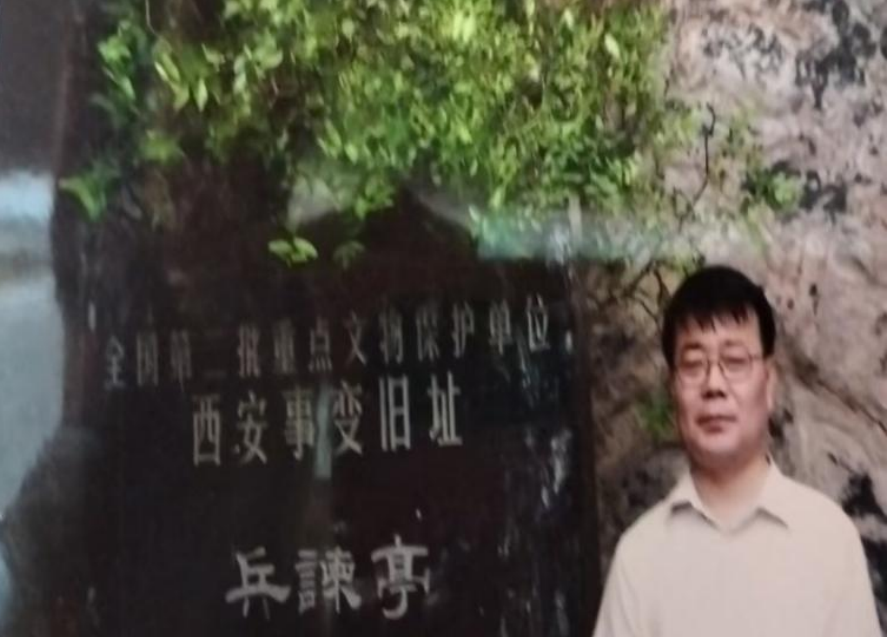
作者簡介:牛銀萬,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九原區作家協會會員,在各級報刊和網絡發表文學作品一百多萬字,詩作獲《草原》·北中國之星詩歌大獎賽優秀作品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