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老味道
作者:牛銀萬
腌豬肉
故鄉的人們,不論有多么難,家家戶戶每年都要喂一頭豬。
進入小雪節氣,就開始殺豬,邀請親朋好友前來吃殺豬燴菜。
殺的那天,找幾個身強力壯的,把豬逮住摁倒,殺死后,抬到院中的開水鍋上褪毛。
殺豬的時候,家里有切酸菜的,有削土豆的,有剝蔥蒜的,說說笑笑,一片忙亂。
褪了毛的豬,吊起來刮凈,割下槽頭肉,過了稱,就拿回家燴菜。
中午,一盤腌蔓菁,一盤炒豬腰,一盤炒里脊,散酒管飽喝。喝上一會兒,酸菜和米飯就端上來,每人一碗。
酒足飯飽,親朋好友散去之后,收拾了杯碟碗筷,休息一會兒,就開始腌豬肉。
腌的時候,把半扇豬肉抱在案板上,用屠刀剔出骨頭切肉,肉片切得又寬又厚,放進鍋里翻炒。隨著溫度升高,肉中的油慢慢浸出來,發出“嘭嘭”的響聲。那時,買不起炭,腌豬肉燒柴火,柴火不是葵花桿兒就是干樹枝,浸出的油,不斷用勺子舀出,倒進腌肉的甕里。肉慢慢變成深紅色,就煉得差不多了。這時,放幾把鹽,大火煮一會兒。煮的過程中,要不停攪拌,最后連肉帶油舀進甕中。
腌完豬肉就接著煉豬油。煉豬油如發現甕里的油沒有浸住豬肉,就再添加些,直到肉全部浸住為止。
腌肉甕和油甕不能放在家里,冷卻后要挪到涼房,用蓋子蓋嚴實,上面壓一塊石頭,以防老鼠爬進去。
故鄉的豬都是家養的,是用苦菜、甜菜和糧食喂大的,因此肉質好無污染。
那時,一家殺豬都殺,一家腌豬肉都腌。小雪節氣過后,幾乎每天有殺豬腌豬肉的,走在村里,總能聞到一股股誘人的肉香味兒。
故鄉不論殺了多大的豬,都是腌一半留一半。留下的那一半切成條,一部分凍進晾房的甕里平時吃,一部分和豬頭豬蹄一起入地窖。
腌豬肉冬天不吃,春天現豬肉吃完才吃。
每年秋天,故鄉家家戶戶都要腌幾甕酸白菜。開春燴酸菜的肉都是腌豬肉。腌豬肉和酸菜一起燴,肉不膩,又軟又香,特別好吃。
故鄉不種菜,沒有炒菜的習慣,有時炒雞蛋和土豆放入腌豬肉,別有一番風味兒。
過節時,故鄉用腌豬肉包餃子。做餡兒時,把腌豬肉倒進熱鍋融化之后,再取出切成丁,和剁碎的酸菜或土豆絲蘿卜絲一起攪拌均勻,再倒點胡油即可。
故鄉的腌豬肉很耐儲存,能儲存到夏天,甚至秋天。為了防止變質,每年要回鍋一到兩次。
在缺肉少油的年代,腌豬肉是故鄉主要的肉食來源。夏天,人們實在饞得不行,就從甕里捻著吃,有時在做飯時,就迫不急待地從鍋里用筷子夾著吃。
逢年過節,故鄉人去城里走親串友時,沒有可送的東西,就送腌豬肉,親友們特別歡迎。
由于故鄉的腌豬肉名聲在外,外面的人到故鄉做客,在燴菜燉魚時,一再安頓放腌豬肉。
在外讀書工作的人,每當想起家鄉的味道時,就讓家里郵寄一罐頭瓶腌豬肉,腌豬肉已成為他們濃濃的鄉愁。
后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買了冰箱和冰柜,即使這樣,故鄉每年殺了豬仍在腌豬肉,腌豬肉已成為故鄉難舍的美食。
腌蔓菁
腌蔓菁是故鄉冬春季特別喜愛的咸菜。
故鄉的腌蔓菁爽脆、色鮮、味兒適中。
在我的記憶中,每年麥子收割后,故鄉都在閑下的地里種蔓菁。那時,故鄉是黃灌區,麥收的時候,上游的閘門早早打開,渠里流滿了水,為了搶時間,就抓緊割麥灌溉和播種。
種進蔓菁,鋤一遍草,施一次肥,澆兩次水即可。
秋天,其它莊稼收獲完,地里只留下蔓菁,遠遠望去,藍天下一片蔥綠,特別顯眼。霜降后,蔓菁葉蔫兒了下來,漸漸發黃,人們就開始起蔓菁。
起蔓菁用小鏟掏,有的直接拽。蔓菁起出,裝上馬車拉回缷在院中,大部分煮熟喂豬,留一少部分腌制。
蔓菁要等白菜都腌完才腌,有的直接腌,有的削去纓和根毛腌。
故鄉的蔓菁不論大小都整腌,什么也不放,只放粗鹽,一層一層碼在甕里,碼一層蔓菁撒一把鹽,撒多少全靠經驗。碼到多半甕,再壓一塊石頭。
腌一周左右,蔓菁浸出水,如水多的話要舀出,為防止出現白沫,每天用高粱穗打掃一次,腌半個月左右就可食用。
冬春季,故鄉每天兩頓飯,上午九點左右一頓,下午三點左右一頓。每頓飯不論吃得遲早,不論吃什么,腌蔓菁必上。
上飯之前,撈出蔓菁,在案板上切成小條,有纓的把纓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放在盤或碗里,早早就端上來。吃的時候,一口蔓菁一口飯。吃蔓菁人們毫不做作,嘴里發出“嚓嚓”的聲音。有的就著吃不過癮,還倒上開水,夾上蔓菁條,卷一袋旱煙,一邊抽煙,一邊喝酸蔓菁湯。抽完煙喝了湯,拿來枕頭,躺在炕上舒服地迷糊一會兒。
逢年過節請人吃飯,喝酒前,必先切一盤腌蔓菁。故鄉有句口頭禪:蔓菁就酒,越喝越有。等其它菜上來時,人已喝得半醉了。
在吃煮土豆、土豆丸子和莜面時,人們要么切蔓菁纓,要么把蔓菁擦成絲,和酸蔓菁湯和在一起,用胡油熗的蔥花提味兒泡著吃。加進酸湯,吃起來一點也不亞于肉湯。
那時,我讀高中住校,因吃慣了家里的腌蔓菁,學校的咸菜難以下咽。每次回家,我除了帶一罐頭瓶豬肉醬外,還要帶幾個腌蔓菁或一小袋紅腌菜。為了防止同學偷吃,我把腌蔓菁和紅腌菜鎖在床頭的木箱里,即使這樣,二三天就吃光了。
腌蔓菁還能止餓。小時候,我等不上母親做好飯,餓了就到涼房里撈腌蔓菁吃,餓得厲害能吃二三個,因空肚,吃進去直返酸水。
故鄉的腌蔓菁一直能吃到初夏。初夏后,隨著氣溫升高,甕里的蔓菁漸漸發軟,白沫多了起來,有了異味兒。這時,蔓菁就不再腌了。于是,人們撈出來,有纓子的如舍不得扔,就反復清洗抓緊吃。撈出來的蔓菁切成條,鋪在蓋簾上,在院中晾曬。晾哂幾天,蔓菁條縮水顏色變成黑紅色,上面結出白色的鹽霜,這時的腌蔓菁,故鄉叫紅腌菜。吃紅腌菜有的在碗里泡軟就著吃,有的干脆直接嚼著吃。那時,人們腌蔓菁要多腌一些,因為春天酸白菜吃完,整個夏天缺菜,紅腌菜就派上大用場。
那時,故鄉婚喪嫁娶都在村里舉辦。宴席上,酒酣時,人們一再要求上腌蔓菁。腌蔓菁上來,一盤不夠,常常能吃二三盤。
我每次回去,都要帶一些家里的腌蔓菁,裝進罐頭瓶,浸滿鹽湯,回來放進冰箱里,吃多久都原汁原味。帶回來的腌蔓菁,我平時吃飯舍不得吃,每頓只切一點兒,只有吃燉肉時才多切,燉肉和腌蔓一起吃,非常解膩。我有時口淡難以入睡,便半夜拉開冰箱捻幾根,吃了后,很快就進入夢鄉。
父親去世后,我常常思念故鄉自然純樸的腌蔓菁老味道……
如今,故鄉的咸菜豐富多彩,除了腌蔓菁,還腌黃瓜、腌豆角、腌芹菜,但我最鐘愛的是腌蔓菁。每年冬天故鄉殺豬時,有人請我回去吃殺豬菜。我都讓準備一盤腌蔓菁。每當我看到桌子上擺的腌蔓菁條時,感到特別親切,不禁胃口大開,該喝二兩酒喝成半斤,該吃一碗米飯就酸菜吃成兩碗。就著腌蔓菁喝酒吃飯,和鄉親們嘮著家鄉的話題,我覺得我并沒走遠,我的根仍在故鄉,我的魂仍在故鄉……
酸粥
故鄉人的籍貫絕大部分是山西、陜西、河北一帶的,他們繼承了先輩的飲食習慣,特別愛吃酸粥。
一年四季,家家戶戶靠近土炕的鍋臺邊,都放著一個不大不小的罐子,里面漿著米,有的漿著谷米,有的漿著糜米。
故鄉是黃灌區,土地肥沃,適合種谷子和糜子。谷子和糜子脫殼后的小米與糜米,無沙粒,色澤金黃,粘性強,營養豐富,用它們做的酸粥特別好吃。
故鄉吃酸粥一般是在早上,有時來不及做其它飯,或想吃酸粥時,中午和晚上也吃。
做酸粥燒開鍋里的水,把罐里的酸漿另倒出去,端起罐子,把米用勺子撥拉進鍋里,一邊攪拌,一邊燒火熬。如果米湯多就舀出,米湯少就加點開水。熬的過程中,鍋里冒起大大小小的氣泡,發出“撲撲”的聲音,特別悅耳,水氣飄進鼻孔,既有米香,又有淡淡的酸味兒。有時米和湯會濺在鍋臺上,火大的時候,能濺到炕沿上。如果因火大或不及時攪拌,米粘在鍋上有了糊味兒,就切一根生蔥插入粥中。
冬春季,故鄉做酸粥放土豆。土豆切成塊,先在鍋里煮得半熟,再倒米熬。粥熟了土豆也熟了,用勺子搗爛土豆,來回拌勻,這樣做的酸粥更筋道爽口。
吃酸粥就腌蔓菁或紅腌菜,有時拌胡麻鹽。胡麻鹽是把胡麻炒熟,在鐵缽子中搗成粉沫,加適量的鹽即可。吃時在酸粥上撒一層胡麻鹽,吃幾口酸粥。夏天,吃酸粥還就苦菜,苦菜有腌的,有現拌的。
下地勞動,故鄉一個大人早上吃二三碗酸粥是常有的事,不夠時還鏟出鍋巴,泡上酸米湯吃。
故鄉吃酸粥一年四季不停,有時連著幾頓,有時隔二三天,隔得時間最長的是年節的初一到初五,這幾天的早飯都是餃子。初五一過,就又漿上米,開始吃酸粥。故鄉有一句俗語:寧舍家財萬貫,不舍一個酸罐子。由此可見,故鄉人是多么喜愛酸粥。
故鄉除了吃酸粥,還喝酸稀粥吃燜酸飯,燜酸飯故鄉叫酸撈飯。吃酸撈飯多是在中午,喝酸稀粥往往是晚上。吃酸粥和酸撈飯的米湯,下地時帶上,喝了即解渴又下火。
因谷子和糜子產量低,人們慢慢就很少種了,大部分人種上玉米。想吃酸粥就到市場上買米,可買的米,做出的酸粥吃起來又粗糙又沒有米香。于是,故鄉的人們就把玉米粉成喳喳,玉米喳喳做的酸粥,一點不亞于小米和糜米。
由于故鄉的酸粥名聲在外,城里的人到故鄉吃飯必點酸粥。有的還帶點酸漿和玉米喳喳,記下電話,回去后,在故鄉人的指點下自漿自做酸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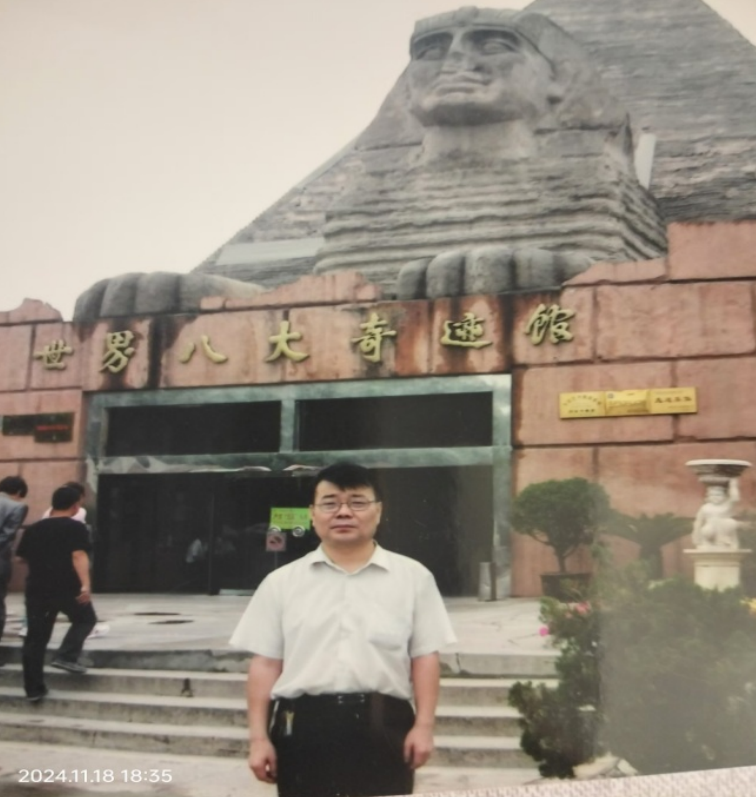
作者簡介:牛銀萬,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九原區作家協會會員,在各級報刊和網絡發表文學作品一百多萬字,詩作獲《草原》·北中國之星詩歌大獎賽優秀作品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