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爐情思(外一篇)
作者:牛銀萬
每當雪花飄飄的時候,我就想起故鄉老屋中的那個火爐。
那個火爐,伴我度過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它給了我溫暖,給了我濃濃的情與愛,不論走到哪里,我都無法忘懷……
那時,每到冬天,父親就從院中的墻角里,搬回火爐和火筒,在老屋中安裝火爐。
火爐安裝在靠近土炕的地方。安裝的時候,在地上放一個鐵架,把火爐穩上,用兩個火柺連接起火筒,插在墻上煙道的圓孔中,然后在火筒上,每隔一段距離纏一根細鐵絲,固定在老屋的椽或檁子上。
那時,故鄉的冬天很冷,每年小雪節氣后,呼呼的西北風刮個不停,窗玻璃外面掛上棉簾,上面的冰花仍整天不化,氣溫有時能降到零下二十多度。白天,人們在家中還穿著棉襖戴著棉帽,晚上睡覺,常常把頭和身子都縮在被子里,不敢輕易動彈。
那時,每天天不亮,父親就早早起來下地生火爐。他先揭開爐蓋,用火鉤慢慢拔拉出爐灰里的炭火,放幾個玉米芯或樹上劈下的干木塊,燒上一會兒,家里暖和起來后,再在柴火上放上幾塊炭。這時,母親在地下喂豬做飯,我們卻賴在被窩里,等父母親把衣服烤熱才起炕。
因生活困難,每年冬天,家里買的炭要省著燒。為了防止風化,父親把炭堆起來用紅膠泥封住,下面留一個小口。燒的時候,用鐵錘打成小塊,隨燒隨取。早晨,父親生著火爐,都要提一大籮筐玉米芯或干木塊,放在火爐旁。當炭火的熱度不夠時,他就和母親不停往火爐里續柴火。
父母平時節省,過年燒起來卻不再吝嗇。小年之前,父親把炭堆上的泥皮鏟開,搬下整炭,用鐵錘打成一小塊一小塊,堆在大炭堆旁。每天燒的時候,母親用鐵簸箕端回去,放在火爐旁。每燒完一爐,她就加一次,每次加得滿滿的。三十那天,伴著火爐里呼呼悅耳動聽的聲音,我們寫對聯、吃飯、包餃子、看電視、嗑瓜子,一家人坐在炕上熬年,心里暖融融的。
每天晚上,父親總是最后一個睡。臨睡前,他給爐里加滿炭,坐在火爐旁,一邊烤火,一邊抽旱煙。當家里熱起來,我們一個個進入了夢鄉,他才在快燒完的爐火上壓一塊炭,蒙上爐灰睡覺。
冬天,母親經常在火爐上烤饅頭。烤饅頭時,因怕烤焦,母親就揭開爐蓋,溫度適中的爐火,烤出的饅頭黃里透白白里透黃,又酥又脆。烤好的饅頭,母親讓我們吃,當時吃不進去,母親就放在最外面的爐圈上,等我們餓了再吃。
冬天,母親有時在火爐上做飯。家里有一個小鐵鍋,她除了熬稀粥、燉魚和炒雞蛋外,還在鍋下燴酸菜鍋上荷糕和饅頭。火爐上做飯時,土灶就燒干鍋,燒干鍋既能熱家,又能熱炕。
為了節省柴炭,母親經常在火爐上用鋁壺燒水。壺中的水快開時,壺里發出絲絲的聲音,特別悅耳,水開時,像咚咚地擂鼓,壺蓋上下跳動,壺口和壺嘴上冒著騰騰熱氣,在家中彌漫,和呼呼的爐火一起,烘托溫馨的氣氛。
正月,當家里來了親戚時,母親就在火爐上用小鐵鍋熬磚茶。熬磚茶要放鹽。母親放鹽很有經驗,往往放得不咸不淡。在火爐和茶的香氣烘托的溫馨氣氛中,母親在地下一邊不停續茶,一邊嘮嗑。這時的火爐,和母親一樣好客和熱情。
火爐是燒土豆的好地方。我們玩得餓了,就把土豆放進爐膛,蒙上爐灰燒。蒙上爐灰燒的土豆皮焦香里軟綿,就上腌蔓菁,別有一番風味。
天寒地凍,我們在外面玩耍,手腳凍得發麻,回到家,不脫衣服,就先沖到在火爐邊烤火。身體暖和了之后,當我們看到爐圈縫隙中跳動的紅紅火苗時,感到火爐特別親切。
冬天的晚上,我經常坐在火爐旁的炕檐邊,爬在大紅躺柜上做作業。做一會兒,就在火爐上烤烤手,烤烤腳。母親見狀,就不停往火爐里加柴加炭,把火爐燒得旺旺的。這時,我充滿了對火爐的感激,充滿了對母親的感激。
冬天,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當我凍得厲害時,我就想火爐,想那呼呼的聲音,想那跳動的火苗。想起這些,我覺得火爐就在身邊,一下暖和了許多,走起路來就有了勁。
如今,老屋已拆除,我再也見不到那紅紅的爐火,但老屋爐火所傳遞的情與愛,永遠溫暖著我的歲月,讓我度過人生的一個又一個冬天……
母親與拌湯
故鄉把疙瘩湯叫拌湯。
我喝過各種各樣的拌湯,只有母親做的拌湯讓我回味無窮,終身難忘……
母親做的拌湯不稀不稠,土豆軟綿不化,面疙瘩一顆是一顆,又小又均勻,且互不粘連,喝起來十分爽口。
母親做拌湯有時放肉,有時不放肉。放肉時,她先把肉切成丁在鍋里蘭炒,蘭炒得差不多加進水,和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塊一起煮。煮得半生半熟,就邊拌邊把拌好的面疙瘩扒拉到鍋里。扒拉的時候,她不緊不慢,扒拉幾筷子,用勺子來回攪幾下,最后再嘗嘗咸淡。如淡的話就加鹽,如咸就倒開水,如稠就再加點水和鹽。不放肉,她要么在煮土豆塊的時候,挖進一小勺豬油,要么在面疙瘩快熟時,倒上半勺胡油,放在爐膛里的火上,熗入捻碎的扎蒙,然后趁熱灑在鍋中的拌湯里。我清晰地記得,當拌湯灑上胡油熗的扎蒙時,發出“赤啦”的聲音,頓時,滿屋飄香,讓人胃口大開,垂涎欲滴。
那時,故鄉每年家家戶戶都種胡麻。收割碾壓后,在村里的油廠榨。因胡麻品質好,榨油不加添加劑,榨出的油色澤金黃,香味撲鼻,很遠就能聞到。秋天,母親把我們從十幾里外沙地上采回的沙蔥花,團成一個個圓餅,用細線串起,吊在家門旁外面的墻上晾扎蒙,晾曬中的扎蒙,在明媚的陽光下,散發著淡淡的清香。
做拌湯火不能急也不能慢。火急土豆塊易化,面疙瘩進不了味兒,又容易糊,火慢面疙瘩表熟里不熟,會夾生。為了控制火候,母親做拌湯燒的都是柴火,通常是是干樹枝和玉米秸稈。干樹枝和玉米秸稈燒完,有時還燒羊吃剩的干草和葵花片。母親練就了做拌湯的硬功夫,她一只手拌,一只手倒水,兩只手配合得十分默契。拌上一會兒,她就往灶里續點柴,每次續多少,她都心中有數,柴火燒到什么程度,她不看也判斷個差不多。
冬天,故鄉一般是兩頓飯,上午九點多一頓,下午三四點一頓。每當上午的飯有肉吃膩了,母親下午就做拌湯。那時,我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光喝拌湯扛不到晚上就餓了。于是,母親就在火爐上烤幾個饅頭,要么讓我們泡在拌湯里吃,要么作零食。
夏天和秋天,母親做拌湯一般是在下雨或下地累了的時候。雨天,柴火發潮,做其它飯費時費柴。從地里回來,饑腸轆轆,腰酸腿困,用拌湯泡舊米飯或篜餅,又快又省事。
夏天,儲存的土豆已吃完,新土豆又沒下來,母親做拌湯只好放些地里摘回來的蔥葉。這時,我們不責怪母親,只能盼秋天快點到來,起出土豆,讓母親做拌湯時放入土豆。
每當我們生病時,母親不是熬稀粥,就是做拌湯。做拌湯要加一兩個雞蛋。為了好消化,她把拌湯做得更稀,土豆塊切得更方,面疙瘩拌得更小更均勻。生病時做的拌湯,母親往往不放肉而用胡油。
不管什么時候做拌湯,在食用前,母親都要切一盤腌蔓菁條,提前放在土炕的舊方桌上。喝的時候,我們頭也不抬,一邊就蔓菁一邊喝,餓得厲害時,喝得發出吱吱的響聲,一頓能喝三四碗。
成家后,我學著母親做拌湯,我到市場買上胡油熗扎蒙,可土豆再怎么切,也切不成她那種方方正正的,拌面疙瘩,往往把握不準,水不是倒得太快就是太多,拌出的面疙瘩大的大,小的小,常常是小的熟了,大的還夾生,經常喝一半倒一半,后來就不做了。
有時我想喝拌湯,下飯館就特意要一小盆。可飯館的拌湯,上面飄著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熗的什么,湯中這菜那菜加得很雜,唯獨沒有土豆,喝起來完全沒有母親做的那種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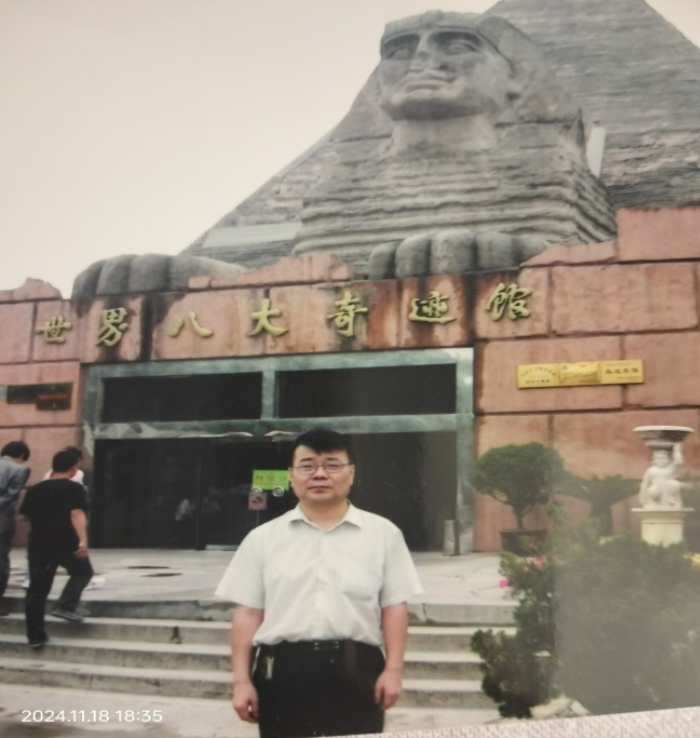
作者簡介:牛銀萬,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九原區作家協會會員,在各級報刊和網絡發表文學作品一百多萬字,詩作獲《草原》·北中國之星詩歌大獎賽優秀作品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