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炮中的童心(外二篇)
作者:牛銀萬
小時候,每到過年,我除了盼吃好的,盼穿新衣服,就是盼響炮。
那時,當父親去供銷社購買年貨時,我就站在院門口,翹首以盼,盼他快點買回炮來。當他回來時,我看到籃子里有炮,馬上高興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
可是,炮的種類很少,主要有鞭炮、麻雷、二蹄角。父親買的時候,各種還是都要買一些,但因生活艱難,哪一種也不會多買。鞭炮最多買十來板,麻雷最多買三四十個,二蹄角最多買二三十個。
每年三十,父親早早從涼房里拿回炮,擺放在土炕臺上往熱烤。烤的時候,我玩都玩不在心思上,借故怕炮烤燃,每隔一段時間,就過去翻翻看看。這時,我恨不得拿幾個,馬上跑在院中響。
到了晚上,我和小伙伴們玩上一會兒,就坐在家里看電視,等著接神。那時,家里沒有鐘表,時間只能在那個舊黑白電視上看。到了十一點,特別是聽到村里的麻雷聲時,我就不停地催父親快點接神。父親下地時,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土炕臺上的炮都抱在院中。父親點著旺火,我剝麻雷他捏在手里響,二蹄角立在地上,他響一個我響一個,交替著響。小鞭炮父親都讓我響。我響的時候,把拆開的小鞭炮,都掛在院中曬衣服的鐵絲上,點著后捂著耳朵就跑開。鞭炮炸響,滿院都是飛舞的碎紙屑。響完炮,父親點上香磕了頭,就回家睡覺去了。我余興未盡,低著頭撿那些沒炸響的小鞭炮,撿起來扔在旺火中,鞭炮在旺火中發出沉悶的聲響,火中騰起一股股灰屑。我們接神的時候,狗蹲在墻邊靜靜觀看。它張著嘴,露出潔白的牙齒,也許是在笑,也許是驚訝。每年接完神,我都要和小伙伴們一家一戶撿鞭炮。如撿到有焾的就裝起,沒焾沒炸的,就集中起來,從中間一個個掰斷,倒出火藥點燃。點燃后,地上升起的火焰,在夜色中分外醒目。
記得有一年,母親給我的一板小鞭炮我舍不得響,在火爐上烤時,不小心燃著了,頓時,家里劈里啪拉地響起來,硝煙彌漫,我用手按按不滅,用水澆澆不熄,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燃盡。母親回來知道后,我挨了一頓臭罵,兩天沒出門。
母親看見我可憐,就又給了我一板。遞給我時,她不停地摸著我的頭,一再安頓響炮時注意點,別把火星濺在衣服上。
最難忘的是大雪天響鞭炮。下大雪時,村莊一片寂靜,點著鞭炮扔向空中,“啪”地一炸,聲音特別清脆響亮。堆起雪人,我和小伙伴們把鞭炮插在雪人的腦袋上,炮炸雪花飛起來,雪人的腦袋瞬間就崩裂。
最有趣的是,我和小伙伴們點燃鞭炮,扔向每天跟在我們后面的小女孩兒。小孩兒膽小,常常嚇得掉頭就跑。跑回去告訴給大人,大人追出來,我們早已無影無蹤。
每年冬天,我和父親常在河中掏魚。賣魚的錢,除了買年貨外,父親盡量多買一些炮,為的是讓我們高興。一次,我撈到一條五斤重的鯉魚,父親賣了后,特給我買了一雙黃膠鞋,剩下的全部買了炮。這些炮,都是我最愛響的小鞭炮。
后來,家里的經濟好轉,過年除了買麻雷、二蹄角和小鞭炮外,還買一些煙花。我膽小,起初不敢響,后來越響越膽大,竟敢捏在手上響。
工作后,我住上樓房,住在高層上,我嫌上下樓麻煩,從此,就不再響炮了。每年三十晚上,當我站在窗前,看到夜空中綻放的煙花時,聽到隆隆的炮聲時,我就想起故鄉,想起兒時過年響炮的那些快樂時光……
那輛難忘的自行車
小時候,我家有一輛自行車。上了初中,我就開始騎著它上學。
那時,學校離家有十幾里,步行需要近一個小時,騎自行車十幾分鐘就到了。
我清楚地記得, 這輛自行車漆皮脫落布滿斑點,無后座,無車閘,無護鏈板和刮泥板,車座上只有幾根彈簧,每個腳蹬上只有一根鐵棍,兩條外胎磨得光光的,還有許多小裂縫,甚至從裂縫的地方,能看見淺紅色的里胎,車上的字跡都已經模糊,唯一能看清楚的是車把中間的“永久”二字。
這輛舊自行車沒有鎖,不論放在哪里,我都很放心,不用擔心丟失。
那時,故鄉的路都是膠泥路,坑坑洼洼,騎車既費力又顛簸。因為車座攢得厲害,為了趕時間,我不得不坐著蹬一會兒,站著蹬一會兒。讓我難忘的是,每當遇到雨天,前輪向后揚起的泥水,濺在我的身上,打得臉生疼,如果濺在眼睛上,我看不清楚路,方向盤來回扭動,車左右揺擺,把不穩就會摔倒。摔倒車壓在身上,掙扎幾下爬起來,全身上下都是泥。
上了高中,學校離家更遠,路上人多車多。為了安全起見,我在前輪后面靠上的地方,安了一塊硬膠皮。安上硬膠皮,雨天既能擋濺起的泥水,又能當車閘用。如果減速,我就向前伸出一只腳,稍用力車就會慢下來,如果剎車,就猛用力,車就會馬上停下。
那時,最愁的是自行車胎破。自行車外胎磨損得很厲害,里胎經常會被硬柴棍和小釘子扎破,防不勝防。有時沙子從裂縫進去,也能把里胎攢破。里胎破了,如果是在半路,我就推著自行車到附近的村里找人補,如果回到家,就讓父親補。后來,嫌找人麻煩,我就買上挫子和膠水,自己學著補。上學的時候,我把挫子和膠水隨身帶上,半路破了就當場補,如果忘了帶補胎的工具,我就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使勁蹬著走。可輪胎泄了氣的自行車,顛開讓人心也疼。開始補胎時,因技術差,我補一個窟窿要花很長時間,有時因膠水粘不均勻或破的地方挫不干凈,補上沒幾天就開始漏氣。如果氣漏得不厲害,我就趕緊騎。如果外胎的縫隙裂得過大,我就用細麻繩穿上大針縫,并在有裂縫的地方,里面墊一塊從廢里胎上剪下的膠皮。因輪胎年久老化,里胎破得地方越來越多,一氣之下,我就掏出里胎,塞進蒲棒毛。可塞進蒲棒毛的輪胎,沒有了彈性,騎開顛得更加厲害。這時,我就只好讓父親買一條新的。
就是這樣,我克服困難,騎著這輛自行車,一直讀完初中和高中。
上了中專,這輛傷痕累累的自行車,就再也沒人騎了,靜靜地躺在土墻的角落里,任憑風吹雨打,上面生滿了斑斑鐵銹。
一年假期,我回來看見它悠閑地躺在那里,就小心翼翼地扶起來,擦去上面的塵土,試著騎。可騎上去一蹬,鏈條就斷了,我被閃了一下,栽倒在地,可栽倒大梁也斷了。這時,我才真正感到,這輛自行車,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后來,父親把這輛自行車當廢鐵賣了。父親跟我說,賣的時候,任憑他怎么講價,對方只給十塊錢。我聽后感慨萬千。我真沒想到,這輛與我摸爬滾打近十年的自行車,在我心中無價的自行車,在別人的眼里,競只值區區十塊錢!
畢業后,我分配在城里,上下班要么步行,要么坐公交車,漸漸地淡忘了騎自行車的感覺。
每當看到大街上有人騎自行車時,我感到特別地親切,就不由得想起那輛永久牌自行車,那輛勤勤懇懇為我鞠躬盡瘁的自行車。這時,我總有一種痛心和感傷,總有一種濃濃的思念……
土坯房的記憶
我的故鄉曾經都是土坯房。
那時,如果誰么家準備第二年蓋新房,就要在頭一年秋天脫土坯。
脫土坯有專門的模子,木制的。模子由四個木框釘在一起組成,長二十公分,寬十公分,厚兩公分。
脫土坯用的是紅粘土。故鄉位于黃河之畔,在荒地上挖一兩鍬深就可見到紅粘土,灌溉莊稼的大渠小渠里,都有黃河水沉積下的五六公分厚的散紅粘土。脫土坯的時候,有的人在野外找一塊空地,挖出土就原地脫,有的人拉回渠里的,在自家的房前屋后脫。
脫土坯要加麥秸。準備第二年蓋房,頭一年打下的麥秸,冬天就不再用它燒火了,脫土坯的時候,用粉碎機粉碎,和在土里,來增加粘性。
蓋房的椽檁是逐年置辦下的。脫好土坯晾干碼起來,就清點椽子和壓棧的蒲簾和柳條塊。如果椽不夠,就到村莊旁的樹林里再砍幾根,剝去樹皮在院中晾曬。如果蒲簾或柳條塊不夠,冬閑時就再編一些。
開春,地里忙完,就召集人蓋房。
那時,村里幫忙的人,沒有報酬,如無特殊事,只要張出口來,都不會拒絕。
故鄉是下濕地,蓋房要選地形稍高的地方。蓋之前,要把下面的地基夯實。打夯時,菱形的大夯石上,綁著木杠,由四個人抬著。抬起時,領頭的人喊著號子,其它三個人齊聲呼應,夯石抬起又放下,放下再抬起,反反復復,直到夯實。一個地方夯實后,再挨著往前挪。夯地基的時候,看熱鬧的人特別多,尤其是晚上,人們在飯后都聚集在這里,人越多,領頭的人就喊得越高,呼應的人聲音就越齊越響亮。領頭人喊的詞都是現編的,喊開像是唱,又像是在說,詞都很押韻。為了逗樂,喊的人常常編一些葷的,贏來看熱鬧的陣陣喝采。
地基夯實后,有條件的人在上面再砌石頭,沒條件的,就直接在壘土坯。蹲在墻上壘土坯的人,都是村里的匠人,下面扔泥遞土坯的,都是身強力壯的后生。泥扔上去,壘墻的人用小鏟抹勻,比著拉線,壘得很認真細心。有時壘上一會兒,就讓下面的人看看正不正。遞土坯的人遞一塊,壘墻的人接一塊,動作都非常熟練。
壘好墻就開始壓棧。壓棧前,要在檁子上壓一塊紅布,用來避邪,然后就開始響炮。先響幾個麻雷接著響鞭炮。響鞭炮時,響的人把鞭炮系在細木桿的一頭,點著后,在看熱鬧的人群中提著炮來回轉,嚇得人們捂著耳朵直躲。
響完炮,架上椽檁,房上地下一片繁忙,有的挑水,有的和泥,有的鋪棧,有的扔泥,有的揮爪刨泥……
壓棧的時候,男人們忙,女主人也不消停。女主人請來幾個伙伴們幫忙,有的篜糕,有的包糕,有的炸糕,有的削土豆,有的切菜,有的切肉……忙得不亦樂乎。
壓棧一結束,灰頭臟臉的男人們,就在女主人提前準備好的臉盆里,一個個輪著洗涮。洗涮完,坐在院中抽煙打塌嘴,等女主人吆喝開飯。
吃飯時,所有幫過忙的,不論是大忙還是小忙,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一律請來。能喝酒的坐在土炕的方桌上喝酒,喝不成的,有的蹲在地下吃,有的坐在鍋頭吃,有的站在院中吃。吃的時候,女主人不忘讓自己的小孩,給左鄰右舍和村里的五保戶端幾個油糕送過去。為圖吉利,不是六個就是八個。這時,討飯的也常常來助興,打著快板,說的都是吉利的話。女主人一高興,就舀一碗大燴菜,夾兩個油糕,邊夸邊遞過去。
土炕上的人,喝的是供銷社打的散白酒,抽的是太陽煙。酒提前幾天就打回來,裝在塑料桶里。上炕時,男主人大方地指著塑料桶說:酒多了,管飽喝!酒酣后,人們有的嘮嗑,有的劃圈,有的哼山曲兒……酒灘一直擺到下午三四點,人們酒足飯飽后,才一個個東搖西擺,晃晃悠悠往回走……
此時,盡管家里家外一片狼藉,女主卻和幫忙的一邊收拾,一邊說說笑笑,為脫了個大愁帽而高興……
如今,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故鄉蓋的都是寬敞明亮的磚房,而且大都包給了小工程隊,故鄉的土坯房和蓋土坯房的熱鬧景象,已成為歷史。但故鄉當年蓋土坯房那種互幫互助不講代價的濃濃情意,人們卻永遠不會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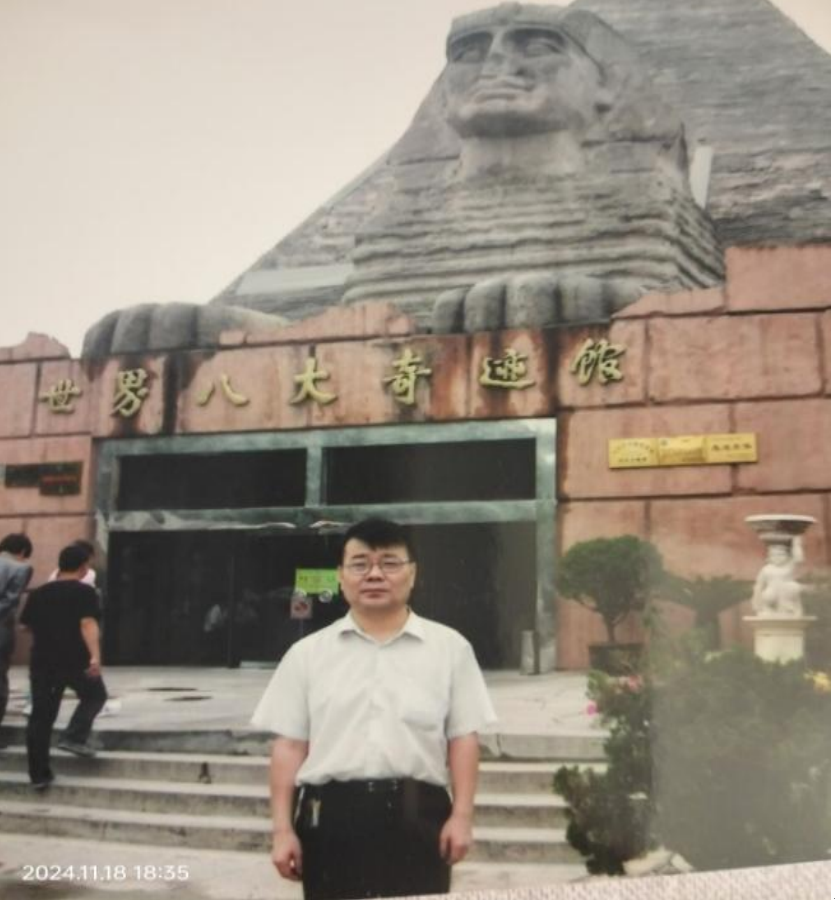
作者簡介:牛銀萬,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作家協會會員,包頭市九原區作家協會會員,在各級報刊和網絡發表文學作品一百多萬字,詩作獲《草原》·北中國之星詩歌大獎賽優秀作品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