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與寧靜
作者:董勤生
其實,早年鄉居的時光更多的是寂寞。假日里,與伙伴玩耍之后,喜愛閱讀的我,在家里翻遍櫥柜也找不到帶文字的紙片,只能和家中的小黑狗戲耍一番。在沒有電視和廣播的夜晚靜得可怕。天一黑,似乎所有的的生命都進入睡眠。偶爾的幾聲犬吠,也是敷衍了事,狗們也沒了興趣。
村莊向南五里是集鎮,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逢集。農人把積攢的雞蛋、鴨蛋、剛滿月的小豬,帶到集市上賣掉,再捎回油鹽醬醋等日用品。這時候,空空蕩蕩的老街便熱鬧起來。這條唯一的老街大致南北走向,青磚鋪就,長不過一里。兩邊參差不齊的瓦房及磚墻雖然異于鄉村的土墻草頂,但都有煙熏火燎的味道,刻滿歲月留下的滄桑。有黃燦燦的剛出鍋的油條躺在黑逡逡的案板上,誘人的香味讓初次見到的兒童賴著不肯離去。我常常跟著母親去趕集,不僅僅圖一個熱鬧,還因為我的外爹家就在街頭。中午,可以吃上半年也吃不到的豆腐和雞蛋,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吃到更稀罕的豬肉。
大一點時候,我會獨自一人去外爹家。外爹家旁邊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公路。偶爾經過一輛帶著拖掛的貨車,鳴著喇叭,揚起長長的灰土陣,呼嘯而過。于我那就是夢幻一樣的存在。車上載的化工用品,據說可以生產化肥和炸藥。車輛到達的終點是國防化工廠和省會城市。每次在外公家前門看到深藍色貨車快速通過,會立即到后門追著目送它離去。這些足夠我在小伙伴們面前吹上半年,而伙伴們和我爭執不休的是汽車有沒有嘴巴,叫聲從哪里發出。
集市名叫高橋,源于早年街南的澗水上有一座高高的青石板橋。是當時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不再滿足,開始向往大人們口中常常提及的一座叫做蔣壩的外縣集鎮。那時候在我們心里,它和南京、上海一樣令人神往。
暑假里,我和另外兩個小伙伴在父母那里爭得幾角午飯錢,早早起身跟著鄰居長輩出發。心里很是激動,腳步也飛快。長輩提醒我們: 路程是去高橋的幾倍,悠著點。
這個座落于洪澤湖古堰上的古鎮,其實就是比家鄉集鎮多了兩條街。飯店大一些,賣魚和炸油條攤子多一些,別的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熱鬧與繁華。真正讓我們大開眼界的是去的途程中。
我們必須經過一座在當時算是宏偉的水利工程。那是政府為解決洪澤湖南岸農田灌溉問題而建設的翻水站,遠遠就可以聽到隆隆的柴油機群聲。到了近前,一排數十米長的藍色瓦頂建筑,整整齊齊地屹立于高聳的水堤下面。數十根直徑近一米的黑色揚水管貼著大堤,像一條條巨蟒一樣攀援到堤頂。一道水泥大壩橫亙于渠壩頂部,數十個出水管如同巨龍一般吐著白花花水柱。第一次見到如此巨大的建筑,我們驚詫得目瞪口呆。
驚嘆之余還得面臨一個抉擇,是直接從寬不到半米高約十米的水泥大壩通過,還是費時繞道下面,再翻越一個個水管通過。看到大人們一個個自信平穩在水泥大壩上行走,自尊讓我們不再猶豫,小心翼翼緊跟其后快速通過。盡管因為緊張雙腿發顫,出了一身汗,但冒險帶來的快感,是平常居家生活里無法體驗的。
離蔣壩不遠是著名的三河閘。那是解放后政府帶領人民響應偉人治理好淮河號召,為了調控洪澤湖水位,在開辟的淮河入江水道上建設的一座交通和調水兩用的設施。數里外就可以聽到轟隆隆的開閘泄洪聲音。踏上橋面,更是忐忑。國道上車來車往,狹窄的橋面十分擁擠,擔心司機一個疏忽會碾壓過來。更讓我們膽顫的,是幾乎垂直而下的旁邊閘門泄出的水直擊下游水面。震耳欲聾巨響,使我們感覺大橋在晃動,隨時都可以坍塌。當我們提心吊膽地走過近一里的橋面,來到河對岸高處回望橋閘才發現,洪澤湖水面要高出橋面數米,如果閘壩倒塌,不要說人,就是巨大的汽車也會被沖落到下游近二十米的河里。漸漸平息了呼吸,再從容地觀望洪澤湖面。藍色浪濤上面迷霧重重,偶見幾只白帆若隱若現。下游水流飛逝,道道白浪里時現漁舟出沒,如同幾片飄落的秋葉。后來閱讀《岳陽樓記》里范仲淹描摹的洞庭湖美景,心中立刻想起此時此地所見所感。歸來后兩腿疲軟走路發飄,第二天都緩不過勁來,但來回一路見聞,會讓沒有去過的小朋友聽得一愣一愣的。
那時候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緩慢,城市化幾乎停滯不前。隨著年齡增長,閱歷豐富,視野的開闊,特別是閱讀能力的提高,不再滿足于現實世界的熱熱鬧鬧。會把探索世界的目光轉向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文學世界里尋覓喧囂與繁華。幸運的是,盡管經過那段特殊時代的疾風暴雨,在民間仍然保留一些珍貴的文學作品。
當托爾斯泰的《安娜 · 卡列尼娜》擺在我的面前時候,是不見封面和封底,也不知作者,紙質泛黃,頁面破損殘缺不全。但這些不足與遺憾并不影響我的閱讀。這位俄羅斯文學巨擘優美神奇的文字引領著我,自由地游覽十九世紀彼得堡和莫斯科偉大的建筑和當時的風土人情,體驗了封建貴族階層的家庭舞會和餐廳美食。渥倫斯基身穿漂亮的軍裝,在貴族家庭舞會出入的生活,像一輪朝陽,照亮了一個鄉村少年的灰暗無聊的歲月。以至于在許多年之后,退休的時間和經濟足夠支撐我出國旅游時,計劃首選的的是去彼得堡看看沙皇時代的宮殿,如果安娜臥軌的鐵路還在,一定去坐一坐。
也許是個人的氣質和心理特質,隨著長大以及到別的城市讀書,見過大城市的寬闊的街道和高層建筑,眼界越來越開闊,漸漸不足為奇,仍然對藝術及虛擬的都市繁華十分神往。
剛工作不久,外國電影如潮水般涌進來。最震撼的是日本電影《追捕》與《生死戀》。夜晚霓虹燈閃爍、街頭車水馬龍、歌舞廳人頭攢動,把國際化大都市演繹到極致。加之代入感極強的電影蒙太奇手法,讓人如臨其境。高倉健扮演的杜丘在摩天大廈頂部與犯罪團伙的斗智斗勇,栗原小卷扮演的夏子與戀人在一起嬉戲追逐的慢鏡頭,更是讓我領略到現代都市的魅力,進而產生一種向往和膜拜。
歲月如流水。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某些感覺發生了變化。有一天,從媒體上突然看到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楊子榮”打虎上山”的長吟讓我有一種特別熟悉和親切,每一句唱詞,每一個旋律,都把我帶入到少年時代。那個特殊時代露天電影場,凜冽寒風吹得銀幕變了形,吐出的吐沫不小心落在衣袖上,立馬就結了冰。長時間站立的雙腿,除了酸脹還因為天氣寒冷,如同立在水中,但仍然不愿離去的一幕幕出現了。
退休之后閑暇時間多了,少不了畢業同學會,久未謀面的朋友聚會,要喝上兩杯。現在經濟條件好了,還得在講究一下規格,非星級酒店不可。酒自然要上檔次,菜從家鄉淮揚風味到川菜,再到閩南菜,從爆炒到蒸煮,再到燒烤,漸感沒味。嘗嘗日式料理及海底生魚的滋味,一次之后再也沒有興致了,至于滲著血水的西餐牛排,不要說送進口中,就是看也會排斥。
剛退休后,曾拍照,多次跑公安局,興致勃勃辦了一個護照,計劃出國走一走。已預訂好的韓國之行因疫情被旅行社通知取消后,旅游的興趣開始漸漸變淡了。
這時候漸漸悟到:隨著年齡增長,心態已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過去那種始終關注外面世界,一心向遠方的蝸牛一樣的思維觸角 開始往回收縮。對于財富、權力、名譽的觀念已悄悄發生轉變。甚至視覺、聽覺、等感覺器官也發生了變化。流行音樂重金屬的撞擊會讓自己的心跳加快,年輕時尚的明星奇異造型和舞姿,會感到不適。
那就把出國旅游的計劃改成國內的吧。在黃浦江畔摩肩接踵的人群里穿越,剛剛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想留下一個鏡頭,一群外國朋友“sorry,sorry”地占了位置。在浦東摩天大廈下,仰著脖子想望到頂部,一片白云飄來遮住視線。等待里,沒有云開霧散,而是暴雨傾盆。不得不躲進附近快餐店,面對來不及收拾的狼藉一片的碗碟。高樓大廈千篇一律,建筑風格不是抄襲就是克隆。人工景點盡顯金碧輝煌、惟妙惟俏,但給人感覺像賓館和飯店前的迎賓小姐,除去妖艷的口紅和漂亮的旗袍,沒有什么實實在在的內容。可惡的是貪婪的雙眼,緊緊盯著你的口袋,大有不掏干凈絕不罷手之勢。
去江南古鎮看看,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初春時節,隨同旅游團走進楊柳搖曳的周莊。陳逸飛描繪過的雙橋上的爬山虎已發新枝,橋下隨著咯吱咯吱的搖擼聲,一位身穿藍色碎花上裝,頭戴藍色花紋巾的婦女,劃著古舊的木船來了。時光似乎倒退了一百年,不由得駐足,掏出手機留下這美好的瞬間。走在沈家大院的灰磚地面,看著留下無數井繩磨痕的井臺,似乎看到數百年前的這戶望族成員的安居樂業的音容笑貌。便慨嘆時光如梭,歲月無情。
古鎮的魅力真的可以讓人上癮。在烏鎮茅盾先生的林家鋪子前久久不愿離去,想多體驗一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普通市民的生活。在當年米農糶米碼頭,掬一捧深綠色的河水,想找尋當年江南稻農絕望的淚滴。
同行者多退休年長者,行色不再匆匆。優雅從容中,游覽與體驗并舉,欣賞與回味同行。在鑒賞當下的景觀中,提升了自己的格局和情懷;在追溯已逝的時光里,拓展了生命的內涵與厚度。歸來難免收獲一些疲憊,但心靈的充盈踏實已沖淡了身體之勞累。
剛退下來的興致,隨著旅游次數的增加,漸漸消減。近兩年,開始把目光轉移到家鄉的山水和古跡。怕打擾別人的生活軌跡,出行方式也做了調整。我和妻子,春天去漆大山公園轉一轉,在山頂草地問候一下剛剛拱出地面的小草。秋天在淮河邊的紫藤長廊里靜坐半日,目送夕陽中遠去的帆影。
更多的時光,留給了自己。中午小憩醒來,打開電腦或者手機,或閱讀一段古今文學典章;或欣賞幾曲傳統民歌;或者與網上同道,交流一下近期閱讀和涂鴉的收獲。
城北老街改造是政府為改善城市面貌,拓展地方旅游業,造福于人民的一項宏大的工程。投入使用后,一時吸引本地及周邊許多居民前來游覽,節假日更是游人如織。
此時,我不湊這個熱鬧。會待到深秋季節,非節假日之上午。這時候,上班族正在辦公室或者車間忙碌。退休族都在菜市場與商販討價。老街一片寂靜,游人稀少。一片金黃色銀杏葉從樹枝上脫落,在空中翩翩起舞,最后像一只蝴蝶一樣落下擁吻青石地面。一片接著一片,圍繞樹根,慢慢鑲嵌完成一個金色的圓輪。獨自漫步于被歲月打磨得光滑的老街,沒有人催促,也沒有人需要招呼,每一刻每一秒都屬于自己的。可以慢敲王記醬油作坊的黑漆大門;輕撫正在給人理發的銅塑老人的手臂;撩撥一下清泉匯集的潭水;與偶園祖先做隔空對話。最后在盡頭市民活動中心成排椅子上任選一個,安靜地坐上片刻。
此刻,沒有喧囂與嘈雜,無需為糧草謀劃,更不為功名惆悵,人世間所有紅塵往事,皆遠離而去。周邊青峰壁立,萬籟俱寂,秋陽漸暖。不覺閉目進入冥想狀態:一個赤身裸體的嬰兒在混沌的空間里,睜著一雙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著世界。
忽然想起老子《道德經》的“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經典名句,是我等后輩與道家師祖心靈相通,還是師祖降臨前來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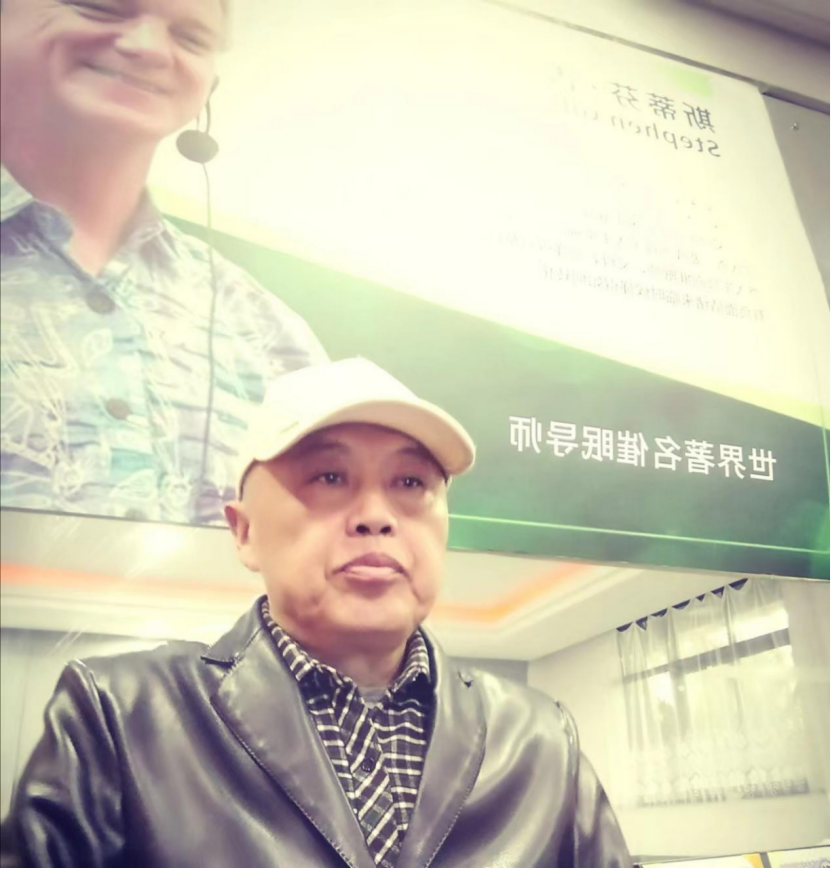
作者介紹:董勤生,江蘇淮安,退休中學教師。早年有散文、小說見刊于《小說報》(吉林)《伊犁河》(新疆)《崛起》(淮安)《揚子晚報》《淮安日報》《江蘇教育報》等刊物。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