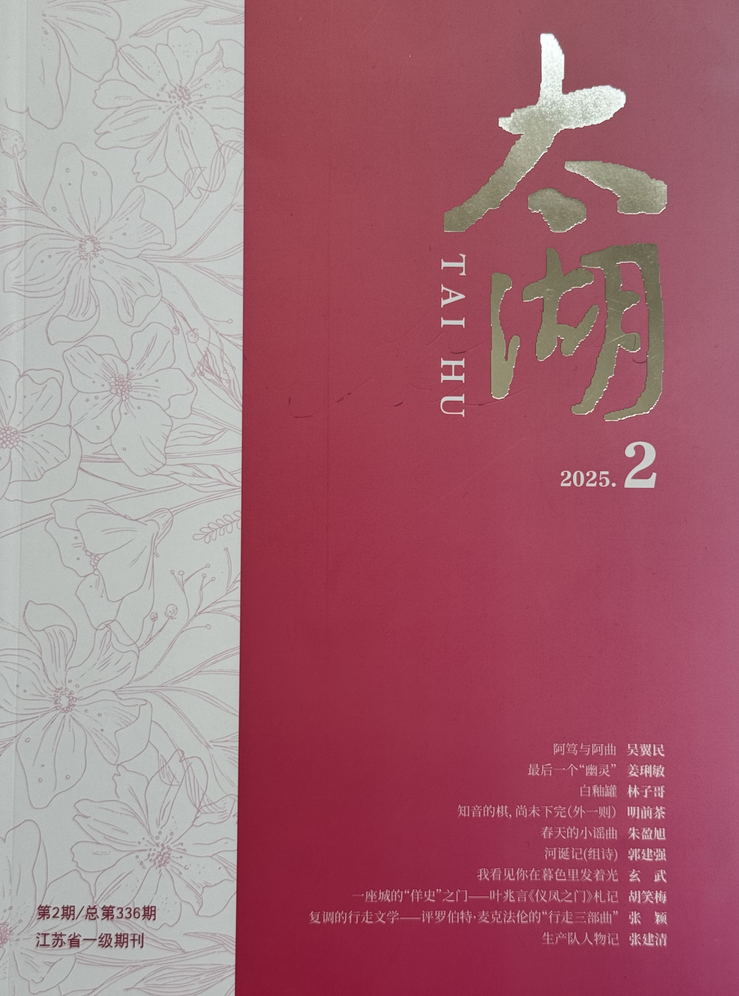
大森林里聽廣播
作者:柳邦坤
一
“剛才最后一響是北京時(shí)間7點(diǎn)整。”“現(xiàn)在是《新聞和報(bào)紙摘要節(jié)目》”“現(xiàn)在是《小說連續(xù)廣播節(jié)目》”……這是我兒少時(shí)幾乎天天都能聽到的聲音。
我們這一代人是聽廣播長大的,廣播伴隨我們度過了寂寥歲月。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文化生活貧乏。家在大森林里,林業(yè)電影放映隊(duì)巡回放映,要一個(gè)月左右才能輪到一回,盼著電影放映隊(duì)來,猶如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當(dāng)時(shí)林區(qū)小鎮(zhèn)和我就讀的子弟學(xué)校,有文藝宣傳隊(duì),會排練文藝節(jié)目,演出也不是經(jīng)常有,一般集中在春節(jié)前排練、演出。地區(qū)和縣上的專業(yè)文藝團(tuán)體,各來過大森林演出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么娛樂活動,聽廣播就成了主要娛樂和求知方式。
聽廣播,離不開收音機(jī)和廣播喇叭。收音機(jī),也叫戲匣子,廣播喇叭即安裝在家家戶戶的揚(yáng)聲器,也俗稱小喇叭,安裝在街道上的大揚(yáng)聲器也俗稱大喇叭。我的童年時(shí)代,收音機(jī)絕對是奢侈品,不記得誰家有收音機(jī)。那時(shí)較為普及的是廣播喇叭,第一次聽廣播是在孫吳縣城,我大概五六歲,隨父母從幾十公里外的林區(qū)小鎮(zhèn)辰清來到縣城,住在一位父母的朋友家里,早晨還在夢鄉(xiāng)里,就被歌聲吵醒,那時(sh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兒?問了父母,才知道那歌聲是從窗戶上面的一個(gè)匣子里傳出來,記得播放的歌兒是《社會主義好》。
后來,父親開發(fā)新林區(qū),工作調(diào)動到愛輝縣,仍在大森林里。1960年代末,林區(qū)小鎮(zhèn)辦起了廣播室,家家戶戶都接上了小喇叭,街道上安有大喇叭,供路上的行人收聽。廣播里主要是播通知,放樣板戲、歌曲的唱片,也播放黑河區(qū)文工團(tuán)、愛輝縣評劇團(tuán)來演出的錄音,演出錄音能播放好久,因此記住了文工團(tuán)、評劇團(tuán)許多演員的名字,如金寶驥、陳圣中、孟西娣、袁世紀(jì)、胡占利、姚淑琴、喬福寶等,聽說文工團(tuán)還有一位知名歌手孟梅,那次她沒有來。
珍寶島事件發(fā)生后,我的老師孫英珍讓我去廣播室錄音,代表全校小學(xué)生發(fā)言,批判新沙皇,然后通過廣播播放。第一次上廣播,既興奮又忐忑。錄音前,孫老師讓我去她家,給我修改稿子,并加上了一句話:“聽到新沙皇入侵珍寶島的消息,我們中國的小學(xué)生表示極大的憤慨!”指導(dǎo)我朗讀時(shí)注意語氣的把握,要把小學(xué)生的憤慨之情表現(xiàn)出來。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憤慨”的詞語,也讓我懂得了用詞的重要性。那時(shí),我剛上小學(xué)三年級。我出外求學(xué)讀高中期間,父親也上過一回廣播,是因?yàn)橥抵u了一點(diǎn)兒自己采的木耳,當(dāng)時(shí)只允許賣給供銷社,為了多賣幾個(gè)錢好貼補(bǔ)家用,便通過鄰居賣給了私人,因此被定為投機(jī)倒把,在廣播里檢查。我是后來聽母親說的,當(dāng)時(shí)真不知道大字不認(rèn)幾個(gè)又訥言的父親該有多為難。
我的少年時(shí)代,已經(jīng)有很多家庭陸續(xù)置辦“四大件兒”了,“四大件兒”包括收音機(jī)、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jī)。但買“四大件兒”挺難,貨源不足,只能憑票供應(yīng),要提前登記、預(yù)約。票是限量的,要排隊(duì)領(lǐng),先來后到,發(fā)完為止。票特別少時(shí),就采用抓鬮兒的辦法,很多人家為了搶到抓鬮的最佳位置,頭一天夜里就去商店門前排隊(duì)。抓鬮兒時(shí)往往全家出動,搞得人仰馬翻,弄壞胳膊腿兒的事也偶有發(fā)生。這情景,在我的少年時(shí)代屢見不鮮,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常見的一幕。
我家買收音機(jī)時(shí),是1970年代初期,那一次,林區(qū)商店總共進(jìn)貨4臺,其中我家買到1臺,好像是等待很久才得到購買收音機(jī)的票,忘記是不是抓鬮搶到的票。因?yàn)檫@4臺都早已有主兒,購買時(shí)就不用搶了,但這四戶人家?guī)缀醵际侨页鰟樱硗馑募矣型瑢W(xué)照敏家,另外兩臺依稀記得有茂森和在全大哥家。把收音機(jī)從商店搬回來,當(dāng)時(shí)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兒。收音機(jī)是挺大的那種,木殼的,上海產(chǎn),工農(nóng)兵牌。
把收音機(jī)搬進(jìn)家,全家人的臉上都寫滿喜悅,那氛圍像過節(jié)一樣。由于林區(qū)遠(yuǎn)離城市,接收的信號不好,噪音大,要用天線。父親從山上扛回一根又高又直的落葉松松木桿兒,立在房前當(dāng)天線桿兒,要對準(zhǔn)黑河城里的方向。接上從窗縫拉進(jìn)來的天線,再打開收音機(jī),噪音小多了,中短兩個(gè)波段都收到了好多臺,有中央臺、黑龍江臺,還有遼寧臺、吉林臺。有時(shí)也能收到更遠(yuǎn)一些的外省臺,不可思議的是,兩個(gè)遠(yuǎn)離林區(qū)的大草原的臺,聲音非常清晰,沒有雜音,不知何故。這兩個(gè)臺,一個(gè)是當(dāng)時(shí)隸屬黑龍江省的呼倫貝爾人民廣播電臺,一個(gè)是當(dāng)時(shí)隸屬吉林省的哲里木人民廣播電臺。被稱為“敵臺”的蘇聯(lián)莫斯科廣播電臺、紅旗廣播電臺,信號特別強(qiáng),聲音也特別清晰,一點(diǎn)雜音也沒有。后來我到廣電系統(tǒng)工作,聽說我們是對其進(jìn)行信號干擾的,但干擾過,信號也沒有受到影響,也許是干擾半徑還不能覆蓋到100公里以外的地域?說句實(shí)在話,我還是在蘇聯(lián)臺里第一次聽到那時(shí)對我還都是陌生的作家名字,因?yàn)槲疑闲W(xué)不久,他們就被打倒了,作品也都被禁,無從看到他們的作品,也就沒聽說過他們的名字。當(dāng)時(shí)聽到的名字有巴金、老舍、曹禺、田漢、夏衍、趙樹理、田間等大作家、大詩人,才知道中國不是只有幾個(gè)作家、詩人。
光靠干擾還不夠,當(dāng)時(shí)為了搞好對蘇廣播,在邊境城市也應(yīng)該辦好廣播電臺,比如像呼倫貝爾、哲里木人民廣播電臺那樣信號強(qiáng)大的廣播電臺,開設(shè)中文廣播和俄語廣播。高滿堂編劇的電視連續(xù)劇《愛情的邊疆》,講述的是1950年代,殷桃飾演的北京廣播專科學(xué)校女大學(xué)生文藝秋,與王雷飾演的同學(xué)萬聲、李乃文飾演的同事宋紹山、蘇聯(lián)播音員維卡等人之間的曲折愛情故事。電視劇寫到了黑河人民廣播電臺,是殷桃飾演的主人公文藝秋的工作單位。文藝秋與一位來華留學(xué)的蘇聯(lián)播音員維卡在京談跨國戀,由于中蘇交惡兩人天各一方,為了能與戀人在電波中重逢,文藝秋要求分配到邊境城市黑河人民廣播電臺工作。當(dāng)然電視劇是虛構(gòu)的,黑河人民廣播電臺到1970年代才辦起來,只有一個(gè)頻率,沒有外語廣播,至今規(guī)模也不大。
二
還是回到我家新買的收音機(jī),收音機(jī)當(dāng)時(shí)絕對是奢侈品,它被擺在家中最顯眼的位置,母親專門找塊紅絨布苫在收音機(jī)上。后來大妹妹長大學(xué)會鉤東西,還鉤了一個(gè)簾兒苫上。
每天都聽收音機(jī),可讓人陶醉、給人們帶來歡笑、叫人長知識的節(jié)目,卻少得可憐。那時(shí)的廣播節(jié)目,單調(diào)、缺乏趣味性、種類和數(shù)量少,一個(gè)節(jié)目反反復(fù)復(fù)播放。新聞節(jié)目聽的最多,當(dāng)時(shí)新聞欄目少,中央臺新聞欄目主要是《新聞和報(bào)紙摘要》和《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lián)播節(jié)目》。此外,也播出廣播通訊、錄音特寫等。1970年代初期,聽到的新聞節(jié)目印象最深刻的是廣播通訊,其中《人民的好醫(yī)生——李月華》,人物事跡讓人感動,播音員的聲音也極具感染力。還聽過一個(gè)錄音特寫,名字記不得了,表現(xiàn)的是幾位在云南上山下鄉(xiāng)知青,勞動時(shí)在大森林里迷路,有關(guān)方面派出人馬全力尋找,歷時(shí)很多天,終于把迷路者找回的感人故事。
文藝節(jié)目聽的最多的是樣板戲,各臺、各時(shí)段,只要打開收音機(jī),肯定能聽到樣板戲,以至于《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戲,我差不多可以把整部戲的唱段、念白都背下來。粉碎“四人幫”后,楊振華、金炳昶說過一段當(dāng)時(shí)很火的相聲,諷刺了這一現(xiàn)象:調(diào)一下臺,是樣板戲,再調(diào)一個(gè)臺,是樣板戲,再調(diào)一個(gè)臺,還是樣板戲。楊振華模仿調(diào)臺時(shí)出現(xiàn)的噪音,可以說惟妙惟肖。1969年夏天,也就是錄制譴責(zé)蘇軍入侵珍寶島的大批判稿不久,母親帶我們兄妹四人回山東老家探親。老家的村里家家都有廣播喇叭,每天早晨都被方海珍教育小強(qiáng)的唱段吵醒,整整3個(gè)月,竟沒換過別的戲,天天都是《海港》。
有時(shí)收音機(jī)里也播一些獨(dú)唱、二重唱、合唱、表演唱等歌曲,其他藝術(shù)形式幾乎沒有。1970年代初期,廣播里陸續(xù)有了一些曲藝節(jié)目,有馬季、唐杰忠、郝愛民、李文華、常寶霆、王佩元的相聲。說到相聲,還對廣播里播出的相聲進(jìn)行模仿,學(xué)著寫相聲、說相聲。1976年高中畢業(yè)回到大森林里工作,當(dāng)年的秋天第一次參加護(hù)林防火文藝宣傳隊(duì)。宣傳隊(duì)長是上海知青張捷,他讓我編寫表現(xiàn)護(hù)林防火的節(jié)目。當(dāng)時(shí)廣播里正播出常寶霆、王佩元的相聲《挖寶》,由于反復(fù)播出,我把腳本記錄下來,仿照寫了相聲《木頭的故事》,由我和張捷合說,到護(hù)林防火聯(lián)防區(qū)演出,頗受歡迎。也模仿用“貫口活兒”講木頭全身上下都是寶,提醒人們要愛護(hù)森林,珍惜樹木。當(dāng)時(shí)還不知道什么是“貫口活兒”,是幾年后到愛輝縣文化館參加文藝創(chuàng)作學(xué)習(xí)班,聽了地區(qū)藝術(shù)館創(chuàng)作干部王國臣老師輔導(dǎo),才知曉“貫口活兒”“抖包袱”等術(shù)語。
馬季、唐杰忠的《友誼頌》,表現(xiàn)中國建設(shè)者援外修筑坦贊鐵路時(shí)與當(dāng)?shù)厝嗣窠Y(jié)下友誼的故事,經(jīng)常播放,差不多可以背下來。還有他們二位說的《高原彩虹》《海燕》,也耳熟能詳。郝愛民、李文華說的一段相聲,名字想不起來了,但記得最后幾句:“二嫂子,你走了嗎?”“我走了!”“xxx,你睡著了嗎?”“我睡著了!”“走了你怎么還在這兒?”“睡著了你怎么還說話?”
聽到的曲藝節(jié)目還有劉司昌、趙連甲的山東快書,如劉司昌說的《扎義打虎》;李潤杰、梁厚民的快板書,如李潤杰的《劫刑車》《峻嶺青松》,聽的最多的是梁厚民說的《奇襲白虎團(tuán)》《犟姑娘》,經(jīng)常聽,也能背下來;關(guān)學(xué)曾、董湘昆、馬增蕙的京東大鼓、京韻大鼓、北京琴書、單弦等,如《送女上大學(xué)》。還有一個(gè)單弦聯(lián)唱《鐵打的骨頭,舉紅旗的人》,是歌頌王國福事跡的,記得第一句:王國福,家住在大白樓……浩然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以王國福為原型塑造的,當(dāng)然,這是很久以后才知曉的。還聽過田連元說的評書小段,名字記不得了,講的是搶救被毒蛇咬傷的朝鮮族孩子的故事,記得評書的最后一句是:“汽車,在革命的大道上前進(jìn)!”聽劉蘭芳、袁闊成、單田芳播講評書,是聽過田連元說這個(gè)評書小段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播放的地方戲,二人轉(zhuǎn)最多,東北的幾個(gè)臺,每天總會有一個(gè)臺播放,特別是吉林和遼寧人民廣播臺播放的最多,二人轉(zhuǎn)在那兩個(gè)省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當(dāng)時(shí)歷史題材都不可以唱,內(nèi)容多是反映新人新事的,有坐唱二人轉(zhuǎn)《處處有親人》,一位大媽來部隊(duì)看兒子,卻忘記是哪個(gè)“浩特”了,因?yàn)椤皟?nèi)蒙的浩特多”,雖然走錯(cuò)了地方,卻得到車站工作人員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還給接到家里,怕老人家寂寞,這家的孩子“晚上陪奶奶看電影,白天陪奶奶聽廣播”,直到聯(lián)系上她兒子的部隊(duì)為止。二人轉(zhuǎn)《女隊(duì)長》,我還清楚地記得里面的一段唱詞并且會唱,“打獵人不怕豺狼叫,打魚人不怕海浪翻……”。經(jīng)常播放的二人轉(zhuǎn)還有《小鷹展翅》,當(dāng)時(shí)也播放過單出頭,名字叫什么忘記了。《處處有親人》《小鷹展翅》是吉林排演的,《女隊(duì)長》是遼寧排演的。還有一個(gè)節(jié)目是常德絲弦《社會主義新事多》,經(jīng)常播放,還記得第一句,“紅太陽光輝照山河,社會主義新事多,伊兒呦伊兒呦……”,旋律好聽,以后再也沒有聽過這種曲藝節(jié)目形式。當(dāng)時(shí)還有一個(gè)河南墜子也經(jīng)常播放,名字記不得了,只記得其中“十個(gè)大雞子”一句,大概是講擁軍的故事。播出的評劇,好像只有一出《向陽商店》。就這些節(jié)目,翻來覆去地放,聽的日久天長,就差不多都會模仿著唱或說了。
三
1970年代初期,大約是1973年前后,聽到了俞遜發(fā)等演奏家的笛子獨(dú)奏曲,如《牧民新歌》《揚(yáng)鞭催馬運(yùn)糧忙》;閔惠芬、王國潼的二胡獨(dú)奏曲,如《賽馬》《江河水》。華彥鈞的《二泉映月》、劉天華的《良宵》,是粉碎“四人幫”后聽到的。聽到的還有劉德海的琵琶獨(dú)奏曲《十面埋伏》,劉明源的板胡獨(dú)奏曲,劉占寬的嗩吶獨(dú)奏曲,還有古箏獨(dú)奏曲《戰(zhàn)臺風(fēng)》、小提琴獨(dú)奏曲《千年的鐵樹開了花》等。由于身邊有上海知青的緣故,喜歡聽用江南方言演唱的《社員挑河泥》,表現(xiàn)的是與北疆迥異的地域風(fēng)情和演唱風(fēng)格。有時(shí)也能聽到上海知青張捷、張時(shí)云等人唱,也學(xué)著模仿哼唱:“撒啦啦子呦,社員挑河泥,心里真歡喜……”廣東音樂也是在這一段時(shí)間聽到的,如《雨打芭蕉》《旱天雷》《步步高》等,旋律優(yōu)美,很喜歡聽。
那時(shí)通過聽廣播和看電影,熟悉名字的歌唱家有:郭蘭英、朱逢博、葉佩英、馬玉濤、馬國光、呂文科、胡松華、孫家馨、賈世俊、劉秉義、鄧玉華、才旦卓瑪、張映哲、張?jiān)侥小②O恩鳳、何紀(jì)光、郭頌、李世榮、韋有琴、黃仁順、郭芙美、張振富、耿蓮鳳、馬玉梅、李秀文、陸青霜、邊桂榮、董振厚、娜仁花、高娃、鄭湘娟、李雙江、吳雁澤、卞小貞、李谷一、莊如珍、邱子敏、劉桂琴、蔣大為等,有些歌唱演員的名字當(dāng)時(shí)是耳熟能詳?shù)模灿械氖墙晁⑽⑿挪胖獣援?dāng)時(shí)聽到的歌曲演唱者的名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的幾年,聽到演唱比較多的歌唱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郭蘭英、朱逢博、李谷一、李雙江、蔣大為、李秀文、卞小貞等人外,還有王昆、寇家倫、李光曦、孟貴彬、姜嘉鏘、付培蒂、王玉珍、王音璇、杜麗華、錢曼華、羅天嬋、任桂珍、于淑珍、韓之萍、張暴默、關(guān)貴敏、殷秀梅、鄭緒嵐、歐陽勁松、靳玉竹、任雁、朱明瑛、遠(yuǎn)征、蘇小明、成方圓、沈小岑、程琳、王潔實(shí)、謝莉斯、吳國松、秦蕾、德德瑪、張正宜、程桂蘭、曹莉、關(guān)牧村、馮健雪、金曼、馬太萱等。
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除了在電影里聽到和在收音機(jī)里聽到的電影插曲外,在收音機(jī)里經(jīng)常聽到的創(chuàng)作歌曲有:《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著作像太陽》《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紅太陽照邊疆》《大寨人心向紅太陽》《我站在虎頭山上》《大寨紅花遍地開》《老房東查鋪》《北京頌歌》《回延安》《延安頌》《千年的鐵樹開了花》《挑擔(dān)茶葉上北京》《我心中的金鳳凰》《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海上南泥灣》《南渡江》《伐木工人之歌》《咱是生產(chǎn)隊(duì)的半邊天》《我為革命下廚房》《我送報(bào)刊走的忙》《真像一對親兄弟》《天安門前留個(gè)影》《阿瓦人民唱新歌》《我愛呼倫貝爾大草原》《我為偉大的祖國站崗》《戰(zhàn)斗進(jìn)行曲》《我愛這藍(lán)色的海洋》《遠(yuǎn)航》《解放軍野營到山村》《師長有床綠軍被》《脫下軍裝不下崗》《軍營套曲(包括投彈歌、夜行軍歌、敵人怕啥咱就練啥等六首)》《愛艦愛島愛海洋》《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銀球飛舞花盛開》《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等。聽過的少兒歌曲有《我愛北京天安門》《我們是共產(chǎn)主義接班人》《友誼開花萬里香》《火車向著韶山跑》《小司機(jī)》《騎上小木馬》《小松樹》《喂雞》《井岡山下種南瓜》《革命故事會》《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等。把被譽(yù)為“萬世師表”的孔子稱為“孔老二”,顯示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的孔圣人的不尊重和蔑視,這是當(dāng)時(shí)開展的運(yùn)動使然,我們當(dāng)時(shí)也盲目跟著批、跟著唱。聽的最多的是帶有那個(gè)時(shí)代特征的歌曲,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學(xué)大寨趕大寨》等,前者近乎綁架式宣傳,反反復(fù)復(fù)唱“就是好”,不容許有任何質(zhì)疑,中間還穿插吶喊,看來沒有更好的詞可以替代了,就像一首“語錄歌”,整首歌只有五個(gè)字,“要斗私批修”,就翻來覆去地唱,中間也穿插一句吶喊。
紀(jì)念長征勝利40周年,復(fù)排了《長征組歌》,在廣播里播放,聽到了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熟悉名字也有不熟悉名字的歌唱家馬玉濤、馬國光、賈世駿、王克正、楊亦然、耿蓮鳳、王伯華等人的獨(dú)唱、領(lǐng)唱、二重唱,對北京軍區(qū)戰(zhàn)友歌舞團(tuán)演出的合唱印象最深。我所在的林業(yè)中學(xué),吳守垣、楊小慧、吳紹春老師帶我們排演了《長征組歌》中的七個(gè)部分:《告別》《遵義會議放光輝》《四渡赤水出奇兵》《過雪山草地》《到吳起鎮(zhèn)》《報(bào)喜》和《大會師》。老師從八里橋部隊(duì)借來了軍裝當(dāng)我們的演出服,在愛輝縣林業(yè)系統(tǒng)和八里橋、三站的駐軍部隊(duì)演出了一大圈兒,也產(chǎn)生一定影響。高中畢業(yè)前,請師生留言,校長的留言是:你在文藝宣傳方面很有才能,希望你畢業(yè)后發(fā)揮這個(gè)優(yōu)勢,為三大革命做出貢獻(xiàn)。沒想到由于參加演出,讓校長注意到,遺憾的是那時(shí)沒有藝考,不然也報(bào)考藝術(shù)類院校試一試。其實(shí)校長高估了我,藝術(shù)方面還談不上天賦過人,尤其唱歌更難登大雅之堂,如果報(bào)考話劇表演或編劇專業(yè),或許有一線希望,這和我曾在小學(xué)和高中時(shí)主演過話劇有一些關(guān)系。
那段時(shí)間,聶耳和冼星海的作品率先復(fù)出了,我們聽到了《黃河大合唱》這部藝術(shù)精品,在當(dāng)時(shí)可以說是空谷足音。近來從媒體上看到當(dāng)事人的回憶,原來是冼星海的女兒給毛澤東寫了信,才有了聶耳和冼星海的作品演出和廣播播放。1975年,是聶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中央樂團(tuán)復(fù)排了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全曲,以為紀(jì)念。指揮是嚴(yán)良堃,演唱者是郭淑珍、黎信昌等,朗誦者是王冰。趕上暑假還是寒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多次播出,其中的大多數(shù)歌曲如《黃河頌》《黃水謠》《河邊對口曲》《黃河怨》《保衛(wèi)黃河》等,就是這樣聽會的。由于多次反復(fù)播放,我邊聽邊記,把朗誦詞記了下來,有同學(xué)還借去傳抄30多年過去了,自己也常常模仿著朗誦,至今還對王冰的朗誦記憶猶新。還有聶耳、冼星海創(chuàng)作的《賣報(bào)歌》《新的女性》《開路先鋒》《大路歌》《畢業(yè)歌》《只怕不抵抗》《到敵人后方去》《二月里來》《金蛇狂舞》等歌曲和樂曲,也是這個(gè)時(shí)期聽到的。在這期間,還推出了《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八月桂花遍地開》《紅區(qū)干部是好作風(fēng)》等江西民歌五首;《高樓萬丈平地起》《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翻身道情》《軍民大生產(chǎn)》等陜北民歌。還有大革命時(shí)期的歌曲和抗戰(zhàn)歌曲,如《工農(nóng)革命歌》《工農(nóng)齊武裝》《抗日之歌》《大刀進(jìn)行曲》《前進(jìn)歌》等。上面這些歌曲都是在收音機(jī)里聽到,其中大部分也是這樣聽會的。當(dāng)時(shí)比較喜歡唱《賣報(bào)歌》《畢業(yè)歌》《二月里來》等,江西民歌和陜北民歌也經(jīng)常聽和唱。近年,我到滬上的一所民辦大學(xué)工作,參加學(xué)校組織的畢業(yè)典禮,唱聶耳的《畢業(yè)歌》是一項(xiàng)重要程序,可見這首歌的恒久魅力。
四
電影錄音剪輯也是那時(shí)廣播電臺的主要節(jié)目,都配有解說。由于林區(qū)個(gè)把月才來一次電影隊(duì),看到的電影有限,好多電影都是聽來的。比如國產(chǎn)電影《火紅的年代》《青松嶺》《春苗》《征途》等;國外電影《瓦爾特保衛(wèi)薩拉熱窩》《沸騰的生活》《橡樹,十萬火急》《追捕》《望鄉(xiāng)》等,也是從收音機(jī)里聽到的。
特殊歷史時(shí)期聽到的文學(xué)節(jié)目不多,記憶深刻的有賀敬之的詩歌《西去列車的窗口》《回延安》,高紅十等作者的長詩《理想之歌》,浩然的長篇小說《西沙兒女》,張永枚的長篇詩報(bào)告《西沙之戰(zhàn)》,王書懷的長詩《張勇之歌》等。
還有廣播劇,也是那時(shí)的主打節(jié)目,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由黑龍江廣播電視藝術(shù)團(tuán)制作的廣播劇,水準(zhǔn)很高,在全國的省級電臺中,都名列前茅,其中廣播劇編劇、導(dǎo)演有高廣義、郭銀龍、王波等,到后來還有王銳、饒津發(fā)、矯崇興,我認(rèn)識的王國臣老師等,演員有鄭淑琴、曹陣、王淑萍、李慧敏、杜玉泉、蕭淑芳、姜萍等,有的既是編劇、又是導(dǎo)演、演員。其中聽到郭銀龍、王波、鄭淑琴、曹陣編導(dǎo)、主演的廣播劇最多,記住了他們的名字,鄭淑琴、曹陣的聲音也銘刻在心。
那個(gè)年代,頗能吸引人的節(jié)目是小說連續(xù)廣播,也記住了省臺和中央臺幾位播講小說的名字。先說省電臺,男聲播講屬曹陣(當(dāng)時(shí)以為也可能是“振”“鎮(zhèn)”“震”)最好。每天播完,播音員說:“是由曹陣播講的,”鄰居孫嬸以為他叫“曹陣波”,說曹陣波講的很好云云,這讓我們樂了很久。他播講最為精彩的一部小說是《桐柏英雄》,在當(dāng)時(shí)“三突出”的創(chuàng)作氛圍里,這部小說的故事可以說跌宕起伏,情節(jié)可以說扣人心弦,無論男女老少,到點(diǎn)兒就齊聚收音機(jī)前或大喇叭下,聽趙小花的曲折故事。趙小花是那個(gè)時(shí)代不多見的一個(gè)亮點(diǎn),尤其是激動了我們少年的心。他還播講了《漁島怒潮》,戰(zhàn)爭和反特故事,永遠(yuǎn)吸引男孩子。當(dāng)時(shí)聽過曹陣播講的小說還有本省作家林予、謝樹創(chuàng)作的《咆哮的松花江》,里面有許多黑龍江鄉(xiāng)土化語言。本土作家寫本土生活的作品聽來親切,留下的印象也深刻,除了《咆哮的松花江》,還有工人出身的本土作家郭先紅的長篇小說《征途》,是以黑河地區(qū)遜克縣上山下鄉(xiāng)知青金訓(xùn)華烈士的事跡創(chuàng)作的。另外還有本土詩人王書壞的敘事長詩《張勇之歌》,是女聲播講,播講人是陳阿喜,她的聲音甜美、動聽,極富感染力,讓我難以忘懷。《張勇之歌》是她和曹陣聯(lián)合演播的,我聽過不止一次,印象深刻。她播講的長篇小說《海島女民兵》、中篇小說《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都膾炙人口。后來她調(diào)到北京,在中央廣播文工團(tuán)任演員,在中央臺繼續(xù)播講小說。粉碎“四人幫”后,聽過她播講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等,還聽過她朗讀的許多文學(xué)作品。
中央臺曹燦播講的《礦山風(fēng)云》《向陽院的故事》《閃閃的紅星》《高玉寶》《新來的小石柱》《戰(zhàn)地紅纓》等表現(xiàn)兒童故事或少年英雄故事的小說,也讓我銘刻在心,因?yàn)樗纳ひ敉μ貏e。還聽過他播講的《艷陽天》《李自成》等。
粉碎“四人幫”后,小說連續(xù)廣播節(jié)目播講的小說,選擇余地越來越大,也有了新的播講者。陸續(xù)聽到了曾被打入冷宮的長篇小說播講,如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暴風(fēng)驟雨》、杜鵬程的《保衛(wèi)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fēng)斗古城》、馬識途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等。也聽過新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如馮苓植的長篇小說《阿力瑪斯之歌》、黎汝清的《萬山紅遍》等。
1978年或1979年,聽過金乃千播講的《東方》,這是當(dāng)代作家魏巍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小說,1982年,獲第一屆茅盾文學(xué)獎,2019年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當(dāng)時(shí)聽的如醉如癡,因?yàn)樾≌f不單單寫戰(zhàn)爭,還寫了愛情,寫了人性。記得小說里,志愿軍軍官里還有反面人物形象,這在當(dāng)時(shí)是覺得很獨(dú)特的。小說里的郭祥、楊雪等正面人物形象,以及陸希榮的反面人物形象,都讓人印象深刻;情節(jié)扣人心弦,抓人耳根。還聽過張家聲、牟云、瞿弦和、張?bào)抻⒌人囆g(shù)家播講的小說。
恢復(fù)高考后,考入師范學(xué)校讀中文專業(yè),我?guī)Я艘粋€(gè)小收音機(jī)去。小說連續(xù)廣播節(jié)目倒是不經(jīng)常聽,因?yàn)椴ブv時(shí)間剛好與上晚自習(xí)時(shí)間沖突。記得班級的幾位女同學(xué),喜歡聽劉蘭芳播講的《岳飛傳》,播講時(shí),就跑到教室外的雙杠前,聚在一起收聽,沉醉其間。
在礦山工作時(shí),一次去北戴河學(xué)習(xí),同行的省煤田地質(zhì)公司的單國俊帶了一個(gè)小半導(dǎo)體。開班那天中午,我們從海邊游泳回來,準(zhǔn)備睡午覺,但單國俊正在收聽小說連續(xù)廣播節(jié)目,當(dāng)時(shí)播的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那天正好講到主人公孫少平的愛情故事,不知不覺間,室內(nèi)七八個(gè)人全都豎起了耳朵,單國俊也適時(shí)調(diào)大了音量。那天的午覺誰也沒睡成,以后的幾天中午也依然如故。小說先在中央臺播出,然后才正式出版,播出和出版后,好評如潮,成為一部難得的、具有里程碑性質(zhì)的上乘長篇,當(dāng)然,這都是很久以后才知曉的。小說人物形象鮮明,故事精彩,播講的也特精彩,但播講者是當(dāng)時(shí)聽了比較陌生的名字:李野墨。這段聽廣播的經(jīng)歷發(fā)生時(shí),已是1980年代中后期。
五
在收音機(jī)里第一次聽到特別悲傷的消息是周恩來總理逝世,那時(shí)我正在愛輝縣林業(yè)中學(xué)讀9年級,住宿條件有限,我們班級所有男生都擠在一個(gè)大寢室里住。當(dāng)時(shí)同學(xué)還沒有一個(gè)人有收音機(jī),周總理去世后,為了及時(shí)收聽新聞,一位同學(xué)把吳守垣老師的收音機(jī)借來了,這樣每天早晨的《新聞和報(bào)紙摘要》節(jié)目,他只好也跑到我們宿舍來聽。學(xué)校自發(fā)地搞了悼念活動,還在教室設(shè)置了靈堂,我們的校長和老師,組織了全校師生參加的追悼會,不知道老師在哪里找到了哀樂的唱片,也記不得在哪里找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后來聽說中央下發(fā)了通知,各地的機(jī)關(guān)、單位、工廠、學(xué)校等,不許設(shè)靈堂,不許佩戴黑紗、白花……也許是山高皇帝遠(yuǎn),我們學(xué)校沒有接到通知?或者校領(lǐng)導(dǎo)沒有執(zhí)行通知?不管怎么說,校領(lǐng)導(dǎo)和老師的舉動,讓我們充分表達(dá)了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之情。我們也是長這么大第一次佩白花、戴黑紗。記得一天早晨,大吳老師又來收聽,當(dāng)收音機(jī)里播音員說:把周總理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土地上……大吳老師激動地、也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浙南口音喊了一句:“好啊!”他的神態(tài)如在眼前。
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消息是在同一年,這時(shí)我已高中畢業(yè)回林區(qū)上班。一天我坐敞車由林區(qū)小鎮(zhèn)去黑河治牙,途經(jīng)一個(gè)叫西山后的村子,車停下來休息,司機(jī)與這里許多人都熟,我們聽到大隊(duì)的大喇叭正播放很低沉的樂曲(后來知道那叫哀樂)。一位司機(jī)熟識的人過來,趴在車廂板上用悲傷的、很小的聲音說:“主席去世了。”過一會兒,大喇叭里開始播《告全國各族人民書》。覺得難以置信,當(dāng)時(shí)有天塌地陷之感,被巨大的悲傷和絕望襲擊著。到了黑河,在縣林業(yè)招待所住下后,我就隨著自發(fā)的人流到三百旁的勞保商店領(lǐng)免費(fèi)發(fā)放的黑紗,然后戴上。記不清是一直住在招待所還是再一次來城里,9月18日,我又去參加了在黑河人民廣場舉辦的追悼會,先是收聽北京追悼大會的廣播實(shí)況,然后黑河地區(qū)再開追悼會。那天,黑河城里幾乎所有人都齊聚廣場,廣場四周還架起了高射炮,估計(jì)當(dāng)時(shí)軍方進(jìn)入了一級戰(zhàn)備,因黑河地處邊境,當(dāng)時(shí)中蘇關(guān)系緊張,擔(dān)心對岸會趁機(jī)入侵,等待開會的時(shí)間,不知是誰發(fā)現(xiàn)了高空有一黑點(diǎn),于是坐在廣場上的幾萬人全都仰頭看,以為是對岸派來轟炸的飛機(jī),氣氛很緊張。當(dāng)時(shí)廣場旁還有救護(hù)車,還真有人讓救護(hù)車?yán)撸恢朗潜从^而暈倒,還是中暑暈倒,那天天氣晴好,溫度也頗高。
六
真正受益于廣播是在粉碎“四人幫”后,1976年高中畢業(yè)回大森林里工作,上班幾個(gè)月后廣播里傳來“大快人心事”。這年冬天第一次去山場伐木,離家有四五十里路,我們住在帳篷里。不知是誰帶了收音機(jī),每晚的精彩節(jié)目陪伴我們度過了漫長的冬夜。也奇怪,在林區(qū)小鎮(zhèn)接收廣播信號需要立桿子,在山場,距離城市更遠(yuǎn)了,信號卻更好,聲音也更清晰,不用外接天線,也許我們采伐點(diǎn)的帳篷,是架在山山坳里,海拔更高一些的緣故?那時(shí)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新的興奮點(diǎn),那些我偷著學(xué)會哼唱的一首首老歌兒陸續(xù)解禁。比我們大幾歲的上海知青張捷、賀永國、談官寶等人,老歌兒都會唱,收音機(jī)里唱,他們也跟著唱,如播《劉三姐》時(shí),張捷等人幾乎全都能跟著唱出來。王昆的《抗日將士出征歌》《夫妻識字》、郭蘭英(她復(fù)出較早一些)的《繡金匾》《八月十五月兒明》、鄧玉華的《革命熔爐火最紅》、王玉珍的《洪湖水,浪打浪》、任桂珍的《繡紅旗》、黃婉秋的《劉三姐》、胡松華和杜麗華的《馬鈴兒響來玉鳥兒唱》等老歌兒,都是在帳篷里跟收音機(jī)學(xué)唱的。還跟收音機(jī)學(xué)唱了一些新歌,如李光曦的《祝酒歌》、韓芝萍的《歌唱敬愛的周總理》等。
每一個(gè)被打入冷宮的藝術(shù)家的名字出現(xiàn),我們就歡呼一陣,聲音傳出帳篷,在山谷里回蕩。兒少時(shí)聽?wèi)T了許多歌曲的激昂、鏗鏘,冷不丁聽這些婉轉(zhuǎn)、抒情的歌曲,真有如品嘗了美味佳肴、玉液瓊漿一般,那感受跟從前就是不一樣。我們上高中時(shí),家在城里的慕華同學(xué)放假回城學(xué)了幾首老歌兒,還有幾位班上同學(xué)跟四中到二站公社搞開門辦學(xué)的同學(xué),學(xué)了幾首港臺歌曲,他們經(jīng)常偷偷唱,被當(dāng)作唱黃色歌曲,受到批判。記得歌中有歌詞“阿哥阿妹情意長”“我愿她拿著細(xì)細(xì)的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再來一杯苦的咖啡”等歌曲,還有一首歌詞是:“再見吧,春光明媚的巴厘海灣,我將到遙遠(yuǎn)的地方……青春是無限美好!”。以后才知道第一個(gè)是歌曲《婚誓》的第一句,是電影《蘆笙戀歌》插曲;第二個(gè)是王洛賓的歌曲《在那遙遠(yuǎn)的地方》;第三個(gè)是臺灣歌手姚蘇蓉演唱的《我與咖啡》中的一句,這是很久以后才知曉的。第四個(gè)旋律最動聽,至今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為慶祝粉碎“四人幫”,紀(jì)念周總理,那時(sh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幾乎每晚都播放詩歌朗誦音樂會。詩歌朗誦音樂會有曹燦、周正、姜湘臣、董行佶、殷之光、張家聲、金乃千、瞿弦和、鄭振瑤、張?bào)抻ⅰ⒛苍啤㈥惏⑾驳热说脑娎收b,有歌唱家演唱歌曲。播音藝術(shù)家夏青、葛蘭、林田、費(fèi)寄平、鐵城、方明、林如、雅坤、虹云、王歡、傅成勵、丁然、黎江、于芳、馬黎、潘捷等也朗誦文學(xué)作品,解說電影錄音剪輯。聽他們的朗誦,真是享受聽覺盛宴,讓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朗誦藝術(shù)的魅力,就從那時(shí)起,我就喜歡上了朗誦。2010年代的一個(gè)夏天,在河南大學(xué)參加新聞學(xué)院成立20周年慶典晚會,現(xiàn)場聽到虹云老師的朗誦,并在同住的酒店大堂見了一面并聊了幾句,這是后話。殷之光朗誦的《周總理辦公室的燈光》,打動我的心,感受到了周總理為黨的事業(yè)日理萬機(jī)的辛勞;董行佶朗誦郭小川的《昆侖山的演說》,使我覺得就如同有一位偉人正站在昆侖山頂,指點(diǎn)江山。聽到朗誦郭小川的《秋歌》《團(tuán)泊洼的秋天》,更讓我體會到詩歌的無窮魅力。
相聲是當(dāng)時(shí)各家廣播電臺喜歡播出的節(jié)目樣式,1976年10月以后,聽到最多的是侯寶林與郭全保、侯寶林與郭啟儒合說的相聲,如《夜行記》《醉酒》《戲劇與方言》《說方言》《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戲劇雜談》《改行》等。還有劉寶瑞、郝愛民合說的相聲《寧波話》,劉寶瑞說的單口相聲《黃半仙》,馬季說的單口相聲《打電話》,楊振華與金炳昶合說的《下象棋》《好夢不長》,蘇文茂、王佩元合說的《批三國》,蘇文茂說的單口相聲《扔靴子》,高英培與范振鈺合說的《釣魚》,姜昆與李文華合說的相聲《如此照相》等,都可以說百聽不厭。
京劇、評劇、昆曲、豫劇、越劇、黃梅戲等都經(jīng)常播出全劇或選段,中央臺、黑龍江臺也開辦了京劇或戲曲欄目,記得黑龍江臺開設(shè)了《老張聊戲》欄目,我這個(gè)時(shí)候從收音機(jī)里知道了許多戲劇大師和藝術(shù)家的名字,如京劇的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李多奎、尚小云、荀慧生、程硯秋、譚富英、裘盛戎、奚嘯伯、李少春、張君秋、李和曾、趙燕俠、關(guān)肅霜、劉秀榮、楊秋玲等。還有評劇的新鳳霞、小白玉霜,越劇的袁雪芬、傅全香、呂瑞英、范瑞娟、徐玉蘭、王文娟,黃梅戲的嚴(yán)鳳英,粵劇的紅線女,呂劇的郎咸芬等。
也聽了很多話劇,最早在廣播里聽到的話劇,大約是我家買收音機(jī)后不久,是關(guān)于南京長江大橋建設(shè)的題材,名字不記得了。當(dāng)時(shí)對話劇的印象并不好,覺得有點(diǎn)兒吵,聽不清臺詞。真正感受話劇的魅力是新時(shí)期以后,陸續(xù)聽到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報(bào)春花》《姜花開了的時(shí)候》《雙人浪漫曲》等。特別是聽到北京人藝的《屈原》《蔡文姬》《雷雨》《龍須溝》《伊索》《丹心譜》等,才感到話劇藝術(shù)的神奇,原來語言能如此讓人震撼。知道了老舍、曹禺、焦菊隱、鄭榕、刁光覃、朱琳、藍(lán)天野、董行佶、于是之、童超、蘇民、英若誠等一批國寶級劇作家、導(dǎo)演、表演藝術(shù)家的名字,被表演藝術(shù)家的聲音所迷戀。
七
漸漸地電臺節(jié)目豐富了,樣板戲播的少了,“文革”前的一些膾炙人口的欄目又恢復(fù)播出了,如《小喇叭》節(jié)目,《星星火炬》節(jié)目。這時(shí)我知道了孫敬修爺爺,喜歡聽他講故事。后來有了適合我這個(gè)年齡段聽的《青春年華》節(jié)目,主播張悅的嗓音異常甜美,一次她回答聽眾的提問解釋她的名字:想給聽眾帶來更多的快樂和欣喜。還有一次在節(jié)目里,她講起了自己,她是從內(nèi)蒙古草原,考入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由于趕上“文革”,當(dāng)時(shí)只有初中學(xué)歷。她邊做好播音工作,邊堅(jiān)持學(xué)習(xí),終于獲得自學(xué)考試文憑。當(dāng)時(shí)聽了她的故事,覺得很勵志,也感到很親切。也很喜歡聽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節(jié)目,多年以后,從黑河籍劇作家、散文家劉邦厚老師的散文里,才知道徐曼是黑河人,小時(shí)候就在黑河西郊的振邊酒廠里長大。
我最喜歡的節(jié)目是《閱讀與欣賞》和《文學(xué)之窗》節(jié)目,它們使我受益匪淺。由于我上學(xué)期間特別是高中的兩年幾乎沒有學(xué)到多少功課,加上在大森林里也找不到書讀,我能獲得一些文學(xué)知識,很大一部分來自廣播。沒有收音機(jī),后來恢復(fù)高考時(shí),我想考上學(xué)幾乎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我能考取師范,主要是靠語文成績。入學(xué)后,班主任趙宗乙老師告訴我,我的語文成績是全班最高的,作文滿分。得以錄取,除了感謝從小學(xué)一年級到九年級教過我的老師、感謝父母外,也要感謝收音機(jī),廣播里的節(jié)目拓寬了我的視野。張家聲、曹燦、牟云、張?bào)抻ⅰ㈥惏⑾病⑧嵳裰{等人的朗誦,如打開了一扇窗,使我認(rèn)識了文學(xué)王國的美麗、神奇。聽他們朗誦楊朔的《荔枝蜜》《雪浪花》、秦牧的《土地》、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王汶石的《新結(jié)識的伙伴》、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賈平凹的《滿月兒》等,有身臨其境之感,文中的主人公如在目前。
我能報(bào)上名參加高考,也得益于廣播。是1970年代的最后一年的高考,也是恢復(fù)高考的第三年。高考通知是由縣林業(yè)科以文件形式發(fā)到各基層單位,由于上海知青等已大都返城,一位主管領(lǐng)導(dǎo)想當(dāng)然地以為林區(qū)子弟沒有人報(bào)名參加高考,這個(gè)通知既沒有在全場大會上宣讀,也沒有在大喇叭里通知。我當(dāng)時(shí)正天天等著報(bào)考通知,眼看時(shí)間臨近,還沒有音訊。忽一日,聽省臺新聞播出:今年的高考報(bào)名工作到今天結(jié)束,全省有多少多少人報(bào)名……我一聽傻眼了,趕緊去找場領(lǐng)導(dǎo),主管的這位領(lǐng)導(dǎo)答復(fù)說:“通知早就來了,我以為上海知青、黑河知青都走了,本地知青就沒有人報(bào)名參加高考了,就沒有發(fā)。”這個(gè)回答讓我無語,也不知從哪里來一股急勁,當(dāng)天就請假坐帶“炮車”(即帶拖斗、無大箱板兒的貨車,可以裝十多米長的木頭)的拉大木頭汽車下山了,坐在十多米長的原木上面,這樣乘車是很危險(xiǎn)的,時(shí)間緊迫,也顧不了那么多,再說林區(qū)小鎮(zhèn)通黑河的客車一周只有一次,沒法等,就急三火四趕到近150公里外的黑河。愛輝縣林業(yè)科主管教育的李桂芬老師善解人意,她聽說了情況,二話不說,冒雨陪我去縣教育科,主管招生的兩位張老師也很熱心,他們從留出的機(jī)動名額中給我報(bào)了名,我還替我妹妹及另外兩人報(bào)上了名。結(jié)果那年我成為“大學(xué)漏子”,被錄取到地區(qū)師范學(xué)校。如果不是聽廣播,我也許就錯(cuò)過了那一年高考的機(jī)會,那我的人生也就會重新改寫。
入學(xué)后,有一個(gè)小收音機(jī)帶在身邊,記不清是父母給我買的,還是我自己買的。當(dāng)時(sh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搞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最后評出15首,和同宿舍的志照、德功、賀偉、郭軍、光明等同學(xué)還認(rèn)真參加投票,結(jié)果出來,我們投票的大部分歌曲入選,活動結(jié)束,還收到中央臺給我們每個(gè)參加投票同學(xué)寄來的入選歌曲的歌片兒(折疊式的),入選歌曲都是我們喜歡聽、喜歡唱的,有《祝酒歌》《妹妹找哥淚花流》《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再見吧,媽媽》《泉水叮咚響》《邊疆的泉水清又純》《潔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陽島上》《絨花》《浪花里飛出歡樂的歌》《我們的明天比蜜甜》《青春啊青春》《永遠(yuǎn)和你在一道》《心上人啊!快給我力量》《大海一樣的深情》《遠(yuǎn)方的書信乘風(fēng)來》等。《歌曲》月刊舉辦的1980年歌曲評獎,我們也參加了,也收到了歌片兒。獲獎歌曲有我們當(dāng)時(shí)喜歡的《軍港之夜》《美麗的心靈》《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美麗的草原我的家》《紅杉樹》《我愛家鄉(xiāng)的山和水》《太湖美》《浪花啊浪花》《清晨,我們踏上小道》《駝鈴》《思親曲》《戒煙歌》《心中的玫瑰》《啊,故鄉(xiāng)》《彩云歸》《生活是這樣美好》《媽媽,看看我吧》《青春多美好》。這些歌曲都是經(jīng)常在收音機(jī)里聽到的,也是邊聽邊跟著學(xué)會唱的。
我曾跟收音機(jī)聽廣播電視英語講座,學(xué)習(xí)英語,是陳琳主編的教材,只是后來畢業(yè)再次上班沒有堅(jiān)持下來。
在師范的第二年,就有電視看了,這是個(gè)傳媒事業(yè)走向新的發(fā)展階段的開端,也預(yù)示著廣播開始走上艱難之路。聽廣播很快就讓位給看電視了,自此,我們與廣播漸行漸遠(yuǎn)。在師范上學(xué)時(shí),還不能直接看到中央電視臺、省電視臺的節(jié)目,看到的是黑河地區(qū)廣播電視局播放的錄像。我們自己還沒有開始拍電視連續(xù)劇,看的都是國外的電影、電視劇,記得看過《復(fù)活》《紅與黑》等。錄音機(jī)的出現(xiàn)也給廣播帶來一定沖擊,也是在師范的第二年,盒式錄音機(jī)悄然出現(xiàn),很快同宿舍的郭軍同學(xué)家里買了一臺,他帶到學(xué)校,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有了電視看、錄音機(jī)聽,就如有了新朋友,但忘記廣播這個(gè)老朋友是不應(yīng)該的,廣播這位老朋友對于我而言,是恩重如山的。我與廣播情緣頗深,后來竟然到電視臺、廣播電視臺從事管理工作十年整,再后來又轉(zhuǎn)行到內(nèi)地高校,從事廣播電視專業(yè)的教學(xué)工作。這是我在大森林里聽廣播的時(shí)候,絕對想不到的。
廣播,幾乎陪伴我度過整個(gè)1970年代,她伴隨和見證了我的青蔥歲月,伴隨和見證了我的成長。她如同一個(gè)魔盒,給我展現(xiàn)玄妙神奇,讓理想張開了飛翔的翅膀;她如同一座看不見的舞臺,讓我如置身臺下,感受時(shí)代的風(fēng)云變幻,人間的悲歡離合;她如同一位老師,傳道受業(yè)解惑,循循善誘,令我獲益匪淺。
那逝去了的如歌歲月,那飄遠(yuǎn)了的如煙往事,那依稀回蕩在耳畔的聲音……
(刊發(fā)于《太湖》雜志2025年第2期)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