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月刊》2022年5期目錄
獨秀
交織萬物的金梭(組詩)/冉冉
隨想錄(隨筆)/冉冉
隧道
手之詩(組詩)/伊甸
中堅
向著風吹來的方向(組詩)/郁笛
勞動的高度(組詩)/羅巴
訪談:真實,或者誠實地表達自己 /郁笛 羅巴
前沿
向武華/陳會玲/郭毅
新銳
安徽新生代詩人小輯
梁京/賈文茜/蘇朵/赤鐵/張子威/只緘默/李解
李安棣/余雨聲/費潤澤
星座
“新生態詩歌”小輯
王子俊/周所同/木喬/葛筱強/許俊/葉燕蘭/姜樺
牧村/朱良德/林新榮
域外
尤金尼奧·蒙塔萊詩選
【意大利】尤金尼奧·蒙塔萊 劉佳怡/譯
版圖
魯迅文學院第四十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詩歌小輯
詩樂園作品小輯
靜得花開詩歌工作室作品小輯
短制
馬笑泉/季風/燕南飛/品兒/龔艷/范文勝/劉應姣
山中子/田雨/趙春秀/周八一/王張應/胡權權/吳笛
王光中/陳光美/進勤/胡曉靖/張詩群/許之格
嚴建文/陳璨/蔡盛/陳虎山/趙俊穩/貞子
欄目主持人語
獨秀
組詩《交織萬物的金梭》是作家、詩人冉冉的新作。在審讀這組詩時,我正在讀她在《人民文學》第四期發表的中篇小說《在米耶的日子》。無論是詩還是小說,冉冉總是給我們新的東西,總不讓讀者失望,因為她堅持的寫作底線是創新,不復制自己過去的作品是寫作者對讀者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嚴于律己。
《交織萬物的金梭》寫作主旨包括了:不同時間、空間里個體的人在物質、情感的存在狀態,和這之間親情、友情、愛情所屬的溫暖和懷念。她用女詩人特有的敏感和敏銳捕捉、把握當下人對于生死、對于人生追求、對于愛恨內在的根本狀況,做到積極的、細膩的、切入式的詩性提取和詩意呈現。她在《最先亮起的》中表達了對先行者的禮贊,在《他攀爬過七八個天坑》中塑造了堅強者的形象,在《閨蜜和伙伴》中抒寫了對隔世的閨蜜和伙伴的懷念,在《還有個天地》中描繪了另一個世界或夢境里的圖景。尤其是她的《交織萬物的金梭》一詩,有著對困頓生活在永恒時間和無限空間里最后被消解的感悟。讓我們看看她的《往前走》一詩吧,她寫到往前走五百米,“有一道莊嚴的大門/五百尊泥塑盤坐屋里”,走四百米,“有一道鐵門/屋里對坐著兩個母親”,走三百米,“有一道木門/少年正傷悼自己的戀情”,一直到一百米,“有一道/清透圓潤的門。一顆露珠……”在這視角前行的過程中,最初眾多的具象(五百尊泥塑)變為最后一個單獨的具象(一顆露珠),這種前視前移放大,而具象后延縮小的觀感,造成內在的審美歧義,給人一種令人感到新奇和愉悅的閱讀感受。此外,她對具象的轉換有著創新的視角突破,即她從一般具象A入手,轉為自己的特殊意象B或C。比如,她寫“玉米”(具象A),轉換成文本里的是“有如火種蟄伏在燧石里面/覺悟發端于苦難的肉身”(特殊意象B)和“虎紋斑斕的流浪貓一閃即逝”(特殊意象C),讓物質的“玉米”變為詩的“玉米”或精神層面的“玉米”。另外,她在選擇具象時,挑選的還有“天坑”“燧石”“星天牛”“彩虹”等,這是她用大宇宙觀來看待和審視萬物蒼生的結果。
在量子時代的今天,誰持有大宇宙觀,誰就可以擁有更深遠的未來。對科學家是這樣,對文學家是這樣,對于我們普通人也是這樣。
——李云
投稿郵箱:shigeyuekan@163.com
中堅
郁笛的詩歌,有一種“由此及彼”的美學。詩歌既不是“此”也不是“彼”,而是“由此及彼”之間那段美妙的過程。組詩《向著風吹來的方向》,不時出現“荒漠”“大雪”“飛沙”“空城”等詞語,意象蒼茫,意境雄渾。這與詩人現在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關,也就是“由此及彼”的“此”。夢中的桃花開了,一首詩從天而降;從無序中回過神來,一首詩戛然而止。郁笛之“彼”,即在返鄉方式日趨多樣化的今天,他在人生的旅途和綿延的紙上對魯南“西水溝”抒寫的物理的和精神的鄉愁——郁笛像是在完成一幅中國畫,這個過程,依然是最為可靠的精神路徑。
和郁笛一樣,羅巴對美術也有一定的造詣。詩與畫相互浸潤,他們比常人更敏感于空間、光線、色彩的布局和變化。前幾年,德國青年藝術家恩里科·巴赫曾在中國舉辦“由表及里”個人畫展,他的作品因呈現了超現實的魅力而備受矚目。羅巴的組詩《勞動的高度》也借鑒了很多油畫的手法,具有超現實特征,可以用“由表及里”來解析。不過,透過超現實之“表”,其本質仍是古老鄉愁之“里”。更何況,羅巴在十幾年前就在安徽懷寧重修了祖屋,一有空閑便待在那里創作故鄉系列作品《何墩村》——也許每個中國詩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處精神上的桃花源吧。
——陳巨飛
投稿信箱:49414742@qq.com
前沿
向武華的詩歌主要書寫的是鄉村的日常生活景象和事件。他的詩歌里有一個“人世”,這使得這些詩歌異常溫暖。雖然他多是以第一人稱書寫,但實際上作為主體的“我”在詩歌中是非常小的,有些詩甚至達到了“無我”的境界。我們堅信,這乃是中國古老藝術的正脈。
從陳會玲的這組詩歌里,我們讀到了這些:她的詩歌里深埋著人生的秘密經驗、時光的消逝之美、退卻和隱約的惶惑之間的靈魂;我們還讀到了這些:她的寫作在具體性和感覺之外,有一種欲辨已忘言的絕對性的東西,它好像不在又確實存在著,存在于她那不易為讀者感受到技巧的詩藝之中。
郭毅的詩歌里有一種修辭帶給人的愉悅。他的詩歌在具體的生活和抽象的思緒之間,在日常的細小和宏大的事物之間、在生命的真實和時空的無垠之間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轉換,讀者因此得以在其詩歌中感受到語言的可能性,并在修辭的愉悅的同時還能感到一種思的力量。
——李商雨
投稿信箱:lisychengdu@163.com
新銳
安徽是現代漢語詩歌的源頭和重鎮之一。如何構建良好的詩歌生態,培育豐厚的詩歌土壤,營造出新生代詩人健康成長的詩歌氛圍,堅持“獨立、探索、多元、開放”多元并舉的辦刊宗旨,積極引導新生代詩人在詩歌寫作中實現文化自信,讓詩歌的真、善、美得以薪火相傳,是本刊在新時代肩負的新擔當和新使命。
在五月我們推出了“安徽新生代詩人小輯”,展現安徽新生代詩人的生機和風貌,亦是本刊的愿望所在。
本期,00后詩人梁京在美國學習視覺藝術,也許受到專業的影響,她的詩歌試圖通過意象來呈現出二維或者三維世界形態,即形象的意象性表達,臨摹某種意象,表現某種情感,也有對潛意識的幻覺呈現;年輕的蘇朵和梁京的詩歌手法很類似,但蘇朵的詩有絕句的空曠與唯美;賈文茜、張子威、赤鐵則多為寓虛境于實境、化情思為景物的呈現,就如同國畫里的無和有,如表現出呈現之物的神韻與形態一樣,同樣的山水,不同的赭石、勾云、夾葉、山道、樹枝、礬頭及小橋,不同的設色就有迥異的結果;同樣,相同的主題,近似的意象,類似的場景在只緘默、費潤澤、李解、李安棣和余雨聲那里,也被賦予了不同的“設色”。編者略感不足的是與本刊近幾年推出的安徽90后詩人閆今、彭杰、星芽等相比,這些年輕詩人的詩普遍輕盈了些、輕巧了些,缺乏某種重載與重負,也少有創新與探索之銳氣。
——樊子
投稿信箱:fanzi1967@163.com
星座
對于生態的關注和參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詩人的感覺基調。自然的力量使得個體對與自然山水生態環境的休戚與共有了切身認識。也許,正是那些不確定的生態變化,乃至生態環境退化和環境改變才使得人類學會了謙卑和虔誠。本輯推出一組“新生態詩歌”,試圖通過詩人與生態自然的真實互動得以管窺詩人對置身生態世界的內在感受。事實上,唯有這些真實感受才擴大了生態的意義。
在王子俊的詩里,你會感到一股豁達和開闊,一位涉入生態空間的詩人,清醒地感知當下的生活與自我,與生態山水之間的親疏關系,“遠一些的黑羊子,/會遇到更爛的路。”(《懸崖上的黑羊子》)而大家行走在同一條路上,“……即使你大聲斥責,這個世界真的變了。”(《不確定的月光》)當暗夜未知來臨,你也許是從黃昏一只鷓鴣的叫聲中聽懂其中的啟迪。
周所同的這組詩歌自然灑脫,富有激情和意趣,“石頭在第八行里綠的更像玻璃/春天從來復雜矛盾。但從未遲到/殘雪在最后一行隱身像褪去一件舊衣”(《春天十行》),揭示了自然的有形和無形,本真與變化之間的內在脈絡,詩中充滿著對自然的禪悟和熱愛。
木喬在他的詩里采用了嶄新的科技視角,古老與現代在沖撞中有一種交融,主觀意識參與給予舊風景以新思考:“收罷莊稼的人,并排坐在護城河邊,/向一株垂柳求教。/順著北過驛巷,轉大寺巷,進入/循理書院”(《無人機視角下的古城》)。
朱良德的詩智性內斂,對事物的描述簡潔有力:“像一只鷹滑向山的邊界,到達/天空的極限/山頂上,一棵樹在風中行走/在匆匆行走中,留下了風的形狀”(《風在吹》)。記憶與現實,生存與夢想,浩瀚時空一切都在悄無聲息地翻轉,與以往相比有了認識的不同,他對那曾認定的事實開始了質疑,而去重新選擇,去和世界重新遭遇,以叩尋存在的本質——他仿佛在察核一群思想的“小小的螞蟻正穿過世界的一道裂縫”。
——微藍
投稿信箱:lingjun0316@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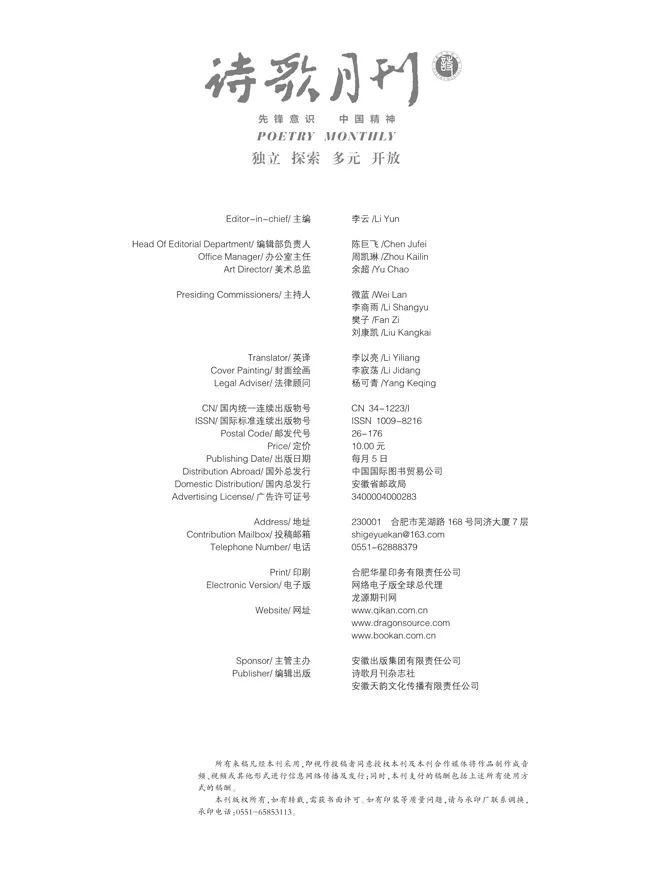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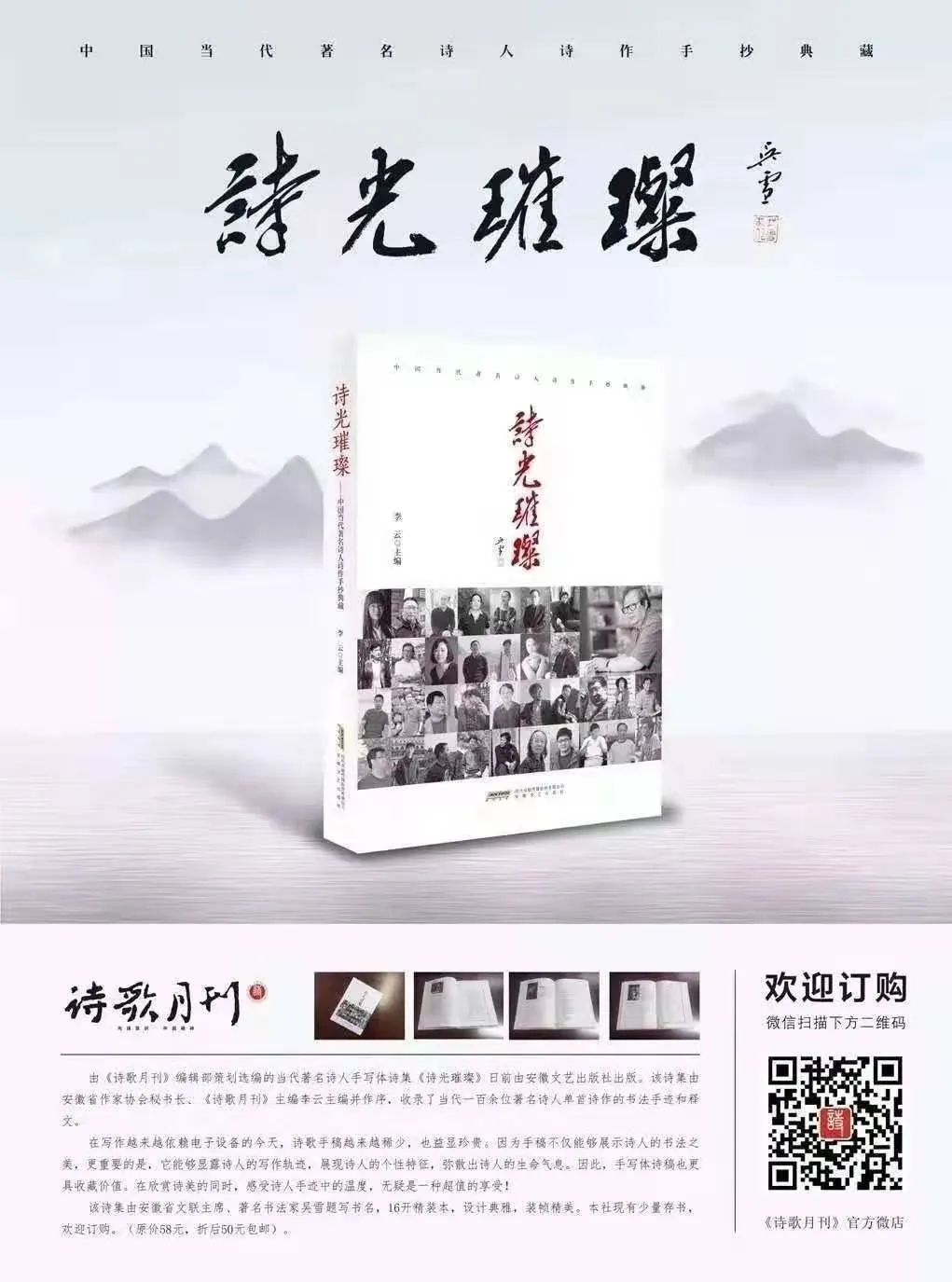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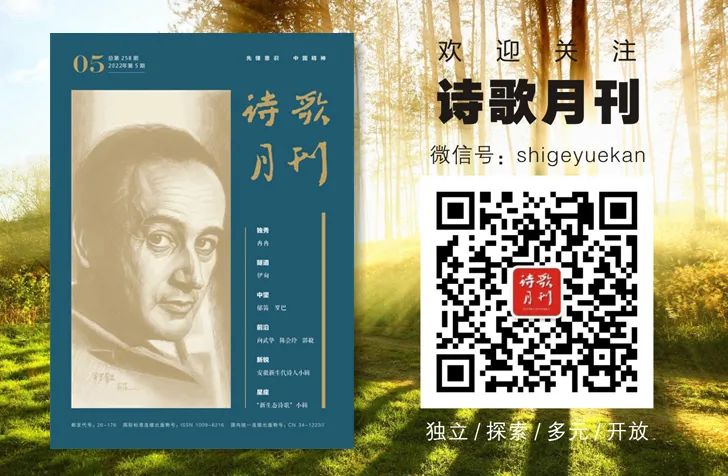
來源:詩歌月刊
https://mp.weixin.qq.com/s/Wz3LeEn0fxKGfjvuiN41ZA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