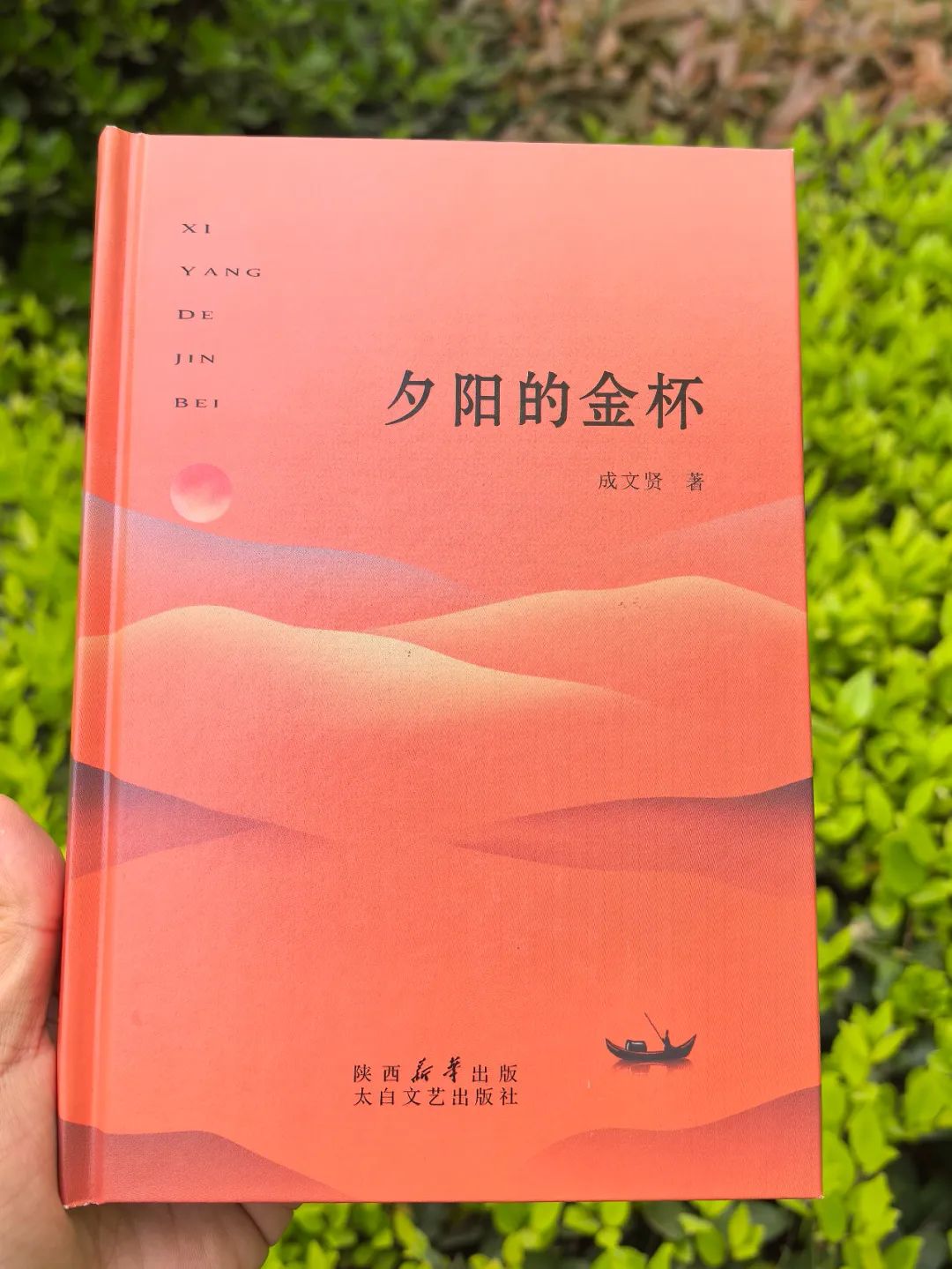
精神領域的“艷陽天”
——讀成文賢詩集《夕陽的金杯》有感
作者:薛婭
繼《篤愛心聲》之后,成文賢成總的又一本詩集《夕陽金杯》問世了,對于這位讓人敬慕的文學圈兄長,除了從心里表達深深的祝福與祝愿之外,我不敢妄加評論,只能淺談一點心中的感受。
相信去過成總艷陽天辦公閣樓的文友,都會喜歡在他室外的藤椅上小憩片刻,更喜歡在室內慢飲幾杯加了陳皮的紅茶,聽他談詩與歌,談長桌上認真寫好的一幅幅對聯要為多少人送去祝福,談如何帶孫子在夜晚用天文望遠鏡望星星…
室內音樂徐徐、茶香裊裊,室外花兒綻放、竹葉婆娑,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淌,似乎很快,也似乎很慢。
有溫度的詩人,有胸懷的儒商,有思想的智者,歷經挫折卻依然淡定從容面對生活的勇者——
接觸越多,越不知道該如何對他去定義。俗話說,文如其人,成文賢的詩的確如此。
詩集中有許多以春天為題的詩,是詩人愛與溫暖的自然體現,也是其內心陽光的一個折射。
比如篇首的《靜等春天》,詩人慨嘆,多好的陽光啊/把風熬成了飛旋的綢緞/鳥兒在波浪上繡花,明亮的針尖一閃又一閃/我欣然接受了時間的飛逝…隨著野鴨一次次潛入湖底又浮出湖面/我忘卻冬天/靜等春天。看似輕松的幾句,卻不失四兩撥千斤的力道,風是最容易讓人想到凌厲與寒涼的意像,而詩人說“熬”成了飛旋的綢緞,這里有生活的磨礪,也有內心的柔軟,有面對生活屢遭波折寵辱不驚的堅韌,也有對春去冬來去留無意的坦然,更是一個人步入天命之年以后的超然。
我努力避開悲傷的部分/給每片落葉起一個蝴蝶名字(《多好的季節》)
太陽再次把人間從黑暗中撈出/陽光抹去苦澀悲傷的部分…/我像一條河流逆著光/走進春天。(《初春的早晨》)
在這里,語言很生動,“把人間從黑暗撈出”,“撈出”是拯救眾生的悲憫,“逆光”是直面人生的果敢。
在《倒春寒》里,詩人說,歷經滄桑的老人們料到了/因為春天里還隱藏著冬天。
這一句與雪萊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形成一種反差,后者是對生活的美好期望,前者是歷經滄桑洞穿人類生存真像后的淡然與沉靜。
同樣,在《冷》里,煙花一次次熄滅/十字街頭,老人守著菜攤/無人問津的她冰雕一般/白發像雪飄…如果說雪萊的“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是希望之問,那么詩人結尾的“不是說春天到了嗎/為何還這樣冷“是對現實里春天的憂心之問。
而在《躺在春風里》與《去愛》里,也存在這樣的反差。《躺在春風里》提到海子,“是不是把貼在臉上的天空當作海/是不是忽略了/溢過山坡的油菜花/他去了他向往的地方/我繼續對幸福心存僥幸/茍活人間”。比之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句,一種是帶著對生活美好期望跌落塵埃之后的絕望輕生;一種是對幸福心存僥幸的頑強茍活。一種是不堪世俗壓力的逃離,一種是洞明世事之后的無畏。無疑,成文賢的生活態度是積極的。正如泰戈爾說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在《去愛》里,“房間明亮的過程/像愛與被愛/這時總有一雙溫柔的的手會撫摸我/告訴我,因為愛你必須活著…做一粒米,或一根柴/去愛…”
這里,詩人的心就像給人溫暖與光明的陽光。比之于海子的“從明天起,喂馬劈柴”,詩人的“一粒米”或“一根柴“,是真實存在的人間煙火。
因為愛,所以愛。
現實里,當真正的愛,面臨選擇真實的痛苦和虛假的謊言時,估計說謊是更難的。魯迅《傷逝》里的涓生,因為選擇把真話說給子君,導致其抑郁而終,愧疚不已的涓生在子君去世后說到,“我不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給她我的說謊”。而詩人在《我不能說》里,面對一對新人的各種不能說,也是因為對子女真正的愛,奉獻了他的說謊。
在《時間跑得太快》里,詩人感慨時間飛逝,來不及愛。在《后中年時代》里,對于父母的愧疚,兒女的憂心,讓“中年的我/白發像野草一樣生長的我/以一滴淚為酒,舉起了夕陽的金杯”。這些都是詩人對家庭的責任與擔當,更是對愛與道義的堅守。
在《巴掌》中,“那只手停在空中/手下有孫子大牛/也有我”看似隨意平淡的表達,卻深刻體現了詩人對半生逝去親情的頓悟。巧妙之處在于,此處詩人對父親或者祖父并未提及片言只語,僅僅由一個舉起卻難以下落的巴掌,滋生出的對親人的追思,繼而流淚。
真正詩歌的語言,是深情的情感構筑,而不是假大空的造勢。詩人總是在質樸的語言中流露出炙熱的情感,在平實的敘說里閃現出思想的火花,這是語言的張力,也是成文賢慣有的文字表達魅力。
在詩人的眼里,萬物皆有生命,可以與其交流甚至換位。詩人的目光所及,通常是常人不大留意的細碎之物。比如在《我是一個對未來不抱希望的人》里,河床的石頭、枯木,路邊殘缺的蛋殼、輕飄飄的蛇蛻,都會觸及詩人柔軟的內心。
在《野草野花》里,看到園子里與牡丹月季共生的野草野花,不忍鏟除,“苦命人何必難為苦命人”,面對為了生存而努力生長的野草野花的包容與惺惺相惜,是成文賢人生經歷的必然反應,就像在《原諒》里,河流對冬天的原諒,歸燕對離家主人的原諒,種子被埋于黑暗的原諒…以及《接受》里,對諸多看不慣的人與物的接受與包容,是詩人佛家“無我”的胸襟,也是其道家“無為”的再現。
而現實中的成文賢,在近年實體舉步維艱的情況下,他的餐飲事業依然經營有序。疫情期間向弱者頻施援手,自發捐出大量救災物資,卻在暴雨突襲,艷陽天被困之際,沒有要政府一根鐵掀,帶領員工排洪重建,繼續打造新的艷陽天。這是他對挫折的淡定,對困難的柔韌,是洞察了現實卻依然積極向上的人生高度。
好的文字,通常會折射出時代的影子。詩人的高度不僅在于他心存陽光,對弱者的悲憫,對春天的留戀,還在于他對現實社會的焦慮以及對民生的憂患。在《深淵》里,聽見一個男人關于母親化療,孩子上學等生活的壓力的話語,以及《冷》里對于賣菜老婦人寒夜枯坐的無人問津,所萌發的悲憫之心;在《農民工》里,發現“曾經拿農具、瓦刀的粗糙的手/拿著幾張輕巧的撲克牌/在一場場數字游戲中/尋找出路”時所萌發的憂患意識。
除此,人到中年的感悟讓成文賢的詩又透出哲思的光芒。
《追月亮》里用對月亮不同年齡段的認知,孩童時天真追趕,少年時對未來的憧憬,青年時愛情的純真,中年后發現月亮如人生,有陰晴圓缺,這種對人生的體驗感是只有經過歲月洗禮的人才可以感知到的。
《道法自然》里,在教孫子畫畫時,“我努力變得簡單/怕我的經驗會畫地為牢”。這種不去抹殺孩子天性的教育是中國眾多家庭所不具備的,在這里,為大牛有這樣的爺爺感到慶幸。
《摩天輪》里,“巨大的輪子多個艙位/只有一個屬于你/每個人都從低處上位…/高處對每個人都是瞬間”
《用一片葉的一生告訴你》里,“秋風的刀,冬雪的箭/饒過誰/…登高的人,會忽略一片葉的墜落。”
漫不經意的簡單陳述,濾掉了太多的濃烈與激蕩,正如其人,漫步人間,嘗盡“人間百味”(其餐廳名),方能行至高處,心無旁騖。
另外,對于鄉土,《過年》是一種極簡的平鋪與記錄,但依然透出真誠與愛,應該說詩人是想用文字鐫刻生命的軌跡,挽留記憶里的年味與鄉情,留給孫子大牛和二牛或者后人心燈,薪火相傳,永不磨滅。
就像《必須有》、《無家可歸的麻雁》等,以及在第五輯《鑲嵌在畫框里的村莊》透露出對曾經心目中村莊的留戀與渴望。詩人的鄉情、親情以及對弱者的悲憫之心,也就是他的溫度,如《夕陽金杯》的封面——一輪緩緩下行的落日,把山川河流染成了溫暖的橘色。恰似一個人行走人間的軌跡,雖然避免不了落幕,卻依然要把余暉靜靜撒向人間。
總之,在成文賢的詩里,可以看見儒家之仁愛,佛家之無我(與萬物和解),道家之無為(順應自然)。《篤愛心聲》如此,《夕陽金杯》亦然。詩人在靜觀世間風物之榮枯的同時,旁觀自我,打造出了屬于自己的精神領域的“艷陽天”,修到了真正的貴族之氣。

作者簡介:
薛婭 寶雞詩人 寶雞市作協理事,寶雞職工作協副秘書長 。出版詩集《停止擺動的時鐘》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