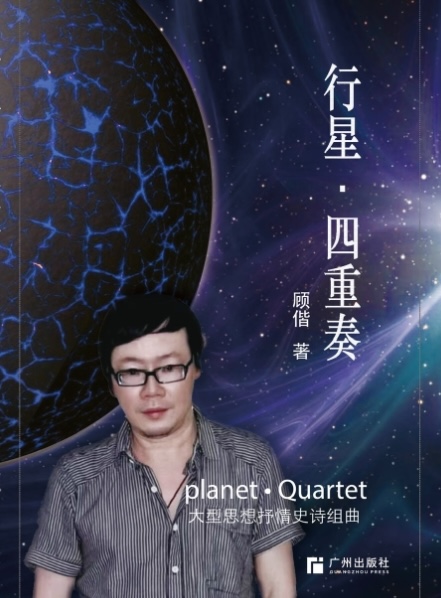
論一種終極美學(xué)的張力結(jié)構(gòu)
——顧偕《行星·四重奏》“消逝紀(jì)”譯作隨筆
林元躍
第二樂章竟然在“破碎”中打開的完整覺知與精神超越,正是第一樂章“一種邊界的轉(zhuǎn)譯不是終點”的殘缺處,召喚圓滿內(nèi)涵的“壯麗張力結(jié)構(gòu)”——引領(lǐng)我走向一個更為深邃、更具主體性精神的“完整”之境。可以說顧偕的意象思維兼具哲人的冷雋,他似乎一直就這么固執(zhí)地引領(lǐng)著人們?nèi)プ穼ふ胬怼U缡兰o(jì)之交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靈光乍現(xiàn)·西川訪談錄》關(guān)于“在場與真在”的主題時西川說的:詩是哲學(xué)的最高境界,詰問終極性對宇宙天地和人性的探索、生命意識的醒覺,以此自覺呈現(xiàn)作品重建詩歌精神的脈律。此話對應(yīng)顧偕的《行星·四重奏》,今天就像大地升起了一個天啟式的鮮活靈氣在翔動和飄浮。顧偕看得見“大地只是一個你存在的距離”,是光年每秒30萬公里飛行“常春藤在醉意中纏繞(出自廣州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行星·四重奏》下同),他的前瞻性,抑或是在穿越平行宇宙時作了哪些超越?他承上啟下地作出音樂的姿態(tài),并從“命運舞會”展開的“腳步在緩緩靠近喧囂的海洋/音樂不愿聽苦難的聲音/沒有一種歌唱再是嘗試”,這種著實超越了無數(shù)邊界的關(guān)聯(lián),就此使我想起上述訪談錄中西川說過的歌詩:“音樂可以表現(xiàn)尖銳沖突與命運激烈對抗,李斯特的輝煌燦爛的燃燒性扭曲”。這種詩壇一直少有觸碰的主題,無論規(guī)模還是內(nèi)容,是否確已構(gòu)成了世界級詩人越性文本寫法的那類格局?亦即既用全球化的人類經(jīng)歷,體驗各不相同的瘋狂與苦難的崩潰,更為當(dāng)代情緒的現(xiàn)實創(chuàng)作,強烈注入了尤為深邃而通透的詩性思想,如“在虛無中發(fā)掘重鑄與超越”,無疑這便是該部史詩全篇的哲學(xué)基石和總綱。它描述了一種積極的創(chuàng)世行為——不是從豐饒中獲取,而是直面“虛無”這一終極背景,并從中“發(fā)掘”意義,“重鑄”形式,最終實現(xiàn)精神的“超越”。如此像是亦更呼應(yīng)了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存在主義思想,驗證了道家“無中生有”的智慧。
也許最宏闊的宇宙美學(xué)詩篇,往往不是給出答案,而是巧妙地劃出可知的邊界,并指向那更深邃的不可知領(lǐng)域。它保留一種神秘余韻,讓敬畏感由此得以續(xù)存在預(yù)言層面。
顧偕為什么會提出“一種終極美學(xué)的張力結(jié)構(gòu)”這個命題?因為在其“思想抒情史詩組曲”第一樂章《我在太陽系》中,解構(gòu)和重構(gòu)存在與虛無,一開始便是個極具深度和魅力的主題。它融合了宇宙學(xué)、量子力學(xué)、詩學(xué)、哲學(xué)與美學(xué);它探討的是一種在極致宏大與無限精微之間產(chǎn)生的、令人戰(zhàn)栗又心醉神迷的那種超凡審美體驗。這種體驗的核心,現(xiàn)在于《消逝紀(jì)》得到了深化,且由多重對立統(tǒng)一要素,構(gòu)成了一個充滿動感的“張力結(jié)構(gòu)”。譬如這些詩句:“生長無非都是熱愛中的匆匆過客/波濤和山峰最懂摧毀的意義”。意象的悖論與恐怖轉(zhuǎn)化的壯美,將終結(jié)與起點的宇宙運行根本法則,形成了敬畏的源頭感官與通感,并將神圣的超越體驗推向了極限,用意象、節(jié)奏和哲學(xué)思辨構(gòu)建起了一座語言的圣殿。在“消逝紀(jì)”這章樂曲里,自然的終結(jié)不過是永恒之書翻卷時抖落的塵埃,無非都是熱愛中的匆匆過客,生長與星河共舞的瞬息現(xiàn)象,惟有身心震顫的“共鳴”,努力在用蔚藍的碎裂雕塑著新的海岸,在創(chuàng)造與泯滅的呼吸間,傳授著太古的箴言!當(dāng)群星如鐘錘,撞擊時間的薄暮靈魂墜入對光明的敬畏,黑洞萬物初生的火焰,坍縮為一粒星塵在引力的詠嘆調(diào)里,浩瀚地再也無法點燃生命的血液,就此所有逆行的光束,照亮了詩人極端認(rèn)知的尺度,同時亦以對比的節(jié)奏,在一切行將“消逝”空間,營造出了從“仰望”到“融入”的另一種更富視角轉(zhuǎn)變的主體與客體不再對立的終極美學(xué)。
“宇宙”與“詩”的張力,秩序與自由的協(xié)奏,物理的、數(shù)學(xué)的引力方程絕對的客觀性和極致的主觀性,這三者潛在廢墟的“破碎與疏離”,仿佛在所有斷裂處,均能續(xù)寫無窮敘事,召喚想象、情感、哲思,并將人生的“碎片”重組為更具深度和韌性的“完整”。終極美學(xué)張力的核心關(guān)聯(lián)指涉,實際就是“虛實相生”與“殘缺即圓滿、破碎即渾全”的建設(shè)性想象的意蘊。這個機制強烈暗示了形態(tài)曾經(jīng)的繁華與當(dāng)下的衰敗,巨大的時空張力,還會迫使人思考世界興衰、諸如存在與虛無、永恒與瞬間等終極命題。“永恒圓滿”幻象的打破,“廢墟遲早是每個人的故鄉(xiāng)”,等等精神迸發(fā)出的最具極致的熱愛與勇氣,它使詩人敘寫了一個靈魂終極與永恒達觀問題的完整性哲學(xué)循環(huán):“我們一生都在學(xué)習(xí)逝者的東西/消失一直在回味歷史”。既然點明了歷史的傳承性與生命的延續(xù)性,在虛無中發(fā)掘與重鑄,在“靈魂歸宿與終極永恒”中展現(xiàn)全詩的核心矛盾,就此便不難揭示出人類精神的兩個永恒面向。一個不斷追求超越與未來(靈魂散步),一個執(zhí)著于回歸與出發(fā),著力營造文化美學(xué)“虛實相生”與“殘缺即圓滿”的意境。
讓我產(chǎn)生玄想的張力結(jié)構(gòu)是否就是律動輪回?如同宇宙本身不斷膨脹與律動的過程,其實便是宇宙處于守恒狀態(tài)的一個獨立空間,無論輝煌還是幻滅,物質(zhì)總量不變,但是空間還是明顯變小了,甚至形成奇點的時候,空間可以說是進入到了無窮小。既然宇宙是一個獨立空間,能量守恒的質(zhì)量與空間可以彼此進行轉(zhuǎn)化,那么在虛無中重建神圣,穿越廢墟,“存在很長時間會突然永不再見。”誠如顧偕早在1998年出版的英漢雙語詩集《太極》“神在檢閱人類的精神”時寫的“今夜是永生的開始……所有報廢的時光/已被進步的代價修復(fù)”,當(dāng)這種本源性言說進入“自然終結(jié)”狀態(tài),意味著語言符號系統(tǒng)客觀真理主觀內(nèi)化的悲壯,可能真的就能憑借輝煌的張力,完成理性與感性的極致。在幾種力量被撕扯的瞬間,湮滅性與疏離感生成出的神圣與敬畏,以及由創(chuàng)造與消逝的不斷拓展的張力,所指向的更為深邃的不可知領(lǐng)域,恰好以宏大法則抽象與具象的兩極貫通,擁有了一種終極的深度:“一一場膨脹之旅后,其實/我已同星河交匯/時空再怎么翻滾,從此我已/不在乎任何永無盡頭的起始”。更高層次動態(tài)的平衡戰(zhàn)栗,永遠(yuǎn)是寧靜”或“狂喜的安詳”的,它直白地揭示了世界的無常性、有限性、以及解脫性。而思考和追求形而上的“無限”與“本質(zhì)”,自是關(guān)乎到宇宙的動態(tài)平衡,亦是一種直覺體驗與理性追求作品的終點。它幾乎能使所有人仰望星空時,不再有那種突如其來的戰(zhàn)栗,由于認(rèn)知路徑上最為深刻的張力展開的神圣景象,世界的循環(huán)消逝,尤讓我們深感當(dāng)下的彌足珍貴。
于此我再作一個驚奇地比較:在這之后顧偕刊載于《歐洲詩人》雜志2025年域外頭條的《不朽者你叫什么名》:“你已開始成了我/ 前所未聞的必尋之物/成了我?關(guān)重要需要理解的寧靜/你廢棄了時間和所有??的敵意……關(guān)于腐朽的破解/鉆?的?臟可能都是由真理換來的”。這首詩所表達的對人類命運終極關(guān)懷所追尋的另一種眼光,更是在宏大的視角下,仿佛讓我們能于一種循環(huán)的引力逆轉(zhuǎn)中凝視星空,反觀自身存在的奧秘,一如《我在太陽系》所述:“事物的終點全將由認(rèn)識拆開”的情景,宇宙不是戛然而止的句號,而更像一座富礦、一首由無數(shù)循環(huán)樂章組成的交響詩,那里甚至有可能還安放著有無數(shù)靈魂充盈的生命境界。
因此,在精神上“完整”地對生命本質(zhì)的洞見,在“消逝”斷裂處續(xù)寫無窮敘事的重構(gòu),并在特定時空超越性地承載所有人的理想,使之作品內(nèi)涵得以無限地延伸,或許這便是“道”的運行與“永恒回歸”的法則,體現(xiàn)在“梵我如一”上的真理。從被動接受轉(zhuǎn)為主動建構(gòu),用毀滅張力甚至包括可知與不可知的張力,即不斷拓展理解的邊界指向那更深邃的不可知領(lǐng)域,也許這就是悲壯的輝煌,共鳴在生命質(zhì)感中的升華。靈魂穿透現(xiàn)象的迷霧,情感于一種深度上感懷,應(yīng)當(dāng)這也是對存在本質(zhì)莫大的一種領(lǐng)悟。
所謂神圣而崇高的主體性超越,頓悟崇高美這一瞬間的照亮,它無疑混合了敬畏、狂喜與平靜,是有限個體觸及無限時的心靈震顫,是康德所言“數(shù)量的崇高”與“力量的崇高”在精神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人類如少女”,“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靜默的來臨,宇宙已說完了它所能說的一切。生命必然短暫,困境亦始終充滿了突破。這是“在場”(Anwesen) 在現(xiàn)象學(xué)中,通常所指事物通過意識直接呈現(xiàn)自身的狀態(tài)。突破新的在場方式誕生,不是通過“說”而在場,而是在“不說”中更純粹地顯現(xiàn)夜空中的星群。它們的在場不依賴任何描述,它們在其靜默的閃爍中自明宇宙規(guī)律,哪怕是不斷地“消逝”。海德格爾那里的本真存在臨界體驗是:“生長無非都是熱愛中的匆匆過客”。所以守護“無言之真”,即從言說到傾聽存在無聲的言說,更當(dāng)成為詩人存在思想顯現(xiàn)的通道。里爾克說過:“我們只是在經(jīng)過萬物,如一陣空氣的交換/一旦離去,我們便成了那無垠。”
“彩虹沒有伸出最終的精美/無限之路,其實/就在過去的岸邊”。這些詩句重建了詩歌精神,表達了瞬間與永恒、親密與疏離、生長與消亡,可以用存在主義哲學(xué)解讀,但需避免術(shù)語堆砌,需要聚焦在詩歌本身的情感張力上。時間是個沒有血統(tǒng)延續(xù)的幻覺,“一千年的事情都可在舞池發(fā)生/如今湛藍的潮水/全是你無法想象的美酒/音樂不愿聽苦難的聲音”。最終,人類都將在宇宙的交響曲中,找到自身位置后與自然重新渾融一體。“人類命運其實是個滑稽的影子”,重建深度體驗,保持本體開放,可以在“光明的界限其實都是/一些世紀(jì)荊棘/波瀾總在孕育陰影”,但絕不可讓任何既定概念封閉在奧秘淺薄表達的盛行處,詩歌守護當(dāng)有不可言說之物的重量。
我之所以樂于沉浸式的解讀《行星·四重奏》,就因為一種終極美學(xué)的張力,它不斷延展的結(jié)構(gòu)如同樂章,已用一種廣闊視角創(chuàng)意性的啟迪,豐富了我在翻譯這部作品過程中的理論突圍或建設(shè)!并將保持詩論“在場”(Anwesen)與“真在”(Eigentliche Existenz)的原則,定然將會開拓出更多文化本質(zhì)創(chuàng)新的路徑。“消逝紀(jì)”以"哲學(xué)循環(huán)"為隱性結(jié)構(gòu),將生命歷程重構(gòu)了作為宇宙能量的暫時聚集與釋放過程,這是一種生命歷程在時空扭曲中,感知碎片化存在的現(xiàn)代性焦慮的"存在危機"。當(dāng)個體意識放棄對"自我"邊界的執(zhí)著時,有限的生命感知惟有融入無限的宇宙意識,所有現(xiàn)實或許就機會,展望到那些不光只有詩中才有的永恒循環(huán)的超越性意義。
2025.10.31于四川自貢

作者簡介:林元躍,筆名嶺南,四川輕化工大學(xué)主任編輯,文化學(xué)者,詩人。著有詩集《意象神雕》、《大學(xué)精神的培育創(chuàng)新》,多篇小說、音樂、文旅、茶文化等詩文作品獲獎,并獲首屆1573金沙詩文二等獎、上海“傅雷杯”全國文藝評論獎、深圳大灣區(qū)詩歌獎、四川疫情防控詩歌一等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