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秦皇島海子詩歌藝術節的發言
文/洪燭
海子和海的關系,不亞于海子和詩的關系。
海子196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查灣村,據說因命中缺水,而被父母起名為“查海生”。也不知這種所謂的命運是否可信,更不知這種一廂情愿的補償是否有效?不管怎么說,這個孩子自生命的起點就和海發生了關系,哪怕他面對的只是一個虛擬的海:名字里的海。直到他長大學會了寫詩,果斷地把名字給改了,為自己另起了一個叫“海子”的筆名。雖然連原初的姓氏都抹掉了,但“海”這個字卻保留了下來。他似乎認可了個人的天命,依然維持著和海的關系。并不僅僅是為了避免辜負父母的一片苦心。海,仿佛比他的父姓更為重要,更不可或缺。海,仿佛成了他后天性的父姓,一直繼承到生命的終點,乃至永遠。他又似乎并沒有另起爐灶地改名,更像是換了個說法:海子,海的孩子,海的兒子,原本就包含著“海生”的意思。
當然,在蒙古語里,海子又指湖泊,湖泊等于小海,譬如中南海、什剎海之類都是這么叫起來的。海子一定是來到那座擁有中南海、什剎海的北方名城之后,才學會寫詩的,才更換了一個詩意的名字。為自己命名,既是對命運的認識與刷新,而且同樣需要從頭再來的勇氣乃至不可一世的靈感。他怎么預感到自己將以新名字而流芳百世?哪怕這種“千秋萬歲名”,注定只能是“寂寞身后事”,未能突破杜甫形容李白而總結的那種“天才詩人生死榮辱的周期律”。但不幸的海子已經足夠幸運了,在身后幾年、幾十年就大名鼎鼎,無需再等若干個朝代。海子的不朽,現在已基本可以肯定了。作為詩人,他簡直比李白成名還要快、還要早。他永遠都是二十五歲,永遠都是二十五歲的名人。即使把死后的年齡加進去,他到今天也才五十歲,剛剛知天命。海子要么早就未卜先知天命,要么就永遠不可能知天命。可這天命卻讓與他同時代的世人清清楚楚看見了,視為奇跡。
是海給了他這種好運氣,還是命運給了他這種好運氣?是意味深遠的名字在暗自幫助他成名,還是他以詩成名無形中使自己的名字篷壁生輝?不僅海子的原名與筆名都和海息息相關,他的成名作同時又是代表作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更是他獻給海的禮物,或者說是海回報給他的一份厚禮。我相信海子從海那里借得了神力,這首在短短時間內就不脛而走的詩,才可能像海潮那樣由遠而近以加速度撞開無數讀者的心扉。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表面上是對大海的贊美詩,其實隱藏著某種不為人知、不便與常人道的犧牲精神:詩人對世俗的幸福可望而不可及,留下對別人的祝愿,轉身將自己獻祭于大海。此詩寫于1989年1月13日,海子在冬天盼望著春天,在城市里眺望著大海,身不由已,情不自禁。海對于掙扎在紅塵中的詩人,不僅代表遠方,還象征著來世。他渴望完成空間與時間的雙重超越。
沒隔多久,海子果然這么做了。同年3月26日,他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搭車前往秦皇島,是私奔,又是踐約。那是和春天的約定,又是和大海的幽會。同時,還是對自己的一份交代。他在秦皇島市海港區東港鎮龍家營村臥軌自殺。這里離山海關不遠。大海近在咫尺。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成了擋住25歲的海子去路的鬼門關。
海究竟對海子意味著什么?母親?故鄉?童年?詩人的烏托邦?藍色的理想國?也許兼而有之。也許還遠遠超過這一切的總和。他投奔大海,作為一生的最后旅途,也就等于回到了起點。父母給起的名字海生,以及自己給起的筆名海子,對他的創作有影響,對他的生死抉擇也不是沒有一點心理暗示。
海子為什么選擇秦皇島作為人生的終點站?道理好像很簡單:這里有一片離他蝸居的北京城最近的海。為盡快地投奔海、回歸海,他走了一條捷徑:縮短了必經的苦難,也省略了可能的幸福。但若往深底里追究,還在于海子對這片海最有感情。海子曾和在中國政法大學相識的初戀女友,于某個周末,即興去過北戴河,享受了一小段美好的時光。我不知那是否算海子第一次和大海的約會?但這個跟他結伴去看海的女孩,絕對是他臨死前一個月追憶愛情履歷的《四姐妹》里的第一位。后來由于對方的高知父母嫌棄海子出身貧寒,投了否決票,這段戀情半途而廢。海子卻不能自拔。1986年以后海子多次一個人重返北戴河,憑吊初戀的遺址。雖然愛情的沙塔早已淪陷為一片廢墟。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就是在這種沒有回應的祝福和強作歡顏的痛苦中誕生的吧?1989年真的春暖花開時,海子最后一次去看海,卻再也找不到回頭路。他被海留下了。正如海也在他的名字、他的詩篇、他的命運里永遠地留下了。海子海子,海的孩子,愛的赤子。他為別人的幸福而夜以繼日地祈禱,卻忘了祝福一下自己。他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卻接受了命運對自己的無情,獨自擁抱著一片苦海。正如他那首《眺望北方》的結尾所述:“我的七月纏繞著我,像那條愛我的孤單的蛇——它將在痛楚苦澀的海水里度過一生。”這是海子對自己的預言,也將由自己來實現。
海子命中真的缺水嗎?不,他缺的是愛。缺愛比缺水更使他倍受煎熬。
海子真的因為命中注定的干渴而對海情有獨鐘嗎?他恐怕想不到:海水是咸的、是苦的,不僅沒法解渴,還會使人加倍地焦渴。
好在詩人總是有辦法的:用大海的千頃苦水,釀出了心里的一滴蜜。也許無濟于生前事,卻有助于身后名。讀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樣的深情詩篇,世人哪里猜測得到:甜美可口的語言,居然是詩人滿肚子的苦水醞釀而成。不,他的人,他的詩,更像是天成。他的人生和他的詩篇,渾然天成。
海是苦的,卻不是無情的。以另一種方式回報了詩人的多情,安慰著詩人的苦心。沒有按其所愿施舍給他幸福的瞬間,卻賦予他永恒的光明。
(選自洪燭新浪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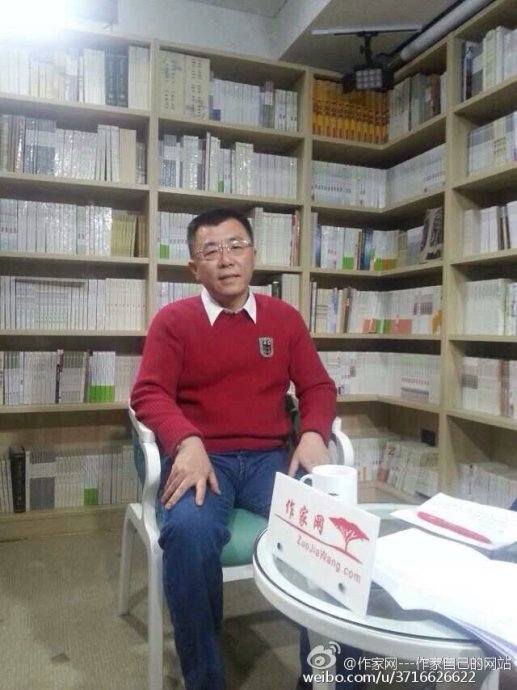 洪燭
洪燭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