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鴻憶童慶炳:他嚴肅的學者風度令我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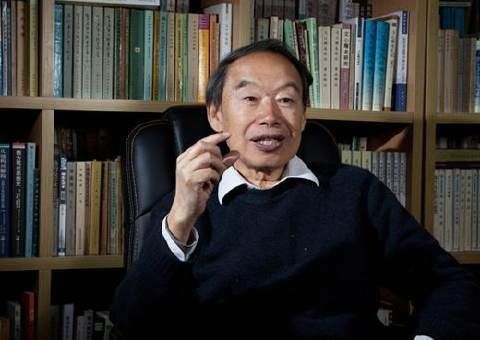
編者按:2015年6月14日,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文藝理論領軍人物童慶炳先生辭世,享年79歲。1987年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聯合開辦創作研究生班,童慶炳擔任該班級輔導員,并有授課,莫言、余華、嚴歌苓、遲子建、畢淑敏、劉震云等均為他的學生。
作家、文學學者梁鴻作為曾經的北師大博士,也旁聽過童慶炳的課程,她在朋友圈中表達對先生的哀悼時回憶了往事:“當年博士時同屋好友是童老師學生,跟著她們一起聽童老師講《文心雕龍》,去那個紅色小樓聽師母講《圣經》,一起祈禱,至今還記得小樓內的樸素和安靜。”鳳凰網文化也就此聯系了梁鴻,請她講了一些當年的情景:
鳳凰網文化:您本身就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看到您的朋友圈說您正好學生時代就聽過他的課。
梁鴻:對。
鳳凰網文化:能不能講一講,當時聽他課的一些故事,比如說他講課的風度、與學生的交流。
梁鴻:我是當年聽他講的《文心雕龍》,實際上他講話比較帶有點南方這種溫軟的口氣,非常文雅,說話也慢慢的,但是非常嚴謹。因為我的同屋是他的博士,寫論文包括平時看書要求非常嚴格,要求他們看多少書,做多少讀書筆記,包括最后的博士論文,我同屋的女孩子還為寫博士論文哭了好幾次。但是我覺得他確實是一個嚴謹的學者,對人當然也很好,他對學生非常好,比如說首先學養要求是比較嚴的,在生活上也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逢年過節吃飯什么。我跟著去過一兩次,但是大部分還是他們自己去,我是到過他的家里面,師母可能是信基督教,跟他們一塊聽過《圣經》。
鳳凰網文化:童先生等于是在您的學生時代就認識了您?
梁鴻:實際上,我跟他一直不熟,也不是不熟,我一直沒有跟他達到一種特別熟悉的關系。
鳳凰網文化:到后來您也做文學研究和教學,也常回北師那邊有一些學術的會議或者討論,應該和童先生打交道還比較多吧?
梁鴻:我了解的他比較嚴肅,我在他面前其實比較敬畏,我跟他一直是較少私人的接觸,比如聊天什么的,我沒有達到那樣一種程度。但是也因為一些開會,我大部分還聽他在講,能感覺到作為一個學者的風度,但私人關系基本上沒有。
鳳凰網文化:現在大學中文系用的文學理論、文藝學方面的教材,應該說百分之八十都是童先生編寫的,當然這個數字不太準確。
梁鴻:大部分。
鳳凰網文化:事實上,現在中國的文藝學方面,應該說是以童先生為首的,可以這么說吧?
梁鴻:或者說他是奠基人,有可能其他學校也有其它的版本,包括他的弟子也在編一個版本。
鳳凰網文化:但是目前還沒有這種影響力的。
梁鴻:對。
鳳凰網文化:我想問,一個是您會怎么從專業角度評價在文藝學這個領域里,童先生的貢獻?還有一個問題,其實文藝學這樣一個學科的建立,是當年從蘇聯的那個文藝學照搬過來的,很長一個時期,其實文藝學的教學內容實際上簡而言之就是告訴學生們文藝是如何要反映比如說階級斗爭、如何要為政治服務的……
梁鴻:對。
鳳凰網文化:所以我不知道文藝學在童先生的那里,得到了哪些改變或者說改善?
梁鴻:這個其實不好談,因為實際上童先生在文藝學界也是有爭議的,不過我不是文藝學的專業人員,所以我來談并不合適。
但是我是覺得不管現在的文藝美學、文藝理論怎么樣發展,我覺得童先生確實奠定了當年以來的一個文藝理論的基礎,即使后來對他的觀點有一些不同看法,也是基于他的一些觀點的建構來的。就像當年的魯迅研究一樣,王培元、錢理群他們奠定了一個基礎,以后包括汪暉他們的研究,不管你是反對他還是同意他,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嶄新的開端,一個人文思想的開端,我覺得還是這個價值還是在的。
來源:鳳凰網文化
作者:徐鵬遠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