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爾芬:水隨天去秋無際
——悼童慶炳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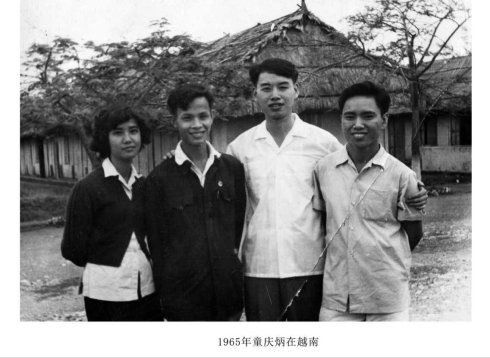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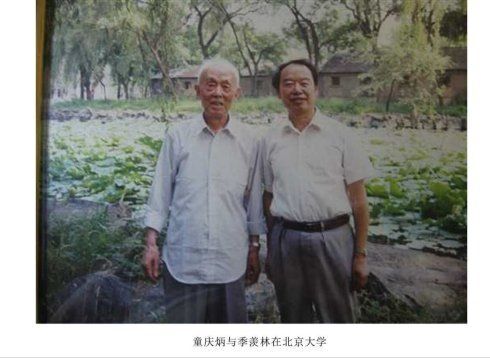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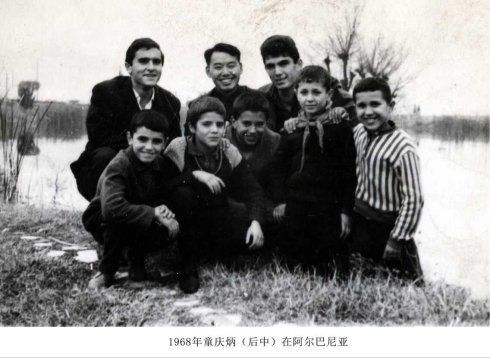
驚悉童慶炳老師仙逝,手頭的工作雖然著急,卻做不下去了,頭腦中盡是童老師的音容笑貌。
第一次見到童慶炳老師大概是1980年代的尾巴,他回老家連城探親,黃征輝請他來縣文化館講座。印象中童老師穿著樸素、話語平緩,不矯揉,不造作,說的都是些平白大實話。末了,黃征輝領大家去吃夜宵,我于是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童老師,趕緊表達自己的仰慕。童老師卻說:“我其實沒什么,只是教書認真。”
1992年我在魯迅文學院進修,童老師上我們的創作美學。他的課講得平實,不比有的老師手舞足蹈演大于講,曠課的同學漸漸多了起來。一天,童老師生氣了,放出重話:“我每次來上你們的課,都要換上干凈的襯衣,你們卻愛來不來。”不知為什么,童老師板起臉說的這句話,鎮住了那些自視有才狂妄無狀的同學,后來的出勤率就高多了。
有一天,我提出要登門拜訪,童老師很高興,說:“來呀,來吃個飯。”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就走出魯院的大門,到十里堡坐車轉地鐵,出了地鐵再轉車到北師大,進了北師大走到童老師家,已經是11點半。坐一會兒,聊幾句寫作的事,童老師送我幾本新書,就吃飯。吃過午飯,我馬不停蹄往回趕,進了魯院的大門,天就暗了。這一頓飯下來,我才體會到童老師來魯院上一次課多不容易。自此,我再也沒有逃過課。
魯院的孫津老師是童老師的博士研究生,有一天,孫津請童老師吃飯,還有莫言,童老師說我是連城老鄉,也拉上了。就在魯院的食堂吃,吃食堂的菜,好象有加了一條魚。吃家常菜,說家常話,無論是童老師還是莫言,都沒有什么微言大義。
魯院的課程結束,已是學生放假的年底。魯院不是正規的院校,不能集體訂票,只能自己解決。頭天跟兩個福建同學去火車站買票,見隊伍排了幾里地長,頭皮都麻了,逮住排前面的一人問:“你幾點來的呀?”他說7點。我說:“不對呀,我們也是7點,怎么排到幾里地去了?”他說:“我是昨晚7點。”這下我們傻眼了,站在寒風中凌亂。
整理好思緒,我們決定玩到天黑,從晚上開始排隊。我們三個福建老鄉吃飽了面條,撿了一個裝電視機的大紙箱,三個人一起裝進去,在售票廳門口等候天亮。售票廳8點準備開門的時候,黑壓壓的人群已經層層推涌過來,把卷簾門搡得嘩嘩巨響,似乎就要倒塌。門一開,我們不沖刺進去都不行,因為只要慢一點就會被后面的人踩踏。迅速的,每個售票窗口都排起長隊,是那種前胸貼后背的、重重疊疊人肉長龍。但是,后面進來的人不甘心落伍,他們使勁撞擊人肉長龍,試圖為自己嵌進一個位置。爭吵、撕扯、肉搏,場面大亂。這時一群保安沖進來,揮舞電棍大喊:“蹲下,抱頭蹲下。”我們都抱頭側身蹲下,犯人那樣看自己的褲襠。晉江來的同學立馬就哭了,對我說:“我受不了啦,我要坐飛機。”
他哭著走了,準備去買飛機票。我是斷乎坐不起飛機的,只能抱頭蹲著排隊。好不容易輪到我跟售票員說話了,我只說“廈門”二字,還沒說哪一天,她就不耐煩地揮手說:“沒票了,廈門的票都賣完了。”
我被后面的人推開,走出售票廳,來到火車站廣場,抬頭看北京灰蒙蒙的天空,心想,這個壓抑的鬼地方真是達官貴人的天堂,貧下中農的地獄。現在怎么辦?難不成在北京過年?問題是這個狗仗人勢的首善之區有地方讓我過年嗎?我想到了童慶炳老師,于是找到公用電話,給童老師掛通了。童老師一聽,教導我說:“你這孩子怎么這么傻呢?去上海、廣州、廈門的火車是最擠的,哪來的票呀?你要買去南昌的,從南昌轉廈門就容易了。”
這下心里有數了,但我不想排隊自取其辱,干脆在廣場上轉悠。果然有黃牛黨過來問要不要去南昌的票?我跟另一個福建同學研究半天,橫豎沒看出真假,決定賭一把,就買下兩張到南昌的票。到南昌后,正如童老師所言,南昌到廈門的票好買得很。
后來,我一直很關注童老師的學術動態,每次見到吳子林,童老師都是我們的重大話題。此間,童老師曾上CCTV—10《百家講壇》,我盡量守著看。看了幾期,我就知道童老師不可能像易中天、于丹那樣大紅大紫。不是因為童老師偶爾會冒出連城地瓜話,而是他講得太實、太干,他總是想給觀眾更多的干貨、更豐富的信息,殊不知,《百家講壇》要的是演講,首先是表演,然后才是講課。演講,是童老師這個客家籍憨厚教授不能勝任的。
近幾年,因為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童老師的名氣忽然大了起來,大家都知道莫言是童老師的碩士研究生。連城一中校慶,莫言題了詞,其實也是托了童老師的關系。事實上,童老師還有另一個博士研究生也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只是這樣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不讓說。不讓說就不說唄,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最后一次見童老師是前兩年在培田,童老師謙卑地站在路邊,身邊陪著弟子吳子林。那已然是個耆耄老人,他就是我敦厚有加、著作等身的童老師嗎?童老師告訴我,他的身體出了問題,每況愈下。我說幾句客套話,心里一陣酸楚。
我讀童老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回憶母校連城一中。那篇文章的語言極為實誠,談不上什么文采,是一個老人對記憶的絮叨。看完了我心里很難過,因為它太像最后的話,充滿溫情與留戀,甚至有一種訣別暗含其中。一個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學者,沒有走到生命的邊界,是斷然不會寫那種情調的文章的。
有人說童老師的思想保守有余而新銳不足,理論闡述有余而開拓不夠。要我說,也許童老師的理論不一定是最前沿的,但一定是最扎實的;上課不一定是最生動的,但對學生一定是最真誠的。我們向童老師學的,不是新名詞、新概念、新手法,是為文的品格與為人的品德。
如今,斯人已去,然文品必百世流芳,人品將永垂不朽。
作者:吳爾芬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