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從2015年期刊寫作看當下文學現場之流
文/郭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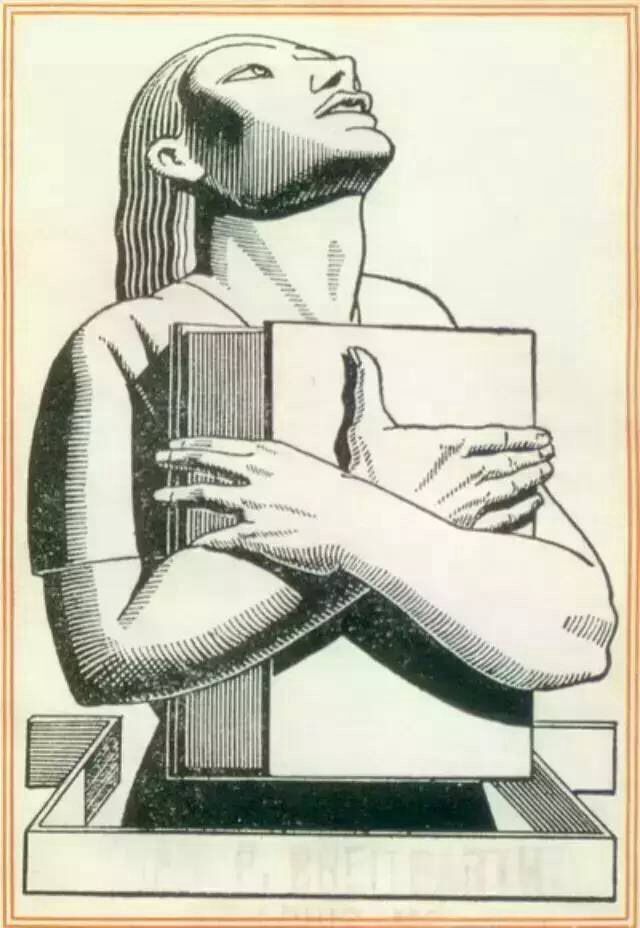
乙未冬,時而碧空如洗暖陽普照,時而霧霾惶惶,陰冷暗殤。此時靜坐書齋,心中已然沒有了“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的清新靜雅,但卻因寫作自身生發出些許“霾里依然唐詩宋詞,霧中細讀方塊漢字”的落拓不羈。心中頗不寧靜,又只能在霾中淡然處之。是為記。
當下中國社會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近三十年市場經濟深度介入個體人的日常和精神生活,這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生存、情感和思維方式。日常生活的溫飽和精神生態的平庸乏力并存,物質欲望的勃興和生存壓力互為表里,經濟繁榮帶來個體與民族自信力的增強,同時個體與當下、歷史與未來的不確定性關系乃至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流行思潮。人之為人,對于當下的中國人來說,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物質主義與精神生活,更加糾纏在對于鄉土社會、現代社會和各類新媒體信息茫然與辨識的混沌之中。與此同時,深度植入日常生活經驗三十年的中國文學也在修生養息的平靜中呈現出了新的特質。
“時代新人”與常態社會的現代人格建構
“人的文學”和“人道主義”分別是上個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中國文學提出的重要問題。而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個體大多解決溫飽之后,“人”的主體性才有了一個較為穩固的現實基礎。在生活欲求獲得基本滿足條件下,現代中國人終于可以在非戰爭、非饑荒、非政治斗爭的社會語境中開始“現代人”的選擇,這也是現實生活對于中國文學提出的新命題。(傳統中國社會有著一套完整的修齊治平的人生路徑,個體人在消融于群體的行為方式中,最終以獲得道統認同為最高的價值訴求。近現代社會中,人在饑餓、戰爭和自然災害等命運遭際面前的選擇是逼仄而極端的,這類選擇有著對于人本質最為直接的拷問,人更多和群體、國家互為表里,個人命運的選擇關乎家國大義,更多是在外辱、內亂、戰爭和政治斗爭中的掙扎和呼喊。)然而,作為一個僅僅解決了自身溫飽又面臨著物質主義和資本全球化語境的中國人,該如何處理自我、他者、世界的關系,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當下和未來?
新寫實以來近二十年的當代文學,更多在個體庸常經驗的生活層面回應市場經濟時代物質和欲望表達,作為被拋入歷史中的人和人的生活來說,先天設定這種生活狀態的合理性,通過削平深度、消解崇高來解構曾經異常強大的詩道傳統和政治意識形態對于文學的干預。近二十年,當代文學日漸趨向文學寫作自身的獨立性,同時也不自覺地遠離“人的文學”及其人文傳統。因此,在這二十年中,文學多是“時代庸人”的一地雞毛,時代庸人成為文學所建構的“中國人”自畫像,群體性的功利主義和矮化人格竟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共識。隨著常態現代社會的日漸形成,更多中國作家開始反思“時代庸人”與個體人格、時代精神之間的關系。面對這樣的時代,現代個體該有著怎樣獨立和自主的選擇和判斷?如何在新的社會政治文化情境中建構“時代新人”?本年度幾位“時代新人”體現了中國作家對于中國人現代人格精神的文學想象,同時也表達了中國作家對于“人的文學”和“人道主義”等重要文學命題的重新思考和現實回應。
阿來筆下的少年桑吉(《三只蟲草》)面對現代文明、自然和宗教的選擇,無疑昭示著當代重要作家對于現代文明的深入思考。藏族少年桑吉的經驗是藏區的地域的民族的,而作者通過這個時代新人闡釋了一個大的轉型時代中國個體所面臨的普遍困境——物質主義來勢洶洶又和實際生存境遇切實相關,宗教靈性和現代智識文明還遠未相輔相成,個體該如何選擇自己踏實可行的未來?又給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啟蒙與心靈的安適?這種困境溢出了城市或鄉土經驗對于個體人的限定,在一個更為遼闊的層面為時代構建一個靈肉皆備清新剛健的少年新人。阿來表達了信息時代科學依然為人類孜孜以求,同時又剝離了科技理性的權威性,穿透時代的浮華進入到對于“人”的宗教、文化更深層次的內省。在物質奴役“人”的時代,我們還有機會選擇嗎?石一楓則塑造了現實生活的傳奇人物安小南(《地球之眼》)。安小南在日常層面是平淡無奇的,甚至于是一個非成功人士。而作為一個現代個體,他無疑抵達了無數當下庸眾無法企及的人生高度——有所選擇的生活,從而獲得一個平凡現代人活著的尊嚴。安小南的選擇是難的,當時代庸人們以俗世的眼光和機巧茍活于城市麻木生存的時候,安小南就是那個試圖從沉淪肉身和墜落靈魂中超拔的西西福斯。荊永鳴《較量》中,主人公鐘志林終于從灰色小知識分子的命運悲劇敘事轉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世俗權力生存網絡的較量。這個人物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是否贏得了這種較量,而是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以個人良知和道德開始反省犬儒生存和鄉愿冬烘。在沒有高韜理想主義、政治信念乃至宗教信仰的支撐下,人何以為善,何以判斷善與惡?如何自律和寬容?現代人文主義和理想啟蒙是否依然有效?鐘志林堅守知識分子職業責任感,具有現代道德情感認知,甚至于有著較為清晰的人生底線和原則,由此小說的敘述視點有別于無價值判斷或者說混亂價值認同,而是在有傾向性的價值判斷中敘述了一個和現實邏輯抗爭的當下中國現代智識分子形象。這一現代智識形象在當代文學中的確屬于稀缺物種。
“好好活著”與人道主義內涵的延展
本年度的文學文本以“慈悲”呈現出對于人和歷史內在和解性的解讀。如果說上個世紀以來的傷痕、反思文學是控訴活著的苦難和不公,那么同樣的題材,當下的敘事則從對于苦難和不公的摹寫轉入對于生存自身的悲憫和寬容——“好好活著”成為人道主義新的內涵和意蘊。近三十年當代文學從《一地雞毛》小林平庸活著的無意義,到敘寫日常生活的大面積瑣屑和碎片化生存,到摹寫人們從蠅營狗茍的現實物質欲望中驚醒而反思,這種反思不僅僅是對于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生活的反思,而更多是置身于歷史和當下的個體試圖通過自身的堅韌努力,保持現代個體有尊嚴的生活。中國人歷來重視世俗生活,儒家也親近世俗而具有超越性。活著是世俗生活最基本的欲求,而如何作為個體有尊嚴的活著則是一個關乎人道主義的命題。中國現當代文學對于灰色小人物的敘事,作家更多是以同情的筆調敘述被壓抑個人的沒有尊嚴的生存,《駱駝祥子》就是描寫祥子作為人的尊嚴是如何一點點被時代和生活摧毀殆盡。與此同時,沈從文、汪曾祺筆下中國鄉土中的尊嚴和性情在當代歷史和當下情境中又僅僅是一個文化的隱喻。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否就真的沒有可能去建構有尊嚴、有擔當、又心胸的小人物?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路內《慈悲》則提供一種敘寫灰色小人物的新路徑。《慈悲》呈現出對于上個世紀工人群體生活經驗的透視與剖析,體力勞動者的盲目和本能沖動呈現出路內一貫邊緣敘事的風格。然而,在動物般糟糕生存的同時,作者又賦予水生和師傅堅韌靜觀中的寬厚與體諒。這是中國青年作家開始用一種同情之理解的筆調來敘述和自己異質的生存樣態,在這樣的敘事中,時代新人水生正是在對于他人“不能好好活著的”堅韌同情中,由現代個體的孤獨荒涼走向人道主義。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學想象中被欲望化為一個個扭曲變形的符號,從紅顏禍水到玉體橫陳,從妻妾宮斗到職場小三……寫盡了“女”和“性”,卻沒有寫大多數女性在這個時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過日子。張策《宣德爐》的女主人公張麗蕓不斷重復一句話:好好過吧。“過”字裹挾著太多的意緒和情感,對于大多數無法傾訴苦難的人來說,沉默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隱忍那種埋藏在心里的苦難才叫堅強,這種隱忍讓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嚴和歷史感。張麗蕓是舊時代的姨太太,屬于灰色小人物的底層,正是這樣一個女性在極端政治化的年代,以自己的堅韌和聰慧在重重苦難面前完成了屬于個體精神的歷史存在感。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是中國青年寫作又一個令人驚艷的文本。現實和歷史是扭曲糾纏的雙面透視鏡,作者更多是通過倒轉的望遠鏡來敘述暴力與苦難,現代個體在人性救贖的路徑上依然可以有所作為,這種作為關乎智識,更關乎心性。雙雪濤筆下“時代新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復歸了1980年代人道主義的文學傳統,又有著中國古典美學中哀而不傷的韻味。
“社會問題小說”與文學重張啟蒙之實
大眾文化時代,新媒體讓地球人幾乎同步獲知最新資訊,然而人類最恐怖的事件也僅僅維持幾天的熱度,就會被新的事件所替代。由此,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異的現象,社會問題是如此普遍地引起關注,人們如此熟悉這些社會問題,而每一個人又都會很快迷失在新的問題中,從而對被刷過屏的舊問題熟視無睹。由此,新媒體盡管有著迅捷和海量的優勢,依然無法在直擊社會問題深層的精神困境與人性維度的復雜性。文學作為個體手工勞動具有“慢”的特質,這恰恰可以對當下的社會問題進行沉淀、打撈和梳理,從而站在一個更為人文的高度和以藝術的方式去重新呈現時代精神病癥和時代問題。敘事文學以反觀世道人心和時代精神氣質為己任,所謂以文學的面目觸及社會問題,以文學之名張啟蒙之實。
相對于百年前“社會問題小說”,當下文學文本更多面對的是傳統與現代轉型裂變中道德倫理和價值失范的中國人及其精神困境。飲食男女是中國世俗社會最重要的現實問題,而恰恰在最根本的食品安全、老年化、婦女婚姻和弱智邊緣人群中,社會問題更為突兀,其所暗含的精神文化問題就更加讓人不安。須一瓜《別人》通過女記者龐貝揭示出觸目驚心的食品安全問題,每一個“生活在別處”的人是如何回避自我、他者真實的生存狀態,從自欺與欺人延伸到個體與群體、個人與體制之間的傾軋與傷害。在當下的商業環境中,東西方文化中的“童叟無欺”和“契約精神”竟然都了無痕跡,這無疑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觀心自省。于懷岸《原路返回》從老年人個體的角度去反思現實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問題,面對著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國老人們無力地抵抗著死亡黑暗的誘惑。姚鄂梅《傍晚的尖叫》描述了老年婦女窮途末路的婚姻和精神狀態,帶著急迫中的狼狽和辛酸,卻有著一股堅韌中的硬氣和悍然。弋舟《我在這世上太孤獨》揭示了當下幾類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無靠或精神上的孤獨無依。對于一個有著父慈子孝傳統倫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文理想的中國人來說,老無所依和老無所養就不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是一個關于文化精神命脈的誅心之痛。申劍《白衣勝雪》借醫患題材提出了一個“信”與“不信”的問題,醫患關系問題歸根結底關乎功利主義的人際關系,而其本質則在于人對于活著之上的“善”和“道義”的“不信”。醫者仁心依然是建立在醫德為先的基礎上。
現代文明讓更多的普通人獲得教育和知識,從蒙昧走向心智的清明和理性的成熟。然而對于弱智人群來說,他們的生存境遇決定于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和方式,一個社會對待弱智群體的態度實質上折射出人們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養水準。鐘求是《找北京》、孫頻《圣嬰》和雷默《傻子和玻璃瓶》通過對于弱智者精神情感狀態的摹寫,還原了他們作為“人”的欲求,也透視“他者”對待弱智者的不同鏡像,提供了對于人性更為豐富的觀察和考量。中國人當下的婚姻狀態依然是暗流涌動,婚姻暗疾往往是社會隱疾最好的注腳,家庭婚姻關系折射出一個時代有關道德倫理的尺度。本年度小說文本敘述的重心依然是常態婚姻的不穩定,人與人之間對于“愛”的懷疑,以及對于婚姻的非理性理解。川妮《暗疾》和艾瑪《有什么事在我身邊發生》深入人性幽暗隱秘的路徑,從婚姻暗疾觀人心的荒涼與頹敗。雨樺《母女》塑造了一個享樂主義女性梅姐,恰恰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出當下女性極其有限的精神生長能力。當女性作為沒有精神皈依的幽靈生活在物質主義的當下,傳統社會的綱常倫理對于人性的壓抑還未在前現代中國全部退去,而正常的倫理秩序卻日益坍塌,無數個這樣的梅姐漂浮在當下的婚姻和日常之中,身形在享樂主義中日漸委頓,精神之荒涼則如游蕩在荒原的鬼魅。當下婚姻暗疾和女性精神的困厄在于更為深廣的社會經濟文化原因,當資本和傳統男權一起向女性和婚姻全方位侵入的時候,女性及其婚姻則陷入更加復雜困厄的境地。
城市經驗、鄉土懺悔與“國民性”問題的再敘事
嚴復最早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批判中國國民性:“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魯迅一代延續著中國啟蒙運動的思想軌跡,著力于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摹寫和反省。當下對于城鄉生存經驗摹寫并非在于批判性的揭露,而大多在同情之理解中探討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問題,這也可謂是現代文學“國民性”問題不同方式的延續。無論怎樣的國族與社會,接受功利主義生活邏輯的人往往淪落為心理陰暗、勢力逢迎、暗箭傷人的庸眾與小人,實在如嚴復所言“作偽和無恥”。這種現象原本很正常,不正常處在于對于這種“作偽”的寬容和對于這種“無恥”的麻木。本年度幾個文本集中探討了職場生活對于人性的侵害,表達的卻是當下中國人對于現實生存功利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從而凸顯出對于重構現代中國國民性的文學想象。尹學蕓《士別十年》提醒當下深陷職場的閱讀者:當辦公室政治對人性進行侵蝕的時候,個體自我是否有過掙扎與反抗?在這個文本中,中國人面對所謂現代日常的兩難和尷尬以追問的方式呈現,世俗的成功是否以喪失常識和常態生活為代價?當下國民的劣根性恰恰是流行的精致利己主義,一代人以小資和拉風時尚與物質主義互為表里,和欲望沉淪饕餮與共。而此時,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自知嗎?李治邦《辭職》題材老套,然而所提出的問題不在于辦公室政治與個人職業、遭際的關系,而在于現代個體人面對職場和官場的職業倫理和操守。小說通過文學建構了一個具有選擇個體自尊的現代人形象,從而在文學想象的層面對于深陷被動生活的懦弱者們施以精神的援手。少鴻《石頭剪刀布》則彰顯了更多中國庸眾的生存現實,這些人不再是無知無識的祥子們或老潘們,他們知道自己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但是卻懶惰、軟弱,在渾渾噩噩的慵懶狀態中也會涌起麻木中的自省與抗爭,但是最終會被強大的現實生活所裹挾,默默退回庸常的沉淪中,無力自拔。然而,這種妥協中的自省和微弱的反抗依然給人以人性復蘇的希望與光亮。
本年度鄉土敘事依然有力,在鄉土倫理和價值坍塌的裂變中,新鄉土敘事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了鄉土人物自身主體性的反思能力,中國國民性終于開始在鄉土個體中生發出自我的覺醒和對個人自尊的維護(當然不能否認更大范圍麻木狀態的存在)。楊仕芳《而黎明將至》以懺悔意識驚醒鄉土敘事沉重的倫理重負,給與鄉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覺和尊嚴。陳繼明《芳鄰》重新敘述當下農村中的“失敗者”形象,其重要意義在于對于農村巨變時代失敗者以足夠的理解與尊重。楊鳳喜《玄關》以一個輕巧的象征隱喻這個時代城市與鄉土之間隱秘關系和撕裂的痛感體驗。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深刻的隔閡內化到父子之間無法溝通的文化異質感,同時深深刺傷無法隔絕的血脈親情。“我”——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生活在城市的小知識分子,因為鄉土血脈和農民兒子的身份,錐心地傾訴了作為一代人的懺悔和哀傷。
“寫實與先鋒”的雙重困境與青年寫作的艱難前行
新寫實以來對于現實生存無間離的敘寫風格一直是當下期刊寫作非常重要的一脈,這類寫作以傾訴療傷的方式低吟生活之下的具體疼痛。本年度大量文本依然屬于這一類,例如姚鄂梅《天際花園的私房菜》、孫頻《無極之痛》、彭敏《北京歡迎你》等等,這些作品依然將筆墨集中在都市生活的漂泊感和無根性。十年前,這類文學敘事承擔了中國社會新生存經驗的文學摹寫功能,城市新人就在這些生存中誕生,其代表作品為《跑步經過中關村》等。然而,十年之后,如果不將這種生存鏡像和時代精神困境相勾連,作家則無法真正深入到已經發生質變的生存經驗內部,以文學的方式想象城市中的人。這類對于“艱難”物質生活窮形盡相的摹寫,其實重心依然在于物欲的鋪敘表達,由此很難在精神性層面進入更深的維度。
1980年代先鋒文學培養了一大批作家先鋒實驗精神的寫作趣味,先鋒文學終結,然而先鋒探索始終沒有停止。本年度依然有著一批作家熱衷于探討和日常經驗間離的人及其生存樣態。曹寇《在縣城》、武歆《比利時藥水》、田耳《范老板的槍》、鬼金《鳥的禮物》、女真《一手好牌》和馬笑泉《荒蕪者》等,這些作品都是和日常經驗有間距的創作。這種間離試圖在現實經驗之外撕開一條生存的裂縫,讓個人性話語和對于世界更為隱秘的感受滲透到同質板結的庸常經驗之中。這些人無限延長的青春期特征讓他們脫離日常生存軌跡,在一路自我任情的路子上顯示出某種讓人唏噓的個人化精神特質。然而,有別于上個世紀80年代這種打破陳舊日常規范的先鋒性,當下這類秉承先鋒余續的寫作,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處理個人化經驗的逼仄與時代整體性經驗的駁雜豐富,個人化的精神特質如何與時代精神氣質找到真正的契合點。
無論是“寫實”還是“先鋒”,這類寫作大多是年輕寫作者,當下中國青年寫作者與古典時代詩學傳統斷裂,寫作既無法家國天下,又無法做太上之忘情,真正做到自娛自樂。在這樣雙重的困境中,近二十年的中國青年寫作依然賦予當下文學自身新的現代性美學特征,也將在更長時間內對于漢語寫作起到根本性的影響。于此同時,當下中國青年寫作仍需從個人化走向時代整體性檢驗表達,從地域的民族抒情走向國際的民族精神建構,從現代中國人當下的生活走向人類精神價值譜系的思考與表達。
抗戰70周年與宏大歷史敘事
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歷史大背景下,抗戰題材文學創作成為本年度矚目的焦點。通過對于二戰中國戰區歷史的重新敘述,無疑會加深中國當下寫作對于歷史和人性雙向的深度思考。抗戰文學敘事在深廣度上繼續延伸,虛構與非虛構作品都呈現出對于中國軍隊和中國人在二戰中地位和作用的重新思考,且在新的敘事方式中表達對于戰爭中的人與苦難新的體認。報告文學方面,有王樹增《抗日戰爭》、徐錦庚《臺兒莊涅槃》、何建明《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余戈《1944:松山會戰》和《1944:騰沖之圍》等等,這些作品以歷史資料為經緯,重新建立起一個充滿硝煙戰火的敘事時空,讓歷史在漢字營造的真實情境中得以再現和延展。小說創作方面,范穩《吾血吾土》、何頓《來生再見》、常芳《第五戰區》、卻卻《戰長沙》、蔣巍《血色國魂》等等,以文學的想象建構起大歷史觀照中的戰爭和戰爭中的人,讓人在歷史中成為活色生香的個體與群體,在人物塑造和歷史情境的打造上都顯示出了獨特的視角。
茅獎的象征寓意與當下長篇小說的困境
2015年恰逢先鋒文學30周年,本年度先鋒寫作的兩位代表人物格非、蘇童以非先鋒寫作的長篇文本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似乎暗示著上個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真正終結;王蒙獲獎無疑標志著1950年代與1980年代文學傳統式微中的微瀾;金宇澄《繁花》則暗示著中國話本小說傳統和敘事方式在新媒體時代某種程度的復興。本年度期刊長篇小說創作盡管勢頭不減,依然在一種無序而繁榮的狀態中呈現出多重蕪雜的面目,也踟躕于重重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好長篇小說最基本的評價標準依然沒有共識性判斷,這也凸顯了當下批評理論界對于文本研究和批評文學性界定的局限和無效;中國經驗敘事如何面對日漸式微的鄉土傳統和人倫規范,在呈現坍塌鄉土的文學想象中如何進入現代性敘事的內省和觀照;中國當下城市經驗駁雜豐富,個體經驗逼仄同質,作為個體該如何呈現豐富駁雜的城市經驗又能在人性的維度抵達悲憫;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時期,中國作家該如何重新思考西方敘事傳統與中國話本源流的異同與流變。
最后還需提及中國科幻文學。本年度因為劉慈欣熱而引發了中國科幻文學熱潮,華語科幻文學異軍突起,在相當寬泛的意義上賦予中國當代文學闊大遼遠的宇宙意識和對于現世生存本質的深刻反省。這種熱潮不僅僅反觀了當下類型文學寫作在中國的勃興,更為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寫作者,寫作非但要有家國天下和全球意識,還需縱觀宇宙時空和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精神境遇,這樣才有可能真正構建大格局的文學。
——摘自作者博客
文中提及2015年作品:
阿來《三只蟲草》,發表于《人民文學》2015年2期,《小說月報》2015年3期選載
石一楓《地球之眼》,發表于《十月》2015年3期,《小說月報》2015年7期選載
荊永鳴《較量》,發表于《人民文學》2015年10期,《小說月報》2015年12期選載
路內《慈悲》,發表于《收獲》2015年3期
張策《宣德爐》,發表于《當代》2015年2期,《小說月報》2015年5期選載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發表于《收獲》2015年2期,《小說月報》2015年6期選載
須一瓜《別人》,發表于《人民文學》2015年7期
于懷岸《原路返回》,發表于《山花》2015年7期
姚鄂梅《傍晚的尖叫》,發表于《花城》2015年2期
弋舟《我在這世上太孤獨》,發表于《美文》2015年3期
申劍《白衣勝雪》,發表于《山花》2015年3期,《小說月報》2015年4期選載
鐘求是《找北京》,發表于《十月》2015年3期
孫頻《圣嬰》,發表于《作品》2015年第4期
雷默《傻子和玻璃瓶》,發表于《十月》2015年3期
川妮《暗疾》,發表于《小說月報·原創版》2015年3期
艾瑪《有什么事在我身邊發生》,發表于《上海文學》2015年5期
雨樺《母女》,發表于《小說林》2015年2期
尹學蕓《士別十年》,發表于《收獲》2015年4期,《小說月報》2015年11期選載
少鴻《石頭剪刀布》,發表于《當代》2015年5期,《小說月報》2015年10期選載
李治邦《辭職》,發表于《長江文藝》2015年9期
楊仕芳《而黎明將至》,發表于《湖南文學》2015年1期
陳繼明《芳鄰》,發表于《十月》2015年3期
楊鳳喜《玄關》,發表于《都市》2015年8期
姚鄂梅《天際花園的私房菜》,發表于《十月》2015年1期
孫頻《無極之痛》,發表于《長江文藝》2014年12期,《小說月報》2015年增刊1期·新聲特集選載
彭敏《北京歡迎你》,發表于《西湖》2015年2期
曹寇《在縣城》,發表于《收獲》2015年2期
武歆《比利時藥水》,發表于《山花》2015年2期
田耳《范老板的槍》,發表于《廣西文學》2015年1期
鬼金《鳥的禮物》,發表于《大家》2015年4期
女真《一手好牌》,發表于《長江文藝》2015年2期
馬笑泉《荒蕪者》,發表于《作品》2015年11期
附:
創刊于1980年的《小說月報》一路上的點點滴滴進步皆得益于廣大讀者的關愛。為了以更豐富的內容、更精美的形式服務讀者,誠邀讀者對本刊的內容與形式進行評點,您對刊物有何意見與建議,歡迎聯系編輯部郵箱xsybtj@126.com或通過小說月報微信平臺留言。期待您發出自己的聲音。
《小說月報》郵發代號6-38,每月1日出刊,定價10元;《小說月報》增刊郵發代號6-139,每年4期,定價15元。
《小說月報》在全國主要城市均有銷售。訂閱可咨詢所在地郵局(所),
網上訂閱可至郵政報刊訂閱網(http://bk.11185.cn)、雜志鋪網店(http://www.zazhipu.com)、當當網(http://www.dangdang.com
)或百花文藝出版社淘寶店(http://baihuawenyi.taobao.com)。
來源:小說月報微信
作者:郭艷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