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逢在歷史哀歌的岸邊
——簡談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沉船》
相逢在岸邊,在多雨的季節(jié)
默認刻骨銘心的時間
是河流的走向
是盛夏殘酷的意念
2015年9月,我到青海省海西州領取《大昆侖》雜志頒發(fā)的“大昆侖文化獎· 詩歌杰出成就獎”,見到互通郵件已久的詩人翼人,讀到了他的長詩《沉船》,上面所引四行,就是這部大作的開頭。短短一節(jié),如一部樂曲的主題動機,呈示出若干重要的信息,乃至詩學特征。它引領著這首長詩,和閱讀長詩的我們,踏上了一首歷史哀歌的茫茫長途。
這里,首先打眼的,是那個無人稱句式:“相逢在岸邊”。“誰”相逢?在哪個“岸邊”?主語的缺席,造成一個懸念,也因此包括了許多可能的答案。
相逢者不清晰,但相逢的場景并不模糊:在“多雨的季節(jié)”。我怎么油然想到艾略特《荒原》的起首:“荒地上長著丁香”?無人稱句式在繼續(xù):某人隱身相逢的季節(jié),本身是時間一部分,卻又不得不強調(diào)“默認”這時間,且為此默認“銘心刻骨”!某人眼中,岸和雨,都是河。而消失,是這時間之河的唯一流向。哦,原來,某人默認的,是一個“盛夏殘酷的意念”!我們不知道,那是哪個盛夏?每個盛夏?那個盛夏!借助漢語動詞的無人稱、非時態(tài),翼人指給我們一個不停流去、更一動不動的“盛夏”。
無獨有偶,我寫于2005至2010年的自傳體長詩《敘事詩》中,在構成第二部的五首哀歌里,有《故鄉(xiāng)哀歌》在。其第二節(jié),也恰恰名為《雪:另一個夏天的挽詩》。那首詩,寫一個從南半球新西蘭眺望的“夏天”,夠冷也夠黑:
“供桌似的雪山/萬匹素白 無鳥的天空滿目煙黑”、“千年之雪 一把抓起多少時空/裹著白綢不愿醒來 每天裹著灰燼/活算什么 夢更難忍”……
兩首長詩,書寫之處遠隔萬里,書寫的詩人素昧平生,作品卻構成了互文性。好像冥冥中真有個“相逢”:翼人的黃河、我的新西蘭,都未離開人生的岸邊,都有一個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我們內(nèi)心深處,像同一個震中,輻射出同一場地震波,讓詩人之心遙相呼應。
翼人是青海撒拉族詩人,他這首長詩《沉船》,寫得悲愴而不聲嘶力竭,哀痛卻更力道沉雄。究其因,或許由于撒拉族一如整個中國,絕不缺乏悲劇經(jīng)驗,相反,它們或許實在太過盛了,尤其二十世紀以來,復雜的歷史、文化沖突,讓無數(shù)“事件”,不僅在歲月水波間載沉載浮,更層層疊疊積壓進內(nèi)心,把每個民族、每個人書寫成一種“處境”。歷史,令現(xiàn)實變得無比深厚。借助它,我們增強了視力,更鑄造了定力。
《沉船》開頭定下的調(diào)子,在整首長詩中貫穿始終。閱讀這首共五十六節(jié)的長詩,常常讓我眼前浮出一幅圖景:一個孤獨的騎馬人,身披斗篷,沿著起伏的河岸,傍著一道浩浩逝水,顛簸著,沉思著,吟唱著。這首長歌,自那個“盛夏殘酷的意念”引出,河流的走向就是歲月的走向,那“憂郁的眼睛正在穿越/遠古的傳說 久遠的往事”(5);生死輪回的人群,如“一顆頭顱替換另一顆頭顱/去追趕一只受傷的黑鷹”(7);無垠綿亙的黃土地,“它縱然生生死死/卻依然長嘯嘶鳴//依然呼喚 山的主人 河的主人”(20);當盛夏變得殘酷,我們的意志反而清晰:“我們便擁有更多的冬天……奇跡般載負著日月星辰/并將注視著另一個冬天的到來”(24);當周遭世界凄涼如許,我的思緒反而深沉:“我便叉開雙腳站立于岸邊/遙望著盛秋的麥穗低下頭顱/疏朗地滾過大片荒蕪的土地/卻不知竟有幾多憂傷/幾多夢幻與我同在”(27);這場處境與內(nèi)心的搏斗,越直面絕境,越激發(fā)出能量,我們“頓足于河岸/丈量滴血的頭顱/使它高出水面站立一種姿態(tài)”(31);一個聲音:“水的洶涌怎及得上血的洶涌……如千噸熊熊鐵漿從喉管迸出”(33);一種審視:“我被突然吵醒……懸掛在半空/站立成一幅活人的眼睛”(38);受難的經(jīng)歷并非虛無,它毋寧說在重建一個精神血緣,“如果說行動是一部情書/……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們更加相依為命”(42);受難,其實是自己體內(nèi)舉行的一場祭祀:“那個涉過河灘的影子/在肉漿中為誰哭泣”(10);并由此獲得一次頓悟:“……而我們/短暫的一生 只不過是這存在的/一種例外……”(11);直到超越終于來到:“精神的內(nèi)海 趨于平靜和安寧”(45);死者或許是真的生者,“讓那些在黑暗中站立的人們看個夠”(46);他們并未遠離,那道“對岸的黑色絕壁……常以淚水拍打胸膛與河流默默相許”(51);他們“化生命為流浪的歌謠”(50);助我堅信,要“毀壞眼前罪惡的長城/重新用鮮血和淚水/選擇自我/選擇黑夜的禱告”(52);也令我反省,是否在“迫使自己默認一個時間的概念/為存在而存在”(53);河水蜿蜒,歌聲幽咽,“宛如我們的船隊吟著古歌/不如漆黑的夜晚/永遠是黎明的前夕”(54);悲愴而不頹喪,“誰能料到這悲壯的一幕/閃耀著燦爛的幸福之源”(55);最終,它所返回之處,是一片兼具人性和神性、歷史與當下的“內(nèi)陸”:“幽幽的靈魂深處——/叩伏于母親的營地/在旭光中向內(nèi)陸挺進”(56);《沉船》向內(nèi)漫漫跋涉,領我們抵達了一種豁然開闊。
《沉船》是一首史詩。但同時,它又超越線性“詩述史”的凡俗史詩概念,而把自己納入屈原開創(chuàng)的“史入詩”空間史詩傳統(tǒng)(想想《離騷》中現(xiàn)實——歷史——神話——現(xiàn)實的追尋吧),通過一個抒情聲音的穿針引線,《沉船》營造出多層次的有機思想結(jié)構,以詩歌空間,不停吸納、轉(zhuǎn)化時間主題,最終,讓這首詩比某個“盛夏”、比撒拉族人的記憶、甚至比任何塞滿沉船的歷史河流更深。一次“相逢”,恰恰因為無人稱,才適用于所有人;“相逢”的非時態(tài),不是沒有時間,而是一舉相逢于所有時間。翼人無須重復套話“子在川上曰”,因為他在自己深處,摸到了那條巨“川”。他深夜捫心,就在沿“川”漂流,甚至就成為了一個無盡加深的川底。用《沉船》,詩人從幽幽深淵向上“俯瞰”,目力所及,能認出到處的沉船,過往的、此刻的、將來的。而且,沉船們還在繼續(xù)向這首詩中沉沒,加入翼人為《沉船》找到的處變不驚、沉思默想的語調(diào),且讓這當代漢語詩歌中罕見的思想音色一貫到底。
《沉船》這首詩,堪稱河漢之歌、草原之歌、曠野之歌。聽它,能聽出民歌的質(zhì)樸、牧歌的蒼涼、情歌的優(yōu)美。我要說:它兼具現(xiàn)代心理的糾結(jié),與茫茫地平線的超越。我數(shù)次談到過:是“詩生成風格”,而非相反。所以,盡管《沉船》從開頭就不否認“刻骨銘心的時間”、“盛夏殘酷的意念”,但它的落點,卻并非歷時性的簡單呻吟,而回歸了對倔強生命的贊美。翼人最終向其挺進的那片“內(nèi)陸”,當然是一片精神境界的內(nèi)陸。詩,一如古老傳唱的民歌,始終在吸納艱辛,提純內(nèi)美,以此支撐著文明的傳承。稚嫩如插隊三年后、寫作《諾日朗》時的我,也已認出:“活下去——/天地開創(chuàng)了。鳥兒啼叫著。一切,僅僅是啟示”;而環(huán)球漂泊后寫《謁草堂》時的我,更能識別:“一個夏天讀出一千個夏天的寒意”;“一行沒有盡頭的詩用盡了漂泊一詞”。這指向了一個更大的話題:詩之境界,在處理激烈的歷史經(jīng)驗時,體現(xiàn)得尤為清晰。或者說,恰恰因為歷史嚴峻,詩歌形式的自律(乃至對其形式主義式的強調(diào)),才體現(xiàn)出詩人作為文化之根的自覺。請注意,詩是文化之根,而非某種宣傳口號(它們從來沒有“根”)。這個意義上,形式最專業(yè)者如屈原、但丁、杜甫,同時也最質(zhì)樸、本色、人性。我該說:甚至最道德!倘若我們再問深一點兒:歷史有悲喜之別嗎?歷史的存在,這條大河,攜著一切人類記憶,渾渾濁濁、莽莽蒼蒼流淌到今天。它本來就既構成我們的苦難,更贈予給我們財富。因此,函括歷史之詩,特別是“史詩”、長詩,正是承載思想深度的極端形式,選擇它,已經(jīng)本質(zhì)上在肯定生命力。時間大河里堆滿沉船的殘骸,可《沉船》之詩恰恰是不沉的。磨難,驗證了這首贊美詩不停“挺進”,無論那磨難來自大自然或人類。
那么,返回本文開頭,激發(fā)翼人創(chuàng)作《沉船》的那個“盛夏”,讓我們領略噩夢的靈感的那個“盛夏”,它在哪個具體日期,有關系么?只要我們大睜靈魂的眼睛,哪個盛夏不是那個盛夏?哪個地點不在處境腳下?哪一天不曾標明河流的走向,因而令我們刻骨銘心?“這無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我這個貌似無情、甚至殘忍的句子,寫于新西蘭,當我從漏雨的小屋里,眺望著窗外白云無盡馳過之時——但,這難道不是對那種涕泗橫流的深層追問?我們曾一次次“刻骨銘心”,但對它們記住了多少?是否正因為遺忘如此徹底,我們反而能虛偽的表演悲傷?“時間”的最佳暗示,正指出了時間(和人)的虛無!
翼人的《沉船》,是我讀到的當代中國最好的哀歌之一。我特意選用這個專業(yè)詞匯:哀歌(Elegy)。因為這個源出西方的詩歌形式,其實深切吻合了我們的中國經(jīng)驗,或者說,沒有什么“中國”經(jīng)驗,有的只是“詩歌”經(jīng)驗:只要它能配得上這徐緩、深沉、一唱三嘆的形式,能承載得起這形式已然蘊含其內(nèi)的經(jīng)驗深度、精神深度,詩,就在重鑄人的質(zhì)地。它能哀,只因為它能歌,且在歌中,還原了美。我們共同吟唱存在之大悲,也最有力地贊頌了共同的靈魂之大喜。
至此,翼人留在長詩起首處那個懸念式的無人稱“相逢”,找到了很好的回答,那里相逢的其實是每個人、所有人。他們——我們相逢在歷史的岸邊、哀歌的岸邊,相逢于這個獨一無二的時代,是一種命定、一種幸運。我們都是《沉船》上的水手,見證過驚濤駭浪,見證過沉船剎那間,人性暴露的優(yōu)美或丑陋,但什么也壓不倒詩歌。大河汩汩流淌,我們始終在凝視它、聆聽它,辨認著歷史哀歌的音色,直到,用我們的歌聲加入歷史雄渾的合唱。
楊 煉
作于2015年11月30日,汕頭大學旅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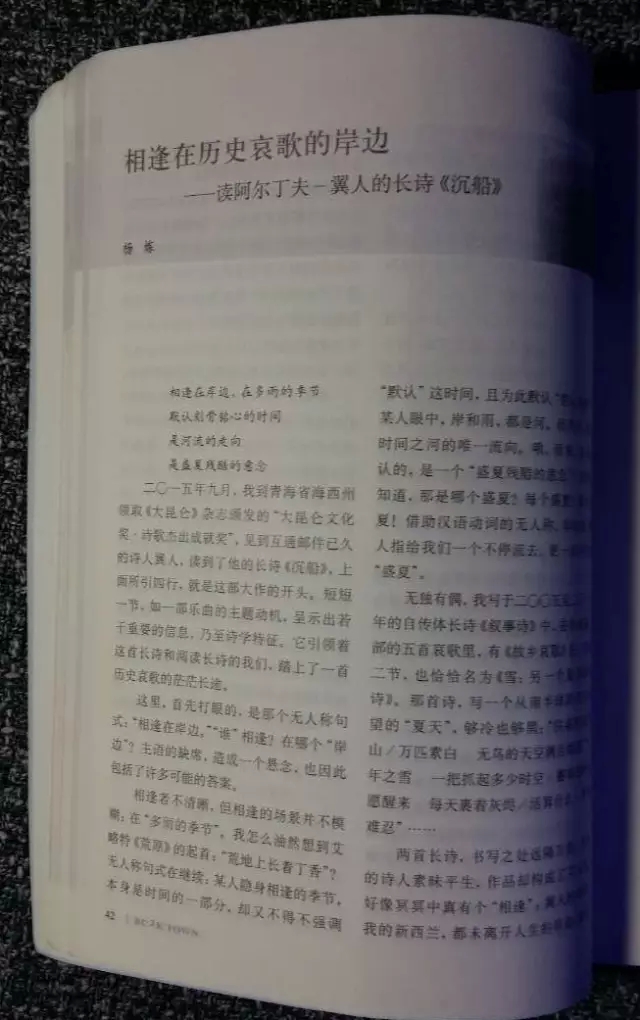
《書城》雜志刊發(fā)楊煉文“相逢在歷史哀歌的岸邊”

翼人與“大昆侖文化獎”獲獎者:何言宏、楊煉、霍俊明
【點評】
在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長詩”寫作版圖上,阿爾丁夫·翼人的長詩寫作具有啟示錄的價值和意義。但似乎有很多專業(yè)研究者對他以及他多年來的長詩寫作缺乏必備的了解。在后社會主義時代的今天,阿爾丁夫·翼人大量的長詩寫作,如《沉船》、《神秘的光環(huán)》、《錯開的花裝飾你無眠的星辰》以及《漂浮在淵面上的鷹嘯》、《放浪之歌》、《古棧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綠色莊園》、《撒拉爾: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題在歷史的懸崖上》、《遙望:盛秋的麥穗》等都秉承了一以貫之的對宗教、語言、傳統(tǒng)、民族、人性、時間、生命以及時代的神秘而偉大元素的純粹的致敬和對話,這種致敬和對話方式在當下曖昧而又強橫的后工業(yè)時代無疑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敬畏的。——霍俊明
無論在現(xiàn)代詩的主題,還是在現(xiàn)代詩形的創(chuàng)造上,阿爾丁夫·翼人都是卓越獨異的探索者。他鐘情于長詩,他的長詩猶如屹立的長城、流動的黃河,涌動著一個中國民族詩人身上的史詩血脈。他的詩歌浩瀚遼遠,波譎云詭,通過整體的象征造成一種詩歌意象與意境上的神秘和尊貴,這使他的詩篇猶如面對人間的“神示”,散布著宗教般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此岸與彼岸。在翼人那里,時間和空間、存在和哲理、生命和死亡、瞬間與永恒、自我與他者……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他的詩歌里,構成了一幅原始與現(xiàn)代、頹廢與新生、激情與憂郁、敞開與內(nèi)斂、明亮與晦暗……不同元素對抗著的充滿張力的畫面。在他的詩歌里,至今充溢著罕見的詩歌熱情。是的,他是一位足以令我們感到驕傲的詩人,但他更屬于整個人類。——高亞斌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