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翻譯:是語言的擺渡是相遇時互放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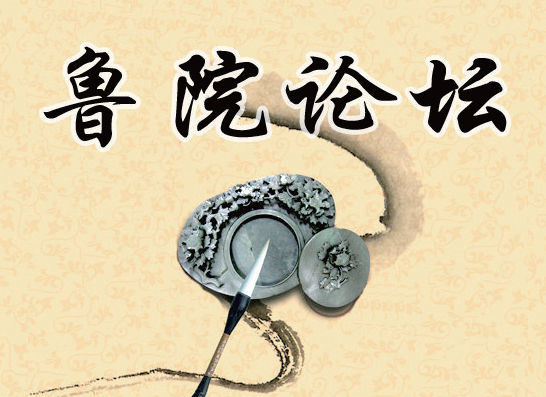


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
五四以來,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或多或少都受翻譯體影響,中國白話新詩與詩歌翻譯幾乎孿生而出,這無疑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奇特現(xiàn)象。在《詩經》《楚 辭》和唐詩的偉大古典傳統(tǒng)之外,翻譯幾乎再造了一個新傳統(tǒng)。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與國際詩壇的交流日趨頻繁,翻譯為不同語種的文學文化交流提供了 多種可能性。為對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做深層次的探討,加強對詩歌翻譯的重視,總結百年來中國詩歌翻譯的經驗,為未來的新詩創(chuàng)作提供更多的理論和實踐 資源,2016年6月20日,魯迅文學院舉辦了主題為“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詩歌的語言、翻譯和可能性”研討會。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魯迅文學院 院長吉狄馬加出席論壇并作主題發(fā)言。論壇由魯迅文學院副院長邱華棟主持。來自北京高校、學術機構、文學刊物的詩人、翻譯家、學者們齊聚魯院,針對詩歌的語 言、翻譯和可能性展開了深入研討。
詩歌翻譯是中國現(xiàn)代詩歌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談論新詩,繞不開翻譯
吉狄馬加: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也是一部中國詩歌翻譯史。從五四開始,中國新詩發(fā)展繼承中國古典,同時在文本、寫作方式、詩歌形式上大量借鑒外國詩 歌,翻譯功不可沒。如果要研究、回顧一百年新詩發(fā)展,不可能回避中國詩歌翻譯史。近30多年來,很多國家的文學界對中國的現(xiàn)當代詩歌投入很大關注,有大量 中國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從世界范圍看,幾千年來,很多國家和民族通過翻譯互相了解,尤其通過詩歌翻譯深入民族心靈,了解彼此的精神價值取向。我們的詩 歌翻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xiàn)在的詩歌翻譯無論是翻譯水平,還是翻譯深度、廣度、創(chuàng)造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中國的詩人、翻譯家,包括一些批評家,他們在選 擇翻譯對象的時候,也更加理性和成熟。對重要的詩人,進行了深入的、整體的、全面的翻譯。
張清華:詩歌的重要性體現(xiàn)在語言現(xiàn)代轉化角度,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轉化為另一種語言的工作。從漢語的發(fā)展歷史進行考察,漢語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語言互動的結果。從《詩經》《楚辭》到《漢賦》,歷次民族大融合,文化的激烈碰撞,激發(fā)出了漢語的豐富性。由此可見,新詩誕生不止是白話化,更 是漢語現(xiàn)代轉型的自覺,這種新的自覺是在其他的民族語言的激發(fā)之下獲得。所以不能忽視翻譯詩歌的作用,翻譯詩歌某種意義上也是漢語的一部分。
歐陽江河:翻譯從源頭就融入了中文詩歌寫作,一開始就構成現(xiàn)代漢語寫作的一部分。作為一種異質文化借鑒,翻譯為中文輸入了新鮮血液。
趙四:在不同國別和民族語言當中,文學和詩歌的發(fā)達時代,都是一個翻譯的時代,翻譯對文學寫作一定會起到促進作用。
汪劍釗:屈原、李白當然是我們的傳統(tǒng),但丁荷馬也是我們的傳統(tǒng)。
安琪:黃燦然詩論《在兩大傳統(tǒng)的陰影下》 :“本世紀以來,整個漢語寫作都處在兩大傳統(tǒng)(即中國古典傳統(tǒng)和西方現(xiàn)代傳統(tǒng))的陰影下”。百年中國新詩幾乎是在對兩大傳統(tǒng)的翻譯和摹寫中起步的。新詩的 發(fā)起人和寫作者譬如胡適、李叔同、劉大白、穆旦、徐志摩、戴望舒,等等,無一不是學貫中西的大家,在他們身上交匯著的兩大傳統(tǒng)總是頑強地抬起頭自他們的筆 下走出,走到今天的讀者面前。白話詩起源時期詩人們對西方現(xiàn)代詩的翻譯就有更多例證,幾乎每個白話詩人身后都站著一個西方詩人,如奧登之于穆旦,泰戈爾之 于冰心。由此可見,詩歌翻譯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 ,詩歌翻譯尤為重要。
詩歌翻譯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它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可能性之一,譯者在翻譯的時候,選譯的標準。
可能性之二,讀者在接受翻譯詩歌時,采取什么樣的標準。
可能性之三,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名言:“詩就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詩到底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還是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保留的那一部分?
樹才:在分析詩歌翻譯可能性的時候,一首詩的語言、物質性層面是可討論的,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能由著譯者的性子來。任何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實際 上都隱秘受制于原文,原作者即使是缺席的,但是永遠像幽靈一樣跟隨譯者,所以也決定了一首詩翻譯過程的無限多樣性,這個無限多樣性是弗羅斯特講了失去的那 一部分,但是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這個非常重要。
汪劍釗:弗羅斯特關于詩歌翻譯的表述只是極端表述,并非真理。因為事實證明另外一種語言里的偉大詩歌被知悉并非不可能。但丁、荷馬、莎士比亞, 大部分中國讀者都不是通過意大利文、英文或者希臘語,而是通過翻譯讀到的。這些詩人能夠被接受,還是因為由翻譯形成的廣泛傳播,翻譯并沒有減弱他們的偉大 聲名。
張清華:偉大詩篇必須是總體性的詩歌。應該有兩個維度,一個永恒性,一個當下性。詩歌的總體性意味著是在說一切的詩歌,是在說古今中外一切優(yōu)秀 經典偉大詩篇的總和,或者關于詩歌所有的規(guī)則,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標準,所有偉大文本的總和。我們每個人寫作的時候應該面向神圣的東西,同時要指向他存在 的當下性。每一個詩歌寫作者,都應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認為極端寫作成為中國先鋒詩歌寫作的一種末流,總是想通過極端化、行為化、偏執(zhí)化寫作獲得有效 性,獲得影響力,但是真正的先鋒精神植根于詩歌的偉大傳統(tǒng)。今天富有精神性、思想高度和藝術難度的先鋒精神日益稀薄。
董強:詩歌的現(xiàn)代性和當代性很難定義。相對而言,小說和繪畫的標準明確,而詩歌的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或者當代性,難以把握和定義。從詩歌的主體性 來說,很難以人定詩,很多知名度并不高的詩人的作品寫的非常好,并不遜色于某些大詩人、知名度很高的詩人。這一點也為譯者選譯的時候制造了難度。
趙四:從語言的角度評價一首好詩,應該反對口語化和散文化。詩人傾向于稱自己寫作是口語寫作,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它不是未經改造的口語,這種文 學化的口語應該視為智慧語言。現(xiàn)代詩歌語言應該警惕散文化表達,如同瓦雷里評價波特萊爾詩歌時所說“波特萊爾詩歌把法語詩歌從三百年只有散文而沒有詩的狀 態(tài)中解救出來了”。所以創(chuàng)作詩歌應該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
李少君:有兩類翻譯詩歌會讓讀者產生強烈的閱讀印象,一類是現(xiàn)場感、畫面感、圖象感比較強的詩歌。比如米沃什《禮物》中的“直起腰來,我望見藍 色的大海和帆影”,;西方翻譯者青睞唐詩,也是因為唐詩表現(xiàn)了詩人在大地上的場景,現(xiàn)場感極強,容易翻譯成圖畫一樣的場景,易于接受。另一類是那些表達普 遍理念和意義的作品,比如歌德《浮士德》中的“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飛升”, 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寫出了很多人的普遍感受。而那些涉及較為濃厚的民族文化、神秘經驗的作品,就相對比較難被 他國讀者所接受。比如蘭波的詩歌,其中神秘、超越的一面,很難被翻譯。以杜詩為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好譯,但“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 思”難譯,詩中有一種神秘的、中國古典的東西極難譯出。
歐陽江河:詩歌翻譯中當譯者取代了作者,主體性的替換帶來詩歌的豐富性和文化的差異,意義的傳遞有可能被修改。有可能變得更精確優(yōu)雅,但也有可 能變得欠缺。這個欠缺可能是自然的欠缺、生命的欠缺,是發(fā)生學和思想史、文化本身的差異和欠缺。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元取代了黃金金本位的地位。黃金在天上 舞蹈,命令我歌唱,歌唱是紙票,美元取代了黃金,這個過程中人民幣必須兌換成英鎊、美元。針對這種現(xiàn)象,在世界詩歌翻譯全球性轉化過程中,翻譯意味著什 么?意義意味著什么?價值意味著什么?東方在被翻譯過程中,在全球價值兌換中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個方面。一種是以韓國詩人高銀為代表的消減性的 自我升華,意味著東方的想象的復雜性缺席,東方被想象成禪宗的,泯滅自我的。但如此處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們豐富的莊子、楚辭缺席了。一種是相反方向 的泯滅自我,就是越來越復雜,不停生成,不停繁殖,像病毒變化。還有一種途徑的缺席,即聲音和聽的缺席。詩歌的翻譯就是從聲音轉化為圖象,從可以聽可以 說,轉化到可以看的過程,意象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
張?zhí)抑蓿阂獜恼娼嵌瓤礆W化。現(xiàn)代漢語發(fā)展歷程中,歐化作為一種重要現(xiàn)象是無可回避的、無可否認的。早期傅斯年、胡適、王力、朱自清以及周作 人、魯迅等等新文學、新語言開拓者都對歐化持有比較支持的、歡迎的態(tài)度。反對歐化者有的持狹隘民族主義態(tài)度,認為歐化有可能會改變我們所謂民族的特性,特 別是我們民族語言的特性。有的則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反對歐化,認為歐化是過于學院化和知識分子氣的語言,是對大眾文化的一種否定。新文學誕生之初,姿態(tài)是大 眾主義的,但是運行過程是精英主義的,由精英主義所導致的歐化現(xiàn)象,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在漢語里找到它的準確定位,消除負面影響。從我們百年詩歌發(fā) 展史來看,更需要“歐化”這樣的陌生力量激發(fā)自身語言生長性和潛能。如黃燦然所言“孜孜不倦閱讀漢譯外國詩,尋求的正是譯文中那股把漢語逼出火花的陌生力 量”。
詩歌翻譯的核心要素:內涵的界定、譯者的重要性及翻譯的過程
董強:翻譯是一種接受,所謂接受就是對話。詩歌翻譯要抓住原詩的核心價值,回避不恰當?shù)脑娗楫嬕狻Wg者在翻譯時,要抓住詩人偉大之處,它最強烈 的風格,同時對詩情畫意要保持警惕。西方現(xiàn)當代詩人不再追求所謂古典唯美,更強調語言的沖擊,或者某個方面的介入。譯者不能以自己主觀的詩情畫意,強加到 以“反叛”“晦澀”“蕪雜”種種特點著稱的現(xiàn)當代西方詩歌中,淹沒它的原文特點。
樹才:“黃金在天上舞蹈”就是一首原文里面?zhèn)ゴ蟮脑姡窃淖鳛橥瓿晌谋荆呀浗Y晶成一道光芒,我們卻因為語言的阻隔,造成“視而不見”。所 以它的下一句詩,“命令我歌唱”, 舞蹈的精神價值在另外一種語言里面重新被歌唱一遍,雖然主體換位了,這種替換的過程就是翻譯。要前所未有地重視譯者、譯者條件和譯者工作。研究譯者如何把 原文和譯文變成一座橋,讓語言之河流淌的時候仍保持活力,讓一首詩的黃金品質經過這個“我”唱出來仍有黃金品質。要從一個極端的角度評價譯者的重要性,一 首詩如果不是碰到適合它的譯者,永遠不能被呈現(xiàn)。蘭波的《奧菲利亞》如果不是碰到葛雷,不能產生如此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安琪:翻譯作為一門藝術和技術的高度結晶物,對譯者的要求十分嚴苛,同一首詩在不同譯者筆下會長出不同的模樣。
汪劍釗:翻譯的過程可以用一個比喻:譯詩是一場冒險的戀愛。原文是待字閨中少女,譯者就像追求者,一場愛情要很好展開的話,追求者要使出渾身解 數(shù),他的漢語能力、外語能力包括對生活的認識、知識準備的積累都很重要。只有追求者充實自己以后,才配得上追求漂亮的少女。但現(xiàn)實中的戀愛,有成功,有失 敗。成功的例子,兩人相愛,最后走進婚姻殿堂,生下一個漂亮的孩子,翻譯成品某種意義上就像漂亮的孩子一樣,可能跟父母長得并不像,但是他身上絕對帶有父 母很多遺傳密碼。失敗也有可能,比方說一首詩翻譯不下去,前面30行特別好,但中間到35行的時候,就卡住了,怎么譯也譯不下去,這就像一場不成功的戀 愛,只能擱置。
樹才:翻譯的過程無法還原,所以翻譯的過程經常變成一個盲點。大多數(shù)人對于詩歌翻譯或者對一首譯詩的研究總是落到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經常毫無理 由跳過譯者,跳過翻譯的復雜性隱匿在里邊那樣一個過程,直接落下一個判斷。在原詩和譯詩之間更多人認為,僅僅隔著一步跨過的小溝,實際上二者之間隔著一條 洶涌的河流,任何人沒法一步跨過。
歐陽江河:翻譯的過程就是閱讀的過程。閱讀有消費性閱讀、審美性閱讀,也有翻譯和批評的閱讀,閱讀里面有才子式的、天才式的、生命激蕩來自藝術 感動的閱讀,也有學究式的閱讀。這時候語言的選擇很重要,到底是采取一種政治的、主流語言意識形態(tài)式的語言,還是才子式、個人式、審美式的語言?選擇的背 后包含了非常深的文化差異,這種文化差異表面看來是一種取決于詞匯源的技術性選擇差異,其實后面可能包含了文化的這種缺席。
蔣一談:翻譯的過程真正逼近文學真實的應該是恍惚型。當一個人走路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抓到他走路的身形與動作,但如果跳舞的時候我們目光會變虛。因此翻譯詩歌時應保持敬畏、恍惚的狀態(tài)。
詩歌翻譯的標準——葛雷之于蘭波,王央樂、王永年之于博爾赫斯,西川之于蓋瑞·施耐德、郭保全之于普希金等等
董強:詩歌翻譯方面標準可以相對寬松。詩歌具有很大可能性,可能性更多是潛在性,因為這種潛在性的巨大,所以詩歌翻譯標準可相對寬松。
樹才:詩歌翻譯標準不應由譯者來判定,而應交于讀者,讀者在閱讀時會自動形成淘汰機制。當一首詩已經被翻譯出來后,最開始評判標準可以稍微寬容 一點。因為譯者總把自己的翻譯視為最佳,但到底翻譯得如何,應該讓讀者來淘汰譯詩。譯者之間的爭論是毫無必要的,可以交給讀者自行評判。每個讀者的文學場 域、詩歌接受能力都不同,他對翻譯詩歌的評價就會不同。
張清華:成功的翻譯植根于語言的內部核心,同時也植根于人的心靈,植根于人的無意識,植根于人的靈魂。
趙四:中國古典詩歌在西方經常由著名詩人如龐德、帕斯等翻譯,但是即使熟讀中國古典詩歌而又懂外語的讀者,也很難從他們的譯本里判斷出每首詩對 應的原文。但是這種翻譯方法在西方被視為一種好的、有效的翻譯。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一個閱讀者的問題,閱讀者選擇的是詩,而不選擇讀哪種形式的詩。有 些學者翻譯中國古典詩歌,非常注重聲音傳遞的可能性,做了大量的工作來保持詩歌原有的韻律,但是另外一個語種當中的詩人、讀者并不認可這個,因為他們要讀 的是詩本身。從詩歌翻譯的角度來看,古典詩歌翻譯的難度要大于現(xiàn)代詩歌,古典詩歌的節(jié)奏韻律和本民族的語言文化無間融合,如果要拆解開來翻譯,非常難,必 須要化成意象來傳播。但是現(xiàn)代詩歌的一大特點就是拋棄了韻律系統(tǒng),代之以節(jié)奏系統(tǒng),翻譯起來容易得多。
歐陽江河:西川在翻譯蓋瑞·施耐德時,是做了嚴肅工作,這翻譯的嚴肅工作相當于康德對崇高的定義,就是判斷力的審美和理性審美這兩者之間產生不 一致,在這個不一致的基礎上,想象力的嚴肅工作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崇高起源。只有看到不一致,因為理性的審美和想象力的審美不一樣,想象力審美是個人的工 作,而理性是集體性工作,這個中間肯定會產生偏差,這個偏差基礎上產生的快感,被康德稱作消極快感,而這個消極快感可能是翻譯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出發(fā)點的 翻譯是才子式的, 美文式的,個人感動式的,另一個理性集體的自然東西、客觀東西缺席了。西川這種嚴肅工作的翻譯彌補了這一缺憾,為詩歌帶來了很多新的東西。
中國詩歌(尤其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呈現(xiàn)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詩歌的特點。
敬文東:與西方文化對語言的推崇不同,中國文化更推崇文字。從這個角度來看,索緒爾語言學觀點對漢語或者漢字并不那么有效。漢字有結繩記事的傳 統(tǒng),起源之初非為記音,而為記事。在中國的傳統(tǒng)里,事和歷史是我們的宗教。所以漢字完全不是記漢語發(fā)音,它跟事有密切的關系。如果西方人覺得語言比文字更 重要,在中國漢語里面,漢字與漢語關系正好顛倒過來。如果我們承認這樣一個基礎前提,就要意識到,雖然荷馬、但丁也是我們的傳統(tǒng),但中國自己的傳統(tǒng)更是傳 統(tǒng)。
中國傳統(tǒng)詩歌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特質?中文詩歌能向世界詩歌貢獻什么樣的經驗?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中文詩歌從《詩經》開始就表達出一種對知音精神的追求。盛唐詩歌中高達百分之四十為贈答詩或離別詩,正是中國傳統(tǒng)詩歌知音精神的 直接體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詩歌寫作,如廢名、戴望舒等自覺繼承了這樣一種傳統(tǒng),寫了大量的贈答詩。這些贈答詩在形式上常用“你”“我”“我們”這樣的對話體展開 寫作,或者有時直接呈現(xiàn)自己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相信對方能了然于胸。中國詩歌的這種知音寫作,傳達出中國詩人對詩的一種理解,即詩不僅僅表達經驗,不僅僅是 對語言本身的追求,同時有安撫性。在現(xiàn)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孤獨已經進入形而上的狀態(tài)。如何解決這種孤獨?中國的知音詩歌寫作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
霍俊明:新詩詩人在海外的形象是單一的,例如北島,他在西方可能更多是和國家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古典詩人在海外的形象是多樣化 的,有非常豐富的符號指向。比如杜甫,宇文所安認為杜甫既是一個封建帝國的歌頌者,也是一位父親,還是一位晚年的流落者。比如王維,帕斯和溫伯格一起寫了 一篇《看待王維的19種方式》。西方翻譯中國詩歌時,固然會結合漢字的特點,強調動詞和意象,但更注意詩人的形象,比如王維是什么樣的形象?他是佛教徒還 是一個貴族?譯者會結合詩人的多種形象來考察漢語的特點。
我們通過譯介西方傳統(tǒng)形成了中國新詩的現(xiàn)代性,這個現(xiàn)代性是否有效轉化為本土經驗?很多詩人既翻譯又寫作,翻譯到底對寫作發(fā)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詩人張棗提出:“翻譯是翻譯,寫作是寫作,寫作時要做到“我在寫作時要殺死史蒂文森”。(史蒂文森是張棗最喜愛的詩人之一)”而更多的詩人在寫作時卻表現(xiàn) 出了對翻譯的暗戀。
結 語
吉狄馬加在論壇最后的總結發(fā)言里高度肯定了本次論壇的成果與意義,與會專家觀點新穎,見解深刻,討論成果有利于中國詩歌的發(fā)展。大家通過討論, 進一步認識到詩歌翻譯的重要作用。不僅僅是對于中國,放眼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建設都離不開詩歌翻譯。在翻譯的過程中,外來語言積極參與了本民族語 言構建,激活了本民族語言的潛能,貢獻出了新的力量,這一點應該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詩人已經自覺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詩歌區(qū)別于西方的一些重要特質,但我們還 要認識到,五四以來的詩人們幾乎都在翻譯和寫作兩個領域里成就斐然,因此我們回顧總結百年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不應遺忘總結百年新詩發(fā)展中的翻譯問題。展望未 來,伴隨著中國詩歌的繁榮發(fā)展,中國在詩歌翻譯方面的廣度和深度都要加強,讓更多、更好的詩歌進入中國視野,豐富和擴大我們的文學版圖。同時,我們還要在 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向世界介紹中國詩歌,展現(xiàn)我們中國詩歌的發(fā)展水平和成果。
來源:文藝報
作者:嚴迎春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