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林最新學術著作《文學問題:后理論時代的文學景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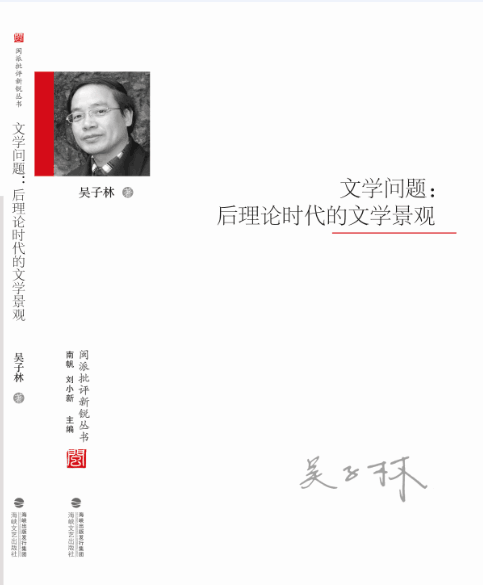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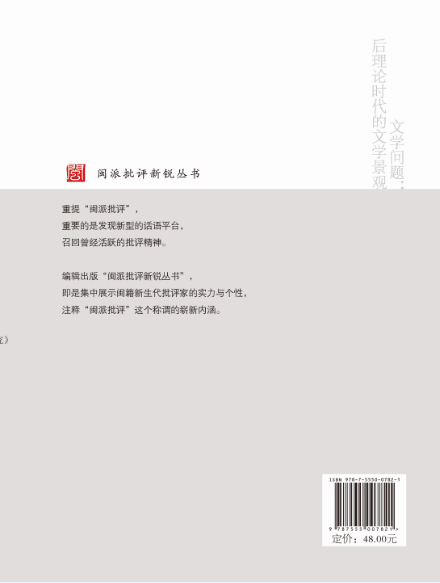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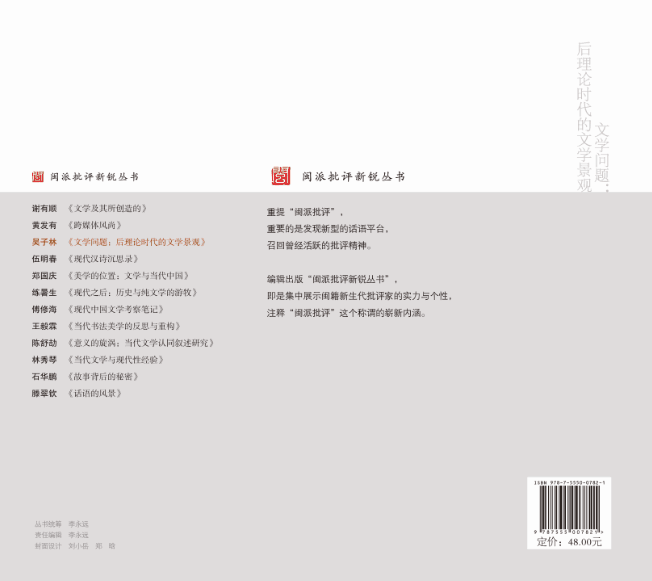
近日,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學者吳子林最新學術著作《文學問題:后理論時代的文學景觀》由海峽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書為南帆,劉小新主編的“閩派批評新銳叢書”之一。
作者吳子林坦言,收入此書的十余篇文字,是完全按照我個人的喜好摸索而得的。不論是選題,還是文體,都不那么“規矩”,不那么“邏輯”,不那么“論文”;它們或迷離跳躍,或直率清淡,或慷慨激越,或靜默低回……
[目 錄]
總序 / 南帆
自 序
“文學的絳蟲”
——當下文學創作、研究之去蔽或敞開
“唯一有價值的就是擁有活力的靈魂”
——講述“中國故事”的方法或主義
“奧威爾問題”
——漢語文學之語言問題斷想
“重回敘拉古?”
——論文學“超軼政治”之可能
“安尼瑪的吟唱”
——《格薩爾》神授藝人的多維闡釋
“你們信仰上帝嗎?
——信仰與寫作的質地
“不可言說的言說”
——信仰敘事的內在難度
“作家們的作家”
——當代作家原創力探源
“修辭立其誠”
——重建誠的文學
“明天會出現什么樣的詞”
——2030年中國文學的可能面相
“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
——當代文學批評的歧途與未來
“用背脊讀書”
——重構文學閱讀的意義境域
“生命的學問”
——文藝學研究的一種可能向度
后 記
[自 序]
歲月在指縫間悄然流走,恍惚間從不惑之年起步奔五;牙床動搖,鬢發稀疏,皺紋加密,肌膚松弛,血壓攀升……
——畢竟是歲月留痕了!
河畔,蘆葦在微風中婆娑作響,晚霞暈染著齊唰唰的山林,葉兒旋著片片金光,空氣中混合著青草和松木的味道。
沉浸在無邊的寂靜之下,我聽到了自己的呼吸聲。“人總要有點東西,活著才有意義”,阿城如是說。
文學是最公平宗教,不估量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計較有無成功機會;盡我心盡我力盡我份,如此而已。
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間;本乎一己之心得,心不容已地撰為文字,將心智置于貌似捕風捉影的事業。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可自拔地寫作,只是源于持久興趣,以文字追逐那碎影流年,夯實貧乏之我。
在《人生之體驗》的“導言”里,唐君毅先生坦言:愈是現代的人生哲學之著作,愈是讓人喜歡不起來。何故?這些著作綱目排列整整齊齊,疊床架屋,除了可助教學或清晰些觀念性知識,實無多價值;它們不能與人以啟示,透露不出著者心靈深處的消息,且足以窒息讀者之精神的呼吸。反之,中國先秦諸子典籍,希伯來之新舊約,印度之吠陀,還有古希臘哲學家斷片式的箴言,其中自有著者的心境與精神、氣象與胸襟,并以其天縱之慧,抉發人生價值,示人以正路。
何以故?唐君毅先生指出:
那些人,生于混沌鑿破未久的時代,洪荒太古之氣息,還保留于他們之精神中。他們在天蒼蒼、野茫茫之時間中,忽然靈光閃動,放出智慧之火花,留下千古名言。他們在才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們開始面對宇宙人生,發出聲音。在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種莽莽蒼蒼的氣象,高遠博大的胸襟。他們之留下語言文字,都出于心所不容已,自然率真厚重,力引千鈞。他們以智慧之光,去開始照耀混沌,如黑夜電光之初在云際閃動,曲折參差,似不遵照邏輯秩序。然雷隨電起,隆隆之聲,震動全宇,使人夢中驚醒,對天際而肅然,神為之凝,思為之深。
千祀之后,讀者諸君遙念圣哲,誦其詩,讀其書,不能不懷想其為人,直接感應其精神氣象及著作方式,而景仰企慕,有以自奮,祈望向往,繼發其潛德幽光。
可是,環顧當今之世,“唯物功利之見,方橫塞人心,即西方理想主義已被視為迂遠,更何論為圣為賢成佛作祖之教”。環顧當今學界,能踐履錢穆先生所云學問之“四部曲”,學貫中西,融會百家,稱心而談,開拓萬古之心胸,做到出才情、出見地、出思想、出斷制者,又有幾人?
凡能稱得上“學”者,絕非一般領域,必是包羅萬象,宏細兼容,有挖掘不盡之思想資源,能拉得住人心,重若千鈞,是一片讓人定氣凝神、依枝棲息的精神家園。此“學”帶給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與自己的生活融為一體,生命因之點燃的火焰永不熄滅。難道不是這樣嗎?
史震林(1692—1778)《西青散記》里有幾句話:
嗟君何感慨,一往不可攀。仰視碧落,俯念蒼生。情脈念痕,不知所始。醉今夢古,慧死頑生。淡在喜中,濃出悲外。
唐君毅先生的名著《人生之體驗》便是在此種有所感慨的心境情調之下寫的。“仰視碧落,俯念蒼生。”上下無依,迥然獨在;上開天門,俯瞰塵寰;既虔敬禮贊,又同情惻憫,其心靈是平靜的、超脫的。因此,唐君毅先生說:“在此心境情調下,我便自然超拔于一切煩惱過失之外,而感到一種精神的上升。”由此心境情調而成之文字,于關節處解隙,于有礙處洞達,豁然醒目,暢然不隔,立意閎中,立論不移,而最為人所珍愛。難道不是這樣嗎?
然而,歷史與現實賦予了太多背離學術自身發展的制度邏輯,幾乎摧毀了人們對于學術的心理依存。在浮躁喧鬧的邊緣,太多的著述是“為人”寫的,不是“為己”寫的;遠離本心,違背初衷。對自己不夠誠懇,也就無法影響他人;除了形式邏輯,及綱目式結論,談何引領思想之力量?既不能“度”己,更不能“度”人,縱使“著作等身”,又有何益?
張潮(1650—?)《幽夢影》有云: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又云:
有地上之山水,
有畫上之山水,
有夢中之山水,
有胸中之山水。
地上者,妙在邱壑深邃;
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
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
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如何繪出“胸中之山水”,每一個有抱負的學者都不能不加以思量。
人生之本在心,文章之本亦如是。朱子有詩云:“此身有物宰其中,虛澈靈臺萬境融。斂自至微充至大,寂然不動感而通。”文章的背后,是悠遠寥廓、不可目視的人格、風骨和境界。人格修養的歸宿即境界,“有境界則自成高格”(王國維語)。
毋庸諱言,許多問學者心智都敗泄在了世俗人際關系上。他們苦心積慮地賺取、提升自己的聲譽,實利成癖,虛榮入骨,總是以各種“幻影”——如科研課題、重大項目及其豐厚資金,還有名目眾多的榮譽、津貼和獎項,等等——充當自欺欺人的逃路,從不再向上攀援,辟以蹊徑,以克服現有研究之困頓、局促。
每個人都絞盡腦汁,為所欲為,每個人實際上也都難有所作為。不僅學養不足,不成格局,更談不上“導夫先路”的創造。“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汪曾祺語),正是心智的壞朽,釀成了文章的邋遢不堪;對此,許多炮制為文者并未醒悟,仍我行我素地“任性”并“幸福”著。
作為一個終極眷顧,生命的境界是依次遞升的。由于每個人的“才”“命”“力”不一,其所進益亦有所至而止,其文章精神層級之境亦自有其極限——或本能性表現身體欲望,處于不識不知的混沌狀態;或滿足于個體功利需求,以博取功名利祿為指歸;或凝合為一道德主體,遵循特定社會標準、典范,滿足于政教人倫馴化;或“上下與天地同流”,“參天地,贊化育”,臻于“自如”的“至樂”之境。
《金剛經》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即不拘執某物,不思得失,不思榮辱;不媚俗,不媚權貴;祛除“計算”、“操作”和“規劃”,是謂“出離”,是謂“得解脫”。寧神靜氣,氣貫于一,則“生其心”,即無中生有,自由創造,生命精華自然噴薄而出。曾國藩詩云:“長將靜趣觀天地,自有幽懷契古今。”
我喜歡讀書,沉迷于理智與情感交融的心境;
我喜歡思考,執著于精神的探險而無中生有;
我喜歡寫作,陶醉于內在性靈的充盈或發現。
我的一點學術理想——
返回內在明鏡靈臺,與純真的生命對談,將理論研究變為自發性的創造,將理論研究轉變為文學問題的專業性參與、學理性反饋;
帶著斑駁的經驗、瑣屑的記憶,裝著一個時代進入歷史,直面中國的文化原典,從“小學”入,由“義理”出,在回歸中實現超越;
以孤絕的勇氣,鮮潤的語言,開辟榛蕪,不讓外部世界壓迫同情心、想象力和創造力,邁向更高的完善與存在,以克服自己的時代。
文學和藝術,始終面對、叩問人類永久的價值;就像隨手撒下的花籽,不久便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
這部自選集收入了我近年來的十余篇新作,它們存留了我個人的某些思考,可謂探索性的“嘗試集”。
是的,“寫作,那是唯一填滿我生命并讓它欣悅的東西。我做到了。寫作從未離我而去”(杜拉斯語)。
我的授業恩師童慶炳先生生前一直關注本書的撰寫與出版,對于我的探索亦勉勵有加。謹將此書敬獻恩師!
是為序。
[后記]
一年又一年,周而復始。
仿佛可以蕩滌一切前塵,從頭再來,如同新生。
夜雨敲窗,山風滾落。
曾幾何時,一個鄉下來的孩子,站立在被風吹得發白的鄉間路口,遙想壯麗原野,癡癡遐想:“遠方有多遠?”
幾條路蜿蜒下來,一個清清瘦瘦的青年,駐足城市繁華街頭,沉默而倔強,他的心里有千萬種聲音在轟鳴,在奔走。
再后來,步入中年,身居嘈雜而蓬勃的京城,無論是尋找迷失的自我,還是緊隨命運的牽引,心頭日夜不息的潮汐與風浪,總將自己推送到未知的海岸。
盡管貫穿脫胎換骨的痛苦,以及重獲新生的喜悅,眉宇間目光清澈如故。
遠方或許真的并不遠,又或許,遠方除了地平線,什么也沒有。
如是而已。
日光之下,萬物簡單如初。
時光起伏、交錯、交匯,文字熾熱、瑰麗、浩蕩;夢想因之掀開,骨骼血肉頓生。奔走在忙碌勞作的命途,我漸漸領悟了此生的宿命。
如果說生命的意義在于體驗,寫作則是極力拓展體驗的邊界;那一篇篇文字便是一個個生命的休止符,一段段悲欣交集之碎片的記錄。
一切紛至沓來,人生真是豐富啊,就讓一切都跟隨命運去嬗變吧!
收入此書的十余篇文字,是完全按照我個人的喜好摸索而得的。不論是選題,還是文體,都不那么“規矩”,不那么“邏輯”,不那么“論文”;它們或迷離跳躍,或直率清淡,或慷慨激越,或靜默低回……
這首先得感謝《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先生,由于他的熱情與大度,這些文字以“文學問題”專欄形式一篇篇面世。
還得感謝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南帆先生,因為他的大力支持與幫助,拙著得以第一次在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
最后感謝我的太太詩人安琪,她是每一篇文字的第一讀者;倘若說這些文字有“詩性”,這多半歸功于詩人的同化!
吳子林
2016年4月5日北京家中
作者簡介:
吳子林,1969年生,福建連城人,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評論》編審,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致力于中國古代文論、文學基本理論、中西比較詩學及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研究與批評,已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等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著有《中西文論思想識略》《童慶炳評傳》《批評檔案——文學癥候的多重闡釋》《文學瞽論》《20世紀中國文學史通論》(第6卷)《中國現當代文學論爭中的理論問題》《經典再生產——金圣嘆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自律與他律》(合著)等,另有《藝術終結論》等各種編著20余部,詩歌散文隨筆若干。現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及巴赫金研究分會秘書長、敘事學研究分會副會長。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