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七)
束曉靜、孫基林、馬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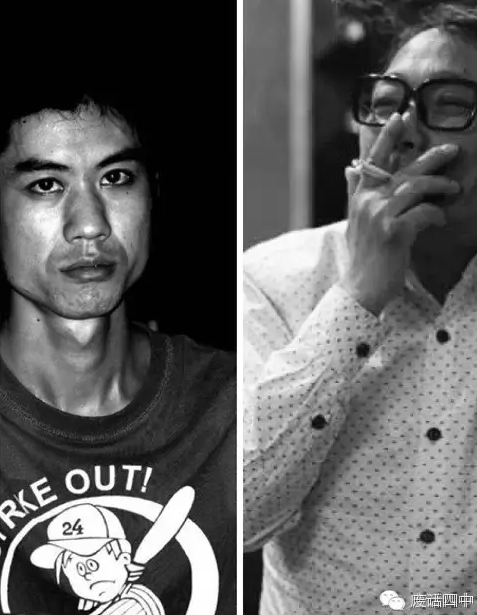
編按:
中國當代詩歌就是指新文化以來,中國的白話詩、新詩和現代詩。今年是這個詩歌的大日子!從胡適發表《新文學芻議》和他的一組白話詩,馬上就到一百年了。為了紀念這個日子,總結與研討,廢話教主楊黎帶著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中國當代詩歌微訪談。為什么說“非常有價值"?從所覆蓋的人群,問題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復一讀再讀。
微訪談覆蓋了老中青百名詩歌寫作者,楊黎采訪部分以老將為主,九如采訪部分以年輕人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血,編輯正在對訪談內容進行整理,陸續在四中首發。正在編輯中的《橡皮》5也會選發一部分,整體訪談最后會輯集出版。
感謝所有參與微訪談的詩歌寫作者。

束曉靜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我不清楚你所謂成功的標準。我覺得不算成功吧。在整個世界當代文學范疇里,中國的詩歌有影響力嗎?中國的詩人有發言權嗎?相比較于其他領域,藝術,音樂,體育,可能我孤陋寡聞,我個人感覺,中國詩歌的國際影響力略等于無。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對于“現代漢語”有什么準確的描述沒有?——方言算嗎?
要說當代詩歌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我覺得沒有。新內容應該是有的,比如說口語化在形式上簡化了現代漢語,在內容上豐富了現代漢語。我看到一篇文章說現代英語的常用詞匯量也很少,英語的口語更生動,但并沒有弱化它的表現力,更適用于今天的生活節奏。
古白話,我沒怎么看過。金瓶梅算不算?三言二拍算不算?我覺得很生動啊。要談本質區別,先要厘定什么是現代漢語吧。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沒那么糾結吧。可以借鑒藝術,當代藝術,現代藝術是怎么分的,詩歌本身也是藝術。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新詩100年,就大陸而言,也就前30年后30年吧,中間40年是斷的。我小的時候,讀過徐志摩戴望舒,后來讀點朦朧詩,北島舒婷,再后來讀臺灣現代詩,洛夫痖弦,周夢蝶鄭愁予,夏宇。在整個少女時代,我對大陸詩不怎么帶感,比較喜歡臺灣詩,因為小時候愛讀宋詞,那種氣息是一脈相承下來的。當然現在不一樣了。
拋開個人喜好放大到詩歌史上來看,我覺得要說有影響,至少要有2個標準吧:作品及寫作方式開一代風氣之先,對后來寫作者產生重大影響;有完整獨立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與作品互相印證。
對百年新詩有影響的人,楊黎算一個吧。他號稱“廢話教主”“一代宗師”,并不僅指他本人的詩歌與理論,而是因為他確確實實影響和改變了一代人的寫作,他那個橡皮寫作群生生不息,而且整體都很優秀,這個就是影響力。他是當之無愧的詩歌教育家。就個人的感受而言,他人詩合一,百年罕有。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沒有唯一永恒的標準,但可能有階段性的標準。我認為詩就是有內在韻律和神秘感的語言,可以分行也可以不分行,就像楊黎曾說過的,詩就是剔除了意義它還存在(此非原話,大意如此)。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為什么寫詩?找了個詩人唄。
寫詩的好處,和享用其他美好的事物是一樣的,與吃美食,看美景,欣賞藝術,和朋友聊天沒什么分別,我愿意寫的時候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上一個問題已經說了,我愿意寫詩的時候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對所有一切都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束曉靜,居南京,寫詩。廢話四中運營人。

孫基林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中國現代或當代詩歌沒有失敗,也不存在成熟不成熟之分,因為成熟總與衰敗相聯系。它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沒有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或把自己當作終點。對此,我尤為贊賞那不斷涌出的旗幟和隊伍,即使在一場戰役之后,也不會全軍覆沒或徹底走散……永遠的先鋒和實驗是它成功的秘訣!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說到當代詩歌與語言,如果從詩學的角度看,它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就是回到了語言本身。也就是從“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式的古典工具性語言觀而回到以語言為本位或本體的現代本體性語言觀。“詩從語言開始,到語言為止”,既揭示了它至始至終的語言屬性,也賦予詩歌從始至終的本質規定性。它是存在和詩的根性,就如詩歌最初發生時的那一聲“啊”,“啊”就是詩,詩就是“啊”,我們從始至終都不能出離“啊”而去理解和進入詩歌。或許只有從這種角度,才能理解當代詩歌給現代漢語所提供的新機制和新內容。至于現代漢語與古白話的本質差異,作為一個當代人,我覺得前者更能切近存在和詩性本身。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對于這些命名和概念,我也有過糾結和混用的情況。但我一般不用“現代漢詩”,總覺這有一點假洋鬼子的感覺,因為日本、韓國等國用漢語寫詩稱“漢詩”,我們總不能和他們一樣吧!當然我明白,“現代漢詩”有種指向現代漢語這種語言質料的意味,如從這角度理解,似乎有些語言的自覺;或許也與我們國家多民族語言的自覺區隔有關。而“白話詩”顯然是一個史的階段性的命名,它大多與五四和那個時段的新詩相關。“新詩”的合理性相對于古體詩和一直存在著的舊詩或古體詩的寫作,如果排除掉這個因素,僅就100年或未來更長遠的詩歌發展歷史而言,“新詩”概念的長久性也就有了疑問。余下就是“現代詩歌”和“當代詩歌”概念了,從國家層面的學科體系說,“當代”是涵括在“現代”之中的,比如“現代文學”包括“當代文學”在內;從社會學和文化層面而言,“現代”顯然也具有“當代”的意義。而“當代”不宜往前延伸得太過長久。從這些角度看,二十世紀或自五四以來的中國詩歌,可稱作“中國現代詩歌”,即使有些詩歌并不具有現代性,但也可理解為是“現代時代的詩歌”。而“當代詩歌”作為一個分層概念,或許指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詩歌更為妥適。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關于現代詩歌100年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段和節點上,都曾出現過為數不少的杰出詩人、作品和影響深遠的事件。相對于一些耳熟能詳的個體詩人、單一作品文本和詩歌事件,或許我更樂于從整體性,包括一個時代的精神癥候和詩學維度來審視、度量詩的歷史與過程。在大寫的人已然走下神壇的年代,或許任何個體都難能去創造一個時代,即使那些最為杰出的詩人,他們也僅僅只是發現、順應,然后拓展、推動了一個時代的進路。所以,如果從時代的精神狀況和書寫史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其意義就會有所不同。對此,我更愿意關注那些因思潮流派的發生、消漲所造成的潮起潮落的歷史波瀾與其狀貌,每個單一個體及作品、事件就如泛起的波紋和浪花,它們是那樣與整體連在一起。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很看重胡適的價值。雖然在那個年代不可說橫空出世,但他應時而起,并適時推動了100年白話新詩的發生與成長。包括郭沫若與他的浪漫抒情主義,聞一多與其新古典詩學,李金發、戴望舒等的前期象征主義,卞之琳等為代表的言智型現代傾向,還有艾青一度倡導的散文化詩歌美學。如果100年現代詩歌有高潮和浪頭的話,我看好五四前后二十年所形成的第一個浪頭。那確乎是一個詩歌獲取了自身并盡可自由探索和實驗的年代。真正屬于這樣的詩與時代的第二個高潮是新時期尤其是八十年代。這是一個具連續性而又斷裂的年代,因而有一個“誰的八十年代”問題。北島、舒婷、顧城們的八十年代,其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遠大于美學的意義;而“他們”、非非們的八十年代則回到了詩歌本身,開啟了中國意象詩學之后一個詩歌敘述美學的時代。因此這不僅標志著八十年代的斷裂,同時也是白話新詩100年歷史的斷裂,甚至是一整個中國詩學觀念的斷裂、發現和重構。在這一向度上,第三代詩歌回到語言、回到事物、回到生命自身的本體論詩學具有重要文學史價值,其中包括韓東、于堅他們的“詩到語言為止”、“拒絕隱喻”說,楊黎、周倫佑、藍馬等非非們“詩從語言開始”、反價值、反文化論述,以及在此一維度上一系列敘述性文本的實驗與書寫。九十年代詩歌知識分子寫作的敘事性,是對現實與歷史的一種回應和處理方式,同時也強化和拓展了另一類敘述美學范式,這在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孫文波和臧棣等詩人的詩學言論和文本實踐中有所體現。當下擺在面前并且也應給予持續關注的,還有那些后起的詩人們,包括安琪、黃禮孩們命名并一直持續推動的中間代、70后甚至80后們的詩歌觀念與寫作,他們如何在“影響的焦慮”中渴望突圍?在哪些方面幾近突圍成功?又獲得了怎樣的文學空間和把握現實與歷史的美學方式?這些都有待進一步回答。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開宗名義,在我看來,現代詩無須設定幾條標準。如你所說,古代詩歌似乎有標準,有規范,像七絕七律還很嚴格。即使到了宋詞、元曲,語句上雖也有了變化,但依然規定了一定的格式。現代新詩的革命和宗旨,首先在于打破這些規范、格式和標準,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自由。所以現代新詩從它誕生的那天起,“自由”就成了它的一種精神元素和基因。當然,如從另一角度說,它既然無須去限制和規約什么,那自然也就有設定限制和規約的自由。這似乎構成了一個悖論,然這正是它的真義和靈魂之所在。正如你可以寫一種天馬行空絕端自由的詩,也可以設定幾條規則或格式,去實驗那種有規范有標準的詩一樣。就是說在形式上,它并沒有一種唯一的永恒的標準和范式。但無論你寫什么,怎么寫,它都應該是詩!這就回到了原點和本質問題。尤其對現代詩而言,它不再是平上去入等等的行文特點問題,甚至也不再是玄奧華美的某些修辭,它是意味,是詩性,這才是最根本的。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對我,確切地說,應該是“你為什么讀詩?”或者“你為什么還把研究詩歌作為自己的志業?”寫詩,那是30多年前校園生活曾經的一種喜好,一種生命體驗方式。現在已難言以往,只滿足于閱讀、體驗或與這種有意味的形式對話。如果為了一種職業,或許我可以去選擇別的,可事實是,我與詩歌卻一直有機緣相守,這也許就是生命中難以拋舍的那一部分,就是這樣。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哈哈,詩與性,詩的力比多,它是詩人想象和行為的內在驅動力,脫不了干系的。還是看詩人們現身說法吧!
孫基林,詩學理論家與批評家。80年代初曾于大學校園參與詩歌活動,后留校從事教學與研究,第三代詩歌主要批評家之一。已出版《新時期詩潮論》(合著)丶《內在的眼睛》《崛起與喧囂:從朦朧詩到第三代》《青秋拾痕》(詩合集)丶《現代詩:講述與評論》等著作多種。

馬策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最大的成功在于純凈了現代漢語,證明了現代漢語有能力隨物賦形、賦形以象,展示了現代漢語的詩性心靈。尤其“第三代詩歌運動”以來,當代詩歌深入日常生活經驗領域,重塑了口語詩性。但不免一地雞毛,瑣碎蕪雜,得之于色,失之于自色悟空。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無論是白話詩、新詩還是現代詩,相對中國古典詩歌格律體而言,當代詩歌都是一種自由詩體,這是它的基本形式,或者說是新機制。就語言而言,一個是古代漢語,“之乎者也矣焉哉”是一個方便的形容;一個是現代漢語,它的基礎話語方式就是口語、說話。
但當代詩歌自覺意識到口語、說話的可能性,或者說真正確立了口語、說話的詩歌形式意味,始于“第三代詩歌運動”。當代詩歌如何“說話”?它首先拋棄了革命話語、意識形態話語、高蹈抒情習氣等各種語言方式,成就了基于個人化日常生活經驗的敘事性語調、語感。它既是態度的,也是口吻的,更是大方向性的。當然,它不僅僅指狹義的所謂“口語詩歌”,也包含某種注重心智、技藝方面的詩歌。它匯成當下詩歌主潮。也不妨說,當代詩之粲然可觀者多出于口語、說話詩。
第二問中,“古白話”應該上溯到什么時代算古?是指明清章回小說還是指宋元話本?我覺得從宋元明清,到胡適、陳獨秀1917年先后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掀起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甚至具體為白話文運動中的白話詩,都呈現出語體掙脫文言文向民間、通俗、淺近方面逐漸下沉的態勢。從白話到現代漢語,自由、解放是它的基本形象。
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因為一代有一代之語言。五四時代,白話文相對于書面語的文言文(古代漢語基本形態)來說就是口語或者說以口語為基礎的語言。此后,白話口語上升為新的書面語言。所以,方便起見,不妨說現代漢語其實就是口語。而白話詩,在當年充當了現代漢語語體探索急先鋒。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本質上乃是解放思維、革新意識、打破思想禁錮的語言運動,內在于近代(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民族國家現代性探尋之中。由器物、制度層面進入文化維度,構成這場現代化進程三部曲。
我不知道說清楚了沒有,當然不算什么“獨特的高見”。可以肯定的是,詩歌作為語言先鋒,它曾經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大打出手,非同小可。在后來的歲月里,“朦朧詩”、“第三代詩歌運動”依然在歷史中出手不凡。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這的確是個問題。但問題本身又有點讓我感到意外。這些亂七八糟的稱謂,的確有點亂七八糟,無非都是“新詩”的變奏性說法。但我還不至于認為“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至少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盡管,孔子講名正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那是有關君臣父子倫理問題。詩歌則不一樣。比如人們喜歡楊黎的詩,那是因為你寫得好,可能并不在意你曾經或正在頂著的“非非主義”、“廢話”這樣的名號、名分。順便問一下,“我們認為”,你說了好幾個“我們”,為什么是“我們”?我的意思是,“我們”好像不像你的用詞啊。
“必也正名乎!”好吧,這些稱謂復雜糾纏,其實不容易說清,倒是很容易把自己繞進去,我嘗試著厘清一下。
“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它們對應的詞語無一例外都是歷數千年的“舊詩”,也就是中國古代詩歌。為了獲得你所說的“最準確的說法”,“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一個一個排除似乎是最便利的方式。
我認為,首先應該排除的是“白話詩”和“新詩”。
(1)“白話詩”是中國當代詩歌(權且這么叫)之肇始,也代表現代漢語、現代文學之萌生。用它來指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顯然無效,有失準確。百年是一段時間歷程,現代漢語也逐步走向成熟。比如胡適寫的中國第一首白話詩《朋友》(又名《兩只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詩歌甚至還采用了古典五律詩體,只是語言相對于文言文而白話化、通俗化了,同時詩意(以兩只蝴蝶表達朋友關系)也不免打油化了。
五四一代作家比如魯迅語言的文白夾雜、聱牙佶屈,在當下中文世界尤其詩歌中幾乎絕跡,除非為了特殊效果,才會保留一些白話或相對古雅的詞匯。整個民國時期的文學語言,半文不白是常見現象,算不上標準的現代漢語。胡適等白話詩先驅的“嘗試”,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為現代漢語提供了巨大機遇。
(2)“新詩”的稱謂,失之籠統、含糊,也不足以指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新詩直接對應舊詩,但“舊詩”本身并非文學史概念。即便在舊詩所指的中國古代詩歌這一大稱謂之下,也有近體詩、古體詩之分,近體詩又分律詩和絕句,也可統領詞、曲。
在現代文學史上,“新詩”也不是文學史上的概念,比如1930年代規模巨大的現代文學選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它的詩歌卷直接叫“詩集”而不叫“新詩”集。有新詩,就會有新小說、新散文。這體現了文學史眼光嚴謹的一面。當然,“現代詩”、“當代詩”也很難說是文學史概念,它更多地屬于批評概念。或者說,它們都是文學的、批評的話語表述,而不是嚴謹的文學史的表述。
(3)其次,可以排除“現代漢詩”。我個人覺得,“漢詩”比較好聽,語感不錯,也很性感。但是,“漢詩”如果不是漢語詩歌的簡稱又是什么呢?所以它指的是民族性,相對于藏語詩歌、維語詩歌之類。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漢民族一股獨大,大學中文系全稱為“中國漢語言文學系”,它可能相對比如西藏大學的“中國藏語言文學系”(有這個系嗎)而言吧,暗示民族平等。平等而自覺,它多少表達了一點漢語言文化自覺的意思。但也沒有必要,因為在中國,漢語言不是自覺不自覺的問題,而是一種壓倒性的文化絕對優勢現實。比如,吉木狼格是彝族人,但他寫“漢詩”,如果寫彝族語言的詩歌,給誰讀呢?所以,現代漢詩的稱謂毫無意義,一個“漢”字,蛇足而已。以前好像有一本詩歌民刊就叫《現代漢詩》,難道這就是“現代漢詩”稱謂的源頭?我沒有考證。現在,武漢還有一本詩歌雜志叫《漢詩》。武漢簡稱漢,如果《漢詩》不是意在暗示它的出產地,我覺得也沒啥意思。總之,在一股獨大的中國漢語言文學世界稱“現代漢詩”,沒啥意思。
奚密有一本研究當代漢語詩歌的專著也叫《現代漢詩》(沒讀過,知道而已),她主要做中西比較詩學研究,本身任教于美國的大學,她的《現代漢詩》作為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詩歌的著作,名稱是合適的。總之,“現代漢詩”這個概念,比較適合在非中文世界使用。
(4)再來談談“現代詩歌”和“當代詩歌”。它們更值得一談。
首先,現代和當代都是傳統的文學史分期中的時間概念。比如,中國現代文學一般指1917—1949期間的中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一般指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當然包括當下正在發生的甚至后來的中國文學。
但“現代詩歌”的現代,不僅僅指時間概念,更多地強調詩歌的現代性,這就涉及到觀念。當然,即使在時間概念上使用“現代”這個詞,也是相當適宜的。我想這樣理解:現代是世界進化論的某種概括。我們要討論的主要是“現代”對詩歌的概括力,不妨從詩歌如何回應、想象“現代”著手。現代的確是一個無限遼闊的世界。但我們只是詩人,不是研究現代世界的學問家,只能像胡適“嘗試”作白話詩那樣嘗試理解現代。
從進化論視角來說,現代世界屬于科技進步的世界,而科技改變人的時空觀,改變人對整個世界的觀感,包括對人自身的認知。相對于現代世界,它之前的世界被稱之為前現代世界。可見“現代”一詞的高度概括力。從一般認知來說,現代世界始于18世紀中期以后的西方工業革命。中國明朝滅亡于17世紀40年代,也就是說大致在清朝乾隆皇帝時期,世界已經徹底變天了,開始進入到現代大時代,即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它的驅動力是科技,或者說最初是機器。以后是后工業/信息化時代,今天是全面的全球一體化時代,差不多也是個唯科技時代。
我們甚至可以說歷史就是、只是現代史,因為世界是不斷現代化的。前現代是被淘汰了的,是過去時,而現代是工業革命以來的進行時。世界是屬于現代的。更主要的是,“現代”還暗示了“現代性”這一大觀念,它對應的就是這個龐大復雜的現代世界。現代性總是不斷朝向前面,朝向未來敞開的。簡單來說,前現代中國只有三個世界:儒的世界,道的世界,釋的世界。比如說在唐朝,三個世界對應三個偉大詩人:詩圣杜甫、詩仙李白和詩佛王維。沉郁擔當使杜甫成圣,飄逸放曠使李白成仙,寄情山水意在言外使王維成佛。前現代世界是軸心化、中心化的世界,相對于復雜的現代世界,它無疑是簡單的、純粹的:觀念簡單,知識純粹,因而人心純凈。他們雖然偉大,有能力關懷社會(權且包含懷古詠史詩),關照自然(權且包含詠物言志詩),但很少關注自己的生命本體,也就是說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個體存在感在前現代世界詩歌中是缺失的,充其量來一點即事感懷(懷親懷友)。這就是前現代詩人的能量。
接著談現代世界。首先,“現代性”處在不斷的生成中,被不斷地要求回應現代世界、現代人心的復雜性。相對古代世界的靜止、精致,“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現代世界簡直是一塊中心坍塌后的野地,它的鏡像支離破碎、變幻莫測:它的無聊無力、它的虛妄,它的瞬間性、邊緣性,它的不完美,它的物質主義的短暫性、它的無窮無盡的欲望、它的朝生夕死的幻滅感、它的悖論化生存、它的個人化、內向性等等——總之,現代世界實質意義上的存在感,有待被詩歌重新命名,被語言重新整合、重新發現。這就是現代詩歌、現代漢語的嚴肅使命。
現代世界有無數個,因為現代人是原子化的,現代詩人不僅要回應風吹鳥鳴,更要回應現代世界(唯科技、復雜的知識觀念系統)帶來的心靈顫栗、眩暈。如果杜甫、李白、王維穿越到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他們將如何寫詩,如何呈現一個“現代性”的杜甫李白王維,這也許是留給現代詩人和中國現代詩歌的巨大懸念。
(5)終于可以談論“當代詩歌”了。“當代”仿佛現代的一個變體,但遠遠不如現代性感,它從屬于現代。說清了現代也就說清了當代。所不同的是,當代更傾向于時間概念而非詩歌觀念。我們說,我們正處在現代世界,這是一種傾向于觀念的介說;我們說,我們正處在當代,這顯然是個傾向于時間概念的介說,大抵多指當下性。當代即現時代,即當下。
當我們強調詩歌觀念時,“現代詩歌”一說是有效的;當我們僅僅想表達時間概念,“當代詩歌”一說也是有效的。另一方面,當代(當下)世界內在于現代世界中,換句話說,現代包含了當代這個時間概念,同時顯明了觀念,所以我覺得“現代詩歌”這種說法比“當代詩歌”說法要好,要更恰當。
在你列出的諸種稱謂中,我傾向于認為“中國現代詩歌”這個說法比較靠譜。關鍵是,它還具備回溯能力,可以溯及百年詩歌史中那些具備現代性的詩歌,比如馮至、穆旦以及1920年代“象征主義”詩人李金發、1930年代“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的作品,如此等等,可以將它們統一打包稱之為“中國現代詩歌”。而新詩草創時期的作品,比如胡適等人的詩歌,就不在這個稱謂之內。同樣的道理,當下寫作的并不具備現代性的詩歌,它們也只好被打發進“當代詩歌”。怎么說好呢,“中國現代詩歌”其實是中西方兩個世界知識觀念交匯的語言現象。
另外,“第三代詩歌運動”以來,我們還有所謂實驗詩歌、先鋒詩歌之說。在觀念上,它們同屬于“中國現代詩歌”。你也許會同意:對語言而言,好詩,甚至一切詩歌,其實都具有實驗性質。一切詩歌都應該是先鋒詩歌,因為詩歌就是先鋒語言,或者說語言先鋒。而偽詩、壞詩不在此列。
(6)由此可見,“中國現代詩歌”概括力相當強。但如果不那么著眼于觀念,比如把1917—1999的詩歌稱之為20世紀中國詩歌,把2000—當下及其以后的詩歌稱之為21世紀中國詩歌(它與網絡時代的詩歌同步,按韓東的說法是自由寫作時期的詩歌),也無不可。這種稱謂看上去相對中性、客觀。世界真的很復雜,我也“費了許多腦筋”,我也“真的很迷茫”……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這也是個大而復雜的問題,頭緒萬千,難以理清。說來慚愧,我對百年詩歌史不夠熟悉,也記不住那么多東西。但是,我感覺盡管寫了整整一個世紀,白寫的時間多,無效的詩歌多,詩歌現象紛紜復雜,現代漢語詩性塑造的有效呈現卻還是晚近的事實。
朦朧詩之前就不談了。朦朧詩作為“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的確是詩歌史上的重要創獲。它們初次整體性實現了詩歌意象、修辭、結構等詩意生成諸多要素的完型化,成就百年詩歌第一座高峰。
隨之而來的是“第三代詩歌運動”的汪洋大海。它們不斷沖刷朦朧詩群抵抗詩學或者文學的政治學的基座,使詩歌前所未有注重個人語言意識。臧棣曾經認為“后朦朧詩”(也就是“第三代詩歌”)的主要美學傾向乃是“歷史的個人化和語言的歡樂”,當年我讀到這個觀點的時候,激賞不已,至今我還認為這是個相當高明的見解。
“第三代詩歌”大潮領軍詩人韓東,一方面稱北島“長兄為父”,一方面對北島們的詩歌美學反抗決絕。他的《有關大雁塔》一詩,寫于1980年代最初,因為清理了政治、文化、歷史重負,從而預告了新的時代文學氣候變化,把握了新的歷史方向。韓東所謂“三個世俗角色”政治、文化、歷史的盡頭,正是他的詩歌出發之地。概而言之,韓東乃是“第三代”源頭性詩人,而《有關大雁塔》實為“第三代詩歌”之冠冕。
在公共閱讀和詩歌史視野中,《有關大雁塔》都是韓東的絕對代表作,盛名如雷貫耳。因應改革開放、重思意識形態之時代征候是一個方面,所謂時勢造英雄;對現代詩歌還原日常生活、回歸語言狀態的特別領悟,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所謂英雄造時勢。韓東是中國現代詩歌名至實歸的詩歌英雄。尤值一提的是,韓東初出茅廬就身手不同凡響,而他的詩歌三十多年來始終維持在高水準平臺上,佳作紛呈,鮮有壞詩,差不多為當代詩人所僅見。他的詩往往簡約、深入、生動,小而精,而純,而美,深可玩味。拿他近年一首詩名做比,他的詩有如“清淡的光”。在我看來,他最擅長捕捉人們渾然不覺的日常生活事態,善于體察人與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比如作于1986的《常見的夜晚》、《你的手》等,不勝枚舉),也善于做自我精神省思,語言精微,詩意純凈,這正是韓東式的純詩。韓東也正是那種詩心惟微的詩人。因其哲學系背景,詩歌不免沾染冥思的氣質,尤其近年作品,對人生色相之虛空多有體悟。這當然好。
他看見別人眼中忽視的事實,然后說出他獨到的事理。詞即是物,詩即是思。韓詩如此。不是說詩分唐宋嗎?錢鐘書就偏愛宋詩。打一個不那么恰當的比喻,我認為韓東寫的是當代宋詩,而且是寫得最好的,實為我個人所偏愛。
楊黎。在“天才詩人”、“詩歌無冕之王”、“一代宗師”(韓東語)面前,沉默是適宜的姿態。的確需要沉默,的確應當沉默,楊黎已被眾口談論太多,偶爾有毀有憎,我當然站在譽一邊、愛一邊。他企圖發明系統語言理論整合詩歌寫作,不免糾纏于觀念(從“非非”到“廢話”),其實并不為觀念所縛。通常,詩歌理論與詩歌寫作就像兩個相互眺望的平行世界。楊黎不僅不為觀念所縛,甚至剝離全部觀念,根植于心的只有語言本體意識。楊黎是中國現代詩歌的特殊景觀。
在他的全部詩歌中,影響最大者,可能還是早年的《撒哈拉沙漠的三張紙牌》。這是一首絕對的語言之詩,神秘而又空虛,特別具有“文本”意義,當屬中國現代詩歌一個特別案例。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首從語言出發的詩究竟能夠走多遠?世界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說,現代詩歌的最大功效在于喚起,喚起我們對存在可能性的種種認知,那么這首詩及時地、經典地將一面存在之鏡遞到我們手上。它完全向閱讀敞開,許諾各種解讀方式自由穿梭于其間,大抵如同史蒂文斯所謂的詩歌乃“最高虛構筆記”,同樣契合史蒂文斯所謂的“世界的迷人之處正是世界本身”——哦,這是廢話。盡管該詩誕生的時候,楊黎還遠遠沒有發明“廢話理論”。
因為名動江湖的“廢話”理論,楊黎又獲“廢話教主”封號,皆因他既是“廢話”理論發言人,又是“廢話詩歌”瘋狂書寫者,而且追隨者日眾。曾經一度舉行全國巡回朗誦會,他的成都方言詩歌朗誦又是一絕。近年主持出版“廢話”成果雜志《橡皮:中國先鋒文學》和“橡皮詩叢”,并創立“橡皮文學獎”。始于今年元旦,楊黎堅持每日一詩(有時甚至是五、六首)的微信“詩日記”寫作,又堪為創舉。楊黎是個永恒的傳奇,楊黎現象業已成為中國現代詩歌場域奇觀。說到“教主”,不免想起白居易。據《唐詩紀事》載,晚唐詩人張為撰《詩人主客圖》,將唐代詩人按作品內容﹑風格分為六類,各以一人為主,白居易列為第一類詩人之首,尊稱為“廣大教化主”。“詩到元和體變新”,同樣的,詩遇“廢話”,體亦為之一新。楊黎白居易之間,還真有一比。更不妨說,元白新樂府詩派尚通俗淺近,務實務盡,打破詩歌創作神秘性,而且白居易屬于高產詩人,一生寫有三千多首詩,幾乎冠蓋唐朝,諸如此類,楊黎的“廢話詩”亦差堪比擬。白居易當年一直為時俗所重,為人之所愛,楊黎亦復如是。
楊黎的“代表作”很多,重要的是好詩很多、太多,尤其是大量短詩,鋪天蓋地。詩遇楊黎,往往脫口而出,渾然天成,《大聲》是最好的證明……我還想說的是,楊黎本質上是個溫柔憂傷的抒情詩人,這一點跟“廢話理論”其實并不沖突,但人們往往被這個霸氣側漏的理論所誤導,不易覺察。視野所及,在中國現代詩人中,楊黎一直是最讓我抱有期待的一位,期待的理由無非是他的變化和可能性,到目前為止,這一期待尚未落空,比如他的長詩《錯誤》、《成語》。
于堅,屬于大刀闊斧刪繁就簡、“拒絕隱喻”還原生活的詩人。長槍短炮并舉,既粗礪又不乏溫情,時而泥沙俱下,使他的詩歌整體呈現出蒼茫的面貌。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他一而再地對云南高原風物的描繪,賦予地方性知識以詩意的普適性。
跟韓東楊黎一樣,于堅也是寫作起步早,持續時間長,好詩跌出,值得整體閱讀、追蹤閱讀。持續地閱讀他們的詩作,正如《在漫長的旅途中》(于堅詩),一路上不時看見燈光閃爍,遠遠地,在山崗在荒野,有時又在身邊“穿過樹林跳過水塘”,“使黑夜的大地,顯得溫暖而親切”。好詩總能惠賜生活一劑特殊的安慰、補償乃至治愈。
以上談到三位我格外喜歡的“第三代詩歌運動”中的重要詩人,假如沒有他們,幾乎就沒有中國現代詩歌,談論這一百年,也就僅僅是談論時光流逝,剩下的就是對時光流逝的惆悵。他們的影響是源頭性的,至關重要。才三十多年的事,在他們之后,中國現代詩歌好歹有底氣了。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中國古代詩歌的標準主要就是格律形式。標準也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是格律獲得了詩,約束了思。因此就有了白話詩的沖動,想要解放思想。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免“先驗的迷惑”,而百年實驗正是現代詩不斷確立自身的過程,因此就有了如今的詩歌形式。我們所感知的現代詩歌標準就存在于這些詩歌形式中。存在是具體的,正如詩歌是一首一首的,每一首都是一個形式,都在具體地暗示詩歌標準。只能是暗示。
這就好比世上并沒有“水果”這個事物,但你可以在蘋果、梨子、西瓜、桔子中部分地找到“水果”。詩歌的標準不是一,而是“雜于一”。詩歌的標準也不是物理度量衡似的標準,不是體制似的外在標準,而是內向性的。詩歌既然是語言形式、聲音形式、心靈形式,也就只能悠然心會了。
但是,現代詩歌到底要不要確立一個類似古代詩歌的標準?應該不需要,也不可能。時代不同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依然可以回到我在上面談論的現代、前現代問題上。格律詩是什么?我也沒有答案。那就只好在蘋果、梨子、西瓜、桔子中找水果了。詩歌可以被顯現,但的確很難定義。無怪乎維特根斯坦會說,“對于不可言說之物必須保持沉默”。他又說了,“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樣的,而是它是這樣的。”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的《道德經》其實就是一部詩集。有必要分行閱讀《道德經·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最初是基于個人興趣,后來是逐漸強烈的興趣。迷戀詩歌這種語言形式。我當然知道,在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里,立德、立功、立言意味著人生三大不朽的事業,所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至少在前現代中國,這三不朽歷久不廢,百世流芳。曹丕也說過,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些都意味著有限人生中的絕大價值,想來并非凡夫俗子可以作為的。同時,中國向來號稱詩的國度,有著漫長的詩教文明傳統。但這些大詞既有效也無效。世界早就變了,變得越來越事功化,人生的意義被具體到現實功利事務中,奮斗意味著一切。我這么說,僅僅是想到就說,說說而已。寫詩當然對我有好處,我活在這個世界上,想通過詩歌的語言形式看看自己的模樣,看看自己存在的模樣。在沒有任何特殊的附帶條件下,我寫詩只針對我自己,實屬自我認識,自我清理,自我對話。自我是接納世界確切有效的唯一的容器。自我的面貌決定世界的面貌,世界并不自外于自我。但話說回來,要做到這一點,方式何止寫詩一種。詩歌畢竟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當我需要用詩歌語言來想象、確證自我秩序、自我存在形式的時候,我就寫詩。這時候,詩歌是一種抵達,詩歌就是自我的光、自我的鹽。努力加餐飯,努力寫好詩。謝謝你的提問。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不回答了。
馬策,詩人,批評家。著有詩歌及評論文字若干。且居南昌。
第八波:祁國、張執浩、高星 敬請期待
全部微訪談版權歸“廢話四中”所有
轉載請聯系編輯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謝謝

長按二維碼,關注楊黎束曉靜“遠飛”詩日記

編輯:@窈窕束女 athenashua
投稿郵箱:351607@qq.com
來源:廢話四中(原創)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