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九) 劉不偉,郎啟波,尚仲敏

編按:
中國當代詩歌就是指新文化以來,中國的白話詩、新詩和現代詩。今年是這個詩歌的大日子!從胡適發表《新文學芻議》和他的一組白話詩,馬上就到一百年了。為了紀念這個日子,總結與研討,廢話教主楊黎帶著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中國當代詩歌微訪談。為什么說“非常有價值"?從所覆蓋的人群,問題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復一讀再讀。
微訪談覆蓋了老中青百名詩歌寫作者,楊黎采訪部分以老將為主,九如采訪部分以年輕人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血,編輯正在對訪談內容進行整理,陸續在四中首發。正在編輯中的《橡皮》5也會選發一部分,整體訪談最后會輯集出版。
感謝所有參與微訪談的詩歌寫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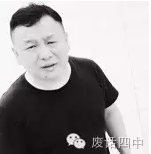
劉不偉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哇,都一百年了,好年輕,活脫脫歡歡的小后生。在成功的人看來非常成功,一百年的寒來暑往一百年的風花雪月剛剛讓詩成為詩。那在不成功的人的角度看就是一坨,為什么會一坨?因為也不能說他看不懂,他只是看不明白,慧根一丟丟。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自由,不僅僅是語言、文字、表達形式等方面,我更看重內心的自由,原創性的書寫,生命力的釋放。中國有很多古語、俗語、諺語、警句以及名人名言,百分之八十都是所謂的經驗之談,這些經驗之談是有毒的腐朽的是不靠譜的是時過境遷絕對靠不住的必須刪除消滅徹底格式化,并且這些腐朽的有毒的渣渣與時代與當下生活是一種南轅北轍拉扯著的悖謬。很幸運這些語言的渣渣正逐漸被清洗掉,新詩功不可沒。
詩言志,文載道。詩可不可以不言志,文可不可以不載道?詩文萬種,不尊獨則。可否。為什么不可以大張旗鼓地去務虛,去打探生命之深幽宇宙之空無。是的,一切阻擋都是反動都是虛妄。而更幸運的,還好,我們聽到一種聲音,“我寫,故我不在”“詩啊!言之無物”(楊黎)這聲音由遠及近由聲至波,以微而至微的斜刺里插入洞穿語言的秘密,提拉起新詩一個新的高度維度并從容敲打哲學的窗玻璃,令探索成為可能,令詩歌精神有了精神,令漢語有了新的質地與硬度,大不易。反對不僅僅需要勇氣,勇氣不值一提,有勇無氣不成大氣,氣者,深諳此道。無實力者折之難騰。我為這詩歌的反對派鼓掌。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是的,多年來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成亂燉模式。這個命名,嚴重燒腦。問的文字里出現了“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有點長,我就選新詩吧。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白話詩運動、七月派、天安門詩抄、朦朧詩、第三代、86年詩歌大展、盤峰詩會、楊黎極限寫作、蘇非舒裸體朗誦、下半身寫作、梨花體、詩江湖被關停、烏青體、十詩人電影公司等等太多不一一羅列。詩人和詩歌作品也是太多了不列了。關于詩的言說依稀記得周倫佑的紅色寫作、沈浩波的下半身寫作。有價值有發展的詩的言說我推薦楊黎的關于詩的所有言說,尤其是他的近作《我寫,故我不在:一個廢話主義者的廢話語錄》。同時推薦法清的新型詩說法。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有標準。但是,標準扼殺詩。絕對的標準不存在。放開了寫。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是啊,為什么?宿命吧。控制不住啊,不寫不行,不詩歌不成活。往玄了說,詩歌是一種生命哲學。或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生存伴侶,一種人生信仰,一種詩宗教。好處是:內心的圓滿與自在,詩友在一起的歡快與暢飲。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有過,然后又沒有了,再然后又有了。像做愛一樣去寫詩,這詩寫的估計很性感。像寫詩一樣去做愛,這一炮估計很詩。
劉不偉,本名劉偉。69年生,遼寧鞍山人。詩人、網站編輯。現居呼和浩特。

郎啟波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個人以為,當代漢語詩歌的成功之處在于消滅了權威和格律詩遺留的語言壁壘,在多形式多層次的探索促使讓身處集權語境中的漢語呈現出更多的可能性;失敗之處是多數的詩人主動放棄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與義務,而讓一大部分詩歌成為看起來更高級的語言段子,或淪為更大的虛無。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當代詩歌提供的最好的機制或可能便是官方語言權威的削減,小圈子的話語壟斷和標準的建立已經成為不可能,因為他們面對的是移動互聯網和民間的自覺,互聯網的泥沙俱下卻也讓官方體系茍延殘喘,當代漢語詩歌如果說提供了新的內容,那應該是對漢語的重建,盡管是少數人但也足夠強大。現代漢語與古白話的真正本質是一樣的,只不過脫節了,今天我們官方語言的普通話是清朝的滿人漢語,表達和發音都早已經天壤之別,有時回想起來小學中學老師講述格律詩的情景,已經成為莞爾一笑的回憶,他們的誤讀和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和詩歌無關。所幸我們還遺留各地的方言,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到舊時的白話與此刻語境的異同,才會因此有在學術上彌補,也因此逐漸認識到我們的前路為何漫漫。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多年前,我們決定將《審視》定位為“漢語詩歌寫作年刊”的時候,我和《審視》其他同人們已經很明確我們自身的寫作和刊物關注的是當下的和當代的“漢語詩歌”寫作。漢語詩歌的說法或許還是籠統的,但可能也是最準確的,當然這個說法也并非是命名。我并不認為沒有一個好的命名會是多么大的隱患,在更久遠的漢語詩歌的高峰的唐宋時期,詩人們也沒有絞盡腦汁去尋找命名,而最終被后人用時代去進行了定義,那么,當下的漢語詩歌寫作最終也可能得到的共同名稱會是諸如“共和國時期詩歌”之類的么?我認為真正的隱患是那些自認為掌握官刊詩歌話語權的家伙們對于詩歌的操縱對于更年輕寫作者的影響。所幸的是,我們身處在互聯網的時代,話語權和表達權已經不只是屬于一小撮人,這是當代寫作者不幸之中的幸事。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這一百年漢語詩歌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文革,朦朧詩出現的前三十年幾乎是漢語詩歌在大陸休克死亡的三十年,而即便是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文革帶來的消極影響仍然甚大;另外一個對詩歌產生消極影響的則是汪國真的橫空出世,將若干青少年帶入歧途并讓他們相信詩歌就應該是那樣的,深究汪詩流行的背后,你會發現此類以詩歌模樣出現的心靈雞湯在較長時間里起到的是維穩和對想象力的麻痹。第三代人的出現是具備積極意義的,在他們成為主流之前,他們代表的是那個時期的先鋒和創造力,而當第三代人在成為主流之后,多數都變成他們曾經要反對的人。徐敬亞操持的詩歌大展,像潘洗塵這樣的詩歌義工,世中人這樣的民刊收藏家,伊沙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新詩典”舉措,等等都是有價值并值得尊重的,;關于詩歌的言說,當我試圖去厘清思路時,發現記得的是失望的、分裂的、破壞的一些,多數人都試圖告訴別人并證明自己的見解或寫作是最佳的,但除了在頭銜上獲得“著名的”并時刻出現在各種研討交流活動上,此外抱歉看不到他們對于人類公共事務上的表達,更多呈現的是自私自大和存在感里,像水蛭那樣。至于名字,記得一大堆著名的,也記得不少無聞的,我認為說出來沒有什么意義;至于作品,能記得住的,那就少之又少。一百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此刻還不到去真正定義并定論這百年漢語詩歌和詩人的時候,起碼現在的語境和環境都不是恰當的時機。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你怎么確定“古漢語詩歌”(我覺得這樣說比“古代詩歌”更妥帖)不是白話?我們先來看看人類的語言發展過程:先是從識圖開始的,在有了聲音語言后才有書面文字的,我們今天能讀到的《詩經》中的好些詩作是先有詩歌而后再被整理記錄下來的,你能說那不是古漢語白話?致于詩歌的標準,我想是它是存在的,但它不會也不可能提供標準的配置參數,無論是寫作者還是讀者,他們都會有各自不同的判斷和標準,這標準便取決于他們的性格、學識、想象力、價值觀、及美學等多個方面的能力。批評家和理論研究者們似乎試圖建立一套可以廣泛適應的詩歌標準,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消滅個性和謀殺想象力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們應該警惕的是任何試圖確定一個詩歌標準本身就是在繼續消滅個性,這與詩歌的自由和個體化體驗是完全對立的。古漢語詩歌也沒有一個大而全的標準,他們建立的是一種書面語言的限制條件,諸如平仄對仗的格律和韻腳等,我個人更原因將這些視為古人對于詩藝探索后獲得了一種恰當的形式。如今的漢語詩歌更加不需要建立標準,但會形成一定的共識,你懂我的意思,我想強調的重點是:d一個真正的詩人必然擁有獨立的人格和悲憫之心,他們對于語言有天然的能力,不受思想的禁錮,不回避作為知識分子的道義和責任。說到這里,也恰好簡單取說我理解的詩是什么,“詩”首先是一種狀態,“詩人”是一種人格追求,“詩作”是一種節制的智力勞動成果,詩歌的魅力在于詩人將個體的體驗進行美學的重塑,這過程是詩人自己完成的,其最終價值與意義取決或受限于詩人本身之于時代的意義,詩歌和其它文學藝術作品一樣承載了第二歷史的作用,最終詩歌和詩人都逃避不了時間的審判。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這么多年,我幾乎很少與文學圈尤其詩歌圈的人有深入的交往,一來是盡量保持一種適度的距離,以免自己無意間陷入一個是非之境,再則這樣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獨立。除了早年間因為工作關系不得不與人打交道外,我從來不會去拜訪任何所謂著名人物,我篤信有緣自然會遇見,我也相信有一些人注定會成為朋友的,不管什么遇見的時間長短。這么多年來,我更多的時候是一度自己為敵,與自己較勁。
6歲那年,我在滇東北一個山村里念小學2年級,我第一次寫下幾行句子后,瞬間有一種電流穿過我的全身,讓我為之興奮不已。我開始為自己找到這樣一個能讓自己很舒服就去完成的文字體例感到自豪,并在那時取了一個筆名“野愁”,那時我還不能真正明白詩歌意味著什么,這一寫就是就過去了三十多個年頭。我幾乎從來不改動自己的詩歌,錯別字的改動當然除外。除去多年前我曾燒毀掉不復存在的大部分少年及兒童時期的詩歌外,有幸留存下來的不少少年之作也原貌呈現。
詩歌對我而言,早就是血液般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我從來都認為詩歌首先的意義是對自己的,我無意聽從誰人的勸告也從來不考慮這些文字會帶給別人什么,我需要的只好好活著,是好好做人,然后完成自己,如此足矣。
2014年秋天,我在《審視》的卷首里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想一而再地拿出來與大家分享——“歷史是可以虛構的,但——作為知識分子,詩人是一個時代的良心和脈搏,在他們寫下的詩句里,無不記錄著他們身處時代的各種痕跡與線索,無論這些詩句是抒情的、敘事的,又無論這些詩句是經過精雕細琢的還是即興速寫的,都將會佐證他們身處時代的語境,并幫助檢驗出歷史中被修飾和虛構的部分,他們和他們的作品無法與時代剝離;數千年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命運多舛,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近代的譚嗣同,再到后來的因言獲罪者,盡管知識分子普遍遭遇和處境艱難,對于詩人而言卻是創作的最佳時期,然而他們的作品是否配得上肉身和精神所歷經的苦難?又或者說,當代的詩人有無更多的擔當去完成知識分子的使命與責任的部分,這一代人是否會將迎來自己的榮光,又或者被釘在恥辱柱上,一切都還在路上,我們走著瞧。”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當然有影響。不過帶來的影響都是積極向上的。(笑)
郎啟波,寫作者,生活家。幕客影視聯合創始人;70年代末生于云南鎮雄。策劃電影作品有《老那》《向北方》,紀錄片《詩行天下》等;著有詩集《蝸牛記》《部分郎啟波》,合寫有電影《精武風云-陳真》同名小說。

尚仲敏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我認為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詩歌不再晦澀難懂,不再曲高和寡,詩歌已經不是什么,又什么都是。當我看到楊黎把一代網吧青年變成廢話詩人時,我就在想,這是一個多好的時代啊,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詩歌變得簡單、通順、可愛、高潮迭起,但仔細一看,又什么都沒有。而另外一些詩人,偏偏要站在詩歌的反面,寫一些復雜的詩,一些看起來更象詩的詩,這些人,雖然只是一小撮,卻把詩人變成了碼字工人,把詩歌變成了制造業。我想說的是,讓他們去裝逼吧,在當代詩歌的康莊大道上,我們繼續一路狂奔。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中國當代詩歌使現代漢語更加逼近世界的本質,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認知世界的捷徑;我們一直困惑的問題,在寫詩和讀詩的過程中,變得水到渠成、豁然開朗。漢語在詩歌中,也只有在詩歌中,呈現出了它可愛、透明、干凈、清純的一面。所以說,當代詩歌為漢語提供了一種新的過濾和提純機制。現代漢語和古白話的區別,就像“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的區別一樣,前者使我們的人生充滿幸福和愛,使我們活得輕松而快活;而后者則使我們活得苦大仇深,使我們的心靈沉浸在苦澀、繁復、艱難的茫茫黑夜之中。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我覺得還是叫中國當代新詩好一些。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新詩100年以來,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有:1,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反舊體詩形式上的各種限制,在音樂性、建筑美和畫面感方面,給新詩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2,“解放”初期,艾青、臧克家、孫靜軒等一批“革命詩人”,他們雖然寫了很多頌歌式的詩篇,但其中也不乏象《大堰河,我的保姆》這樣的好詩。這些革命詩,客觀上使新詩在語言形式和內容表達方面,又向前邁了一大步。3,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以北島、舒婷、芒克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使新詩真正貼上了“現代派”的標簽。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大量使用意象、隱喻、歧義等現代派的表現手法,把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不折不撓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不能說不是新詩的一大進步。4,80年代后期到現在,所謂的“第三代詩歌”對“朦朧詩”進行了顛覆性反叛。韓東的《大雁塔》,于堅的《作品11號》,楊黎的《冷風景》及廢話寫作,徹底拋棄了以往的詩歌傳統,使詩歌回到語言本身。詩歌不再承載種種道德說教、人生意義、哲學思考,詩歌從語言開始,又到語言為止。可以這么說,中國詩人摸索了近百年,終于知道了什么是詩,終于使詩歌成為了詩歌本身,而不是別的什么。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說到詩歌的標準,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可能沒有人能說的清。我只能說,好詩是有標準的,而鋪天蓋地的壞詩,似乎誰都可以寫,你看有多少詩人,寫了幾十年的詩,出了一大摞詩集,你要說他寫的是詩吧,卻又沒有一首是詩;你說他寫的不是詩吧,他又孜孜不倦地寫了這么多,甚至還寫出了名氣,還很著名。我只好說,寫詩是他的權力,我們可以不看,我們必須捍衛人家寫詩的權力。
壞詩各有不同,好詩卻有共同的地方,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標準。
好詩,我認為,必須讓人一看就懂。我為什么愛看于堅、韓東、楊黎、何小竹、狼格的詩,在他們那里,我發現了一個標準,那就是,他們的詩,我一看就懂。但他們都寫了什么,為什么這么好,我又說不清楚。進入2016年以來,楊黎每天都在寫,我也每首必看。為什么要看?因為看起來很舒服。那么問題來了,好詩的另一個標準,就是,讓人看起來舒服。而有的詩,就讓人看起來很傷腦筋。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我在什么情況下寫詩?在非寫不可時,一首詩就誕生了。而光是等待這個非寫不可的時刻,我就耗費了漫長的歲月和為數不多的激情。詩歌不是制造業,詩歌是一項天賦的偉大事業。一個人如果不具備這項天賦,還不如去干點別的。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我曾寫過一首詩,叫《詩是什么》,最后一句是,“詩就是,你遇到一個美女,就對她說,有什么事,我們躺下再說”。不知道這能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尚仲敏,大學生詩派發起人。第三代代表詩人。
第九波:潘洗塵,彭先春,李霞 敬請期待
全部微訪談版權歸“廢話四中”所有
轉載請聯系編輯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謝謝
往期回顧: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一) || 于堅、譚克修、小安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二) || 孫文波、周亞平、李亞偉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三) || 韓東、春樹、徐敬亞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四) || 余怒、楊小濱、湯巧巧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五) || 俞心樵、葉匡政、文康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六) || 邵風華、不識北、而戈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七) || 束曉靜、孫基林、馬策
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八) || 祁國、張執浩、高星

長按二維碼,關注楊黎束曉靜“遠飛”詩日記

編輯:@窈窕束女 athenashua
投稿郵箱:351607@qq.com
來源:廢話四中(原創)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