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凸凹:敘述的速度之美
在周李立小說集《透視》(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中,作者此前寫小說的手法與特點依然熠熠生輝、存于其間——這構成周李立作品的地標式符號。也有異處,就是此前她慣用的那些西化長句、讀來令人像登山一樣喘氣不休的結句手法不見了,代之的漢語傳統的造句策略與習慣。
集子收入兩個中篇(《火山》《另存》)、五個短篇(《去寬窄巷跑步》《透視》《酋長》《他們家的暖氣》《天使的臺階》),其中,北京藝術區題材三個。《火山》中,文亮的父母通過假認親入了日本籍且無法回國,文亮留在東北老家由奶奶、姑媽帶大,靠父母源源不斷的隔海匯款過著滋潤可炫示的生活。他去過兩次日本,一次遇到火山爆發,一次遇到人為的“火山”——他在兩次火山爆發中痛苦憤怒,并緩慢成長。《另存》中,喬遠、娜娜、蔣爺、于一龍等人捆綁在“朗波蒂現代藝術展”的平臺上,從策展到開展的衍進,推動故事發展,呈現畫界的功利浮躁、畫家喬遠的藝術堅守及道德底線。《去寬窄巷跑步》提供三個不同年齡女人的愛情標本:理性的、癡迷的、抑郁的。《透視》說的是災難殘留在當事人日常生活中的余震。《酋長》展示對既有追求的不舍、對現實的無奈與屈從。《他們家的暖氣》講述一位南方女子對北方物候的敏感和不適,以及由此牽連的命運轉折。《天使的臺階》以“天使的臺階”為道具,用兩代人的愛情歷程表達有傾向性的婚姻觀。
周李立小說的藝術長項是多方面的,但最能說服我的,是其敘述的速度之美。速度并非節奏,因為速度比節奏更細密、精致和理性。從泛速度的視域看,速度大于節奏。節奏只是速度的一種。勻速、變速、靜止⋯⋯都是速度。周李立的敘述速度自然是多種速度量值的復合反應。敘述速度的快慢,一定會帶來多種情況。把一個故事說清楚,敘述越快,言說越粗簡,時間就越短;反之,言說越細繁,用時越長,字數越多。在周李立作品中,我直接感覺到的美,并不是敘述的速度之美,而是作品的疏朗美。而這種疏朗美又確實是敘述速度帶來的。一種變化帶來另一種變化。敘述速度顯形的是快慢的變化,快慢的變化又導致敘述的粗細變化。這些變化促使謀篇布局文字比重的變化,最終導致結構和故事的變化。再則,速度還波及到語言,進而波及到語境和作品的整體氛圍。敘述速度這一指標,處于牽一發動全身的地位。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第四部分《關于小說結構部分的談話》中說:“因為速度還由其他東西來決定:一個部分的長度跟所敘述事件的‘真實’時間之間的關系。第五部分《詩人嫉妒了》,表現了一年的生活,而第六部分《四十來歲的男人》只講述了幾個小時之內的事情……我認為速度之間的反差對比是非常重要的!”無論由什么來規約速度,速度都是生發和研判小說的一個重要指標。
周李立作品中的疏朗情狀俯拾皆是,比如《他們家的暖氣》講“我”在男朋友家的種種遭遇,讀者以為作者還會細說“我”如何道別、如何離開。但沒有,直接就到了很遠的時空。兩個時空之間的留白,成了讀者“茶歇”的好時光。她細起來,也不得了。寫“我”男朋友的父親當著“我”的面在客廳脫外褲的橋段時,刻畫入微的耐心與運力,達到不厭其煩、不說不快的程度。周李立有女作家共通的細膩、敏感,而她對衣飾、色彩、飲食、氣味、氣候、酒水、性別等的細膩、敏感程度,尤勝同類一籌。粗細搭配,簡繁隨行,半遮半掩,點到為止,欲說還休,欲言又停,說一半留一半,拒絕面面俱到、平均分配,這是她把控速度、制造疏朗之美的殺手锏。
周李立對故事走向的安排路數也令我側目。一般小說家的路數是:故事這樣開頭,那樣結尾;具體操作策略是:一路向西寫,結尾陡轉,讓故事向東。這是為達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周李立也遵循反其道而行之的創作鐵律,但她不是反故事的道,而是反同行的道。她的故事很多時候都是從A到A,而不是從A到B。《酋長》中,酋長一開始就要離開藝術區回南方老家去,一開始畫就賣不出去,到結尾畫也賣不出去,到結尾也還是離開藝術區回南方去了。《透視》中的主角老關,一開始就寄居異鄉過一種一層不變的庸常生活,到最后還是。《另存》中喬遠一開始就畫不出畫、參不了展,到結尾還是畫不出畫、參不了展……正是得心應手用好了這種一反再反、負負得正原理,周李立才得以讓她的那些平凡事、小題材作品出了意思,出了意味:自然、生動、雋永、清澈、真摯,素面朝天又儀態萬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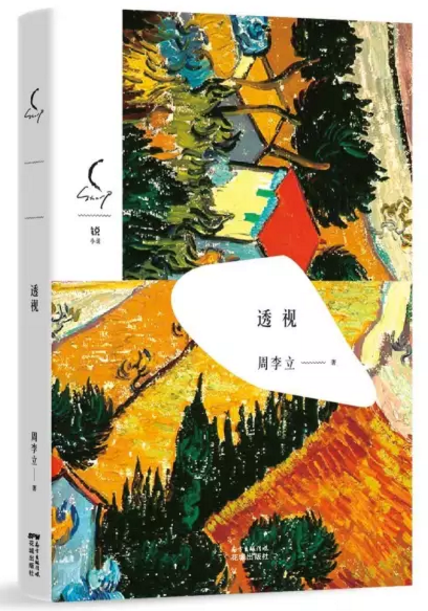
作者簡介:成都凸凹(詩人、小說家,成都龍泉驛區文聯專職副主席)
來源:《收獲》(微信公眾號)
作者:成都凸凹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