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勝:《木府血脈》,滴水鑒大海
今春以來,我在主持國家重大課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之余,一直奔忙于籌建成立北京納西學會、主編《納西學博士論文叢書》及《國際納西學譯叢》。至5月下旬,愉快接受劉瑞升托付,為其所著《木府血脈》作序。
劉瑞升是一位資深記者,供職于《中國知識產權報》,而木光則是納西族退休干部。他們之間結緣于徐霞客研究事業。木光曾先后參加在云南麗江、江蘇江陰等地舉辦的多次徐霞客研究學術活動,并作為木增嫡長與徐霞客第九世孫徐挺生歷史性會晤,再話納漢友誼新篇章;劉瑞升不僅長期致力于徐霞客研究事業,而且實際擔任中國徐霞客研究會副秘書長、《徐霞客研究》雜志編委,并多方尋訪徐霞客在滇云大地遺留的蹤跡,進而踏上麗江的土地。
木光作為生于民國初年、進于新中國成立、成于改革開放、退于新世紀伊始的麗江木府第48代后裔,雖歷史光環奪目并曾任云南省政協常委,聽政問政于官民之間,但畢竟只是一名普通的電影工作者,絕非“木天王”再世,先祖于元明清的輝煌已經不再。為這樣一個普通納西族老者作譜,其價值何在?因為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似乎只有帝王將相才能立傳、才子佳人方可作譜。
看得出,劉瑞升為木光作譜,除了被木光之人品、人性所感動,除了木氏祖先與徐霞客的一段淵源,看來主要還是出于木光作為一個木府傳人,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納西族與各民族之間、在政治與文化之間、在麗江與周邊地區之間、在個人與諸多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之間具有社會、歷史、文化連結點的意義,足以通過展示這滴“水”而知納西文化之“海”,可以借助析理其年譜葉片來呈現當代普通納西人的人生際遇、社會關聯、喜怒哀樂,以折射波瀾壯闊的中國現當代歷史“百年潮”。
《木府血脈》以主人公從1929年出生至今的生命歷程為經線,在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廣闊時空中全面梳理其生存、生業、生活的年年月月,并縱溯納西族與木氏家族的興衰脈絡,橫窮木光多采、多樣、多舛的活動印跡,直至對云南及麗江的大量社會歷史進行了精細的鉤沉,展示了納西族文化的昨天與今天,廓清了種種籠罩在木府、木氏研究領域上空的迷霧。如對徐霞客是否曾經為木增《山中逸趣》作序之辯便是極精彩的例子。作者通過縝密的鑒別,確定徐霞客為《山中逸趣》所作者為“跋”而非“序”,了卻了一件學術公案。又如作者進行細致考據,矯正了《木氏宦譜》中的部分地名、人名、時間、事跡、人物關系,使之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它以木光為中心,以木府為線索,以徐霞客與木增友誼為依據,集結了大量的相關文獻、人物、事件、活動,將云南邊地,尤其是麗江近百年來的社會風云悉數記錄,將納西族的歷史與現實呈現得淋漓盡致,將始自明代、特別是徐霞客以來中原文脈在納西族社會的傳播回放得翔實生動,不僅讓人們照見了木光這個“時代大舞臺上的一個小角色”不平凡的一生、木府“誠心報國”的文治武功,而且揭示了納西族那種維護團結、維護統一、開放進取的精神,以及木氏后裔及納西族優秀兒女在國內外全新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忍辱負重、生生不息、尋找前路、實現生存發展大突圍的氣度。竊以為,這也是對《木氏宦譜》的一種個性化、個別化、當代版續寫。我所能做者,除了認真學習理會,只能是理順一些表述、糾正個別訛誤、提出若干建言、補充某些史料,如此而已。
我有幸作為第一個讀者閱讀這部書稿,強烈感受到了作者與木光的友誼之深厚,以及作者對木府的尊重、對納西文化的禮敬、對納西族命運的深切關懷。我想,沒有博大的人類情懷,沒有平等的民族觀及強烈的國家意識,沒有科學的思想指導與方法武裝,沒有系統的理論知識儲備,斷然不會有這部著作問世,更不會有它高超的立意與華美的品質、優雅的文字、謹嚴的敘述。而這正是徐霞客的文風與精神的延續,無疑也是對納西學研究的一大貢獻。從而,我欣然命筆,作序以志感銘。
由木增與徐霞客等先輩開啟的納漢文化交流之江河正在匯涌成汪洋大海的今天,劉瑞升之作《木府血脈》乃是一朵格外耀眼的新浪,我自喜不能勝,由衷祝愿作者與木光的友誼地久天長,更期待納漢文藝界、學術界再續促進中華文明偉大繁榮的弦歌,以同圓中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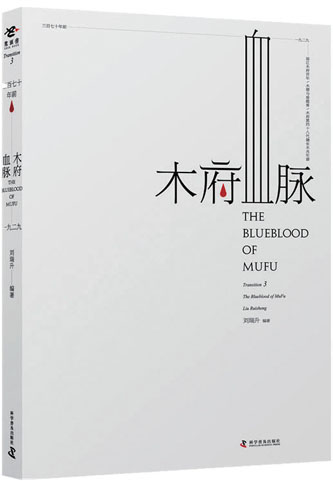
(《木府血脈》,劉瑞升編著,科學普及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來源:文藝報
作者:白庚勝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