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呂約對談: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風雨同行”?

呂約(左一)與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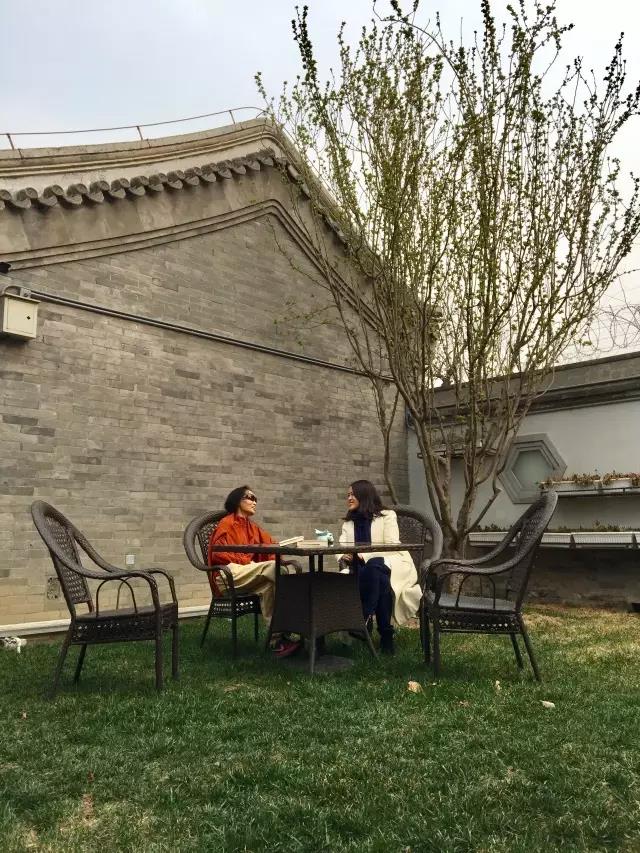
林白(左一)與呂約在十月文學院
編者按:
“約會作家”是十月文學院公眾號的常設欄目之一,每周末邀請作家前來做客。
在位于永定門公園佑圣寺內的十月文學院,品一杯清茶,談一本好書,賞一春勝景,尋一處怡然。聊生活,聊文學,談人生。
本期,我們邀請到了作家林白,與詩人、十月文學院副院長呂約對談。一起來聽聽她們閨蜜約會的“婦女閑聊錄”吧~
位于北京永定門公園內的十月文學院門口,詩人呂約頭戴黑色針織線帽、身穿米白色長風衣,正在向遠處眺望。
不一會兒,一位戴著墨鏡、身背雙肩包腳踩運動鞋的女士向這邊走來。看著那個酷酷的、走路帶風的身影,呂約說:“林白來了!”
二人熟悉的打扮,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第一次見面:帽子與墨鏡
呂約:哎,林白,你還記得我們倆第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嗎?
林白:我記得是2001年元旦前后,要不就是2003年,總之是2004年我去武漢之前,不過也可能記錯了。
呂約:記憶真不可靠啊。我印象中是2004年元旦,那時我剛從南方來到北京,接到邀請去普陀山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廣州詩人楊克打電話來,托我一路照顧你,因為你有點“生活不能自理”。我一聽感覺很奇妙,還有一種重任在肩的感覺。因為以前讀過你的《一個人的戰爭》和《說吧,房間》,見過你的照片,早就對你充滿好奇。個人風格強烈的作家,總是讓讀者想知道她本人是什么樣子的。
林白:想起來了,我們的接頭地點在首都機場。我先到,你后來的,我當時沒見過你照片,但一眼就認定了你是呂約。你年輕漂亮,一頭長發,給人很好的印象。
呂約:然后我們就一起坐飛機去了上海,再坐船去普陀山。
關于“自理能力很差?”
林白:我們在上海見了朱大可和張閎,在人民廣場喝的茶。為什么楊克說我自理能力很差,因為我害怕出門,出門就迷路,還有就是當時剛買了新手機,不會發短信。這兩條就成了我生活不能自理的證據。是你當時教會我怎么發手機短信,這是我科技使用史上的重大突破。
呂約:記得是在去普陀山的船上,我們住上下鋪,我爬上爬下,教你發短信。
林白:后來朱大可問我的處女短信發給了誰,我說發給了池莉,因為我要到武漢去工作。到了普陀山,我們倆還一起去吃了海鮮,你買的單,你請的客。
呂約:哈哈,買單我不記得了。
林白:對啊,我們剛見面,你就帶我去吃海鮮,吃什么不記得了,但我還記得那個生姜,切成一片一片的樣子,有點厚,明黃色的,方塊的。
呂約:你的細節記憶好厲害。怪不得你的小說里,總有那么多的物質意象和細節,這是你小說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我們待會兒再聊這個。當時我們聊得起勁的一個話題,是穿著打扮。
關于“帽子和墨鏡”的秘密
呂約:昨天翻出我們倆第一張合影,是在普陀山法雨寺,我戴一個黑色的帽子,你說戴帽子酷,讓我別摘,你戴著墨鏡。
林白:對呀,真巧,我今天也戴著墨鏡過來的,你也戴著帽子。
呂約:為什么我離不開帽子,你離不開墨鏡?仔細想想,難道是因為帽子和墨鏡都有遮掩作用?帽子是半遮半掩,墨鏡是一種完全的遮掩。你喜歡躲在墨鏡后面看世界,但阻止別人窺探你。這就是作家的視角。我突然想起楊絳在《丙午丁未年紀事》里寫過,文革開始時她和其他“牛鬼蛇神”們被安頓在一個屋子里,革命群眾隨時可能闖進來檢查,她向難友們獻計說:“別撤簾子”,因為隔著簾子,外面看不見里面,里面卻看得見外面,可以早作準備。楊絳的簾子,就像你的墨鏡。
林白:這么一說很有意思,有可能是這樣。
北京不冷了,卻刮起了沙塵。海紅到王府井買了一副墨鏡,一條絲綢大方巾,還買了一件上海產的長風衣,寶藍色,闊下擺,束腰。她像北京的女子一樣,用絲巾包著頭發,只露出前額一綹卷曲的劉海,看上去有一點嫵媚,然后,她穿上風衣,扎好腰帶,出門之后戴上大大的墨鏡,這使他有了些時髦的氣息。邊遠省份的人到了北京總是很快就變的。京城有一種氣象,這氣象浸入到海紅身上,改變了她的氣質。她已經頗像一個京城的文化人了。
——節選自林白《北去來辭》
呂約:對了,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第一副墨鏡的?墨鏡是八十年代時髦青年的裝扮,戴墨鏡,穿喇叭褲,提著三洋牌錄音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是八十年代時髦青年的標配。
林白:我的第一副墨鏡,可能是來了北京以后才有的。
呂約:你最時髦的時候是什么年代?
林白:方方覺得我八十年代很時髦。那時發型很前衛,右側頭發非常短,左邊頭發挺長的,不規則的前衛發型。他們認為我最酷的一張照片是在花山巖畫前拍的,穿一個明黃色的夾克,底下黑褲子。
呂約:你到了北京以后,穿著打扮發生了變化,是因為發現北京文藝青年的打扮風格不一樣,想要融入北京的文藝圈子嗎?
林白:那倒不是。八十年代可能是我個人比較時尚的時期,跟生活狀態有關。八十年代我是典型的文藝青年,在廣西電影制片廠,全廣西最文藝的地方,很酷。但到北京的那幾年就不行,頭發就隨便扎成一個辮子,最好打理,也最不時髦。因為有了家庭和孩子,在報紙當編輯還要忙工作,所以穿得很隨意,更生活化的感覺。
從《萬物花開》到《婦女閑聊錄》
呂約:你的生活和寫作狀態的階段性變化特別明顯,這直接體現在你的主題和題材上。你的寫作軌跡,基本上是從女性個人的成長經歷,到走向人間走向萬物的過程。2004年元旦我們認識的時候,你的寫作處于什么階段?
林白:大家普遍認為,我前期的寫作是內心的、封閉的女性世界,后來走向了萬物,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其實這里面是有誤解的。我剛開始寫作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第一篇小說叫《土平房里的人們》,寫的是一群住在土平房里面的人。1987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從河邊到岸上》,寫一個撈紗女的故事。所以我的早期作品并不是一個人的、封閉的,那時描寫的就是我所觀察到的社會。我和你認識的那一年的夏天,2003年七月份,剛好出版了《萬物花開》。
呂約:哦,那我們認識就是在《萬物花開》那一年,這就好記了。我感覺那時你狀態很好,正是從一個人的獨白封閉狀態,興高采烈地走向人間和萬物,是一種蓬勃的打開狀態。
林白:《萬物花開》在2002年冬天寫完,2003年3月計劃出版,但那一年正好趕上非典,所以推遲到7月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
呂約:我感覺到當時你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和熱情,什么都想了解。記得你還跟我說,我在媒體工作對寫作很好,因為寫作的人不能過一種封閉的生活,我在媒體能廣泛了解社會,這對一個人的長期寫作來說很重要。這是你在寫作觀和人生觀上跟我談過的一個話題,至今我還深有同感。你當時最關心的是如何走向萬物,這個恰恰和你自己的狀態相關。
林白:這跟我寫完《萬物花開》還是很有關系的。以前楊克說我生活不能自理,有一定道理。因為我那時焦慮,不敢坐飛機,出門遠行,又不認路什么的。后來確實有打開自己的想法。
呂約:《萬物花開》之后的作品,是《婦女閑聊錄》還是《致一九七五》?
林白:是《婦女閑聊錄》。2004年我給《十月》雜志首發,是趙蘭振找我要的,后來出書也是他聯系的。
呂約:你寫了《萬物花開》以后,馬上就寫了《婦女閑聊錄》。這本書花多長時間寫的?怎么會想到用這么有意思的文體?
林白:幾個月。對對,我后來覺得這樣的文體很有意思,當時倒沒覺得,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當時剛看了周作人翻譯的《枕草子》的隨筆體例,受了些啟發。我就干脆寫一段一段的,每一段有個小標題。最近,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章德寧要把《婦女閑聊錄》再版,3月底就將和讀者們見面。在十月文藝出版的這兩本書,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呂約:那我們就閑聊一下《婦女閑聊錄》吧,你是怎么想到要和家里的保姆“木珍”聊天,把她的話記錄下來的?
林白:我最早不怎么愛和人聊天。是1999年和李敬澤、龍冬一起參加“走馬黃河”的活動,去到哪里就和當地人聊天閑談,養成了和農村婦女聊天的習慣。回到家后就和保姆閑聊,一聊就發現很有意思。我打算寫成小說,但又不想寫成一個長篇小說的樣子,就設置了一些聊天的主題,包括一些家鄉的人與事、地方風俗、回鄉經歷等等,對她提問。當然書中我的問題是全部隱去的,留下的是她的回答。后來回憶,應該受了《枕草子》的影響。我覺得《婦女閑聊錄》就是個典型的非虛構作品,但當時還沒出現所謂“非虛構”的潮流。
呂約:你寫完了這本書,主人公木珍看了嗎,她有什么反應?
林白:她看完了,很開心,特別開心。她以前是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后來慢慢有所提高,就能看懂這樣的文學作品了,她很喜歡這本書。
呂約:女主人公變成了文藝青年,文學的使命就完成了。
“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
呂約:你的小說一開始就充滿了密集的物質意象,這些物質也變成了小說很重要的線索。你不是傳統小說的敘述方法,但你時代色彩挺鮮明的。
林白:對,你理解得很到位。我覺得呂約真的是很能理解我和我的小說。
呂約:我們還有一個緣分,是《致一九七五》出來以后我寫了一個評論,發表在《南方文壇》上,叫《小說的飛行術》。當時是你寫完這本書后去我家,送了一本給我,還有題辭。我看完就有評論的沖動。《致一九七五》女主公李飄揚吃胎盤,“吃胎盤”是個很重要的意象,《北去來辭》也有,海紅的媽媽說,“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這個可能和你自己的童年記憶相關。中國人經過漫長的匱乏時代后,首先想要“把營養搞上去”。
“插隊的前一天,為了給我加強營養,母親特意弄來了一只胎盤燉給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腳步疲憊,卻神情亢奮,她從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狀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邊緣是深濃的藍紫色,胎盤就在器皿里。浸泡著血水,剪成了一塊一塊,臍帶剪成了一小節一小節,像花生米那樣長短。母親直接倒進砂鍋,放進生姜和酒,像燉雞一樣,大火燒開煮五到十分鐘,再小火慢燉。
我像等待一只燉雞一樣等著胎盤燉好。
——節選自林白《致一九七五》”
林白:對,我媽媽是縣醫院的婦產科醫生,那個時候流行“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吃胎盤是我自己的童年記憶,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
呂約:我那篇文章里還分析了《致一九七五》里物質序列內部的轉化,發現你復活了大量容易被忽視的物質與感官經驗,組成了各種物質序列,比如從空間到人體到物品,從廚房到食物到糞便的轉化等等。你喜歡描寫各種動物糞便。可以說你的寫作是無所顧忌的,很多內容一般女作家不敢寫。在女性成長經驗、性別的經驗外,你能坦蕩地寫所有的物質和感官經驗,毫不顧忌,而且物質意象特別豐富。比如衣服鞋子,胎盤,自行車,縫紉機,游標卡尺等等。游標卡尺這個物件給我印象很深,有種工廠師傅的感覺。
他就是在水塔邊把我做的游標卡尺折斷的。
我沒有見過一個老師這么粗暴,我不明白,他憑什么。我完全懵了,意外、震驚、全身的血往頭上沖。……
這把游標卡尺,是我們物理期終考試的考卷。書面考試廢除了,強調實踐,自己動手。
——節選自林白《致一九七五》
林白:游標卡尺就是一個尺子,有個滑動的卡子,和游動的標,是那個年代的測量工具。我們經歷過學工學農,對工廠物件和車間都很熟悉。我覺得,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非常好,我以前沒從這個角度來看物質環境描寫的重要性。我們這一代人學工學農,大量接觸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獲得的物質印象格外多。現在的年輕人,比如90后,長時間關在學校接觸書本,或者宅在家里,很少能有其他經驗。
呂約:你的女主人公總是騎在自行車上飄飄然,騎在自行車上還幻想騎飛馬。她們總是帶給人飄揚的感覺,比如李飄揚、海紅這些名字,都給人濃烈的八十年代的印象,一種理想主義的飛揚姿態。而且你也擅長寫從革命時代到后革命時代的變化,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這代青年。他們雖然經歷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年代,又經歷了一個幻滅時期,但和當下的小說相比,還是具有理想主義的氣質,李飄揚、海紅她們是很有生命激情的。李飄揚是一個在革命狂歡中很陶醉,又有點迷糊的女性形象。你著力刻畫她的心理,是坐著大卡車去文藝演出,在集體之中很興奮。在這種興奮中,她照鏡子,化妝時看自己的臉,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萌發。在你筆下,革命變成了一面巨大的化妝鏡,她們從中看到自己被放大的面容。
林白:對,我的女主人公都蠻興奮、迷狂的。《致一九七五》,我的創作目的在于一個革命時代,在中國邊遠小鎮的日常生活、政治環境,它和北京這種政治中心是完全不一樣的。根本沒有反思一個時代、對歷史質疑這樣的啟蒙姿態,完全不沾邊。這些小人物就在邊遠小鎮上興奮、迷狂,這是那個特定年代小鎮上的真實生活,和北島他們對時代和政治的反思完全不同。
丁玲蕭紅和我們有什么不同?
呂約:你們剛冒出來,男評論家們就趕緊往你們身上貼標簽,叫“女性主義寫作”。以你和陳染、海男她們為代表的這一批女性作家,的確集中展示了獨特的女性經驗、女性意識和女性語言。在革命年代的宏大敘事中被壓抑和刪除的個人意識和性別意識,在你們這代人的筆下重新出現了,特別是女作家的筆下。
林白: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那些現代文學的女作家呢?丁玲、蕭紅她們的創作,和我們的差別到底在哪里?
呂約:廬隱主要是發現了女性友誼,“海濱故人”,將同性之愛浪漫化和感傷化。丁玲早期作品是有強烈的女性意識的,最典型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將女性意識和兩性關系欲望化和戲劇化。延安時期的《三八節有感》,是她的女性意識在受到壓抑之后的一次爆發。丁玲小說最為大膽的是兩性關系的描寫,特別是直接把男性身體作為女性欲望的直接對象物,但她筆下的情欲中,幾乎沒有物質意象,沒有中介。張愛玲不一樣,她筆下充滿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物質形象。你筆下的女性欲望,既有身體本身的欲望,同時也有很多是被分解到各種物質中介上去的,比如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跟張愛玲不同的是,你筆下的女性,不僅有圍繞她們身體的日常生活和物質經驗,還有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經驗——一會兒學校,一會兒工廠,一會兒舞臺的。
林白:是嗎,很有道理,我對丁玲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她很有才華。我很喜歡讀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說。
呂約:那個時代還沒有現代社會這種物質欲望。比如說蕭紅,她的小說都和她的故鄉記憶有關,她筆下的女性,進入的是一個生產過程,或者說生死過程。《生死場》寫了鄉村日常生活和戰爭爆發后的不同狀態,對于女性來說,抽象的民族國家的概念,離她們很遙遠。村里地位最低的男人至少還可以上戰場,喊著保家衛國,在女人面前表現出一種男性的尊嚴和優越感,而女人呢,她們無法上戰場,只能生孩子或生病,服從于“動物般的”的自然生死規律。在戰爭背景下,女性就進入更加弱勢的一種狀態了。蕭紅筆下的女性,不僅物質更貧乏,連她們的身體都是生病、傷殘、變形或腐爛的。《生死場》中最漂亮的月英,生病后被丈夫折磨和遺棄,身上都生了蛆。她們就像動物,動物是沒有什么物質生活的。
林白:對,今天這討論很有價值,起碼從一個新的角度,把我們和丁玲那一代人的女性寫作做了一個對比。比如你說的物質欲望的差別,這是很有價值的話題。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
呂約:可以說丁玲那一代是中國女性意識的第一次覺醒。在之后的延安文學和“前二十七年”文學中,個體意識和性別經驗都處于一種被壓抑、被刪除的狀態,所以你們這一代相當于女性意識的第二次覺醒。八十年代中國出現了現代社會的一個雛形,你的女主人公都置身于集體生活之中,社會交往面也很廣。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重要標志就是物質生活的變化,所以你的小說中出現了很多全新的物質形象,既有社會性的物質,比如火車、大卡車、自行車、喇叭、鋤頭、游標卡尺等等,也有私生活的物質,比如服裝、食物、家庭生活的器物等等。
“見到新鮮東西總是要伸手摸一摸的。頭三個月,每次乘電梯她都要摸一摸電梯壁。這玩意兒,這燒電的梯子沒聽見動靜就上了九層樓,稀罕!她把手心貼到梯壁上,鐵的,硬的,光溜的——像拖拉機的機殼。她還要把鼻子湊近,仿佛要聞一聞這電的梯子是何種味道。樓道門,鑲嵌著大玻璃,也要摸,一摸,手上沾了灰塵,她就在玻璃上畫道道,畫了一個菱形,又畫了一個菱形——像她納的鞋墊。畫完道道后還不盡興,又在旁邊寫下了“史銀禾”三個字,不過,她很快又笑瞇瞇地抹掉了。”
林白:對,所以我老就想,為什么我的小說總不能按照傳統的小說模式去發展,將一個故事啊,一個人物啊,設置一個戲劇化的沖突等等。我當初寫的時候是無意識的,但現在想來這種創作思維其實是很重要的。這對我今后創作是一個提醒,我接下來的小說也會出現很多物質的意象,以后就會更加變成隨筆式的敘事,而不是小說腔調。小說腔調的敘事,很難吸納那么多物質。
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風雨同行?”
呂約:你寫完《婦女閑聊錄》,準備創作《北去來辭》時,來我家聊天,還聊起你的困惑。你說:“我有時候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標準的小說家,你覺得我的小說是不是真正的小說?” 我覺得你和傳統的小說家不一樣,還不僅僅是女性經驗的問題,你是很有詩性精神的小說家,除了對詞語的敏感,你感興趣的東西太多了,比如對萬事萬物的好奇,并且想用自己發明創造的新鮮語言去表達它。
林白:對。我有好奇這一條,原來自己不覺得。二十多年前,我和楊克去廣西看佛手瓜。我在老家也看過這些,但再一次見到之后,我還是會感嘆“呀!這是什么”。楊克就覺得,這有什么好奇的,又不是沒見過。
呂約:對萬事萬物都好奇的眼光,是詩人的特質。詩的精神,就是仿佛第一次與事物相遇,用新的語言去跟它對話。在你這里,事物不再是“革命”所定義的狀態,而是還原到了原本的樣子。所以說你很有詩歌精神的小說家。王國維將詩人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觀型詩人,一種是客觀型詩人,你更像主觀型詩人。評論家們對你的解讀,往往是從女性經驗、女性意識的角度來談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女性語言”,還沒有得到充分解讀。
林白:我現在有點覺醒了。我寫過那么多書,現在回過頭來看,會明確一些東西。下一步寫作會知道哪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呂約:評論家們認為,你的創作軌跡就是從“一個⼈”走向“萬物花開”的過程,⽅向是很明確的,很線性的。但我總覺得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比如,你筆下的女主人公總是既渴望融入集體,又時刻準備一個人逃離。你有一段話,可以作為你創作思想的注解。
一個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與天地萬物他者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條遼遠的漫漫長途上,做一個與天地萬物風雨同行的人。——林白《北去來辭》后記
可是,在另一處,你又說:“但我一意孤行。”你筆下的主人公經常有一種逃離外部世界、逃回自我深處的沖動,給人的感覺也是一意孤行的。比如海紅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就是很反常,很輕率的。這是你個人性格和思想的矛盾,但變成了小說主人公在行動上的矛盾。
海紅突兀的婚姻也像是這股瘋狂氣息的一部分。
既像是輕率的,又像是慷慨的。她有一股子蠻勁,說得上是一往無前;她又有試錯精神,人生就是用來犯錯誤的,這時不錯,什么時候錯!
——節選自林白《北去來辭》
林白:你的感受非常敏銳。你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點,提煉得非常好。我現在還有這個矛盾。我現在也經常疑慮和搖擺,我是到底向外,走向社會的廣闊世界中去,還是永遠向內,通往內心無限的深處。我很掙扎,感覺永遠在矛盾之中。
呂約:這是你個人的特點,也可能是一個作家處理自我和外部世界關系時,永遠存在的矛盾。很多時候我們寫作的沖動也就從這⾥來。
林白:我發現其實你也是這樣。寫詩是非常自我的過程,但同時,寫詩也是在對外部世界進⾏敏銳的反應和應答。
呂約:對,我也有這種矛盾。寫詩必須扎根于自我深處,同時,我的詩有很大⼀部分是基于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觀察。
林白:你的詩歌很有力量,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炸彈漫游》,寫現代社會的⼀種危機感,我喜歡你的詩歌的開闊和力量。
呂約:無論是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同行,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狀態,寫作永遠在這兩者之間徘徊,永遠在中途。你是⼀個能夠扎根于個人,同時又能走向萬物的作家,所有的作品正是在這樣的交接點上,才能有社會性和藝術性的交合。你通過階段性寫作,強化了某一方面,但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矛盾。兩極之間有一個永不停息的對話,這恰恰構成了寫作的真實性,寫作的生命力。這是我們作為寫作者的一個精神矛盾,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當代寫作不必解決的矛盾。
林白:對對,跟你對話這個很有價值。你這樣說,我就很清晰了,以前我總想解決這個問題,但老解決不了。如果這是一個不必解決的矛盾,那就太好了。
文字整理|康春華
圖文編輯|葛方圓
林白簡介:
林白,生于廣西北流,現居北京。目前為自由撰稿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寫作,先詩歌,后小說。著有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北去來辭》等多部,另有中短篇小說《回廊之椅》《西北偏北之二三》及詩歌散文。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十月文學獎,獲當代2013年度長篇小說五佳、新浪中國好書榜年度十大好書等榮譽,曾獲首屆及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獎。
有日、韓、意、法、英等文字的長篇和中篇單行本出版。
呂約簡介:
呂約,詩人,文學博士,現任十月文學院副院長。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十月》《今天》《現代詩》等國內外刊物,著有詩集《回到呼吸》《破壞儀式的女人》,學術專著《喜智與悲智》,批評文集《戴面膜的女幽靈》等。曾獲首屆駱一禾詩歌獎,應邀參加德國柏林詩歌節。
作品被翻譯成德語、英語、日語。
來源:十月文學院微信公眾號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