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中國詩歌排行榜》談新詩的走向
——“紀念新詩百年”上海臨港理論研討會發言
(會議題目:“中國當代詩歌的現狀、問題和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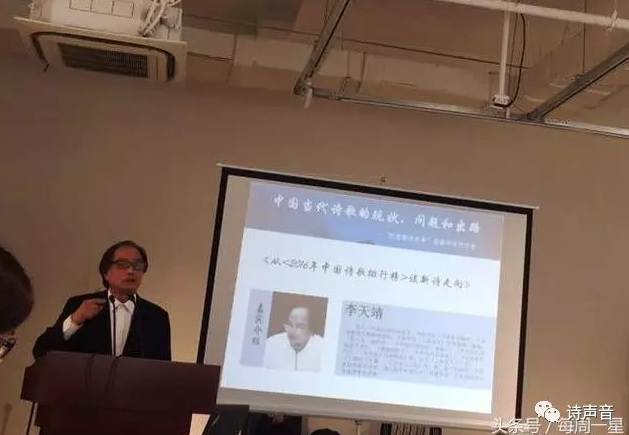
(詩人李天靖在發言)
一、當前的現狀
在新詩百年之際,今天,我們有幸在這里,展望它的未來。
2017年4月11日在文匯報筆會發表了復旦的張新老師一篇名為《躺著中槍的新詩》的文章,這篇文章的最后說“把它們的關系(古詩和新詩)看成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系,對詩歌的整體發展有害無益”,換言之,張新老師期待百年的新詩應承接漢詩傳統的血脈,而非對抗;文白兩種不同的語言,如何承接,或曰如何繼承?這是漢語之痛,是橫亙在自新詩誕生起一種歷史的悖謬。
2016年第4期《上海詩人》詩刊封二,發表了鄭愁予寫于一九五0年一首《雨絲》,詩中“我們的車輿是無聲的。//曾嬉戲于透明的大森林,/曾濯足于無水的小溪”,“車輿”“濯足”等是古代漢語,自足的典雅與鮮活,于口語詩大行其道之時的回眸一見,盡顯傳統的漢語之美,此詩在口語的寫作中,藝術地運用古典的書面語,對如何傳承漢詩語言與新詩的詞語寫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式。
立足當下,與縱的傳承、橫的移植的三維坐標的這個交點上,我以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邱華棟、周瑟瑟主編的《2016年中國詩歌排行榜》一些最新鮮的詩歌文本,來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首是伊沙的口語詩《吉隆坡云頂賭城聯想》。
面臨地球水和空氣的污染,百份之四十的可耕地長期被破壞,每年1300萬公頃森林消失,四分之三的漁場枯竭,物種死亡超過自然繁殖速度的1000倍,溫度上升冰蓋的厚度比40年前減少百份之四十,2050年2億人淪為氣候難民。
在這個令人驚駭的背景下,伊沙的一首口語《吉隆坡云頂賭城聯想》,寫地球的毀滅。
伊沙說,他作為最后的撤離者,告知先他而到達外星球的撤離者——他們正在一座超級大賭城里為“地球毀滅”下注,得知地球已毀滅這消息后,彈冠相慶,因為他們賭贏了。此詩對于地球人的鄙夷與批判,無疑是深刻的。詩中的反諷與戲劇性,是西方的技術。
第二首臧棣的《體位性窒息死亡入門》,是口語詩。
揭露了某些地區現存的教育的罪惡。一個10歲的小男孩在學堂里偷吃零食遭遇的懲罰,“從上午開始,直到晚上8點,/他們一直把小男孩吊在倉庫門梁上。”“第二天凌晨4點,他們又接著/將他吊掛起來,直到早上7點。”最后詩人寫道:“就只差一小時,這個叫小柳的福建男孩/終于沒能再活到,他就像/八九點鐘的太陽的那一刻。”臧棣用中國詩歌傳統中的“賦比興”中的“賦”的寫法,以冷峻的語言真實記錄了令人發指的事件經過,刺穿這個癰疽。鞭撻了中國教育普遍與博愛背離的嚴酷的現實。
最后三行的結尾,是現代主義的反諷。
第三首于堅的《鱷夢》,也是一首口語詩。
寫一條鱷魚來到夢中,如長尾的坦克開進來,詩人用寫詩的手取下它的“履帶”,并叫它學習“退卻”,“吐掉你腹中的推土機”;詩人直擊社會現實,捉住了拆遷者“藏著一堆撬棍”, 對強行動遷的暴力的批判;另一方面,鱷在詩人的夢中被馴服,“從殘暴回到善良”,“從自大回到謙卑”,也道出了作為詩人的使命與良心。最后鱷夢到了黎明,詩人說出“我不知道如何將我塑造的這個生物放回現實”,表達了詩人對現實的一種絕望。
全詩魔幻的、荒誕主義的手法,以及用隱喻寫鱷夢一般的現實,前者是西方的技術。
這三首口語詩,可以看到詩“可以怨”——這個漢詩傳統詩歌精神的傳承,對于社會存在的問題的揭露與批判,或者說社會性或公共性,正是詩歌的使命。同時也看到在技術層面上“橫的移植”成為他們詩歌的肌質。
以上這些。無疑是新詩百年之后繼續努力的方向。
詩人的精神決定了詩的存在。
《2016年中國詩歌排行榜》中,王家新的一首《你在傍晚出來散步》,希望在日常平庸的生活中,“你抬起頭來——”,發現“一顆冬夜的星,它愈亮/愈冷”,表達了人應該對于星空的這個內心的道德律令的敬畏。
現代詩區別于傳統詩歌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視詩歌傳達人生的經驗,更勝于人的情感。經驗是經過過濾和升華的情感,現代詩表現的知性化是必然的趨勢。嚴力的一首《保持硬度》,充滿了智性;冰面的硬度隱喻了詩人即使在“睡姿縮成一團”,也要“保持冰面的硬度”,即思想的硬度。
詩,從言有寺,它既標明言語方式的特殊性,又標明它是與現實生存對稱或對峙的另一種高于我們生命存在的形式。朵漁的一首口語《在獵戶星座下》,像一個語言的方陣朝你壓來,通過敘述——你我之間的對話,我們或我的內心獨白,將玉龍雪山的“碩大”“無名”,如一顆宇宙的心、一個大神,“在群山之上,有一種更高的秩序…..那是獵戶星”,呈現在讀者面前,超越了星空道德律令的人的自身的存在,也即神性的寫作。
“詩是一道被技藝護持的生命泉涌”。(陳超語)
中國當代詩人更多地轉向口語或詞語的寫作;在技法上成熟了,作品中可以看到了它的豐富性。《2016年中國詩歌排行榜》中,譬如劉川的《通往火葬場的路上》戲劇化處理的悲憫等。周瑟瑟《一個男人在馬路邊大聲喊》的吊詭,即我就是我自己的另一個他者令人驚異的轉換。李少君的短詩《雪夜》尖新的陌生化的比喻,以及虛而實之,使全詩呈現生死互襯且動靜交織的意境。商震的《風雪中的蘭》,于意象善變的橫向展開,又朝著縱向的深入直至一種極致,即萬物為一體;洪燭小說體的《在科爾沁的可汗山,與成吉思汗對話》、徐江的《死人》語言的言說等詩歌的形式具有獨創性。堅持具有難度寫作的有谷禾的《許多的骨頭》、余怒《在什么邊緣》、胡弦的《飲酒》、余笑忠的《木芙蓉》,以及路云的《紫藤》的非理性的言說。
另外,詩人在創作中開始對于進入語言內部努力的探索。已故的河南詩人馬新朝這方面的努力,引起人們的關注。嚴力的詩集中《體內的月亮》、姚風的“從一滴海水中,打撈沉船與銀幣”,以及藍藍《一穗谷》,如她所說詩人的“言說即對無限世界的敞開,容納他的想象力所能達到的任何邊界和精神的地平線。”《2016年中國詩歌排行榜》里,陳先發的《登岳陽樓后記》、李承恩的《瑜伽》等也作了這方面的嘗試與探索。
什么是詩的創造? 面對未來是一種未知的敞開,每一首那是給詩的命名與定義。詩人應保持一種藝術的自覺,未來的新詩朝向永遠在未知的追求中。海格德爾說“詩即語言”。但詩歌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黑格爾說過“內容本身并非藝術的主導、獨立因素,使尋常內容發射出奪目光彩的還有更重要的因素——‘詩的形式’”。這個形式我想應包含詩歌的音樂性、修辭、結構、風格等的元素,詩人須更為自覺的使之成為詩歌內容的本身,或曰語言肉身的獨特的形式,進行元文本的創造,且永葆蓬勃的活力。

臨港理論研討會主要與會人員合影
二、存在問題
在縱的繼承中“詩無邪”傳統的詩歌美學,必須堅持。余秀華的“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睡你”,竟引起詩壇,以及詩壇外很多人的追捧和興奮,值得反思。詩歌的千人一面,有目共睹。如何確立詩人自己的一個坐標,是詩人面臨的問題。對人性之惡的揭示、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判,顯得軟弱。西方的譬如美國詩人默溫的《憑著黑暗》,波蘭女詩人辛博斯卡的《越南》《酷刑》等,批判性遠勝中國新詩一籌。但白樺的長詩《從秋瑾到林昭》在中國是一個例外。他花了十年時間寫成——十年磨成一劍,對千百年來國民奴性的極為深刻的解剖,他對人性自由追求的熱切,難望其項背;對這首詩更深入的研究與評論,遠遠不夠。
何言宏說,新詩百年是對自由的追求。
但它是不自由的。“躺著中槍”的新詩,只有“中槍”的自由。那些秉承漢詩的“可以怨”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受難而又一往無前的詩人,如牛漢、穆旦、彭燕郊、公劉、卲燕祥、白樺等。在百年新詩的回眸之際,應向這些前輩致敬。
三、中國現代詩離諾獎有多遠
2011年1月4日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在“北回歸線”的首發式上,李笠的一撥北歐詩人朋友依次朗誦自己的作品后,我向前諾獎評委埃斯馬克提出了“中國現代詩離諾獎有多遠”的問題,他顯然措手不及,他說“這距離是一米,還是一里?”大家聽了都笑了!我又說,“詩人韓作榮曾說過,中國現代詩人中不乏有世界的詩人。”埃斯馬克說:“中國確實具有世界性的詩人,我和漢學家馬悅然一直關注中國的現代詩,但具體細節有50年的保密期。”他的回答顯然也讓我們失望。我的這個敏感的問題,對于埃斯馬克來說,確實是應該很好思考的問題。李笠后來來信說,埃斯馬克在回到瑞典后,“他一再談到我提出的問題。”
詩人趙麗宏最近在北京兩會上說了,“中國要有文化的自信”。要突破西方的話語權,中國的詩歌在自媒體時代,在未來……要有所作為。
今天這個關于新詩百年的研討,很有意義。吳思敬老師說:“詩歌的現代性相當突出的問題在詩的語言方面。詩歌的形式的變革往往反映在詩歌語言的變化中。”“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體、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后世莫能繼焉者也。”(王國維:《宋元戲劇史》) “凡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立足當下,可知未來。百年新詩之后的百年,或更長的時間,又孰能知之?
李天靖于華師大
2017.5.5
(作者:著名詩人、評論家 李天靖。 薦稿:朦朧詩社社長 牧野。)
來源:詩聲音NO.079~2017詩者雅13
作者:李天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M2MzM5OA==&mid=2651231811&idx=1&sn=2381a9b293651c128b5cbed11af6d4e7&chksm=843bea2ab34c633cf537e2af40e88ded0623925dba4607ad2eceab7f4dc7692d9ccc31a654a9&mpshare=1&scene=1&srcid=0508kDFD4XtII2RV7aDTV8YV&pass_ticket=16eSsM6Rr86bceOs4JYqqT7SsyPhCSdWphZ4uIGTnBKgwZgw7hskEMCz6vuxXYgR#rd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