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尋求那些寂靜中的火焰"——詩人林莽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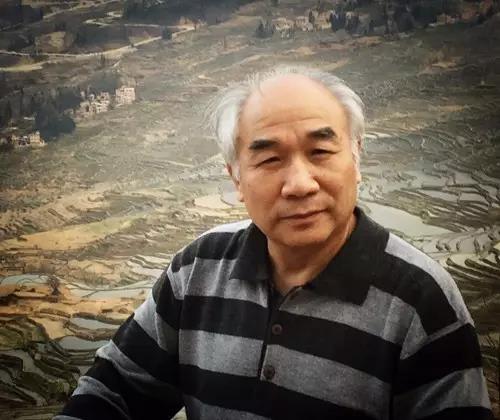
詩人林莽
吳投文 一九六八年生,湖南郴州人。二〇〇三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xué),獲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湖南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教授,出版有學(xué)術(shù)專著《沈從文的生命詩學(xué)》和詩集《土地的家譜》《看不見雪的陰影》等。發(fā)表論文與評(píng)論一百五十余篇,多篇被《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文摘》、人大復(fù)印資料《中國(guó)現(xiàn)代、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等學(xué)術(shù)期刊全文轉(zhuǎn)載。兼職有中國(guó)新文學(xué)學(xué)會(huì)理事、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理事等。
林 莽 原名張建中,一九四九年生。白洋淀詩歌群落主要成員、朦朧詩代表詩人之一。著有詩集《我流過這片土地》《永恒的瞬間》《林莽詩選》《秋菊的燈盞》《記憶》等,詩文集《時(shí)光瞬間成為以往》《穿透歲月的光芒》《林莽詩畫集》等。現(xiàn)任《詩刊》編委,《詩探索·作品卷》主編。
吳投文:一九六八年,你到華北水鄉(xiāng)白洋淀插隊(duì),在那兒你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學(xué)青年,成了“白洋淀詩群”(一九六九--一九七六)的重要一員。一九六九年,你創(chuàng)作了《深秋》,可能是你最早的詩歌了。后來,你又完成了《自然的啟示》(一九七〇)、《凌花》(一九七二)、《列車紀(jì)行》(一九七三)、《二十六個(gè)音節(jié)的回想》(一九七四)、《盲人》(一九七五)等詩歌的創(chuàng)作。這是你的早期創(chuàng)作,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dāng)成熟而富有個(gè)性的詩歌了。你當(dāng)時(shí)如何想到去白洋淀插隊(duì)的?也請(qǐng)談?wù)勀阍诎籽蟮聿尻?duì)時(shí)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情況。
林 莽:一九六八年,我的同學(xué)和朋友們大多都離開北京,到各地的兵團(tuán)、插隊(duì)或跟父母到五七干校了。我因父親在文革中被審查,沒有資格到兵團(tuán),只能插隊(duì)。那年我被分配到陜西和東北白城,因?yàn)閷?duì)文革的懷疑,因?yàn)椴辉敢庾鳛椤翱梢员唤逃玫淖优备w去插隊(duì),這時(shí)恰好聽后來同在白洋淀插隊(duì)的同學(xué)崔建強(qiáng)說可以自己聯(lián)系去白洋淀插隊(duì)。于是,一九六八年秋冬兩季,我和幾個(gè)朋友連續(xù)幾次騎自行車到白洋淀考察,并決定選擇到更自由、離北京更近的白洋淀插隊(duì)。
到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多是文革中家庭或個(gè)人受到?jīng)_擊的干部或知識(shí)分子家庭的子女,大家有著基本相同的社會(huì)意識(shí)和文化追求.那些年白洋淀同全國(guó)一樣,是經(jīng)濟(jì)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不同的是,那里是中國(guó)北方唯一的水鄉(xiāng),有較好的人際環(huán)境。
社會(huì)動(dòng)蕩,家庭危難,那個(gè)時(shí)候,一個(gè)有問題家庭的子女是看不到未來與前景的。但作為不甘于沉淪、心中有夢(mèng)想的青年,我在白洋淀找到了詩,這種可以抒發(fā)內(nèi)心的感悟與苦悶的藝術(shù)方式。一九六九年,在插隊(duì)生活的第一年的夏天,我開始了最初的寫作嘗試,那些年保留下來的第一首詩《深秋》,就是一九六九年冬天完成的。《凌花》《列車紀(jì)行》《悼一九七四年》《二十六個(gè)音節(jié)的回響》應(yīng)該是我那個(gè)時(shí)間段的代表作。
吳投文:一九七〇年冬天,你寫了《自然的啟示》一詩:“初冬的原野上/掙扎著違時(shí)的嫩苗/寒風(fēng)的冬日把它/由蒼綠變?yōu)榻裹S/孤獨(dú)的柳樹/在狂風(fēng)中不時(shí)地彎下腰/灑下枯干的樹葉/無奈地抖動(dòng)著光裸的枝條/赤紅的落日/依舊現(xiàn)出柔和的微笑/在紫色云霧的簇?fù)硐?投入群山的懷抱//淡漠、恬靜、死肅/這就是初冬黃昏的格調(diào)”,詩中有一種清幽冷寂的情緒意味,可能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你對(duì)生命的某種反思。這首詩得到了很多讀者的喜愛,我也注意到不少報(bào)刊和網(wǎng)站轉(zhuǎn)載了這首詩。還記得當(dāng)時(shí)的寫作情境嗎?請(qǐng)談?wù)劇?br />
林 莽:《自然的啟示》一詩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寫的,那是我插隊(duì)生活的第二年。我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那是一些在孤島上的日子。既有正午的陽光,也有深夜的冷雨。對(duì)于一個(gè)心靈充滿壓抑的青年,對(duì)于一個(gè)離家孤獨(dú)生活的青年,那些年到底意味著什么?深夜,闊葉樹發(fā)出嘩嘩的聲響,我住的村邊小屋外是一片開闊的水面,沒有星光和漁火,我在孤單中思念,既凄楚又擔(dān)憂。在夕陽西下的堤岸上,一邊是一片紫色的土地,一邊是一片無聲無息的湖泊,我默默地走著,世界無依無靠。冬日的樹木枯干凋零,幾叢蘆葦在岸邊搖曳,孤雁的鳴叫聲聲遠(yuǎn)去。冬日的白洋淀一片冰川,灰褐色的云層籠罩著天空……盡管,我關(guān)注著每一天的新聞,但是家庭及個(gè)人的命運(yùn)被一只無形的手把握著。那些日子雖是青春卻充滿了陰影,那些日子向誰訴說?向誰哭泣?也就是那時(shí),在寂靜的寒夜中,我找到了詩:這種與心靈默默對(duì)話的方式。”以上這些文字就是我寫這首詩時(shí)心靈的背景。
這首詩應(yīng)用了一些象征手法,我們的確像一群反季節(jié)的嫩苗,在那片冬日的土地上抗?fàn)幹还拿\(yùn)。
吳投文:在你的創(chuàng)作中,長(zhǎng)詩《記憶》可能算是一首比較特別的作品,觸及到了你對(duì)歷史的某種沉痛記憶,也可能有現(xiàn)實(shí)原因的觸發(fā)。詩的抒情風(fēng)格也發(fā)生了某種變化,由原來的內(nèi)斂、沉靜轉(zhuǎn)向了激越、噴發(fā)。這首長(zhǎng)詩展開了對(duì)過往生活、對(duì)白洋淀歲月的回憶,也融入了你的現(xiàn)實(shí)感嘆吧。請(qǐng)談?wù)勥@首長(zhǎng)詩的創(chuàng)作,是在什么樣的情緒體驗(yàn)下創(chuàng)作的?
林 莽: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際,我讀到了許多回憶文章,我的青春年代的許多難忘的記憶不時(shí)地在我的心中閃現(xiàn),那年我有了創(chuàng)作一首相關(guān)長(zhǎng)詩的沖動(dòng)。
這是一首以個(gè)人的個(gè)體生活體驗(yàn)講述一段歷史的長(zhǎng)詩,我選取了一些我所經(jīng)歷的生活細(xì)節(jié),想用一個(gè)人的經(jīng)歷還原那一段非同尋常的社會(huì)歷史,以有別于那些大而空的所謂的寫宏大敘事的政治抒情詩和空泛而艱澀的偽現(xiàn)代詩。
即使是講述自己親歷的生活,我們知道一首長(zhǎng)詩是需要文化底蘊(yùn)和寫作功底來支撐的,我寫到第三大部分時(shí),就覺得底氣很不足了,因此又拖了一段時(shí)間,進(jìn)一步做了閱讀和思考的準(zhǔn)備,三年才斷續(xù)完成了長(zhǎng)詩《記憶》的寫作。
這首詩中第一部分是那場(chǎng)風(fēng)暴的初期記憶,第二部分是插隊(duì)生活階段的記憶,第三部分是我對(duì)那段特殊時(shí)間的認(rèn)知與感悟。歷史就像我在另一首詩中講到的:“有時(shí)候/人們離去的比時(shí)間還要快”(摘自《秋天在一天天迫近尾聲》)。僅僅三十年,許多沉痛的記憶已經(jīng)被許多人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那是我們這一代人被虛度的青春年華,那是人們必須汲取的慘痛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歷史,也許一首詩是微弱的,但我想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是永遠(yuǎn)不能泯滅的。
六十年代春日北京的沙塵暴,那些隱約感知的大動(dòng)蕩前的雷鳴;突如其來的八月的風(fēng)雨,父親堅(jiān)毅的腳步,母親含淚的眼睛,凄冷中熄滅的希望之火,青春蒼涼的記以及埋入心中的反抗的種子。
那多雪的凍裂冰層的冬天,那些詛咒春天,不只是青春?jiǎn)适У哪攴荩瑸槭裁次覀兣c時(shí)代總是相差了半個(gè)時(shí)辰?是誰說青春無悔,我看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依然冒著貧困的炊煙。
在燕南趙北的大澤白洋淀,蘆葦蒼蒼,孤雁哀鳴,在荊軻告別之地的古秋風(fēng)臺(tái),我們也曾放歌,我們也曾悲鳴,當(dāng)我們回到了劫后余生的古城,我們心中依舊充滿了哈姆萊特式的疑慮。
這些斷續(xù)的詞語也許還不能說明我的初衷,但那些記憶的確讓我在許多個(gè)夜晚不能平靜,我的確不能用平靜的語句將它們敘述出來,我們盡量節(jié)制內(nèi)心的洪流,讓它更沉郁,更接近歷史的真實(shí)。剛剛寫完時(shí)我對(duì)后一部分還存有疑慮,不是很滿意,現(xiàn)在讀來,感覺還是基本完成了我最初的設(shè)想。
吳投文:很多讀者注意到了,一九九一年九月,你寫了一組“夏末十四行”。在一九九七年和二〇〇一年,你又寫了兩組“夏末十四行”,這三組詩對(duì)照來讀,別有意味,似乎都具有自言自語的性質(zhì),流露了你真實(shí)的心跡。在新詩史上,很多詩人嘗試了十四行詩的寫作,像朱湘、馮至等人的十四行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你怎么想到要寫十四行詩的?怎么看待十四行詩的本土化?
林 莽:進(jìn)入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我在詩歌寫作上已經(jīng)走過了二十年,目睹中國(guó)新時(shí)期的詩歌發(fā)展歷程,感到我們?cè)姼鑼懽髦写嬖谠S多的弊端。在先鋒寫作群體中,許多詩人為先鋒而先鋒,一些詩人寫了許多似是而非,虛張聲勢(shì)的作品,一些人仿照翻譯體的詩歌,隨意分行,簡(jiǎn)單敘事,缺失了漢語寫作的語言魅力。也因此倒了許多閱讀者的胃口,令他們遠(yuǎn)離了詩歌。
詩歌是語言和情感經(jīng)驗(yàn)的藝術(shù),缺少了內(nèi)在情感,缺少了漢語語言的藝術(shù),也就沒有了詩歌。鑒于這些,我針對(duì)自己的詩歌寫作進(jìn)行了反思。嘗試著用十四行的方式控制詩的語言和結(jié)構(gòu),努力在一定的行數(shù)內(nèi)完成好一首詩的構(gòu)想,目的是讓自己的寫作不再過于隨意和松散,讓詩的語言更講究?jī)?nèi)涵,跳躍和空靈。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努力,我對(duì)寫作有了一些新的認(rèn)知,同時(shí)也寫出來一些自己較為滿意的作品。如:《夏末十四行·谷倉》《夏末十四行·滿月》《夏末十四行·玫瑰》《夏末十四行·老樹》《夏末十四行·夢(mèng)舞》《夏末十四行·裂痕》等等。
嚴(yán)格地說,我所寫的十四行僅僅是外表形式上的,它們的樣式很不嚴(yán)格。但這種練習(xí)對(duì)我的詩歌寫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它讓我在結(jié)構(gòu)的控制,在語言的表達(dá)上有了新的體驗(yàn)。詩歌是一門講究語言精確和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shù)乃囆g(shù),詩歌寫作是語言藝術(shù)中最難把握的,它要求每一位詩人都應(yīng)是語言精湛的匠人,正像茨維塔耶娃所說的“作為匠人,我懂得手藝”。
吳投文:從長(zhǎng)詩《二十六個(gè)音節(jié)的回響》到長(zhǎng)詩《記憶》,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年時(shí)間,中國(guó)詩壇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你也經(jīng)歷了個(gè)人風(fēng)格的變化。不過,在你的創(chuàng)作中,還是保持了一些基本穩(wěn)定的東西。張清華先生認(rèn)為,你的創(chuàng)作與芒克有相近之處,都稱得上是自然詩人。我覺得這把握住了你的一個(gè)重要?jiǎng)?chuàng)作特色,自然似乎構(gòu)成了你的一個(gè)創(chuàng)作情結(jié)。
林 莽:我基本同意張清華教授的判斷,我在給《草堂》詩刊的一篇短文中說:“我是一個(gè)依賴感覺寫作的人,因此大部分詩歌都是些零散的短詩作品。當(dāng)然也寫過一些較長(zhǎng)的和同種主題的組詩,因?yàn)榍橹拢驗(yàn)閮?nèi)在情感的積淀,構(gòu)成了一首長(zhǎng)詩或組詩的體量,才在具體寫作中逐步謀篇完成的。……詩歌記述了我生命中的真情歷程。將感性的記憶,通過詩歌的方式,建立一個(gè)與現(xiàn)實(shí)世界息息相關(guān)的藝術(shù)的世界,是我的詩歌理想。……詩歌給了我某種救贖,是詩歌讓我內(nèi)心的愛有了方向。”
可以說,我的每一首詩都是有感而發(fā)的,沒有內(nèi)心的波瀾我從不動(dòng)筆。
從另一個(gè)角度談,我的詩中自然意象、自然風(fēng)光較多,山川海洋,四季輪回,鳥雀植物,都會(huì)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我的詩句中。色彩和畫面感,和我從少年時(shí)代就喜歡繪畫相關(guān),它們?cè)黾恿宋业脑姼璧母惺芰Α?br />
我想一個(gè)人內(nèi)在的本質(zhì)是很難改變的,一個(gè)忠實(shí)于內(nèi)心的寫作者,他的作品一定會(huì)具有一脈相承的寫作風(fēng)格。
吳投文:陳超教授生前寫過一篇文章《林莽的方式》,這個(gè)題目就很好,文中分析了屬于你個(gè)人的詩歌話語方式。他在文中還談到了你創(chuàng)作的幾個(gè)階段,這樣說,“林莽經(jīng)歷了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初期寫作;一九七三年--一九八三年約十年對(duì)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尋求;一九八三年后有意識(shí)地脫離群體而進(jìn)入‘個(gè)人性’的創(chuàng)作;以及九十年代以來對(duì)人的內(nèi)在精神、人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及語言藝術(shù)本質(zhì)的關(guān)注四個(gè)創(chuàng)作階段。”(陳超《林莽的方式》)你覺得是這樣的嗎?請(qǐng)談?wù)勀愕膭?chuàng)作在不同階段的變化。
林 莽:我從一九六九年開始詩歌的寫作,經(jīng)過最初五年和后來近十年的學(xué)習(xí)、閱讀、練筆,到一九八三年開始思考尋找屬于自己的詩歌之路。我覺得前些年的詩歌,無論是語言應(yīng)用、構(gòu)思方式與大多數(shù)的朦朧詩人們過于相近,作品更多地關(guān)注社會(huì)表象問題,缺少了對(duì)語言藝術(shù)更深入的追求。那年我寫了一篇短文,后來收錄到北大五四文學(xué)社編輯的未名湖詩叢《青年詩人談詩》一書中。在這篇短文中我提出:應(yīng)該退去我們習(xí)慣的社會(huì)色彩,更多地回到對(duì)詩歌藝術(shù)本質(zhì)的尋求上來。
以后幾年,我有意識(shí)地脫離群體,尋找屬于自己的詩歌品質(zhì)與風(fēng)格,我前后用了三年時(shí)間,一九八五年我寫出了《灰蜻蜓》《晨風(fēng)》《滴漏的水聲》《水鄉(xiāng)紀(jì)事》等一些詩歌后,我覺得我已找到自己的詩歌之路。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我更自覺地沿著這條道路進(jìn)行著自己的探索與追求。
我同意陳超教授的描述。當(dāng)然,在這一過程中,我還在不斷地自我修正。詩人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社會(huì)的變遷,年齡的變化,詩歌中的情緒、認(rèn)知、感悟也一定會(huì)有所改變,這種變化是正常的。
吳投文:現(xiàn)在“白洋淀詩歌群落”成了朦朧詩研究中的一個(gè)熱點(diǎn),你一九六九年到白洋淀插隊(duì),應(yīng)該是“白洋淀詩群”中去得比較早的吧。在現(xiàn)在的一些描述中,白洋淀似乎成了當(dāng)時(shí)知青的世外桃源,甚至令人神往了,真實(shí)的情況如何?當(dāng)時(shí)白洋淀的物質(zhì)生活怎樣?你們可以忍受嗎?請(qǐng)談?wù)劇?br />
林 莽:白洋淀的詩人們大多是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到那兒的。我一九六八年底確定去白洋淀插隊(duì),因?yàn)楫?dāng)?shù)匚母镏泻笃谂尚誀?zhēng)斗激烈,無法下到村里。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事態(tài)平息了,我才下到生產(chǎn)隊(duì)。
說白洋淀是知青的世外桃源,我以為不太準(zhǔn)確。和其他各地知青不同的是,我們不是由國(guó)家指定跟隨集體到一個(gè)地方插隊(duì)的,沒有帶隊(duì)干部,也沒有人具體管理,因而有了一個(gè)相對(duì)寬松與自由的環(huán)境。插隊(duì)之前的考察,讓我們知道了白洋淀的生活條件和整體情況。因?yàn)榻?jīng)歷了幾年文革的歷練,我們知道如何和當(dāng)?shù)剜l(xiāng)親們更好地相處,如何避開地方文革后期的紛亂,并不卷入其中,這些讓我們?cè)诋?dāng)?shù)赜辛艘粋€(gè)較好的生存環(huán)境。
上世紀(jì)六十年代的中國(guó)農(nóng)村,基本是自然經(jīng)濟(jì)的農(nóng)耕時(shí)代,生產(chǎn)方式落后,交通不便,物資匱乏。那里距北京一百六十公里,我們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往返半個(gè)月時(shí)間,從那兒回北京坐船、步行、坐車,幾乎要用一整天的時(shí)間。那時(shí)的中國(guó)糧食等等一切都是定量的,白洋淀是水鄉(xiāng),糧食要靠國(guó)家供給,我們當(dāng)時(shí)得到的知青口糧是玉米、高粱和發(fā)霉的白薯干。
我們?cè)诋?dāng)?shù)剜l(xiāng)親們的幫助下,生活調(diào)理得還比較好。有的村的知青因?yàn)槎喾N原因生活得很不好。我在那兒生活了六年,結(jié)交了村里的很多朋友,到現(xiàn)在我和他們還有很多來往。
白洋淀最難能可貴的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較為寬松的環(huán)境和相對(duì)于其他邊遠(yuǎn)地區(qū)較好的生活條件和自然景觀,當(dāng)然還有距北京近,信息較快捷,也許因?yàn)槿绱耍庞辛撕髞淼摹鞍籽蟮碓姼枞郝洹薄?br />
吳投文:一九七三年底,你寫出了《列車紀(jì)行》,開始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主義創(chuàng)作。你最早接觸現(xiàn)代主義詩歌是什么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有什么樣的感覺?當(dāng)時(shí)在知青中閱讀比較多的外國(guó)詩人有哪些?
林 莽:一九七二年前后我開始接觸現(xiàn)代主義文化藝術(shù)的思潮,它像一股嶄新的陽光射入了我們幽暗的心靈。《在路上》《麥田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海鷗喬納森》,存在主義,印象派等等哲學(xué)、繪畫和小說與我們當(dāng)時(shí)的心境一拍即合。
那些黃皮書和灰皮書告訴我們這些在那個(gè)特殊年月中迷失的一代青年,我們也是“垮掉的一代”,他們頹廢中的尋求和反叛中的抗?fàn)幰舱俏覀兊纳鼘懻眨覀円苍卺葆逯袑ふ遥苍谀婢持羞M(jìn)行著人生的自我設(shè)計(jì)。也像海鷗喬納森一樣:天生就應(yīng)該飛翔,自由是生命的實(shí)質(zhì),任何妨礙自由的東西都應(yīng)該擯棄,不管什么形式的限制。
梵高、塞尚、畢加索、薩特、波德萊爾、聶魯達(dá)、洛爾迦、艾呂雅、阿拉貢、金斯伯格、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布洛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愛倫堡、葉甫圖申科、沃斯涅辛斯基等一批偉大的詩人的作品開始出現(xiàn)在我們的抄詩本上,是他們的啟示讓我們的寫作有了新的方向。
吳投文:波德萊爾對(duì)中國(guó)的現(xiàn)代主義詩歌影響很大,也對(duì)朦朧詩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duì)這個(gè)問題很感興趣,請(qǐng)談?wù)劇鞍籽蟮碓娙骸睂?duì)波德萊爾詩歌的閱讀。
林 莽:我一個(gè)抄詩本上開頭便是波德萊爾的九首詩,《太陽》《朦朧的黎明》《薄暮》《天鵝》《窮人的死》《仇敵》《不滅的火炬》《憂郁病》《黃昏和聲》。這些作品有一種基調(diào),這種基調(diào)在食指、北島、江河、多多、芒克的詩中都能找到。我的詩中那種憂郁的情調(diào)也應(yīng)與此相關(guān)。
我記得我們?cè)谟蜔艋椟S的聚會(huì)中,總有人會(huì)讀起波德萊爾的詩:“我的青春是一場(chǎng)陰暗的暴風(fēng)雨/星星點(diǎn)點(diǎn)透過來明朗朗的太陽”。昏暗、憂郁、狂吹的獵角、黑色的墓穴、青春的祭壇,這些成為了我們心中經(jīng)常閃現(xiàn)的詞語,也如同波特萊爾詩中說的“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從來沒有嘗過家的甜蜜,從來不曾生活過”這些觸動(dòng)我們心靈的語句,令我們愛不釋手,它也漸漸地融入了我們的心靈與詩行中。我們也同年輕的法國(guó)詩人一樣:“我獨(dú)自一身鍛煉著神奇的劍術(shù)/在各自的角落里尋找偶然的韻腳/我在字眼上躊躇,像在路上一樣/有時(shí)也會(huì)碰到夢(mèng)見已久的詩行”。他應(yīng)該是我們的啟蒙者之一。
吳投文:在“白洋淀詩群”中,芒克、岳重、多多的關(guān)系比較特殊一些,他們是北京三中初二七班的同班同學(xué),而且同齡,在十六歲同乘一輛馬車到的白洋淀,被稱為“白洋淀詩群”的“三劍客”。這個(gè)“三劍客”的說法是你們當(dāng)時(shí)插隊(duì)時(shí)就有的,還是后來被追加的?你對(duì)他們?cè)诎籽蟮聿尻?duì)時(shí)的創(chuàng)作情況很熟悉,請(qǐng)談?wù)勊麄儺?dāng)時(shí)的創(chuàng)作情況。
林 莽:我印象中“三劍客”的談法是九十年代初才在一些文章中出現(xiàn)的,究竟是誰第一個(gè)提出的我記不得了。關(guān)于他們?nèi)齻€(gè)人的創(chuàng)作情況在芒克的回憶中講了許多,我就不多重復(fù)了。據(jù)我所知,根子近些年還在整理他的一首寫于當(dāng)年的長(zhǎng)詩。
吳投文:你和多多等人都在文章寫到過,當(dāng)時(shí)白洋淀寫詩的人有不少,除了“三劍客”,還有宋海泉、方含等人。北島、江河、袁家方、史保嘉、甘鐵生等許多詩人、作家也到白洋淀游歷過。北島到白洋淀的次數(shù)多嗎?你當(dāng)時(shí)見過他沒有?
林 莽:白洋淀詩群廣義上說,是一個(gè)北京知青那些年一同追求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以白洋淀為中心的群體,真正在那兒生活過的有作品留下來的詩歌寫作者有十多人。北島、江河、食指等都曾到過白洋淀。江河曾有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在那兒逗留,他的第一首詩就是在我插隊(duì)的村子里寫出來的。北島去過白洋淀,但時(shí)間較短,他到過芒克插隊(duì)的大淀頭村。我和北島相識(shí)于七十年代末,我在白洋淀時(shí)沒有見過北島。
吳投文:你在一個(gè)訪談中說,“北島有一本詩集送給食指,是油印的小冊(cè)子,《峭壁上的窗戶》,上面寫著‘送給郭路生,你是我的啟蒙老師’(郭路生是詩人食指的本名,訪談?wù)咦ⅲ@個(gè)我親眼看見過。”你了解北島和食指當(dāng)時(shí)的交往嗎?
林 莽:《峭壁上的窗戶》是北島繼《陌生的海灘》后的另一本油印的詩集,我在食指百萬莊的家里見過北島送給食指的這本集子,扉頁上就是這樣寫的。我以為北島是一個(gè)真誠(chéng)的詩人,他對(duì)食指的敬重,是源于對(duì)詩歌歷史的敬重,我們那一代詩人幾乎都受到過食指的啟示和影響,他的確是我們那一代的先驅(qū)者。
北島和食指的交往應(yīng)該也是在七十年代的后幾年開始的。他和芒克主辦的《今天》的第二期上就刊登了食指的詩歌《相信未來》《命運(yùn)》《瘋狗》等三首作品,那是一九七九年初。
吳投文:你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白洋淀距離北京一百六十公里,當(dāng)時(shí)乘火車再換汽車,六至八小時(shí)可以到達(dá)。有的插隊(duì)知青騎自行車十二小時(shí),可從白洋淀回到北京。”(林莽:《關(guān)于“白洋淀詩歌群落”》)在當(dāng)時(shí),這個(gè)距離實(shí)際上也不是很近啊,你當(dāng)時(shí)每年回北京的次數(shù)多嗎?與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龍或文學(xué)沙龍有過聯(lián)系沒有?
林 莽:當(dāng)年我曾多次騎自行車往返于北京和白洋淀,插隊(duì)的后幾年我在村里的小學(xué)當(dāng)代課教師,因?yàn)闀r(shí)間關(guān)系,每年回家的次數(shù)不多。每年的寒假在北京住的時(shí)間較長(zhǎng)。參加過一些文學(xué)的聚會(huì),也就是傳說中的文化沙龍吧。如在孫康家的聚會(huì)和在宋海泉家的聚會(huì)。我還曾在那些聚會(huì)上讀過我最終也沒有完成的小說的片段,我的詩歌也同樣有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更多的是大家對(duì)讀書的體會(huì)和時(shí)局的漫談,這些交談和心靈的碰撞,對(duì)我而言受益匪淺。
吳投文:詩人食指(郭路生)在文革結(jié)束之后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默默無聞,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之后才被逐步鉤沉出來。在食指“復(fù)出”的這一過程中,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的《詩探索金庫·食指卷》就凝聚了你的大量心血。謝冕先生說過,“一九九八年我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將食指浮出水面。”作為重要的當(dāng)事人,你怎么看待食指的“復(fù)出”現(xiàn)象?
林 莽: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我曾經(jīng)講,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是一個(gè)欠債的歷史,許多詩人、作家本應(yīng)得到的榮譽(yù),被歷次社會(huì)動(dòng)蕩或政治運(yùn)動(dòng)所遮蔽。食指就是這樣,在他那些與時(shí)代同步的優(yōu)秀作品傳播之時(shí),他卻因不合時(shí)宜而跌倒在塵埃中,我一直想應(yīng)該還歷史以公正,這就是我做這件事情的最初動(dòng)力。我記得,八十年代末評(píng)《今天》詩歌獎(jiǎng)時(shí),我就表達(dá)過我的意見,我認(rèn)為應(yīng)該評(píng)給對(duì)我們這一代人都有過影響和啟示的詩人食指,但后來沒有實(shí)現(xiàn)。
為了詩歌的榮譽(yù),為了還歷史以公正,九十年代后幾年,為食指卷的出版我大致用了三四年的時(shí)間搜集、整理食指的詩歌作品和生平簡(jiǎn)歷,聯(lián)系出版事宜。《詩探索金庫·食指卷》出版后在北京、山東進(jìn)行了多次的宣傳和推廣工作,為那一年食指在文化領(lǐng)域的全面復(fù)出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年電視、廣播、報(bào)紙有眾多的宣傳和報(bào)道,那一年我們?yōu)槭持搁_了多次售書、朗誦、報(bào)告和生日等多次活動(dòng)。應(yīng)該說那一年食指的復(fù)出是文壇的一件大事。
食指的復(fù)出不光是還食指以公正,也是對(duì)中國(guó)新詩史的一次修復(fù),也是新詩再次走出低谷的一個(gè)標(biāo)志。這之后的“盤峰詩會(huì)”和隨之而來的新世紀(jì)新詩的復(fù)蘇,為漢語詩歌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吳投文:一九六九年,你通過江河讀到了食指的《相信未來》、《煙》、《酒》等幾首短詩。那年,你也在筆記本上寫了幾首詩。你最初寫詩是受到食指的影響嗎?此前寫過詩沒有?據(jù)說食指的詩在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的知青中影響很大,不過,現(xiàn)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質(zhì)疑,說食指的詩還是局部的影響,只是局限于北方幾個(gè)知青集中的地方。可否談?wù)勈持冈姼柙诋?dāng)時(shí)的傳播情況?
林 莽:在讀到食指作品之前我已經(jīng)開始了詩歌寫作的嘗試,那時(shí)是受中國(guó)古體詩,俄羅斯、法國(guó)、英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巴爾扎克、左拉、托爾斯泰、普希金、萊蒙托夫、泰戈?duì)柕刃≌f和詩歌的影響。但那些畢竟是遙遠(yuǎn)的,而食指的詩,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他所寫的就是我們真切的生命體驗(yàn)和感受,那種觸動(dòng)和激勵(lì)是不言而喻的。
問題中所說的:“現(xiàn)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質(zhì)疑,說食指的詩還是局部的影響,只是局限于北方幾個(gè)知青集中的地方。”這種說法很可笑。試想,一個(gè)影響了一代人,影響了多位重要詩人的寫作者,他的地位還用懷疑嗎?何況還有他的作品清晰地?cái)[在那兒,那些為一個(gè)時(shí)代立言的詩歌,一位填補(bǔ)了歷史空白的詩人的重要性還要懷疑嗎?
據(jù)我所知,許多北京青年都曾讀過和手抄過食指的詩,我認(rèn)識(shí)的無論在北京、東北、內(nèi)蒙古、陜西、云南、白洋淀的那一代青年,都有人是食指詩歌的傳播者,他們都曾為食指詩歌中所寫出的一代人的聲音所感動(dòng)。
食指詩歌的傳播雖然不是家喻戶曉,但是最有效的,他的詩歌填補(bǔ)了那個(gè)特殊年代文學(xué)的空白,促進(jìn)了中國(guó)新詩的發(fā)展,他無疑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先驅(qū)者。
吳投文:我參加過多次學(xué)術(shù)會(huì)議,談到文革“地下寫作”的真實(shí)性問題,一些學(xué)者對(duì)標(biāo)注時(shí)間為文革時(shí)期的作品表示質(zhì)疑,認(rèn)為一些作品可能存在很大幅度的修改,不宜被定為文革“地下寫作”的作品。這大概也涉及到了白洋淀詩歌的時(shí)間真實(shí)性問題。你怎么看待這個(gè)問題?請(qǐng)談?wù)劇?br />
林 莽:我同意這種質(zhì)疑,因?yàn)橛行┤嗽谖膶W(xué)史的研究上,為了挖掘而挖掘。把許多沒有多少依據(jù)的作品都列入“潛在”寫作的范圍內(nèi)。我以為,對(duì)一些作品應(yīng)該有所甄別,有影響和傳播的詩歌是有效的,有的只是寫了,但沒有任何傳播,甚至都沒有第二個(gè)人讀過的作品,應(yīng)該另當(dāng)別論。
也有些作品是有過多次修改的,我知道白洋淀詩人的有些作品基本是原始的,如芒克那時(shí)的一些詩,是由趙一凡保留的最原始的版本,根子、多多的詩也是有當(dāng)時(shí)的手抄本,我的詩也同樣有最原本的底稿和他人抄本。我以為詩人應(yīng)該尊重文學(xué)的歷史,研究者應(yīng)該更為嚴(yán)謹(jǐn),并言之有據(jù)。
吳投文:一九九四年五月,你全程組織了一次“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dòng),芒克、宋海泉、甘鐵生、史保嘉等與白洋淀知青相關(guān)的人參加了尋訪活動(dòng)。“白洋淀詩歌群落”這個(gè)提法就是在這次尋訪的討論會(huì)上確定的。我注意到,有些白洋淀知青詩人缺席了,參加尋訪活動(dòng)的人員名單是怎么確定的?請(qǐng)具體談?wù)勥@次尋訪活動(dòng)。
林 莽:“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dòng)是《詩探索》編輯部計(jì)劃對(duì)七八十年代詩歌團(tuán)體進(jìn)行尋訪研究工作中的一個(gè)具體課題,因?yàn)槲伊私猱?dāng)時(shí)和當(dāng)?shù)氐那闆r,就由我牽頭組織和安排了那次尋訪活動(dòng)。這其間華北油田的詩人張洪波和華北油田文聯(lián)給予了很多的幫助。
當(dāng)時(shí)白洋淀的詩人有些聯(lián)系不上,有些在國(guó)外,比如:多多在荷蘭,根子、江河在美國(guó),孫康沒有聯(lián)系上等等。這次尋訪活動(dòng)后,許多老朋友又逐步地恢復(fù)了聯(lián)系。
這次尋訪活動(dòng)應(yīng)該說是很成功的,尋訪中確立了“白洋淀詩歌群落”的名稱,不再是一些人所稱呼的“白洋淀詩派”等等混雜的概念。尋訪后,宋海泉,史保嘉,甘鐵生等寫出了很有價(jià)值的回憶文章。后來?xiàng)顦濉②w哲等又有一些后續(xù)的文章,陳超為這次尋訪撰寫了《堅(jiān)冰下的溪流--談白洋淀詩群》的研究文章。這些為以后對(duì)“白洋淀詩歌群落”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吳投文:一九九八年,你率先提出并協(xié)助組織了“盤峰詩會(huì)”。由于會(huì)上“知識(shí)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分化成了兩個(gè)對(duì)立的陣營(yíng),這次詩會(huì)產(chǎn)生了極大的沖擊波,也使人們對(duì)會(huì)上的情形產(chǎn)生了種種誤傳和猜測(cè)。“盤峰詩會(huì)”攪動(dòng)了沉寂十年的中國(guó)詩壇,可以說成了中國(guó)當(dāng)代詩歌的一道分水嶺,尤其對(duì)新世紀(jì)以來的中國(guó)詩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什么要組織這次詩會(huì),會(huì)上的具體情況怎樣,可否談?wù)劊?br />
林 莽:一九九八年我閱讀了沈奇的文章《秋后算賬》,這是一篇針對(duì)程光煒主編的九十年代詩選《歲月的遺照》所引發(fā)的“民間寫作”和“知識(shí)分子”的爭(zhēng)論而撰寫的傾向于批評(píng)這本書有偏頗的文章。從這篇文章我想到了八十年代以來的有關(guān)詩歌寫作中借鑒西方文化還是更多地關(guān)注本土意識(shí)的美學(xué)傾向,這一問題雖然沒有提到表面上來,但十多年來一直存在著。我想這一寫作美學(xué)觀念下的爭(zhēng)執(zhí),一定會(huì)有助于中國(guó)新詩的發(fā)展。因而我在《詩探索》編輯會(huì)上提出了開一個(gè)“打架的會(huì)”的想法。將主張“知識(shí)分子寫作”和主張“民間寫作”的詩人召集在一起,進(jìn)行一次當(dāng)面的爭(zhēng)論。這一提議得到了謝冕、吳思敬、楊匡漢三位主編和編輯部全體同仁的贊同。
因?yàn)橘Y金問題,我找到了北京作協(xié)秘書長(zhǎng)李青和《北京文學(xué)》社長(zhǎng)章德寧,這一會(huì)議的內(nèi)容也得到了她們的認(rèn)同和支持。通過北京作協(xié)我找到平谷的作家柴福善,他幫助聯(lián)系了平谷的“盤峰賓館”。這樣,這次會(huì)議得以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平谷盤峰賓館舉行。
當(dāng)時(shí)吳思敬教授為詩會(huì)定名為“世紀(jì)之交中國(guó)詩歌創(chuàng)作態(tài)勢(shì)與理論建設(shè)研討會(huì)”。會(huì)議由《詩探索》編輯部,北京作家協(xié)會(huì)、《北京文學(xué)》編輯部、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hu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等單位聯(lián)合主辦。
當(dāng)時(shí)的邀請(qǐng)名單里有謝有順和韓東,但他們兩個(gè)沒有出席。沈浩波本應(yīng)在邀請(qǐng)之列,但他當(dāng)時(shí)剛剛本科畢業(yè),雖然寫了《誰在拿九十年代開涮》,但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雙方詩人和會(huì)議組織方三十多人出席了會(huì)議,張清華撰寫了本次會(huì)議綜述。
會(huì)議開了三天,發(fā)生了激烈的爭(zhēng)執(zhí),各個(gè)劍拔弩張,有時(shí)甚至就要相互動(dòng)起手來。有人找我要求晚上不休息接著開。中間有一個(gè)傍晚,詩人到金海湖大壩上散步,相互間還是比較友好的,身體勾肩搭背,但嘴上卻互不相讓。
詩人們就各自的主張和對(duì)方寫作的問題進(jìn)行了開誠(chéng)布恭的辯論與爭(zhēng)執(zhí)。也有人將相互之間具體的矛盾和對(duì)某些問題中的積怨拿到了會(huì)議上。這是自八十年代以來先鋒詩人之間第一次對(duì)詩學(xué)觀念面對(duì)面的論爭(zhēng)。“盤峰詩會(huì)”之后,中國(guó)新詩開啟了一個(gè)寫作的新時(shí)代,許多新的詩人大量地涌現(xiàn)出來。
我在這次會(huì)議的最后總結(jié)階段有一個(gè)簡(jiǎn)短的發(fā)言,我大致說的是:中國(guó)先鋒詩壇不只是“知識(shí)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這一對(duì)矛盾,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現(xiàn)象,有許多的人自我膨脹,大師滿天飛,我們?cè)谠S多地方會(huì)與大師相遇,在詩人的聚會(huì)中、在朗誦會(huì)上、在文章的字里行間,我們都會(huì)遭遇大師,有時(shí)大師與大師的相遇,令空氣凝結(jié),讓我們幾乎喘不過氣來。我們的許多詩人淺薄地忘記了對(duì)詩歌的敬畏之心。在藝術(shù)面前,我們應(yīng)該永遠(yuǎn)虔誠(chéng),永遠(yuǎn)靜心以求。
“盤峰詩會(huì)”期間,作家柴福善作為旁觀者,有一個(gè)相對(duì)完整的個(gè)人聽會(huì)筆記,《詩探索》曾在“會(huì)刊”上全文刊載。
這次會(huì)議后,與此相關(guān)的雙方詩人還各自撰寫了大量的爭(zhēng)論文章,許多無知者隔岸觀火,一些心懷叵測(cè)的人說:先鋒詩人為掙地盤打起來了。這種說法絲毫不了解其中的詩學(xué)價(jià)值。
這次會(huì)議被與會(huì)詩人們稱之為“盤峰論劍”,它成為了中國(guó)詩歌開啟新時(shí)期的分界線。
吳投文:你長(zhǎng)期擔(dān)任《詩刊》和《詩探索》的編輯,在《詩刊》和《詩探索》的工作中有許多獨(dú)特的創(chuàng)意,付出了許多辛勤的勞動(dòng)。請(qǐng)結(jié)合你所做的工作和貢獻(xiàn),談?wù)勀愕捏w會(huì)和想法。
林 莽:我自八十年代就一直想為中國(guó)新詩的發(fā)展做些事情,現(xiàn)在回憶一下,我的一想法還是有了一些兌現(xiàn)。
上世紀(jì)九十年代詩歌鉤沉和修復(fù)詩歌史的努力:組織了一九九四年的白洋淀詩歌尋訪;完成了一九九八年詩人食指浮出水面兩件事。一九九九年提出和組織召開“盤峰詩會(huì)”,為新詩發(fā)展開啟了一個(gè)新起點(diǎn)。
一九九八年我到《詩刊》工作,當(dāng)時(shí)有人問我到《詩刊》工作有什么想法?我曾明確地說:只想為詩歌做些具體的事情。
后來在《詩刊》工作期間,我提出了創(chuàng)辦并主持了《詩刊》下半月刊的各項(xiàng)工作:設(shè)計(jì)了“華文青年詩人獎(jiǎng)”;推出了中國(guó)最早的“駐校詩人”的方式;與漓江出版社多年合作編輯年度詩選;組織開展遍布全國(guó)的“春天送你一首詩”大型詩歌公益活動(dòng)。這期間還在自一九九四年復(fù)刊的《詩探索》兼職,提出創(chuàng)辦了《詩探索》作品卷,二〇一〇年退休后創(chuàng)辦了會(huì)員制的“詩探索詩人會(huì)所”,創(chuàng)辦了“紅高粱詩歌獎(jiǎng)”和“發(fā)現(xiàn)詩歌獎(jiǎng)”。
在《詩刊》工作期間,創(chuàng)辦和主持《詩刊》下半月刊和“華文青年詩人獎(jiǎng)”,一個(gè)是為青年詩人建立了一個(gè)展示的平臺(tái),一個(gè)是為青年詩人樹立了優(yōu)秀詩歌寫作的榜樣。下半月刊為一大批青年詩人走上詩壇,起到了助力作用,也開辟了中國(guó)詩壇下半月刊的新模式。而“華文青年詩人獎(jiǎng)”則推出了幾十位優(yōu)秀的中國(guó)詩壇的有生力量,并以一個(gè)獎(jiǎng),一個(gè)研討會(huì),一本書和一個(gè)“駐校詩人”的四個(gè)一的方式建立了立體的評(píng)獎(jiǎng)理念和方法。
以上這些,包括近些年在《詩探索》的許多工作,都是想為中國(guó)詩歌的發(fā)展做些具體的建設(shè)性的工作。這些年我一直在兌現(xiàn)著“為詩歌做些具體的事情”的諾言。
吳投文:一九八〇年代被認(rèn)為是詩歌的黃金時(shí)代,詩人的桂冠叫人羨慕,很多詩人懷念那個(gè)年代。現(xiàn)在,詩歌有時(shí)候成了人們?nèi)⌒Φ脑掝},詩人有時(shí)簡(jiǎn)直成了瘋子的代名詞,這帶來了詩人文化身份的尷尬。一些詩人掩飾自己的詩人身份,甚至有的詩人在詩壇有不小的名聲,但他身邊的人并不知道。你如何看待當(dāng)下詩人的文化身份與世俗身份的沖突?
林 莽:這種說法我以為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現(xiàn)在這種情況有所好轉(zhuǎn)。這里面有社會(huì)的偏見,也有詩人自身的問題。
我們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詩歌中,有很多簡(jiǎn)單的口號(hào)式的詩歌,還有粗鄙的大躍進(jìn)民歌、工人詩歌、戰(zhàn)士詩歌、小靳莊詩歌等等,這些讓對(duì)詩歌滿懷虔誠(chéng)和敬畏的人們失去了詩歌的崇高之感。
八十年代詩歌的回歸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地又被多種社會(huì)問題所遮蔽。先鋒詩歌的興起,一些跟風(fēng)者也都寫起了似是而非的現(xiàn)代詩來,許多作品讓人如墜云霧之中而無法閱讀,而我們的刊物編輯和一些批評(píng)家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于是一些本來的讀者也只好敬而遠(yuǎn)之。
八十年代走在時(shí)代藝術(shù)最前列的詩歌,在九十年代成了許多媒體、電影、電視劇,拿來恥笑的對(duì)象。詩人的個(gè)人身份問題被新聞無限放大,詩人成為了人們心中可笑的角色,詩人成了愚人、病人和瘋子的代名詞,這令許多寫作者為之尷尬。但近十幾年來,由于詩歌的多元化和不斷的發(fā)展與成熟,社會(huì)文化需求的變化,詩人群體的共同努力,詩歌正在逐漸恢復(fù)它的聲譽(yù)與光榮。
我以為詩人首先應(yīng)該是一個(gè)活生生的人,一個(gè)世俗生活中的人,一個(gè)有社會(huì)責(zé)任感和有七情六欲的人,然后才是一個(gè)詩人。
那些總拿自己的詩歌說事的人,那些將自己扮演成為類似詩人的人,那些冒充詩歌大師到處裝腔作勢(shì)、招搖撞騙的人,那些隨意亂寫的人,是詩歌的敗壞者,他們被人鄙視,我以為是好事。而一個(gè)不慕虛榮,虔心寫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人,一定不會(huì)被人們看不起。
詩人也是一個(gè)普通的人,寫作只是他表達(dá)自己的一種方式,那個(gè)不正常的時(shí)期正在過去,詩人要用自己的作品證明自己,文本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與詩人的名稱不相干的。
吳投文:你認(rèn)為要成為一個(gè)詩人,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請(qǐng)談?wù)劇?br />
林 莽:我認(rèn)為,良好的感知力和語言藝術(shù)的天分,生命對(duì)世界的真切體驗(yàn)和感悟,廣泛閱讀的文化積累,人生經(jīng)驗(yàn)和文化經(jīng)驗(yàn)的融會(huì)貫通,是一個(gè)優(yōu)秀詩人必須具備的才能。
吳投文:《林莽詩選》扉頁上有一句題詞:“我尋求那些寂靜中的火焰,它們是屬于我的。”這是否代表你的詩觀?你的詩歌創(chuàng)作從白洋淀開始到現(xiàn)在已有四十多年了,你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林 莽:應(yīng)該說這不是一種詩觀,只是我希望進(jìn)入的一種詩歌境界吧。寂靜,但蘊(yùn)含著閃耀生命之光的溫暖與魅力。
在近五十年的藝術(shù)追求中,我理解了里爾克所講的:“藝術(shù)也是一門學(xué)習(xí)真誠(chéng)的功課。”詩歌和其他藝術(shù)一樣,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只有虔誠(chéng)的人,才會(huì)寫出被歷代人們不斷發(fā)現(xiàn)的好作品。
來源:鳳凰讀書
作者:吳投文 林莽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28/c405057-29367561.html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