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巢:正在籌拍一部有關海子的電影
老巢:如果有一天我不寫詩了,那讓我不寫的人就是我自己。那一天的到來,就不是“失落”這么簡單了,那意味著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一首大詩,要用“悲壯”來形容。這首大詩的最后一句是:死亡。
編者按: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詩歌在一定層面已經進入了當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時,中國詩歌網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也讓越來越多的實力詩人滲透到了中國詩歌網的各大板塊!正值中國新詩走過百年之際,為了展示中國實力詩人的氣質和風彩,我們有了這次獨家策劃,對中國實力詩人進行系列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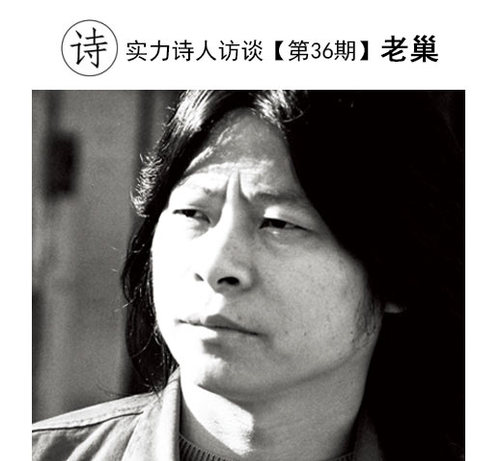
老巢
詩人
老巢(詩人主頁):
http://www.zgshige.com/c/2017-06-27/3689255.shtml
原名楊義巢。1962年10月生于安徽巢湖,現居北京。詩人,影視編劇,導演。現任中視經典電影工作室主任,詩歌中國網主編,北京巢時代影視文化公司總裁。北京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版有詩集《風行大地》、《老巢短詩選》、《巢時代》、《春天的夢簡稱春夢》等。作品入選《中間代詩全集》、《新世紀5年詩選》、《北大年選.詩歌卷》等選本。獲全國年度“優秀詩集獎”、年度“十佳詩人”和“詩歌貢獻獎”等。被評為“新世紀安徽十大詩人”。策劃并主持“新經典·重提學院派——全國高等美術院校名師作品展”。編導專題紀錄片《永遠的紅燭》、《敦煌百年》、《啟功先生》等,獲政府星光獎。參與《李宗仁歸來》、《警世調查》等電視連續劇的編劇工作。國內首部反映當代的藝術家生活的長篇電視連續劇《畫家村》的編劇和導演。執導二十三集電視連續劇《兵團往事》,并擔任制片人。交通部和央視聯合攝制大型紀錄片《長江交響》總導演。現以導演、制片人的身份籌拍一部關于詩人海子的院線電影。
訪談
1、花語:老巢好!您是著名的詩人導演,這么多年的導演生涯,都拍過哪些電影電視劇?
老巢:拍過的就不去說它了,可以忽略不計。說說我正在籌備的一部關于海子的電影吧:
都在說“詩和遠方”,是因為我們只有“眼前的茍且”。活在今天中國尤其是都市里年輕人,在應該寫詩和去遠方的年齡,卻被高房價和就業難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死死地捆住了手腳。粗糙的環境,殘酷的競爭,巨大的壓力,使他們越來越冷漠,越來越不動感情。他們起早摸黑,擁擠在地鐵和公交車上,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掙扎,流汗流淚,疲于奔命,沒時間也沒心情抬頭“仰望星空”。他們與掛在嘴邊的“詩和遠方”,漸行漸遠。
到今年,中國新詩就誕生100周年了。一個叫“海子”的詩人離開我們也快30年了。在這時候,拍一部關于他的電影,既詩獻禮,也是紀念。作為中國(大陸)電影史上第一部以真實詩人為主人公的故事片,也可以理解成是主創們聯手寫給當代中國人的一首詩。什么是詩和遠方?我們用電影回答:這就是詩,這就是遠方。
1988年夏天,24歲的詩人海子路過德令哈,青藏高原上“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寫下《日記》,吟出了他詩歌中影響力僅次于“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名句:“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半年以后的1989年春天,他在山海關臥軌自殺。那么,誰是“姐姐”?到底發生了什么?
2、花語:最早寫詩是哪一年,因何與詩結緣?影響您最深的詩歌是哪一首?
老巢:確切哪年記不清楚了。初中時開始模寫舊體詩,寫新詩,或者叫現代詩、自由詩,應該是上高中的事了。都寫了些什么,因為沒保存,也講不清楚了。那個年紀,不外乎夢想、愛情和友誼吧,少年也識愁滋味。前兩年與高中的老同學們聚會,據他們說,畢業那天,我在各奔東西的火車站讀了一首我的詩,傷離別的,弄得男同學熱淚盈眶,女同學泣不成聲。那應該是一首好詩,很煽情,但我記不得了,連那感人的場景一起忘了。
說到與詩的緣分,應該和情緣一樣,是天注定吧。我認為真正的詩人都是天生的,何時遇見,開始動筆,可以是一件小事,甚至是一場小雨,一片在雨中偶爾飄零的綠葉。也可以是一杯酒。至于影響最深的一首詩,我也說不準確,那時候我熱愛歌德、雪萊、拜倫和普希金、萊蒙托夫,修辭上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莎士比亞,他的詩劇臺詞和十四行詩,我幾乎都能背誦。
3、花語:在您眼里何為詩歌,哪些是值得作為詩歌去記錄的?
老巢:用詩歌的眼睛去看世界,則世界就是詩歌。世間萬物,包括我們肉眼看不見的,都可以入詩,換句話說,就是:都值得我用詩歌去表達。可以寫太陽,月亮,高川大河,海闊天空,也可以寫小花小草。可以寫雄鷹和駿馬,也可以寫阿貓阿狗,屋檐下的麻雀。關鍵在于我們用怎樣的心態去打量,萬物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可以是詩歌的。人類的情感也是這樣,可表“大愛”,也可抒“小情”,光明和黑暗,動我心者,皆可入詩。
4、花語:詩歌在你生命里占有怎樣的位置?
老巢:這需要舉例說明。比如年少輕狂的我,以為生活在別處,爬上一列貨車就開始流浪,險象橫生,茫然失措,兩年后,是詩歌讓我從建筑工地一群青年中脫穎而出,避免在世俗的下坡路上滑得更遠。比如一句“家,在任意一塊天空下”,讓我在人滿為患,壓力山大的京城過了二十幾年沒心沒肺的的“慢生活”,在別人眼里,我是在“虛度光陰”。比如坐在電視機前看汶川地震的直播,那么多孩子的死讓我痛不欲生,一首《他們都比我更應該活著》,止住了我的哭泣。比如看完邁克爾的紀錄片,走出電影院坐上酒桌,一提起他,就掉眼淚,寫完《或者我瘦成邁克爾并像他一樣死去》,我恢復了正常。更多黯然神傷的夜晚,是詩歌幫我熬到了天亮。詩歌,讓我的情緒得以宣泄,是我生命的又一個出口。正如我在自己第一本詩集《風行大地》的自序里所說:寫詩,當我疲憊的心要求嘔吐。
5、花語:如果不讓您寫詩,會怎樣,會失落嗎?
老巢:起碼現在看來,沒有誰會不讓我寫詩,進一步說,誰也不能讓我不寫詩。所以,這是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是問題。如果有一天我不寫詩了,那讓我不寫的人就是我自己。那一天的到來,就不是“失落”這么簡單了,那意味著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一首大詩,要用“悲壯”來形容。這首大詩的最后一句是:死亡。詩意點說是:消失在路上。

詩人導演楊義巢,攝影:劉不偉
6、花語:必答題:好詩的標準。
老巢:沒有標準。對我而言,讀著舒服,就是好詩。而讓我“舒服”的詩又可能讓另一個人“不舒服”。所以,舒服的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在我們這一代詩人中,我個人比較喜歡楊黎的詩,他從去年開始,每天都“遠飛”都寫詩,還不止一首。我也每天都點開他的微信看。但我身邊也有不喜歡甚至看不上他詩的人,我還因此與一個美女絕交,而她是因為喜歡我的詩才走近我的。這么說,我的心中其實還是有標準的。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都有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標準,但,不能強加于人。
7、花語:如何看待趙麗華的梨花事件和趙麗華這個人。
老巢:關于“梨花體”和趙麗華,事發當時,我先后寫過兩篇文章:《趙麗華的宿命和破綻》、《作為一個詩歌符號的趙麗華》。我指出:一天早晨醒來,她突然發現自己上了網絡頭條,并被命名為“詩壇芙蓉”、“梨花教主”。回憶當時的情況,她說:“我想跳樓,但廊坊的樓太矮。怕摔成殘廢,給殘聯和民政部門添麻煩”。這話今天聽來像是調侃,個中滋味在她自己心里。這也是當代中國詩歌的“命中注定”!“朦朧詩”以后,詩歌很快退出公眾話語平臺,逐漸演變成詩人們的“自言自語”。就在要被大眾徹底忘到腦后的時候,2006年9月,詩歌選擇了這樣一個人,以一種“娛樂”的方式再次回到了“現場”,回到了時代文化視野和人民日常生活中。這在我們的“意料之外”,但卻在歷史的“情理之中”!
今天,事情過去10年之后,趙麗華已成功跨界,成為一名畫家,她的“梨花公社”已成為宋莊的一處醒目的文化地標,事實也驗證了我當初的判斷:詩歌選擇了趙麗華,因為她的優秀和明顯的“破綻”!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閱讀的廣泛和深入,她的優秀會得到更多的共識。而她的“破綻”說不定就會成為大家最為熟知的流傳最廣的互動詩歌文本。
8、花語:現在很多詩人都在畫畫,您怎么看?
老巢:首先肯定與“智能”無關,更談不上“時髦”。我不反對詩人選擇一種體面的謀生方式,寫詩畢竟養不活自己。今天的詩人畫畫不丟人,但別往傳統上扯。古人詩畫不分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是“寫心”的姿態,加上宣紙與毛筆所決定的。這里還有一個“跨界”的問題,我是支持的,在文字之外,多一種表達總是好事。
9、花語:對于快樂和幸福,您的注解是什么?能否說一下您認為的最快樂的事?
老巢:這個問題因人而異。別人世俗層面上的“快樂和幸福”,對我,可能一錢不值。而我的快樂和幸福是我的私事,不說也罷,或者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當然沒有什么“最快樂”,只有“更快樂”。有個底線必須指出:我們的快樂和幸福不能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而快樂著別人快樂幸福著別人的幸福,是一種境界,難能可貴。

詩人導演楊義巢
10、花語:請描述下您的故鄉和成長經歷。
老巢:高中畢業之前,合肥是我去過的最大的城市,它是省會,有一條全省最寬的街,長江路。我出生在離合肥百里開外的放王崗,行政區域屬當時的巢縣,現在已改為巢湖市。而我父親的老家長豐縣當時是合肥市轄內唯一的縣。父親出生的地方叫都崗,懂事以后尤其是開始寫詩,我一直在尋找這兩個崗之間隱秘而虛幻的關系。我記得有一些夜里,我跟隨父親從巢縣車站上車,路過合肥到一個叫做下塘集的車站下車,再走上七八里路,就到了住滿了我的親戚的村莊。我似乎就應該在有“崗”的地方出沒吧。合肥,又叫廬州,有一出戲叫《陷巢州》,民間有個傳說“陷巢州,漲廬州”。前些年,有媒體報道,在巢湖的底下,考古學家們果然發現了一個陷落的城池,似乎映證了這一說法。離開校園,在合肥渡過了我人生中最雜亂無章的歲月,我不停地變換著自己的身份,從一場酒到另一場酒,我活在半醉半醒中。
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離開它登上開往北京的火車,一轉眼已有24年。對故鄉,我的記憶有難言的喜悅,也有難言的苦楚。我的青春歲月,不像詩里寫的歌里唱的那樣明亮而浪漫,基調是灰暗的,零亂而唐突。我犯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錯,也為此付出了很多代價。當年離開合肥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為了夢想,為了追求,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現在還沒到講那個故事的時候。記得有句古話,逼上梁山。這些年我去過很多城市,最喜歡的城市是我現在居住的北京。而在我夢里出現最多的城市,是過去的那個合肥。
11、花語:如何看待口語詩?如何寫出一首好的口語詩?
老巢:在我這里,只有詩和非詩、好詩和不好的詩,用書面語還是所謂的口語,是詩人自己的事。在我的詩里,有成語,也有口頭禪,寫得自然讀著舒服就可以。我目前創作上的困擾只有一個:怎樣寫得與昨天的老巢不一樣。重復自己難以避免,甚至是形成風格的前提,但創作者要有個自覺,一直重復是可恥的。
13、花語:說來,您也算是多年的北漂。從何時開始北漂的,北漂的原因是什么?
老巢:上個世紀末,1993年8月中旬。原因很復雜,也可以說沒有原因,是命運的牽引或擺布吧。遠方,對于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詮釋。比如古人就既推崇“行萬里路”,又奉行“寧靜以致遠”。而對于8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遠方,就是別處,生活在別處。所以他們北漂,他們去西藏,有人徒步走中國,有人漂流長江和黃河。那是一個追逐夢想、激情燃燒的年代,也是一個文學的年代。具體到我,非要說兩條的話:一、當時我已是而立之年,對在老家那種一眼可以看到老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逆反心理,想換種活法。二、當年5月份進京參加一個現代詩研討會,第一次踏上帝都的土地,有種莫名的認同感,覺得這才是我的城市我的地盤。說到底,還是那句話:梁山,都是逼上的。
14、花語:北漂途中,是否遭遇困境,有沒有想過打退堂鼓,回家鄉?
老巢: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困境,所有活在哪,關系不大。換句話說,在哪里,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其實這些年我的情感與事業都一直不順,當“不順”成為常態,也就一天天削弱著對我的負面影響,到今天已基本等于零了。一個年輕的、被巨大的文學野心驅使的天才詩人,一個身心疲憊的游子,偶然又必然地闖入人生地不熟的京城,只能被動接受生活的賜予和剝奪。憧憬愛與被愛,又無法掌控大局。實際情況是,渴望幸福,又對幸福心存疑慮。現實的力量足以擊碎人們對幸福的那一點癡心與妄想,命運的強悍,幾乎是不容置疑的。
真沒打過退堂鼓,往哪退?怎么退也退不出命運的手掌心。無路可退,處理得好,并不是一件壞事。我反對“落葉歸根”這樣的陳詞濫調。

在電視劇《畫家村》拍攝現場
15、花語:是什么讓您堅持到現在,能否說下北漂途中最讓您感動的事?
老巢:我沒覺得自己是在“堅持”。起碼從表面上看,我在北京這些年一直過著讓別人羨慕的“慢生活”,喝酒,做夢,寫詩,拍戲,日子過得好像還不錯。請注意,我使用了“從表面上看”和“好像”,也就是說,到底過得怎么樣,只有我自己知道。北漂,意味著一切,或者說,什么也不意味。“北漂”這個詞是可疑的。我以為,什么樣的人都可以來北京生活試試,要想在這里活下去并且活得好起來,一句話:別把自己當回事(你先要承認自己什么都不是,才有可能是點什么)。我是個容易被感動的人,感動我的事很多,但沒有“最”,我不喜歡這樣的選擇和表述。孤獨和寂寞,我常掛在嘴邊,并不是抱怨,而是希望它們來得更大些,我想要“大孤獨大寂寞”。
16、花語:除了寫詩,您還有別的愛好嗎?自評,你是個真誠有趣的人嗎?
老巢:我說我沒有酒癮,沒人相信,朋友們說“你每天都在喝當然沒有癮”,這話不好聽,但指出了我的一個愛好:喝酒。睡懶覺,當然要做夢,一個人總比一個國家,更有理由在夢里撒點野。如果K歌能算,也是一個,多少個夜晚我在聲嘶力竭中迎來東方的魚肚白。那件事就不說了,正常人都喜歡,我也不例外。綜上所述,詩歌以外,我是一個性情中人(大部分時候缺性,多情),一個像年輕人一樣荒唐的老男人,愛我的人會覺得我可愛,討厭我的人從本質上說都很可憐。我沒有敵人,我活著,尚且自由!
17、花語:您的口頭禪,座右銘分別是什么?
老巢:我以前有過什么口頭禪?忘了。最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戒酒等于戒人生。座右銘這種“高大上”的東西,我目前還沒有。
18、花語:請薦讀十本好書。
老巢:什么樣的書是“好書”?我只能說幾本我喜歡的不同時期對我有影響的書:1、《金薔薇》、2、《約翰.克里斯朵夫》、3、《悲劇的誕生》、4、《夢的解析》、5、《金瓶梅》、6、《孫子兵法》、7、《喧嘩與騷動》、8、《閑情偶寄》、9、《我的奮斗》、10、《梁小斌如是說》。
19、花語:目前的寫作狀態如何?除了寫詩,還有何長遠打算?
老巢:狀態一般。猴年堅持每天寫一首詩,到了雞年,零零星星地寫。不是寫不出來,是不想重復自己。與自己較勁,老巢要突破老巢,極其困難,又讓我欲罷不能。除了寫詩,還干一些與影視有關的活,最近在籌拍一部關于詩人海子的院線電影。我要養活自己。
長遠能遠到哪呢?前50年,以“老巢”為筆名寫詩,獲得點名聲,接下來,我要用原名“楊義巢”做紀錄片、拍電影。要讓“導演楊義巢”比“詩人老巢”有名得多。這是我的虛榮心,說出來,是我不夠成熟的表現。但,憑什么要成熟呢?

在電視劇《兵團往事》拍攝現場(劉不偉/攝)
簡評三則
藍棣之:
欲望詩和血淚詩是老巢創作的一個新的發展,全球范圍內的“以人為本”的文化思潮和相應的政治轉型,使欲望詩和血淚詩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合法性。人的情感、身體、欲望和情緒等給詩歌創作帶來了廣闊的天地。這就是老巢這些創作的時代背景。欲望詩的主題就是對于欲望的向往和體驗。比較起傳統所謂“性愛”來說,“欲望”進了一步,含義也更確切。老巢的欲望詩寫作,可分為前期和后期。前期欲望詩帶著好些感情色彩,含蓄輕松,講究藝術上的表達,單純稚氣。后期則深入地進入欲望,描寫刻骨銘心的欲望追求與體驗。前期以謀篇為勝,后期以琢句為尚。血淚詩則直接陳述愛恨情仇,悔恨和傷害,見血見肉,相當真實。老巢的詩創作于是來到并且面臨一個新的拐點。欲望詩也好,血淚詩也罷,作者的寫作態度都是嚴肅的,坦白,誠懇,實在,始終遵循著人類有史以來傳統的真、善、美這三個終極標準。作者自然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但他已經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苛刻的拷問,他已經縱身跳進前面的“火湖”,他是有勇氣,有擔當的!
梁小斌:
“誰能對癥下藥/誰就是我的美夢/誰是我美夢/誰就非常痛苦”,這樣也極易造成誤解,好像我要借老巢的詩來當什么醫生。他的那本《風行大地》我在半夜里讀過,通常都是一個主題,我不要觀音,我要詩。在兩個相似、完全逼真的事物之前,此物很像彼物的時候,這實際上就是苦難。靜默中的祈禱肯定有跟詩歌酷似的地方。它們本來只是一個靈魂,不料卻分裂成兩半,如同他所說:這里面惟有鮮血?誰能誰就是醫生,而不僅僅是象醫生重新說點什么呢?像是有誰在說,而當我掩卷沉思:我又確認是自己在說:他的精神苦難就是他的自身。是他的對苦難的虔誠。他給我刻骨銘心的印象每一首詩的標題都是一道傷痕,他害羞。把傷痕寫得很美,很富有哲理,他怕別人不承認這是痛苦。所以才充滿著哲思。“其實我們遠離現場/坐在城市的漏洞里”,至此我想說,“坐在城市漏洞里”的老巢正處在中國新詩想有話要說的關口上。
中島:
老巢對時間是沒有態度的,但對詩歌是有態度的,他從不因跟隨而對詩歌隨波逐流,他的詩歌堅硬尤如他的骨頭,他的詩歌孤獨尤如他不羈的靈魂,高處的“寒冷”我想他無時無刻都在感受,他的生命里藏著天使,他的生活中喂養從不低頭的猛獅,這就是老巢。每次聚在一起參加詩歌活動,他都珍愛般的為他的詩行敞開心扉,從不矯情。他是不折不扣的大男子主義,有呼出兒女換美酒的氣魄,他的詩歌尤如他的胸心一樣豁達,詩歌與他生命沒有邊界,作為老巢,他的內心可以裝下”天空與海洋”,也可以像一滴雨和一片葉一樣藏著柔情,這是他內心的全部,空曠中飄著樹葉,那粒水珠就是他。從《時間的態度》和《人間愛情》里我們讀到老巢靈魂,他以自己的生命價值體系完成對她的澆灌,這種“血濃于詩”的情感又歇斯底里的被他喊出,詩就是老巢,老巢即是詩,非常合情合理,這就是老巢的詩與人生。
作者:老巢 花語
來源:中國詩歌網
http://www.zgshige.com/c/2017-06-27/3684689.s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