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訪談|樹才、李心釋:“詩歌寫作,本來就是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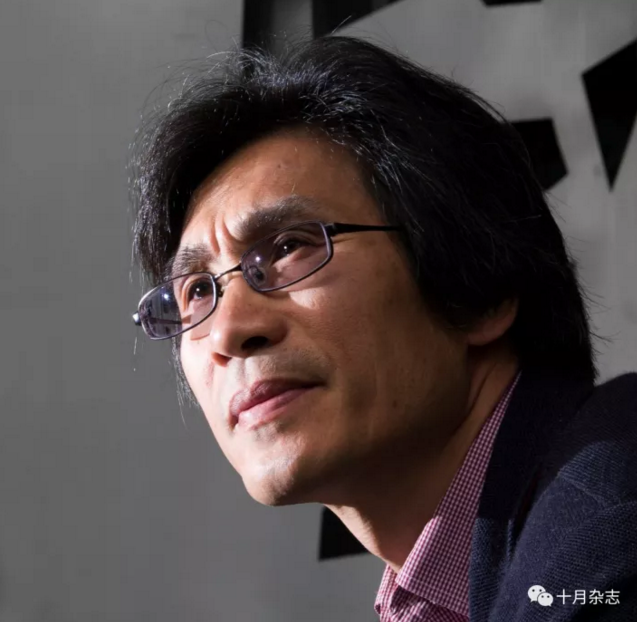
“詩歌寫作,本來就是難的”
——答李心釋關于當代詩歌語言問題的九問
李心釋:在您的詩歌寫作歷程中,遇到過哪些詩歌語言上的問題、障礙,或者有意的探索?
樹才:這個問題太大。不知道從何答起才好。實際上,寫詩的全部問題,都可以歸結為“語言”問題。一個人愿意寫詩,就意味著與語言“作對”,或者對語言表示“信任”。一個人的詩歌寫作,開始時常常是自發的,不自覺的,但只有到“自覺”的份兒上,詩歌寫作本身才會“自然而然地”綿延下去,并與個人生命中“時間的綿延”纏繞在一起。有人說詩歌寫作需要“堅持”,不,靠“堅持”是堅持不了多久的。要靠“自覺”。自己去覺悟:詩乃個體生命感覺、認知、評價世間萬物的一種方式。它可以嵌入到一個詩人的“活命”當中。長久以來,人們似乎已經忽略:詩始終具有憑感覺去直抵事物的那種認知力。
李心釋: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詩歌更是這藝術中的藝術。就您的寫作和閱讀體驗,您認為詩歌與小說、戲劇、散文等相比,在語言上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和特點?
樹才:也許只有一個“本質”的區別:節奏。那么,小說和散文就沒有節奏嗎?有。但小說和散文的那種節奏,還不是詩歌的“節奏”,因為前者達不到后者必需具備的那種強度。“那種強度”是什么?這就必須結合語言和生命的關系來談。嚴格說來,一首真正的詩的節奏,總是與詩人的“生命呼吸”(有時自己都不察覺)有關。當我說一首詩的節奏的時候,我是指我聽見了那首詩在“呼吸”,當然,它不是通過肉身的“一呼一吸”在呼吸,而是通過語言的“張力關系”在呼吸……小說和散文的節奏,離不開“敘事”本身,它是行文本身的一種起伏,是情節發展的各種轉折,一句話,它屈從于“敘事”本身。而一首詩的節奏,完全是這首詩的形式本身,是這首詩的“命根子”。極端地說,正是語言節奏“生成”了一首詩的血肉之軀。拋棄了格律和韻腳的可見可聽的外在特征之后,人們憑什么說“這是一首詩”?只能憑語言節奏。節奏像氣血一樣,流貫在一首詩的全身,并且通過這首詩的意象力量,使這首詩的“意義”不光是它所寫出的,還喻示它未寫出的。一首詩的節奏同它的“意味”緊密地生長在一起,一句話,詩歌語言從本質上說是一種隱喻語言。當一句詩“敘述”什么的時候,實際上它仍然是一種“偽敘述”,仍然是對抒情的一種“奉獻”。說到戲劇,它是需要人去“演”的,它的節奏是演員和劇情相遇時的一種現場“說話”狀態。不管怎么說,“節奏”(甭管它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是一首詩的語言生命的呈現方式,也是一首詩存在下去的美學理由。
李心釋:注重語言問題,不僅是詩人,也是包括小說、散文……等一切文類寫作者的分內之事。但具體在詩歌中,又有所不同:談起詩歌語言,很容易讓人想到注重語感、進而想到“語感寫作”。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詩人威廉斯的《便條》,以及大陸九十年代口語寫作中對語感的注重。您如何看待詩歌中的語感寫作?以及,如何看待“注重詩歌語言”和“語感”之間的關系?
樹才:在我看來,不存在什么“語感寫作”。理由很簡單:光是沖著“語感”去寫作,不可能抵達詩歌。詩歌寫作就是詩歌寫作。古往今來,哪一首傳世之作沒有所謂的“語感”?!“語感”說到底,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它總是同一首具體的詩“一起生成”。離開一首具體的詩去談“語感”,我認為沒有什么價值。但很不幸,這恰恰是目前詩界的狀況。語感,是詩人和語言在寫作實踐中活生生地相遇時才會產生的,它并不獨立于詩人對語言的具體運用。語感總是個人的語感,總是黃梵的語感、李心釋的語感或樹才的語感,也就是說,語感總是指向某一位詩人的寫作。不存在一個籠統的、對什么詩人都有效的“語感”。瞧吧,語感必須“有效”:產生詩的效果!從詩學角度看,語感是指一個詩人對語言的敏感性。一個詩人必須有對“語感”的意識,然后才能產生所謂的語感。語感離不開一個詩人的個性、生長、地理、氣候以及言語氛圍等等足以影響“語感”的因素。語感值得強調,因為它是對語言個性的強調。中國詩人的寫作,在幾十年的政治話語壓迫下,對語言的使用已經失去了最起碼的個性。如果曾經有過“語感寫作”,那么我希望它是對這種“無個性”的可悲寫作狀態的一種反抗。但這里,舉威廉斯的《便條》為“典型的例子”,我認為不妥。憑我對詩歌翻譯的認知,《便條》的“語感”恰恰是無法被譯出的。那就很清楚了:譯成漢語后的《便條》中的“語感”是譯者在漢語中“再生”出來的(當然威廉斯也功不可沒),并不是《便條》原文詩的語感。語感語感,一定是對語言的最直接的敏感。它只能體現于對語言的使用,即“言語”之中。我們最好避開在譯文中談論一首詩僅僅存在于原文中的“語感”。別忘了,譯詩自有譯詩的語感,那就必須結合譯者來談。
李心釋:“詩歌就是對語言表述情感的極限的探測”。在語言和詩由以產生的情感之間總會有緊張和對立,因此,在寫詩過程中就難免會遭遇語言表述情感的不足和挫敗。請您回憶一次自己寫作過程中遇到的語言與情感之間的角力,以及如何在二者的角力中完成一首詩的寫作的經歷。
樹才:語言是語言,情感是情感,看上去它們是分開的,但在一首詩中,它們又是合在一起的。在一首寫成的詩中,語言和情感變得無法分開。它們分不開。你讀一首詩時,你能指明哪兒是語言哪兒是情感嗎?你不能。別人也不能。沒有一個人能。為什么?一首詩中,除了語言在詩人對它的妙用中“生成”的形式本身,別無其他!是的,情感常常觸發詩人去寫詩,但詩人一旦投身到寫作之中,其注意力便移向語言的具體運用。語言運用得越好,越巧妙,情感才會呈現得越真,越動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寫作又是對情感狀態的一種觀照,一種疏離。情感迸發之時,詩人無能為力。你不可能在情感迸發的當下,碰巧拿筆寫下一句表達這種情感迸發的詩。這是不可能的,盡管我們夢想做到這一點。由此可見,也許情感刺激、促成了一首詩,但一首詩總是一首詩。一首詩首先是一首詩,比它“由以產生的情感”更重要,更致命,因為情感在化身為一首詩時,已經慷慨地奉獻了自己,或者超越了自己。與情感不同,一首詩總是屬于“語言形式”的東西。對于這樣的寫作“轉化”過程,很顯然,任何詩人的“回憶”都是不可靠的,充其量只是一種自我闡釋罷了!情感一旦發生,就已融入生命,成為一種蘊藏,詩人在任何一首詩中都不可能把一次情感經歷“寫盡”。好在,詩人總是可以試著去寫“另一首”。而情感也從來不會閑著,新的情感又在不知不覺中上路了。“語言與情感之間的角力”,將會伴隨詩人的一生,且難分勝負。
李心釋:西方近代詩歌史歷程中,有從浪漫主義到反浪漫主義的軌跡,中國大陸新詩從朦朧詩到當下的三十多年歷程也可以看出從最初的抒情語言到后來的敘事語言和去情感化寫作的軌跡。您如何看待這種寫作傾向的變化?在看似與西方相似的轉變中,我們的寫作有什么需要與之加以區別和反思之處?
樹才:“浪漫主義”一去不返,但“浪漫”精神在一代又一代詩人中延續。“浪漫主義”之后,是“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前者催生了后者,后者又在一種“反”的態度中實現了自身。詩歌發展中的“傳承”,是一種辯證關系,并不總是“斷裂”。說到底,語言本身無法真正“斷裂”,無法另起爐灶。就中國大陸新詩而言,“浪漫主義”的氣息彌漫了很長時間,也許確實太長了。但我們很難說,現在的年輕詩人就不是從“浪漫”情結開始寫第一首詩的,只是他們的寫作也許過渡得更快,轉向得更“不知去向”(如今“后現代主義”的寫作就具有“不知去向”的特征)。至今健在并且仍然寫作的老詩人比如鄭敏、牛漢一代,他們一生的絕大部分時光都籠罩在“象征主義”詩歌的偉大陰影之中。我說“象征主義”詩歌的陰影是偉大的,是因為“象征”從未結束,而且永遠不會結束,詩的力量就在于既是自身又指向他物的那種象征力量。“朦朧詩”一代詩人,骨子里都迷戀“意象”,他們的寫作是一種通過“意象”尋求詩歌表達個性的可貴努力。“朦朧詩”之后,到了在改革開放和高等教育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詩人,是他們真正把寫作的關注點從“政治話語”艱難地轉向了“語言藝術”。我想反問一下,有過“去情感化寫作”嗎?我很懷疑。抒情、敘事、情感等等,都是被語言包含之物,不會專門有什么“抒情語言”、“敘事語言”或“去情感化寫作”。它們是詩歌寫作的一些“傾向”或癥狀,卻不具備“變化”的力量。在我們的寫作中,真正值得反思的問題只有一個:怎樣才能讓詩歌寫作自成主體?換個問法,也就是:怎樣才能讓詩歌真正成為“語言的藝術”?
李心釋:國內的部分詩歌寫作者強調詩歌寫作的技藝和難度,但是技藝和難度的標準在哪里,能找到具體的參數對照嗎?寫作的難度落實在語言上就是修辭和表述的難度,您如何理解這所謂的難度?
樹才:詩歌寫作,本來就是難的,是難上加難的事情。小說和散文則要自由一些。難在對語言的要求,對節奏的要求。把一句話說活,是難的,把一句詩寫活,就更難。一句詩不是你想怎么寫就能怎么寫的,它取決于你和語言相遇時發生的那種活生生的關系。與一個人的表達愿望相比,語言總是別的東西。難在使用。誰都在使用語言,誰都想表達一點什么,但詩要求詩人在“活生生”的程度上妙用語言,使之生動、鮮活、富于意味。這種語言的工作,這種語言的勞動,其難度我們怎么設想都不會過分!但新詩在其發端處就被一句“我手寫我心”的口號給簡易化了!“我手寫我心”,本來也沒錯,簡單得深奧,含義很廣闊,但一旦淪為口號,它就被濫用了,而在濫用過程中,其含義就被簡單化、容易化了。強調詩歌寫作的難度,在當前是非常必要的,它有針對性,因為“口水”式寫作已經把詩歌對語言的要求降到歷史上最低的水準了!當詩失去其本身的“難度”時,一切句子(甭管分行不分行)都能混入到“詩句”的行列,那也就從根本上取消了“詩”。
李心釋:現代漢詩寫作不僅在大陸,而且也在港、澳、臺與海外。相比大陸,臺灣詩歌在語言表述的音樂性和意象的運用上相當成熟,當然,這不是說他們的寫作不現代,相反,他們的寫作實際上也更現代。很難否認,這在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傳統。總結我們幾十年的寫作,現代漢詩在大陸有傳統嗎?是什么?兩相比較,帶給我們的思考是什么?
樹才:我對臺灣詩歌了解不多,無法做一個總體性的判斷。我接觸過洛夫本人,對他的詩讀得比較多。他的詩確實以意象取勝,在意象的運用中,他打開了個人的詩性語言空間,并呈現出奇異而豐沛的想象力。這個特點得自他早年對超現實主義的領悟和實踐。余光中的語言,似乎更具有中國古詩的簡潔和音樂感。但我認為,把大陸詩歌與臺灣詩歌做籠統的比較,沒有什么意義,因為這種比較是不自然的,更致命的是,這種比較撇開了現代漢詩寫作的個人性。我只對某個具體的詩人的寫作感興趣。成熟不成熟,現代不現代,都只跟具體的詩人寫作真正有關。也許只能從語言“演變”的角度來做一點分析,誰都知道,大陸對漢語的使用是簡體字,漢語的字形結構一簡再簡,直到觸底反彈,因為這種“簡化”已經超出了漢語自身的承受極限(如今社會的某種混亂同語言的混亂有關),而港、澳、臺仍然使用漢語的繁體字,字形結構里保存了更豐富的傳統文化元素和信息。至于大陸的現代漢詩有沒有一個“傳統”,我認為,有,但這個“傳統”還只是“在路上”,也就是說,還在“生成”之中。這個“傳統”畢竟只是不足百年的一種時空積累,畢竟還只能一個“小傳統”,而且它不能撇開整個漢語古詩的那個“大傳統”來孤立地談。傳統是活的,它流動,像血液一樣,而且是通過變化在流動。現代漢語詩人的命運只能是“向前看”,同時冥想我們偉大的古代詩人的所作所為。
李心釋:廢名曾說,新詩與舊詩的區別在于,舊詩是詩的形式散文的內容,而新詩是散文的形式詩的內容。這個判斷現在看來雖然有些簡單籠統,但也的確道出了新舊詩之間的一些區別。從詩歌語言的角度看,您認為新詩與舊詩本質上的不同是什么?哈佛大學的田曉菲認為不在于形式與內容之分別,而在于表達方式和美學原則的根本不同。如果是這樣,您覺得這樣的表達方式與美學原則會是什么?
樹才:廢名的話,我不同意。從第一次讀到這句話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同意。詩是詩,散文與散文,混在一起談,本來就沒有道理。我以為,這種區分不足為道,也許他當時有一個特別的說話語境,或者只是率性一說而已。反正,我不贊同他的這種區分。詩到現代,一個大的突破,就是讓“形式”找到了新的意義。古體詩的“形式”,可以就整個詩體而言,而現代詩呢,“形式”只在每一首具體的詩中,甚至可以極端地說,“形式”就是每一首現代詩本身。這“形式”,同上面論及的“節奏”,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對新舊詩的區別意識,得自一個中學生在我博克里留下的一個問題:“不押韻的詩還是詩嗎”?我認為,對舊詩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而對新詩而言,答案是肯定的。新詩不押韻為什么還可以是詩呢?因為新詩就是為了打破押韻,但不是為了打破而打破,而是因為它變成了一種必須打破的外在束縛,因為押韻本身作為詩藝也已經爛熟到了必須被“新詩的語言表達需要”拋棄的地步!新詩的“新”,就是不押韻,或者說押不押韻,對新詩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節奏。瞧,節奏作為新的詩藝挑戰擺在了“新詩”人的面前。韻腳有書可循,節奏只能產生于詩人在每一首詩中對語言的妙用。所以,比較而言,新詩比舊詩更難寫了,因為更難寫好。新詩又叫自由詩?但詩什么時候“自由”過?!只有詩人的心靈想象力和語言創造力同時抵達時,一首詩才可能是“自由”的。詩的困難越大,詩的自由也就越大,它們是成正比的。我認同田曉菲的看法:一首詩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表達方式本身,是“表達方式”而不是別的什么主題或構思,讓詩人在語言的妙用中“生成”了一首詩本身。美學原則只是“原則”而已,不談也罷。
李心釋:舊詩對新詩而言,既是巨大的障礙,也是巨大的資源。舊詩的格律我們已經拋棄了,但格律要素——比如用韻、節奏等等——總還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新詩中。所謂內在的節奏總還有外在的語言形式來體現,或者說,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內容,我們的新詩寫作,怎樣才能更有意識地、更有效地挖掘現代漢語的潛力,將格律要素結合進來?
樹才:“障礙”部分,也許新詩已經越過去了。如今,“自由體詩”沖破各種阻力,已經赫然成為詩歌寫作的主體,也就是說,“新詩”業已獲得它賴以生存的合法性。“資源”部分,恐怕才是問題所在。二十世紀是一個不斷地反“傳統”的世紀,反來反去,現在都不知道“傳統”在哪兒了!二十世紀也是一個加速度的世紀,是一個革命成為全球狂熱的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一切都將逐漸“慢”下來。二十世紀發生的一切必將經歷一種新的反思。這不光是“舊詩”和“新詩”的關系問題,也不只是“傳統”和“創新”的關系問題。就詩而言,像“詩本身可以是怎樣的?”、“人們應該怎樣閱讀詩?”這樣的問題,將會提到桌面上來。語言在變,人們對語言的認知在變,一代又一代詩人的生存環境和思維方式在變……詩里面究竟有沒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本質呢?我表示懷疑。詩是一種整體力量,我認為,詩人寫一首詩(如同過一生)時,必須有一種整體觀。詩的秘密躲在語言和生命的關系之中。為了寫好詩,詩人除了投身于語言的勞動,還必須通過“生存”最大限度地去感受生命本身所包含的豐富人性和復雜個性,此外沒有更好的方法。確實,“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內容”,但我認為可以說得更直截了當:“在一首詩中,形式就是內容。”因為這里所說的“形式”,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它已經不再是一提起“形式”就讓人想到“內容”的那種“形式”,“形式”與“內容”已經不再互為“皮肉”,而是“帶肉之皮”和“帶皮之肉”,它們是同一個生命體,同一個血肉體。在一首現代詩中,“形式”和“內容”不可分割,它們同時“生成”在同一首詩的“寫作過程”中,而“寫作過程”恰恰就是詩人對語言的運用。所以我才說,“寫詩寫詩,關鍵是寫”。我至今堅持這種樸素、開放的詩學主張。

作者:樹才、李心釋
來源:十月雜志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M4ODYzNA==&mid=2651949512&idx=2&sn=e36368677dda9cf46b31c04ec03cdf36&chksm=8412187db365916bfa05550d3ed8a377d7e692f3b721dba40fd9cb453d07759c0cc2a6e1ada4&mpshare=1&scene=1&srcid=11017AM0Fv9MKxqBAQHfPTHH&pass_ticket=rSyZ52srRa59GUJk%2Bb33BpcGijo4sZ62mz1kR0QmWSF4iCAOjjONbE7UcIA93Iag#rd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