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屆詩歌人間嘉賓詩人訪談(一):歌叩詩門 以境映心

宋 琳:詩歌總有新的境界需要去探求
“詩人幾乎都屬于情之深者,詩歌的慰藉力量是對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的一種補救”。詩人宋琳如是說。
宋琳寫詩不喜歡倉促急就。好的題材需要時間醞釀,但不寫詩的日子他也沒閑著,他在等待一首詩自己成形。閱讀,冥想,調試音調,有時走開去做別的事,這些都是寫作的一部分。因為宋琳相信詩迫而成,“有來斯應,不以力構”,保持感應器的警覺和敏銳,這并不容易。
近兩年他寫的稍多些,可能是現實的急劇變化促使他做出反應,能否發表并不去管它,總不能只為發表而寫?他告訴記者,這次參加“詩歌人間”活動的詩,有處理現實的,也有處理神話和歷史軼事的,解讀權還是交給讀者吧。
幾年前宋琳和詩人趙野相約寫六朝人物的同題詩,因各自都有新的東西要寫,所以進展緩慢,只完成了數首。今年他在寫《山海經》系列,已寫出十余首初稿。宋琳說,詩歌總有新的境界需要去探求,譬如古代神話世界,體現了古人的宇宙觀和想象力,以詩的方式去修復文獻和傳說中的片段,亦是對個人想象力的拓展,是接引與再造。很多事情等著詩人去做,其中被歷史敘事所篡改的部分,尤其需要運用訓詁學和考古學的微觀知識,這方面是需要補課的。
去年“詩歌人間”主題是致敬新詩百年,如今放在當代詩人面前一道題目,就是新詩百年之后如何更進一步?宋琳說,新詩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才能與偉大的舊詩傳統媲美,新詩的歷史還很短,站得住腳的經典還不多,但現代性的遭遇給新詩帶來巨大的生機。他在《新詩的百年孤獨》一文中回顧了民國時期新詩觀念的演變與紛爭,當代的情形大體相似,新舊、雅俗之爭還會持續。
面對新時代,詩歌如何為時代發聲,如何深入時代與生活?事實上,宋琳對時代有著細致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信息化時代,詩人的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詩歌一度起到引領文化思潮的作用,而在當下,整體文化環境和詩歌自身的處境要復雜得多。
在宋琳看來,詩人必須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透徹的理解,有為而作的儒家詩學觀一定程度上并未過時,但以功利性取代詩性則是危險的,介入現實之作仍要在詩歌的內部發聲。“我注意到,真正的詩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在精神上都選擇了隱逸一途。與塵囂的距離感,對基本良知的呵護,對惡的不妥協和對美的專注,使他們沉潛下來,有望見證一個時代的詩作將出自他們之手。”(尹春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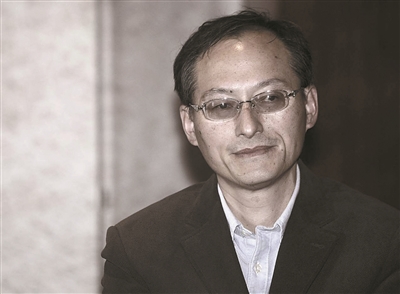
小 海:要與生活和時代保持一點距離
詩人小海曾多次參加“詩歌人間”活動。今年“詩歌人間”步入第十一屆,小海既是“詩歌人間”成長的見證者,更是“詩歌人間”的老朋友。
今年“詩歌人間”研討會將以“以境映心——新時代·新詩篇”為主題,展開討論。對于這個主題,小海如是解讀:“以境映心,心是主體,心不是要簡單隨著境轉。優秀的作品在產生時,都需要有一個沉淀、積累與轉化的過程。記得少年時代我去北京拜訪一位‘九葉詩派’的老詩人陳敬容先生時,她曾告誡我,要與生活和時代保持一點距離。幾十年后,我體會到,這種距離感可以保證觀察的全面與理性。有時看上去似乎是落后于生活與時代的,但可能還又恰好走在時代的前面。詩歌既面對生活世界,也面對文字世界,既面對喧囂的那部分,也面對廣闊的無聲的那部分,或者說面對文字無法表達的那部分。任何時候對文學的敬畏之心都不可缺少。”
他同時強調,“筆墨當隨時代”的前提是,藝術家要時時察知自己的內心,要能保有覺察、覺知自我的能力,保持清醒。也就是說,詩人在處理個人與時代、現實與歷史的關系時,要有叫醒自己靈魂的能力。小海說:“記得前些年,我在參加‘詩歌人間’活動時,在回答‘這個時代詩人何為’這個問題時曾提及,詩人能做的就是小心呵護心靈,不斷去作‘叫醒服務’的工作,喚醒什么?喚醒心靈,喚醒人性,不至于讓她沉睡、壞死,要去做心靈或者說是人性的修復工程。”
對于新時代詩歌如何發聲的問題,小海認為,沒必要刻意求新。“新時代詩歌的發聲,我想,是在尊重詩歌藝術規律的基礎上,無論是個人小情小調還是基于時代命運的宏大敘事,可以是李商隱的‘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于老鳳聲’,也可以是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指認的‘對于任何想在二十五歲以上還要繼續作詩人的人,歷史意識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從而不斷豐富、拓展與完善當代漢語詩歌的內涵與外延。 ”
今年“詩歌人間”,小海帶來了五首詩作。他說:“提供的五首詩中,有兩首是舊作,比如《詠臘梅》,但做了很大修改。我過去沒有修改自己詩作的習慣,作品都喜歡一蹴而就,覺得與其花力氣修改,不如新創作來得省力。近幾年,我花時間重新整理舊作時,也會順手修改一部分。修改也是重新審視自己過去與當下的一個過程。另外幾首詩,也會有一點新的變化,希望有一些新的實驗與探索,避免文本重復與自我消費。”(劉莎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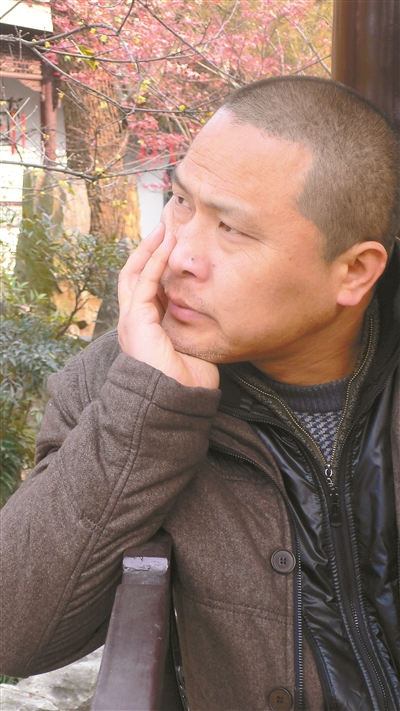
楊 鍵:寫詩是不斷溫故知新的過程
對詩歌人間來說,楊鍵是老朋友。因為詩歌與繪畫的關系,楊鍵多次來到深圳,與這座城市結下了不解之緣。
楊鍵是當代中國杰出的詩人,而且以數年對繪畫藝術的執著與潛修,以專業的技法與深邃的意境帶給人們新的視覺審美。談及最新的創作,楊鍵表示,他最近很少寫詩,都在畫畫,一整個夏天過來,畫畫的過程中,感覺像是一次閉關。“我不寫詩的時候就畫畫,而畫畫一投入進去,就會很瘋狂,每天都會畫十幾個小時,最大的成果就是,領悟到藝術的善、樸實、厚重,是通過勤苦才能到達的,沒有其他的捷徑可走。”
在整個過程中,他對生命的感觸更深入更真切,他形容他的領悟就跟他小時候見到的老家人,臉上由勤苦所抵達的善是一模一樣的,有一種感人的力量。他也有一種擔憂,這樣的善在今天是越來越少了,沒有勤,沒有苦,舊有國人臉上的那種特有的善是越來越少了。
從重心轉向繪畫之后,楊鍵越發勤奮了起來。2014年,他曾在關山月美術館舉行《冷山水》個人畫覽,大獲好評。之后,他筆耕不輟,持續在藝術的道路上探索。他告訴記者,今年他創作了新的系列,起名叫《空碗》。
為什么叫這個名字?他解釋說:“對我而言,一個傳統的梅蘭竹菊的象征世界已經死亡。所以,我才畫下了離自己最近的日常之碗。它看似一口碗,卻像一口缽,或是一只鼎。在最形而下的意義上獲得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無物堪比,教我如何說?一個難言的自性世界,充盈與空無集成一體;往淺處說,這口碗更像是黑暗光陰里的意志,我似乎只有回到這里,才能真正地回到起點。”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著名的詩人之一,楊鍵也從未放棄過對詩歌的思考。尤其是新詩百年之后,當下的詩人們如何繼往開來,更進一步。他說,我們這幾代都是吃羊奶、吃“翻譯體”長大的,現在就是要由從前的二手經驗,轉變為一手經驗來創作,新詩才有希望可言。新詩的自主性,只有通過回歸自然與心性的現場才有可能。
寫詩到底對他意味著什么?楊鍵說,寫詩是不斷溫習語言,溫習思想的過程。“太陽底下無新事,人所能做的,就是溫故而知新。”(尹春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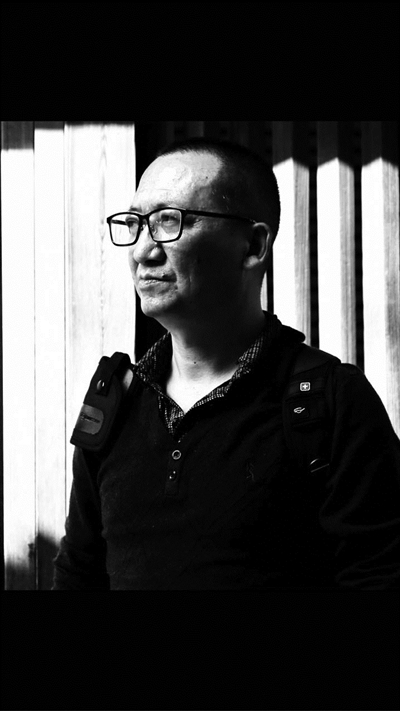
林 舟:詩歌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溫度計
林舟是文學與文化批評家,這次“詩歌人間”,他是一位純粹的觀察者。
林舟本名陳霖,安徽宣城人,文學博士,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生命的擺渡》《文學空間的裂變與轉型》《事實的魔方》《迷族:被神召喚的塵粒》等。在《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研究》《上海文化》《詩探索》《今天》《花城》《上海文學》等發表文學評論和論文多篇。
說起詩歌評論,林舟非常謙虛,他說:“我不寫詩歌,讀的也很少,偶爾寫一點詩歌評論,所以,談詩歌觀點真不敢,只能說說我在閱讀詩歌時所抱的期待。我覺得好的詩歌總是能讓我有一種或被觸動被撞擊或被升華被超度的感受,內心里某種混沌不明的東西在這樣的一個時刻一下子澄澈起來。這看起來純粹是個人化的體驗——與一首詩偶爾相遇。”
“安徒生的故事更多地諷喻了現代的許多神話,那恰恰是知識對人的血肉之軀的謀殺——人的知識、信息、思維得到極大的強調,強調到它們拋開人、控制人的地步,以至于人無法確認自己作為肉身存在的價值。影子殺死學者,隱喻了知識殺死了知識的主體——人。從安徒生回到小海,我感到,對影子的表現上,兩位詩人有著特別的共通之處,那就是關注人與影子的若即若離、互相取代、互相對立、互為他者、共處一體。不同的是,在小海這里,影子不只是作為人的肉身的影子,而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里萬物存在的影子……”
盡管不寫詩,但是林舟的詩歌評論本身就像是一首詩。
“但是當循著這樣的感受去追索,我想詩歌應從時代的深處發聲,帶著對這個時代的敏銳感知,穿越層層厚壁障,仿佛從地心來到地表,超越于她所處的時代,卻又構成這個時代的精神測溫計。”林舟認為,詩歌并非可有可無。今年第十一屆“詩歌人間”研討會將以“以境映心——新時代·新詩篇”為主題。林舟感嘆說:“ 這個主題好。‘以境映心’是何等的境界!如果說在這個時代寫詩即是修煉,它或許省略了、懸置了‘以心造境’這個前提。在我看來,‘以境映心’意味著心與境互動互構,互相激發和映射。‘心’是長流不斷的水,‘境’是生生不息的土,詩歌便是莊稼、花朵或任何的植物甚至動物。當然,也免不了雜草和害蟲,除草和殺蟲也就必不可少。”
在新詩跨越百年之后,新時代詩歌當如何發聲?對此,林舟的觀點是:“這個問題對我而言,真的是太大了。我只想說一點,在‘跨越,百年,新時代……’這類詞語標注我們當下存在的時候,我們或許格外需要弱弱地問一聲,有哪些東西其實從來沒有變過。”(劉莎莎)

余幼幼:我的寫作是一場“被選擇”
“戀愛吧,攜手去磨刀/你和我一人捅對方一刀/沒有人死亡/也沒有人生還/磨好刀,把愛情都/留在刀刃上”這是詩人余幼幼的新作《磨刀》。很難想象如此“重口”的詩句出自一位90后詩人的筆端。實際上,這并不是余幼幼最生猛的文字,她還有很多大膽、直率,甚至讓人“觸目驚心”的詩作。這份“觸目驚心”里包含的早慧、敏感和銳利,原本只是在自己博客上“自言自語”的余幼幼,很快就得到詩歌圈和出版圈的關注。
2012年,四川文藝出版社以《7年》之名出版了她的150首精選詩歌。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余幼幼被稱為是“國內最具實力的90后詩人之一”。她的成名也一直伴隨著爭議。在知乎上,甚至還有人專門“開樓”討論“如何評價余幼幼的詩?”余幼幼,1990年12月22日生于四川,2004年開始詩歌創作,出版詩集《7年》《我為誘餌》。曾創辦“大學生詩歌網”。 她形容自己是:“清淡飲食,重口味審美。”
詩人沈浩波評價她:“當一個詩人的名字在一個個詩歌小圈子里漣漪一樣秘密擴散時,意味著,你該正視了。她年輕得連新浪都來不及給她加V。余幼幼,90后,好詩人。擁有直接的才華。”詩人楊克稱她,“桀驁狂妄”。
余幼幼開始寫詩,要追溯到13年前,當時她還是個初中生。與詩的結緣被她自己回憶是,“除了閱讀,更大原因要歸于網絡,那些年特別流行BBS論壇,有很多文學論壇,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表作品的地方,無門檻、無限制,在此刺激之下慢慢接觸詩,然后開始寫詩。”有寫作的沖動,就有了補給的沖動,一邊寫,一邊讀,她慢慢找到了一種自己的表達方式。2006年,她申請開通了自己的新浪博客。那里“簡直就變成了我的一個靈感流瀉的秘密基地,一個勁兒地寫,然后貼上去。”直到被某詩歌刊物的編輯發現。如今,不在新浪博客上貼詩,余幼幼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繼續寫。
她告訴記者最近創作詩歌不是很多,一直在尋求內在的突破。“這種突破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而是揮刀革自己的命。”余幼幼認為,詩歌要以自我為中心的情況下不斷向前,詩歌首先是私人的然后才是公共的。談及本次“詩歌人間”研討會的主題“以境映心——新時代·新詩篇”,余幼幼說:“環境對人的影響應該是個體的反映集合成大的反映。”至于詩歌創作,余幼幼說:“我沒有特別刻意地去選擇,有感知的東西都會寫,應該說是事物選擇了我,而并非我選擇了它們。”此次帶來“詩歌人間”的作品,余幼幼說:“本次選的詩歌是最近的新作,比較能代表最近的自己,沒什么可解讀的,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吧。”雖然看似大膽、出位,但其實余幼幼骨子里還是熱愛傳統,她說:“不想說和傳統達成契合。但我不得不回頭再學習傳統。為的是更好地擺脫掉我認為的創作上的限制。”(劉莎莎)
相關鏈接:第11屆詩歌人間嘉賓詩人訪談(二):凝視時代 熔鑄詩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1130/c405057-29677204.html
來源:深圳特區報
作者:劉莎莎 尹春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1130/c405057-29677227.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