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海子詩歌中的幸福主題
有一種東西比痛苦還悲慘,那就是幸福的人的生活[1]。
——阿貝爾·加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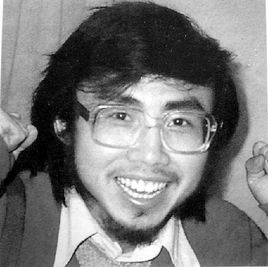
海子(資料圖)
1
海子的自殺令他的詩歌具有了不同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海子的自殺激活了他的詩歌想象力本身所具有的差異。一方面,流行的詩歌文化趨向于簡化的識別,即將海子的自殺看成是他的詩歌意圖的一種顯示。按照這樣的解釋,詩人的自殺反證了他對世界的絕望,以及對生活的厭倦。而海子自己在詩歌中反復觸及死亡和痛苦的主題,似乎更加驗證了對他的詩人形象的一種概括:他是一個關注死亡的詩人,就像他在《春天,十個海子》里聲言的——“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傾心死亡”。[2]另一方面,海子在詩歌中反復呈現的幸福主題,以及美麗主題,又令讀者感到深深的困惑。之所以會陷入困惑,原因似乎和讀者面對的選擇有關:假如海子在詩歌中對死亡的描繪是真誠的,那么,他對幸福和美麗的描繪就會顯得虛幻,甚至會因為詩人以激烈的方式來自殺而顯得格外虛假。此外,還有一種折中的論調,認為海子雖然也描繪過幸福的情境和美麗的意象,但總體上看,他的詩歌意志傾向于悲觀和哀怨。他是一個過度關注死亡主題的詩人。
不可否認,看待詩人海子的這些方式,都能從他的詩歌中找到看似充分的依據。但也存在著一個盲點,即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海子的自殺當成了解讀他的詩歌的一個現實基礎;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把海子的自殺看成是他的詩歌中的一個核心事件。而我的建議是,海子的自殺固然強化了他的詩歌中的死亡意象,但是,出于對詩歌的尊重,也出于對海子的詩歌天賦的尊重,我們還是應該把海子的自殺看成是他的詩歌世界之外的一個意外事件。換句話說,從詩的解釋學的角度看,我們對海子在詩歌中反復呈現了那些基本主題——死亡主題,美麗主題,復活主題,幸福主題,孤獨主題,野蠻主題,黑暗主題,都保持一種開放的審美反應。海子對死亡的關注是嚴肅的、強烈的,但這種嚴肅和強烈,還不足以遮蔽或降低他對幸福的關注。如果說他在詩歌中對死亡的關注具有一種震撼性,那么也可以說,他在詩歌中對幸福的關懷也具有同樣的想象的強度。也就是說,海子對死亡的傾心是真誠的,這源于他的世界觀——向死而生;同樣,他對幸福的熱愛也是認真的,這源于他的生命觀——生命的秘密在于創造。
對詩的閱讀來說,如何協調海子詩歌中的死亡主題、悲傷主題與幸福主題之間的關系,確實一個不小的麻煩。所以,面對海子的詩歌譜系中的這些糾結和矛盾,我們尤其應避免任何簡單化的傾向,時刻保持一種開放的視野。這種開放性是基于這樣一種想法:我們應盡量避免依據海子的詩歌主題來描繪他的詩人形象。比如,依據海子在他的詩歌中對死亡的關注,就認定他是一個陰郁的沉迷于死亡的詩人。同樣,我們也不應簡單地依據他的詩歌對美麗意象和幸福幻象的熱情,就判定他是一個內心明亮的積極樂觀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此相似的另一種簡單化的做法是,用一個簡陋的詩人類型來詮釋他的詩歌。比如,將海子定性為青春詩人或浪漫主義詩人,然后據此來評估他的詩歌意圖。海子的詩,從想象類型上看,確實帶有浪漫主義詩歌的痕跡,他對死亡的看法,經常會顯得很浪漫;他對幸福的描繪甚至也不乏浪漫的想法,但假如我們以浪漫為理由,輕慢他在這些詩歌主題上表現出的詩歌洞見,我們的輕率和怠慢差不多也和對詩的犯罪沒多少分別了,且顯得相當狹隘和小氣。
對海子詩歌中的幸福主題的闡釋,還必須考慮到他寫下這些詩歌時的文學風氣。在海子開始寫詩的時候,1980年代真正能觸動年輕一代的文學風氣,基本上非現代主義莫屬。現代主義詩歌對死亡和孤獨的熱衷,無疑也對海子產生了某種強勁的影響。當然,海子對死亡主題的關注,從詩歌的影響上看,還有其他的來源。可貴的是,海子并沒有讓他的詩歌想象定型在現代主義的美學視域中。和他同時出道的詩人,很少會像他這樣富有激情地描繪詩歌中的幸福;因為按現代主義的詩歌標準,那會在審美觀念上顯得很幼稚,而且很容易在詩歌類型上滑入傷感的浪漫主義末路。海子不是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但即使在1980年代,面對現代主義的詩歌美學的強大的“崛起”,他依然大膽選擇了將自己的詩歌想象偏向于激情、天賦、壯烈、民間想象、和幻象詩學;面對同代的先鋒詩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詩的幸福主題,他并沒有患得患失,猶豫不決,而是以亢奮的想象和宏大的基調反復書寫詩的幸福。這不能不說是他的詩歌創造力的一個特異之處。
2
海子早期的詩歌中,一直洋溢著對“幸福”的關懷。對詩人來說,幸福既是一個詩的主題,又是生命的主題。在詩歌中,展現對幸福的注視,反襯著我們對生命的意義的一種訴求。這種訴求,意欲在廣闊的生存圖景中勾勒出一種生命的覺悟。為什么是訴求而不是追求,答案在于訴求更偏于直覺,更絕對,更迫切。從風格的角度看,我們也許會疑慮海子的想法有點浪漫,但從信念和語言的關聯看,海子在詩中呈現的對“幸福”的關懷,雖說有浪漫的成分,但它所包含的詩的洞見,卻并不因浪漫而有所減損。在短詩《云》中,海子將對幸福的注視納入到一種高亢的基調中,他已決意將“幸福”呈現為一種生命的圖像:
我歌唱云朵
我知道自己終會幸福
和一切圣潔的人
相聚在天堂[3]
在海子看來,“幸福”為生命的境界奠定了一種歌唱性:“我歌唱云朵”。這種基調在針對人生的貧乏和世俗的懷疑時,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信念。沒有對云朵的“歌唱”,“幸福”就絕無可能被體會。在這首詩中,“云朵”和“幸福”之間的意象關聯也很耐人尋味。從意象的暗示性上看,“云朵”高高在上,有脫俗和超逸的含義,它們不受人世的羈絆,在廣大的領域里行動自由,這種視覺特征也暗示了“幸福”對我們的啟示。此外,“云朵”雖然可以被眺望,被目力所及,但它們又絕非是我們憑借人的能力所能完全掌控的。“云朵”飄行在天空中,仿佛構成了天路歷程中的一個中轉站。海子將“圣潔的人”和“幸福”并置在一起,意在挑明這種并置的想象來源——“相聚在天堂”,以揭示這樣一種洞見:作為一種體驗,“幸福”也關乎到人生的歸宿。
寫于1985年的《活在這珍貴的人間》,也頗能代表早期海子對幸福的詩歌想象:
太陽強烈
水波溫柔
一層層白云覆蓋著
我
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徹底干凈的黑土地
活在這珍貴的人間
泥土高濺
撲打面頰
活在這珍貴的人間
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
愛情和雨水一樣幸福 [4]
這首詩富于浪漫的吟詠。表面上看,詩人是在表達一種生命的喜悅,這種喜悅源于對我們和土地的重新辨認,且浸透著自然主義的生存態度。但與此同時,不以為人察覺的是,它也包含了一種嚴厲的自我告誡。這種告誡指向我們應如何看待生活的本質。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海子在這首詩中悄悄重申了希臘哲人對生活的追問——如何看待生活才能投映出生命的本質。通常,人們會依據生存的現實狀況來看待生活的性質,并以此來規訓生命的可能性。但在這首詩中,海子表達了另外一種想法:即人們事實上應該依據他們對生存的強烈的直覺來辨認生命的可能性。生活的能力取決于我們獲得幸福的能力;對我們的生命來說,獲得幸福的能力,首先就在于重新辨認出我們和世界之間最本質的聯系。現代人的生存狀態過于倚賴我們的社會身份,但這種倚賴卻越來越不可靠。這些社會身份正日益變得錯雜復雜,正是在這種錯綜復雜的糾結中,我們的生命力已漸漸喪失了與自然、與世界的單純的聯系。可以說,從一開始寫作,海子就對現代性的復雜懷著一種強烈的抵觸。所以,在這首詩里,通過對“珍貴的人間”的亢奮的想象,海子展示了他對生命和幸福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洞見。詩中的場景是熱烈的,也是澄明的,它全然不同于像艾略特這樣的現代詩人對我們的生存狀況所做的描繪。海子的想象針對的是另一種真實:如何我們想活得有意義,我們就必須學會辨認出“人間”的“珍貴”。“珍貴”的本質在于存在的單純和生命的天真。在新詩的傳統中,可以說,還從沒有一個現代詩人像海子這樣赤裸裸地呼吁詩的天真。也許,在海子的潛臺詞中,他的意圖還指向與他喜愛的英國詩人布萊克相近的思辨:我們實際上不該為了獲得人的經驗而失落生命的天真。經驗的代價遠遠比不上天真的代價。海子的意圖是,人間之所以“珍貴”,就在于人和土地之間淳樸的“親和力”,就在于我們是否能感受到“泥土高濺/撲打面頰”,以及我們身心中大地的“干凈”。無論現代世界對自然主義還有怎樣的敵意,我們的生命態度中的自然主義傾向都具有一種神圣的喜悅的特點:即“人類和植物一樣幸福/愛情和雨水一樣幸福”。
也不妨說,在這首詩中,海子試圖扭轉世人對幸福的誤讀。他試圖用一種原始主義的態度,去克服人們以往在幸福和物質之間所建構的那種習慣性關聯。這首詩中,詩人對幸福主題的演繹,鋒芒直指在現代復雜的生存中我們應如何確定生命的態度,以及我們該如何辨認人的生命意識中最根本的傾向。“活在珍貴的人間”,就像是一個命題,與其說它是一種焦急的勸誡,莫若說它是一種大膽的建議。這個建議的本質在于,面對塵世的惡濁和生存的腐敗,我們是否還有能力站在生命的立場想象——人間的珍貴。某種意義上,海子所使用的強烈的修辭,似乎暗示了他的另一個想法:人生觀的本質在于幸福觀。
進入后期,海子同樣沒有減緩他對幸福的洞察。在更為出色的寫于1987年的短詩《幸福的一日 致秋天的花楸樹》中,海子對幸福主題的描繪顯得更為熱切,也更為絕對:
我無限的熱愛著新的一日
今天的太陽 今天的馬 今天的花楸樹
使我健康 富足 擁有一生
從黎明到黃昏
陽光充足
勝過一切過去的詩
幸福找到我
幸福說: “瞧 這個詩人
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
在劈開了我的秋天
在劈開了我的骨頭的秋天
我愛你, 花楸樹[5]
這首詩中,海子將幸福和熱愛聯系起來。這也進一步揭示了海子對幸福的辨認:幸福在本質上反映出生命中蘊藏著的愛的能力。幸福是一種生命能力的體現,而最能體現這種生命能力的,就是我們對世界的熱愛。沒有這種熱愛,就不會感覺到人間的珍貴。不能釋放出這種熱愛,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生命還處于束縛之中,還沒有獲得一種自我解放。為了突出生命和幸福之間的戲劇性,海子特意設計了一個獨白——“幸福找到我/幸福說:‘瞧 這個詩人/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這個獨白的獨特之處在于,海子暗示,人們對幸福的體驗,是無需通過現實世界來印證的;它更像是一場心靈之間的對話。幸福的體驗,反襯著生命的神秘。假如從認知的角度講,幸福很容易被現實所粉粹。但從生命的體驗與生存的洞見之間的關聯上,幸福在現實面前所表現出的脆弱和飄渺,恰恰反證了幸福在生命主體中的內在性。這種內在性表明,對生命而言,幸福是一種自我機遇。
在《幸福的一日》中,幸福的形象學也很耐人深思。這首詩的措辭并不復雜,詩人的修辭動機建立在強烈的抒情性之上,而它包含的美學意味卻非常深邃。在海子的表達中,幸福,首先基于一系列絕對的對比:新和舊,現在和過去,熱愛和麻木,封閉和敞開,文學身份和日常身份。這些對比都不是隨意的,它們的審美邏輯圍繞生命的自我體驗而展開。熱愛,是海子非常看重的一種生命能力,也是他很愿意在詩歌中展現的一種生命姿態。在海子看來,現代人由于深陷于各種社會壓力,逐漸喪失了熱愛的能力。現代人可能會顯得很熱情,但他身上缺少熱愛事物的能力。所以,幸福的體驗首先牽涉到我們是否還擁有熱愛的能力。幸福,還意味著一種自我改造的可能,從舊我如何脫胎為新生。作為一種生命的機遇,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在“新的一天”里體會到生命的絕對意義。按海子的說法,“新的一日”中必然會呈現新的自我。這個新的自我,扮演了新的生命角色,它的出現足以抵得上“一生的富足”。其次,幸福,意味著需要不斷敞開自己的生命。按海子的表達,這種敞開會非常劇烈,就如同我們的身體被從中劈開。奇異的是,這種劈開沒有疼痛,反而讓我們更加坦然地面對秋天的盛大。“劈開”這一意象,在海子的意象譜系里多和生命的覺醒有關。這里,海子的詩歌意圖是,每個人的生命都不應封閉起來,而是應該不斷向大自然敞開,向自然中更大更美的事體開放。從這個角度講,幸福,意味著從個體的有限加入到萬物的輪回之中,從而進入到一種絕對的生命狀態。之所以會顯得絕對,是因為我們已無懼身體的劈開。某種意義上,這種身體的開裂反而讓人的生命開始變得大氣起來,不再猶豫和自然融合為一體。從想象的來源上講,這也許和中國古典詩學中的“縱情山水,物我兩忘”的境界頗有暗合之處。此外,海子的生命觀受德國的生命詩學的影響很大。雖然年紀輕輕,海子卻有點像是一個老練的熱衷于主體性的詩人。他更看重積極的主體創造力。如果說中國古典詩學,在寄情山水方面,強調的是適應;那么,海子強調的是創造。也可以這么講,在海子看來,幸福強化了生命的創造,正是由于這種強化,使得幸福首先可以用于對生活的改造。
對詩歌而言,體驗的核心是自我辨認。在這首詩中,海子還表達了這樣的看法,由幸福引發的自我體驗,由于觸及到了生命的秘密,所以它才會“勝過過去一切的詩”。法國詩人蘭波說過,每個人都是一個詩人。換句生活,按蘭波的直覺,生命的原型角色事實上是詩人。我們“必須是天生的詩人”[6]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面目和身份,但從生命原型上說,詩人是我們的生命的最根本的角色。也是從這個角度上講,詩意的辨認構成了生命中最出彩的戲劇性。同時,這種辨認也是生命的最根本的特征。由于投身于“無限的熱愛”,“我”被他者從世界的荒涼中辨認了出來。這種辨認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蛻變,也展現了一種生命的飛躍,它甚至讓“幸福”都感到驚訝和羨慕。“瞧 這個詩人/他比我本人還要幸福。”比幸福本人還要幸福,意思就是,幸福絕不是一種表面的東西,它根植于生命的本質的沖動,并構成了生命最內在的特征。這里,海子也反駁了那種認為幸福是虛幻的觀念。所以,從根本上講,幸福,主要不是生活的一個問題,而是生命的一個問題。
3
按海子的直覺,關于幸福的體驗,還涉及到人的終極形象。幸福不僅是一種內在的感知,而且更是一種積極的觀看。在“日出”時刻,我們能看見什么,我們能辨認出什么,這遠比我們能感受到什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足夠自信地將我們的觀看轉化成一種洞悉,并給出有說服力的可體驗的情境。對海子而言,僅僅把幸福描繪成一種主觀的體驗還不夠,還必須將幸福展現為一種生命的視域。或者說,只有將幸福塑造成一種生命的視野,幸福的體驗性才會獲得一種內在的真實。在《日出》中,海子用詩的想象將幸福的時刻和幸福的場景交融在一起,突出了幸福在生命的歷程中的視域特征:
日出
——見于一個無比幸福的早晨的日出
在黑暗的盡頭
太陽,扶著我站起來
我的身體像一個親愛的祖國,血液流遍
我是一個完全幸福的人
我再也不會否認
我是一個完全的人我是一個無比幸福的人
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陽升起而解除
我再也不會否認 天堂和國家的壯麗景色
和她的存在.....在黑暗的盡頭![7]
這首詩中,海子依然沿用了對比的手法。這些對比牽涉到基本的生存情境:黑暗和光明,未完成的人和完全的人,肯定和否定,出發點和盡頭,個體和群體,站立和匍匐,灰暗背景和壯麗景色,解放和羈絆。一個疑問是,在如此紛雜的交叉對比中,作為生命的視野,幸福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首先,幸福是一種強大的生命的決斷能力,以及行動能力。我們必須敢于出發,敢于走到盡頭。幸福才會向我們的生命展示它的奇遇性。對人生的道路而言,幸福可以劃出一個絕對的界線——在本詩中,“黎明”是一個界限,“黑暗的盡頭”也是一個界限,這兩者分別從時間和空間上造就了一個生命的轉捩點。過去的我——日出前的我,黑暗中的我,還沒有被太陽扶起的我,不完全的我,痛苦的我,深陷于自我否定中的我,突然在壯麗的日出場景中蕩然消失了。之所以會消失,是因為新的自我誕生了——“一個完全幸福的人”出現了。這里,海子實際上以幸福主題重演了他的詩歌中的復活母題。換句話說,從生命意識的角度看,幸福是一種徹底的自我改變。幸福關乎到人的新生。詩中呈現的誕生場景,與其說是一種經歷,不如說是一種奇遇。由于奇遇的暗示能力,幸福也促成了生命中一種全新的體驗。我猜想,曾被薩特的思想吸引的海子,應該很熟悉法國哲學家薩特的一個說法,我們都想成為一個完全的人。這首詩中的“完全的人”,[8]除了有尼采的“超人”的身影外,還很可能借自薩特。而薩特的說法,正源于他從生命視域的角度對人的形象的一種覺察。按海子的描繪,幸福作為一種生命能力,它不僅可以提升生命的質量,而且可以在根本上改造生命的形象,將我們從生命的殘缺拯救到生命的完全。換句話說,一個人在生命的意義上是否完全,和他是否幸福密切相關。
從修辭方式看,海子在《日出》中把幸福置于黑暗和光明的沖突中來展現,反映出他對幸福的重要性的看法。就對生存境遇而言,幸福絕不是一種邊緣體驗,可有可無,而是一種決定性體驗,涉及性命攸關。按詩人的暗示,如果我們否認幸福,或是無法辨認出幸福,那么,生命的姿態以及生命的形象,對我們來說,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完全的。如果沒有幸福,沒有幸福給予的奇遇,沒有幸福本身所具有的揭示性,我們很可能會永遠匍匐在黑暗中,無法站立起來。我們很可能會永遠處在一種奴役的姿態中而渾然不覺。在這首詩中,海子對幸福與時間的關聯所做的隱喻,也很有深意。幸福的時刻與日出的時刻同時顯現,預示著一種覺醒的時刻。幸福強化了這種生命的覺醒,也昭示了對黑暗的徹底擺脫。“黑暗”這一意象,在海子詩歌的隱喻系統中,多指一種生命的麻木,也喻指一種生命的神性的缺席。而在“黑暗的盡頭”,幸福與太陽同時顯身,表明幸福給予我們的啟示,就如同太陽給予萬物的養育一樣強大。從生命的覺悟這個角度講,幸福照亮生命的晦暗,足以堪比太陽照亮世界的幽暗。
海子還追究了一種典型的現代的態度,即我們時常會表現出來的對幸福的懷疑,對幸福的否定。由于現代對世界的祛魅,幾乎所有的現代人都陷入到一種過度的懷疑之中。按現代性的暗示,幸福通常被歸入一種淺薄的樂觀情緒,無助于我們對存在的荒誕的認知。在這樣的現代心潮中,每個人都傾向于否定性的人生態度。無形之中,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深受現代虛無主義觀念的影響。而海子正如他在私底下喜愛的尼采一樣,將現代虛無主義看成是生命的死敵。海子的想法是,為了抵抗現代虛無主義,我們必須從生命的態度上端正我們的視野。否定的認知固然能增進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以及促進我們對生存的省察;但人們也必須意識到,生命最根本的用途在于肯定。幸福,意味著一種肯定性體驗。幸福激活了潛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再也不會否認”的那種生命的本能。我們能否通過對幸福的秘密體驗,從一個否定的人轉化為一個肯定的人,關系到人的完成。在這首詩中,海子潛臺詞也埋伏得很有震懾力:假如沒有對幸福的絕對感受,我們每個人就走不出“黑暗的盡頭”。所以,作為一種生命的肯定的角色,幸福還是人生的引導者。幸福,引導我們走出“黑暗的盡頭”,并讓我們從一種匍匐狀態躍升到一種直立狀態。站立的意象,意味著一種完成,一種人的形象的自我完成。
也許最為人們熟知的關于幸福的詩歌,就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了: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喂馬、劈柴,周游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9]”
詩的開篇,詩人劈頭就說: 從重新“做一個幸福的人”。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很突然,但也經過了一番深思。促成這一決定的原因,我們固然可以從世俗的現實場景中找到一些線索,但毋庸置疑,這個決定所包含的絕對的態度,又帶有神秘的特點。這個決定,既是一種告別,向不幸福的生命情境告別;又是一種自我召喚,召喚新的自我,新的人生。并且更本質地,這種召喚直接對應著生命的覺醒。這里,覺醒,帶有頓悟的特性,它絕不是一種緩慢的漸進的領悟,它必須喚起生命中最根本的行動能力。所以,海子會說,這個決定可以在今天做出,但它的施行只能放到未來之中——即“從明天起”。為什么會如此呢?這就又涉及到今天和明天的對比。在海子的想象譜系中,今天,已深受現代性的侵蝕,今天已沒有希望了。所以,新的生命行動必然是一種絕然的脫胎換骨。它的絕對和徹底,都需要一個全新的開始,它不應再被今天的陰影所拖累。
在這首詩中,最為感人的是,海子對幸福和行動之間所做的描繪。幸福,首先意味著一種行動能力。幸福的可體驗性,就在于我們有充分的行動能力將新的生命姿態投身到新的人生中。“喂馬”“劈柴”“周游”“關心糧食和蔬菜”,這一系列行動,既預示生命的新的方向,又是顯示了人生的新的追求。從形象上看,這些行動都很淳樸,很原始,帶有強烈的游牧色彩——甚至令人吃驚地聯想到德魯茲的將生命游牧化的呼吁,而且兩者在逃逸的審美路徑上也格外吻合。或許,海子正是想通過這些行動來展示一種自由的生命狀態,并暗示,作為一種生命的行動,幸福本身確實具有一種原始主義的審美傾向。這里,海子再次通過舉例強調了幸福和天真之間的關聯。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生命的幸福和存在的單純之間互為影像。周游即漫游,它是吟游的變體。“周游”意味著對物質的最少的依賴。更重要的是,隨著依賴程度的陡然降低,我們可以讓身心保持一種無拘束的自由狀態。“關心糧食和蔬菜”,意味著對烏托邦想象的矯正,意味著從抽象的原則回歸到對大地的敬畏。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對大地的物產的關心,是我們回到新的辨認的開始。這種關心也促使我們在生存中保持一種細心和敏感。而假如缺少這種關注,幸福也必然會走樣;沒準還會墮入一種無邊的虛妄。“和每一個親人通信”,意味著向別人盡可能的開放自己。也不妨說,在這里,海子再次重復了他在《幸福的一日》中申明的幸福和開放性的關聯:幸福就是走出舊我,出離舊有的狹小天地,重新敞開自己——必要的話,甚至是重新劈開自己。一句話,幸福,意味著我們必須學會從自我的開放中獲得一種生命的博大。
為什么“我的幸福”會是“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這里,有兩層含意。第一,幸福是一種頓悟能力,它是瞬間的,富于啟示性的。第二,幸福關系到體驗的神秘性,它是極其強烈的,甚至是帶顛覆性的。幸福對生命的啟示,猶如“閃電”對黑暗的洞穿和照亮。“閃電”這一意象,帶有激烈的含義,這恰好符合海子對幸福在生命的體驗性中所具有的激進特征的強調。此外,將幸福的來源追溯到“閃電”,也多少暗示了這樣的詩的想法:幸福近乎一種天啟。幸福不是一種價值觀念,而是一種感知能力。不僅如此,幸福還是關乎到生命的樣態的最核心的秘密。就漢語的詩歌經驗而言,我覺得,海子對幸福和秘密之間的關聯的反復強調,是非常有獨創性的。正是由于這秘密的存在,幸福將生命引向了一種無畏的自我體驗。沒有這種體驗,生命的形象終究是不完整的。
另一方面,語言和幸福的關系常常顯得很詭異。作為一種內在的體驗,甚至是作為一種生命的秘密,幸福能被言說嗎?在海子對幸福的演繹中,最為可貴的,就是他自始至終堅信詩的語言有能力呈現幸福。詩的語言能克服我們的懷疑,甚至是克服我們的現代性,將幸福以原始場景的方式揭示出來。在這首詩中,轉述的意象,凸顯了幸福和秘密的關聯。它表明,和幸福有關的生命體驗絕不是無法傳遞的。幸福和生命中最深的秘密有關,而這種秘密是可以共鳴的。“告訴我的”,我也將“告訴”他人:這是共鳴的一種方式。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積極從事新的命名。“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詩人的意思是,從啟示開始,幸福必然會演化成一種神奇的力量;幸福不僅可以激活個體生命,而且通過共鳴,它也可以烘托出一種宏大的生命氛圍。幸福讓我們多少獲得了一種轉化痛苦的能力,讓我們重新據有一種寬廣的胸襟。對事物的命名,對環境的命名,反映出我們改造世界的一種能力。某種意義上,積極的命名,是一種強大的創造力的體現。而命名本身也是人的最基本的能力。通過命名,我們不僅能認識事物和環境,也完成了生命自身的改造。所以,取一個名字,絕非看上去那么簡單。海子將命名和幸福聯系在一起,將命名行為演繹成幸福的一種自我體驗,顯示了詩人的一種洞見。此外,在海子看來,幸福首先意味著一種體驗,但它也帶有先驗的色彩。
4
通觀海子的詩歌,我們會注意到一個顯著的傾向:海子對幸福主題的關注,既有即興的一面,又深奧的一面。有趣的是,即興和深奧都源于他的帶有激進色彩的肯定詩學。從早期寫作一直貫穿到后期寫作,他幾乎從未間斷過對幸福的想象。的確,他的詩歌也涉及到大量的痛苦主題。人生的孤寂,交流的艱難,存在的冷漠,生命的衰敗,在他的詩歌中都有涉及。但無論怎樣描寫痛苦和孤獨,他都沒有減弱或放棄對幸福的關懷。為了避免這種關懷滑向一種主觀的臆想,海子也常常從痛苦的視角出發,來深究幸福的審美意義。
從早期到后期,海子一直在他的詩歌中將“幸福”和“痛苦”并置;并在想象的系譜上,將兩者塑造成了一種對等的生命視域。可以說,這種并置反映出詩人的兩個最基本的審美意圖。從體驗性的角度看,海子從一開始就無意在“幸福”和“痛苦”之間做價值上的區分。如果說痛苦意味著人生中一種根本性的體驗,那么“幸福”也同樣是。世俗的觀念通常會對人生做如此假定:“痛苦”是漫長的,“幸福”是短暫的。“痛苦”是根本的,“幸福”似乎是虛幻的。海子從來沒有接受過這樣的想法。相反,在他的詩歌中,憑借突出想象力的強度,他努力想傳達的是,“幸福”和“痛苦”對生命體驗而言是同等的,兩者包含的感情色彩同樣都很強烈,它們都觸及到了生命的本質。在《重建家園》中,海子寫道:
“生存無需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10]”
這里,海子將“幸福”和“痛苦”并置,并將它們演示成“大地”呈現自身時的兩種最根本的能力。在海子的直覺中,即使在重建的人類的“家園”中,“幸福”和“痛苦”也是最根本的生存情境。它們之間不是相互取代的關系,我們不能允諾用“幸福”消除“痛苦”,也不能一味沉溺于“痛苦”,而喪失了對“幸福”的體察。在這里,海子還巧妙地使用了一種反諷:“生存無需洞察”。這句話的真實意圖很可能是,“幸福”和生命之間的關系當然需要我們的洞察,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明白,就像“痛苦”和生存之間的關系一樣,我們的洞察無論怎樣深刻,怎么犀利,都不足以抵達“幸福”本身對生命情境的揭示能力。
在《太陽和野花》中,海子也呈現過相似的并置:
“太陽是他自己的頭
野花是她自己的詩
總是有寂寞的日子
總是有痛苦的日子
總是有孤獨的日子
總是有幸福的日子
然后再度孤獨 [11]”
這些反復出現在海子詩歌中的并置,體現了一個總體性的詩歌意圖:即“幸福”和“孤獨”一樣,也和“痛苦”一樣,指向最根本的生存體驗,也指向最本質的生命情境。“幸福”不僅僅是一種感受,它也是一種最基本的生命能力。假如把“幸福”僅僅當作一種生存的感受,那等于把“幸福”簡化為一種對外部世界的反應。在海子的信念中,“幸福”應內在于生命的能力之中。在這首詩中,使用“總是有……日子”這樣的排比句式,還暗示了一種人生觀。從體驗的角度,海子建議我們這樣看待我們的生存圖景。“幸福”“痛苦”“孤獨”的并置關系表明,“幸福”和“痛苦”一樣,它們都是生存情境中最基本的面貌,它們之間既彼此交叉,又難以完全混和在一起;與此同時,它們還將一種交替的時間節奏賦予了我們的世俗人生。對我們的生存而言,“總是有痛苦的日子”,但這顯然不是生活的全部真相,另一方面,也“總是有幸福的日子”。換句話說,就人生的真相而言,“痛苦”無論多么強烈,和“幸福”一樣,它們都只反映了生存圖景中的一個側面。
為什么說海子描繪的幸福涉及到我們對人類的生存圖景的一種想象?要厘清這之間的關聯,我們就必須討論海子在詩歌中呈現的關于“幸福”的形象學。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內在的生命能力,作為一種生存感受,“幸福”在哪里可以找到?“幸福”和我們周圍的何種事物關系最密切?海子在詩歌中反復暗示,我們對“幸福”的體驗實際上應該遠比我們的感受強烈。假如不是如此,或者,假如在我們的生存記憶里,“痛苦”的體驗超過了“幸福”的感受,那么,這種情形只意味著我們對生命的麻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這么理解,海子對“幸福”的描繪首先是為了喚醒他自己,以徹底擺脫他在普遍的生命境遇里觀察到的那種麻木的狀態。就技藝而言,擺脫事物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修辭的方式提純某些東西。海子使用的提純方式是,將“幸福”安置在遠離人世的自然情境之中,這種情境要么是強烈的,要么是純粹的,要么是壯麗的。換句話說,這些詩歌中的自然情境,實際上是海子意欲為我們展示的一種生存的原始情境。它們無一不具有一種強烈的想象色彩。在《太陽和野花》中,詩人將對“幸福”的關懷投映到強烈的寓言想象中。在詩篇的開頭,詩人說:
“太陽是他自己的頭
野花是她自己的詩”
在詩篇的結尾詩人說:
“到那時 到那一夜
也可以換句話說:
太陽是野花的頭
野花是太陽的詩
他們只有一顆心
他們只有一顆心”
這里,“換句話說”使用得很有機趣。在海子看來,由于現代的都市文明對生命的敗壞,我們已幾乎喪失了對“幸福”的體驗能力。為了扭轉這一困境,我們需要通過強烈的甚至是暴烈的想象,來激活我們的這種體驗能力。“幸福”是一種體驗,但從生存的迫切性上講,它首先意味著關于這種體驗的想象。只有激活了強大的想象,并通過強烈的想象對世俗偏見的顛覆,我們才有可能重建我們對“幸福”的體驗。“太陽是他自己的頭”,這本身已是一種想象,但在這首詩中,隨著“幸福”的介入,詩人的想象發生了一次顛覆性的逆轉——“太陽是野花的頭”。關于“幸福”的介入,詩人還有更具體的說法:
“我會在我自己的胸脯找到一切幸福。”
這里,“自己的胸脯”而非別人的胸脯,可視為一種更為果決的界定。“自己的胸脯”,意指有限的狹小的范圍,但海子申明的信念是強大的:這么小的范圍已足夠,足以讓我們找到“一切幸福”。要充分理解這句話的蘊藉,恐怕還須注意到“胸脯”的意象中所包含的私密、溫暖、珍貴的喻指。在這些細致的想象紐帶中,海子再次強調了“幸福”和生命之間的個人關系。按照海子給出的邏輯,一旦我們進入到生命的自覺,我們不需要到我們自身以外的地方尋找“幸福”,我們完全有能力在我們自己身上體驗到“幸福”。并且,我們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幸福”不是局部的、殘缺的、個別的,它觸及并已包含了“一切幸福”。所以,“幸福”的含義在于,我們必須智慧地覺察到即使在像個體生命這樣有限的范圍里,全部的幸福也已蘊含在其中。此外,詩人的表達里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切的意圖:既然我們最終找到“幸福”的地方就是我們身上最隱秘的部位,這就表明“幸福”不僅是涉及一種生命的覺察,它更是一種自我給予能力。這種能力包含兩個向度:我們將生命引向“幸福”的意志,和我們將“幸福”給予生命的欲望。
5
從形象學的意義上看,海子對“幸福”的描繪,既像是出于一種謹慎的思量,又像是源于一種本能的領悟。換句話說,對生命情境來說,“幸福”是可體驗的,但它又帶有超驗的色彩。從海子的呈現方式看,他的想法是,假如我們對“幸福”的覺察及其體驗不具超驗性的話,那么,我們對“幸福”的體察最終必然會被世俗的觀念所腐蝕。所以,在海子的描繪中,他更傾向于將“幸福”呈現為一種生命的境遇,這種境遇既向日常存在開放,又帶有奇遇的意味。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日常生存中,出于生命的領悟,我們隨時都有可能遭遇“幸福”的時刻。但這些時刻一旦反映到我們的記憶中,它們就會顯得更像是一種“奇遇”。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么理解,海子將“幸福”呈現為一種奇遇,并不是說“幸福”很稀有,罕見于我們的日常生存;相反,他突出“幸福”的奇遇色彩,意在強調“幸福”作為一種體驗,它對生命本身的啟示是非常強烈的。這強烈的程度絕不亞于“痛苦”和命運的關聯。如果說“痛苦”是一種命運的表征,那么對生命而言,“幸福”同樣意味著一種命運的化身。
在《黑翅膀》這首旅行詩中,海子通過他在西藏日喀則的夜宿經歷,將一次失眠鋪墊成通向“幸福”的一種線索。他這樣描繪高原的夜晚中“嬰兒的哭聲”:
“為了什么這個小人兒感到委屈?是不是因為她感到了黑夜中的幸福[12]”
通常,感到“委屈”是源于不幸,但在這里海子卻一反常態將“幸福”定義為“委屈”的原因。而且更有意味的是,原本連成人都不容易感知到的“幸福”,海子偏偏說,“嬰兒”卻能憑哭喊(一種本能的隱喻?)而捕捉到。通過在“嬰兒的哭聲”和“黑夜中的幸福”之間建立的隱喻關系,海子突出了這樣一種洞見:“幸福”可以說是一種觀念,但從生命的本意上講,它很可能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之所以會“感到委屈”,是因為生存中存在著普遍的腐敗,在這樣惡濁的環境中,“幸福”有時會變得很敏感。“幸福”敏感于我們的信念,同樣,我們也敏感于“幸福”在我們的存在中所遭遇的遮蔽和損害。但是,另一方面,即使非常荒涼的偏僻的地方(比如日喀則的荒野),我們對“黑夜中的幸福”的向往和領悟也是無法抑制的,它們就像寂靜的荒野中“嬰兒的哭聲”。
如果說日喀則的荒野顯示的遙遠,還缺少一種詩歌的說服力,那么,海子在他的后期代表作《遠方》中則更加明確了“幸福”對于生命自身的神秘的啟示:
“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遙遠的青稞地
除了遙遠 一無所有
更遠的地方 更加孤獨
遠方啊 除了遙遠 一無所有
這時 石頭
飛到我身邊
石頭 長出血
石頭 長出七姐妹
那時我站在荒蕪的草原上
那時我在遠方
那時我貧窮而自由
這些不能觸摸的 姐妹
這些不能觸摸的 血
這些不能觸摸的 遠方
遠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13]”
在這首詩中,在形象學的意義上,海子異常堅決地將“幸福”和“遠方”聯系在一起。這首詩體現了海子最根本的世界觀。某種意義上,寫于1988年底的這首詩,也反映了海子對“幸福”的詩歌形象所做的一次自我矯正。他將人們對“幸福”的體驗范圍更加絕決地限定在“遠方”。“遠方”這一意象有幾個突出的標識:遠離城市,荒蕪,壯闊,孤獨,景色單一,貧瘠;與這些相隨的,它又是奇跡發生的場所——“石頭長出血/石頭長出七姐妹”。如果詳盡地思量“幸福”和“遠方”之間的隱喻關聯,就會意識到海子作出這樣的安排是有其深遠的思量的。就現代漢語的傳統而言,海子可以說是最具有宿命感的詩人之一。將“幸福”內化于命運,已是海子的驚人之舉。但更令人吃驚的是,海子對“幸福”的關懷還反映出他對宿命的認知。或者說,“幸福”之所以會成為一種生命的動機,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種宿命的體現。在《遠方》中,詩人描繪了“幸福”和人生歷程的一種關系。“幸福”首先意味著一種決然的行動能力,我們必須投身于人生的旅程——“路慢慢其修遠兮”,才能抵達作為一種境遇的“幸福”。在這里,海子再次強調了尋找對“幸福”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清晰地作出了這樣的暗示,這種尋找意味著在喧囂的人世中放棄一些東西。唯有決然的放棄,才能辨認出“遠方”的意義。不過,在這里,放棄和棄絕還是存在明顯的區別。海子的本意也許并不是要將我們引向一種棄絕,詩中呈現的放棄,更多的指向我們應從心靈深處排除那些人生的雜念,更坦然地面對生存的真相——“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某種意義上,“幸福”首先意味著一種單純的能力,它不會因“一無所有”而陷入絕望,也不會因“一無所有”而恣意抱怨;相反,“幸福”通過它自身對“一無所有”的接納和擁抱,完成了它對生命的內在的召喚。從“不能觸摸”一詞的使用上,我們也可以推斷出海子的一個想法。即對生命的秘密而言,“幸福”具有一種神圣的特性;它是不可妥協的;它無法被賄賂,它不以我們的世俗意念為轉移。換句話說,人們不能僅僅依據世俗的感受來衡量“幸福”的存在與缺席。人們也無權因感覺不到“幸福”就否認它的存在,更沒有資格因自己的無知和麻木而懷疑“幸福”帶給生命的啟示。
海子從未想過在詩的想象中壓抑這種內在的啟示。事實上,他一直傾向于通過詩的言述來公開幸福的啟示。在早期寫下的最出色的抒情詩《明天醒來我會在哪一只鞋子里》中,海子宣稱:
“我不能放棄幸福
或相反
我以痛苦為生[14]”
在這首涉及“覺醒”主題的短詩中,海子嚴厲地審視了詩人的自我在叵測的世俗生存中的“自畫像”。針對生存的虛幻和生命的美好之間的裂痕,特別是針對“我是誰”的現代困惑,海子亢奮地寫道:“老不死的地球你好”。但即使在發出這樣的詛咒之后,海子依然將“幸福”歸結為生命中“不能放棄”的一種體驗。在詩中,海子又一次將“幸福”與“痛苦”相提并論,這種做法表明,在詩人看來,我們對“幸福”的關注,如同我們對“痛苦”的體驗一樣,是終生的,也是根本的。假如說在人生的體驗中,“痛苦”是無法避免的,它關系到最根本的生存體驗;那么,“幸福”同樣是無法回避的,它也同樣關系到最本質的生命體驗。這里,海子用“以痛苦為生”作為一種參照的條件,來強調“幸福”絕非是一種虛幻的東西。換句話說,海子憑借他對人生的痛苦所懷有的洞察,領悟到了這樣一種觀念:無論我們在人世中經歷怎樣的“痛苦”,這種“痛苦”都不足以否定“幸福”。到了這一步,我們已可以大致判斷出,海子在詩歌中對“幸福”主題的突出,絕不僅僅限于一種浪漫的表達,而是包含對生命的本質的一種省察。
總的說來,在對幸福主題的想象演繹中,海子最具獨創性的地方是,把幸福從一種社會觀念重新還原為一種個人體驗。在短詩《幸福的一日》中,他很好地示范了這一蛻變過程。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有意避開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幸福,轉而以一種強勁的詩歌想象,將幸福凸現為一種有關生命本質的獨立的審美:幸福不僅是一種基于物質的人生感受,更是一種純粹的生命體驗。在海子看來,這種體驗契合了尼采的生命輪回之說。幸福揭示了來自生命內部和大地深處的雙重召喚。真正的幸福不是來自生存外部的給予,而是一種生命的自我給予。這種給予,在本質上體現的是生命的自我創造。這樣,海子就把幸福從一種世俗的主題上升到一種存在的主題。在海子的詩歌中,幸福既是一個核心意象,又是一個貫穿性的主題。假如在詩歌的意義上存在著一種幸福的詩學,那么,它關乎的是生命的自我認知,也牽連到人生的秘密感受。不可否認,它帶有一種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但這種神秘主義,并不虛幻,它恰恰針對著我們的狂妄與無知,它和我們每個人對生命的自我體驗息息相關。
注釋:
[1] 薩特,《答加繆書》,《薩特研究》,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2]《海子的詩》,2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3] 《海子的詩》,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4] 《海子的詩》,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5] 《海子的詩》,1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6] 蘭波,《致保羅德美尼》,《傾訴并且言說》,45頁,北京出版社,2003年。
[7] 《海子的詩》,1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8] 薩特,《七十歲自畫像》,《薩特研究》,11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9] 《海子的詩》,21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10] 《海子的詩》,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11] 《海子的詩》,17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12] 《海子的詩》,1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13] 《海子的詩》,1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14] 《海子的詩》,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來源:《文學評論》
作者:臧棣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501/c404031-29959051.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