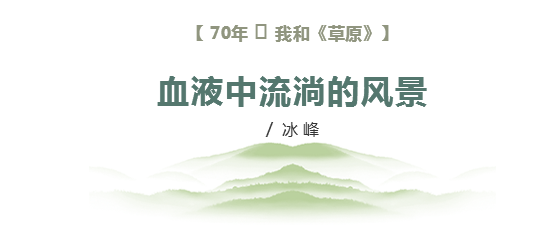

詩人們相聚在白云鄂博詩會上。左起張鐘濤、尚貴榮、白濤、蒙根高勒、楊曉旭、陳榕
【70年 · 我和《草原》】
冰峰:血液中流淌的風景
作者:冰峰
歲月無痕,往事如煙。
1987年,我第一次見到《草原》編輯部的尚貴榮時,他年輕、帥氣的樣子一下子侵占了我對《草原》的最初印象:《草原》是年輕的,也是充滿活力的。之后,我又陸續見到了丁茂主編以及趙健雄、路遠、白雪林、任建等《草原》編輯部的朋友。我與他們雖然來往不是很多,但“同志”般的感情一直保持著溫度。因為我們都喜歡文學,又是編輯圈子里的同行。唯有尚貴榮,除了“同行”之外,還有著更多的情誼,那時候包頭的“呦呦詩社”正是繁盛時期,尚貴榮是往來最為密切的“知音”和老師。
1989年,“呦呦詩社”組織了“白云筆會”,內蒙古當時很多重要詩人匯聚白云鄂博,在那一片神奇的土地上,一首首詩作應時而生。后來,《草原》編發了“白云詩會專輯”,讓“呦呦詩社”很多會員的作品登上了省級刊物的殿堂。那時候,我和“呦呦詩社”社長白濤的工作單位都在包頭市東河區,貴榮一進入包頭境內,第一站就會在我和白濤的“領地”落腳,談詩論道,淺酌豪飲,友情日深。文學帶來的友情,用文字恐怕是難以詳盡的。
“呦呦詩社”現在雖然失去了往日的“繁榮”,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呦呦詩社”在內蒙古詩歌界有著響當當的名號。2015年,“呦呦詩社”成立30周年,我主編了《呦呦往事》一書,把“呦呦詩社”與《草原》來往的歷史記錄其中。可以說,沒有尚貴榮、趙健雄等《草原》編輯的參與,“呦呦詩社”不可能有當年的盛景。現在想來,那是一段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時光,雖然已經漸行漸遠,但留給內蒙古詩壇的輝煌卻是永遠無法抹去的。
2001年,我離開包頭來北京工作,距離并沒有讓我和《草原》的關系疏遠,反而顯得更為親近了。我在《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的時候,貴榮已是《草原》的主編。幾次路經呼和浩特,貴榮都會約天男等詩友小聚。一晃二十年,貴榮已退休離開工作崗位,阿霞成為了《草原》主編,我也離開《人民文學》,現在回想起來,恍如隔世。但對《草原》的感情和惦念卻是永恒的。
阿霞做主編,雖然年輕,但她文學情懷很濃,把《草原》辦得風生水起,在不景氣的文學大氣候中為內蒙古乃至全國的文學事業開辟出了一塊繁花似錦的芳草地。她把敕勒川、楊瑛等有名的詩人、作家聘請到編輯部,還著力培養年輕的編輯隊伍,讓《草原》有了更加持久的生機活力。
近年來,我身在他鄉,一直在關注《草原》,他們選發的作品,前衛、先鋒,但又保持了傳統的本色;既有老作家的經典之作,也有年輕新秀的開山力作,可謂兼容并蓄。作家網主辦的全國高校征文活動中的獲獎作品,也受到了《草原》的力推,在全國高校的文學愛好者心中,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草原是廣闊的,也是博大的;《草原》的情懷牽扯著我漂泊的心。每當想起我的故鄉——那片遼闊的草原,都會想起與《草原》有關的人和事。我希望無論到何時何地,我的內心,也會像草原一樣壯美、遼闊,更像文學的《草原》一般溫暖、包容、純凈。祝福《草原》!

冰峰,本名趙智。作家網總編輯、北京微電影產業協會會長、北京詩社名譽社長、亞洲微電影學院客座教授。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人民日報》《詩刊》《隨筆》等報刊。出版個人文學作品集多部。雜文《嘴的種類與功能》入編《大學語文》。有作品曾獲第29屆世界詩人大會(在匈牙利舉行)漢語寫作最佳詩歌作品獎、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等。曾參加第五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在亞洲微電影藝術節“金海棠”獎、全國高校文學征文、《北京文學》年度獎等評獎活動中擔任評委。先后應邀出訪北美洲、南美洲、歐洲、大洋洲及東南亞等地參加文學活動,并發表主題演講。2014年,獲美國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榮譽博士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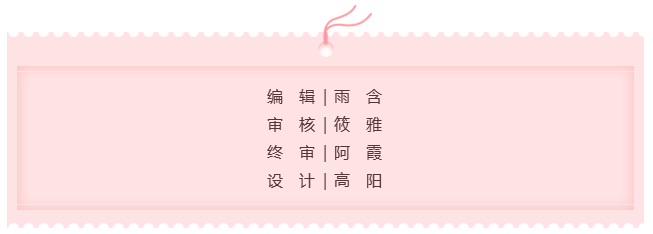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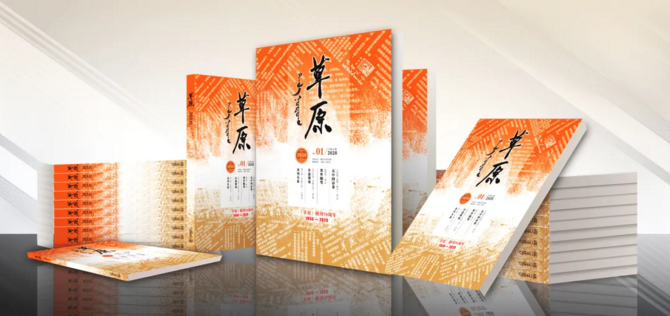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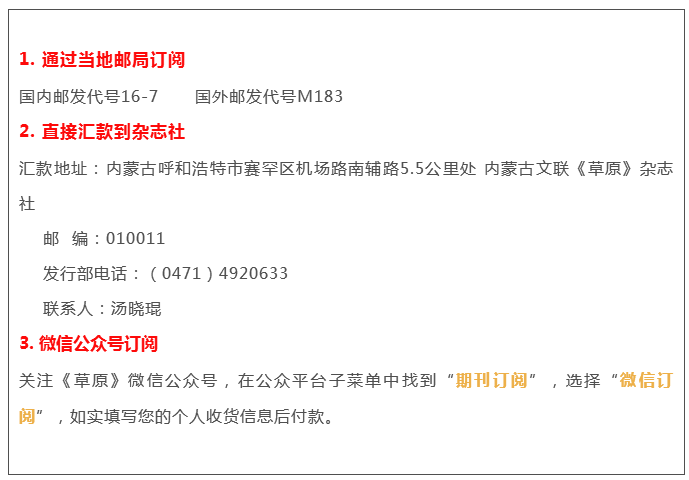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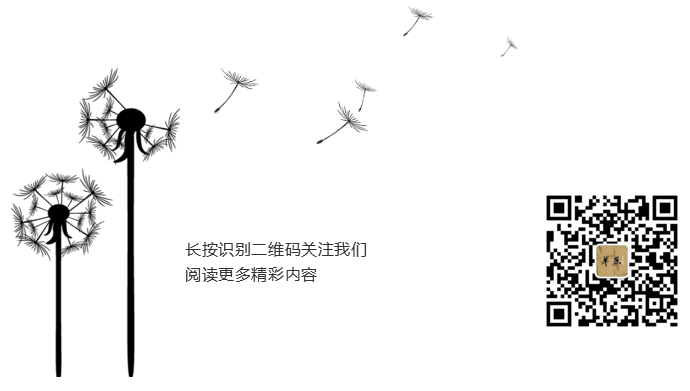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