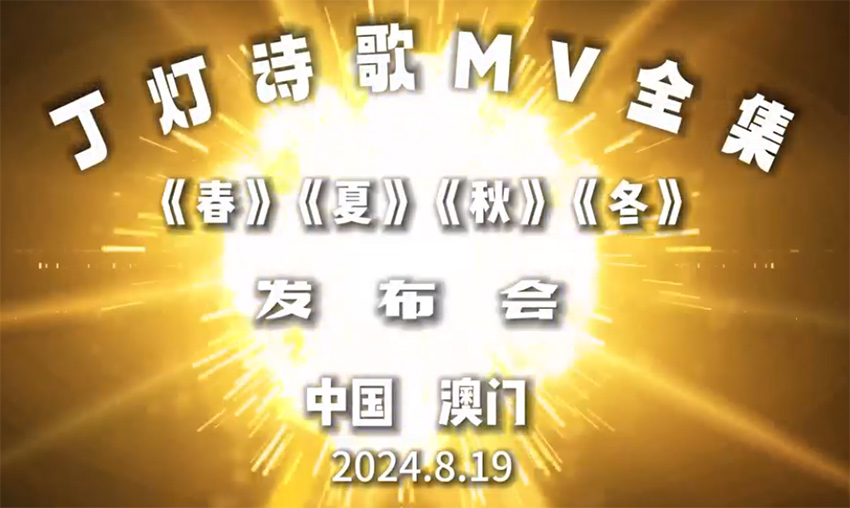北京出版社2023年1月
論顧艷的疼痛詩學與女性靈魂之音
作者:張益偉
新世紀以來,北美華文文學出現了新氣象,一批杰出的新移民作家諸如嚴歌苓、張翎、陳河、陳謙、曾曉文、葉周、陳九等競相將創作筆觸對準了北美在地化生存或中國經驗,以紛繁復雜的書寫表達他們和西方多元文化的共存情境和融入鏡像。這其中,旅美作家與詩人顧艷是其中的佼佼者。顧艷在出國前已創作不少長篇小說。1998年出版長篇小說《杭州女人》,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2011年出版長篇小說《辛亥風云》,2009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九堡》。同年她去斯坦福大學訪學,并在康奈爾大學進修了創意寫作。2017年,顧艷正式定居美國教書。近幾年來,顧艷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她先后參與了《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選》年選的編纂,在國內外文學刊物上接連發表詩歌和小說作品。詩集《風和裙裾穿過蒼穹》2023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這部詩集是對顧艷三十多年來詩歌符號藝術表達的一次集中檢閱,距其第一部詩集《火的雕像》(1989年)出版,已經過去了34年。正如她在詩集序言中所說,這是“一部個人精神的成長史”。該詩集一共分為五輯,200多首詩歌,涵蓋和匯聚了詩人由青年到中年等不同階段的思想經驗,交匯著詩人對情感、生活、社會的具象思考,流露出詩人一以貫之的對詩意靈魂和高潔情趣的追求,同時也以題材上的多元表呈現著新移民在新時期的書寫命題。
一、疼痛詩學與女性靈魂的凝視
顧艷酷愛文學寫作,并與文學有著天然親近的聯系。這一方面反映在她30多年不間斷的創作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她為文學付出的代價上。在自傳性長篇小說《疼痛的飛翔》中,小說主人公和顧艷具有高度相似性,兩個人都為了文學藝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小說《杭州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池青青高度重視尋找個人的精神家園,而非物質生活。其筆下的女主人公對精神世界的追求,甚至走向偏執和極端,盡管他們難逃在現實中孤寂和失敗的種種境況。陳駿濤曾結合小說“自我傾訴式”的基調指出女主人公和顧艷經驗的相似性,女主人公為了實現文學夢,與家中父母關系冷淡,還被迫與丈夫離婚,個人生活“一塌糊涂”,唯獨對文學的憧憬始終如一。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顧艷對文學創作和精神生活的高度依賴。顧艷出國前在大學任教,近十五年來,在美國經歷了訪學、求學、工作、專職寫作等過程,異域離散經驗使其人生更為豐富,視野也更為宏闊。這突出反映在其詩歌題材的多元和詩歌主題的開放性上。但是從整部詩集來看,詩歌充滿著疼痛感,這種疼痛感突出表現在疼痛詩學的探索和建構上。
顧艷的詩歌寫作自覺秉承了80年代初朦朧詩派的創作成就,延續了翟永明、舒婷等詩人對女性意義的探尋主題,在凸顯和生成女性氣質這一主題上,顧艷與80年代崛起的女性詩歌的創作宗旨是一脈相承的。顧艷的詩歌首先集中表現了對女性位置和意義的發現。《組詩:一個人的島嶼》很明顯體現了女性的獨立。“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一個人就是全部/我沉重的思想/虛無,除了/在那顆心的宇宙中/我是自己唯一的王”,在這里,女性以桀驁不馴和倔強的姿態得以表呈。其詩歌與翟永明的《女人》也有著某種暗和。“從天上掉下的月亮/就像一把匕首/它冰冷的刀鋒刺向我/每一個深夜/我觸摸它,并不畏懼”,女性一開始不是懦弱者,性別中的強弱之分只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在詩歌中,女性的凌厲和力量十分充盈卻又富有變化,女性不懼漂泊,并且主動選擇遷徙和漂泊,詩歌文本中不斷出現流動性、離散性和叛逆性特質,進而生成新時代女性在地理空間上的不確定感。《貓頭鷹的品質》這樣寫到:“我們都在黑夜里飛翔/它蹬開大樹 我避開喧囂/我們的共同目標/飛向低處 飛向深淵/我們與藍天白云漫天的星星無關/我們的飛翔是形而上的飛翔”。在這里,抒情主體將貓頭鷹的品質化為個人的一種追求,貓頭鷹在黑夜里起飛,抒情主體也敢于飛向深淵,抵達對“形而上”的真理的獲取。貓頭鷹是夜晚的清醒者,是黑夜的主宰和洞悉者。貓頭鷹的無懼無畏顯示出女性的力量和勇氣。
顧艷在詩集序言《飛翔之姿》中說:“正因為有那么多現實世界、精神世界的痛苦,我的詩歌才創造著我的主體世界——精神內核”。顧艷的詩與主體的痛苦感受有著緊密的聯系,而痛苦作為經驗也是其詩歌創作的動力。這種疼痛感一方面源自于現實體驗,另一方面源自詩人對世界的把握和表現方式。在具體指向上,詩歌主要傾訴了女性精神上的疼痛和孤獨。《長詩:女性獨白》中的《獨舞》《劫難》《聲音》最能夠體現這種經驗,詩歌突出對痛苦內在機制的展示,細致捕捉主體生命的孤寂、多舛和坎坷,也在時間的脈絡中審視女性面對痛苦的態度。但是顧艷的這種疼痛包含著個體的“再生長”,疼痛不再是一種絕對的施壓,與八十年代初女性詩人性別寫作中對男性的絕對反擊不同,顧艷筆下的疼痛并非只是簡單的決絕式的控訴,而是流露出灑脫和清醒,盡管痛苦經驗增添了詩歌的愁緒和傷感質素,但是詩歌在總體風格上并不走向頹廢和虛無,而是呈現出于絕境和痛苦之中尋找希望的不懈努力。“我,一個女人因為疼痛/喝著自釀的音樂酒/冷風飄在臉頰上/我的微笑像一座廢墟/我的雙眼睥睨一切/我奏響的音樂/與我裹著露珠和塵埃熟睡”。因此,詩歌在絕望之境中在尋找希望,詩歌話語中總是裹挾著蛻變的渴望與沖動。
另一方面,疼痛詩學表現在詩人對生命本身的缺陷抑或脆弱特點的觸摸,從而構成詩人對生命內在隱秘機制的展示。《秋季》《紅鳥》中的部分詩節都體現了對生命內在曲折性特征的呈現。同時,疼痛感還包括詩人對人類個體的渺小和卑微的一種深切體察,一種對歷史和女性個體命運關系的省思與對接。詩歌因此構成了對“天地神人”整個宇宙空間的深沉思考,進而在宏大世界和卑微個體之間巧妙地建立聯結。由此,對疼痛感的把握逐漸從個體轉移到對普遍性精神的捕獲。在詩歌空間上,也逐漸從個體抵達對人類更大的活動空間的開辟,疼痛的形狀和疼痛的樣態自然也從形而下逐漸上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層面,進而使得詩歌具有了更飽滿的闡釋空間。
詩歌將疼痛感與女性情感經驗融合在一起,呈現出女性對疼痛的承受的同時,也在嘗試表達對疼痛的超越和突圍。在詩集第一輯“女人”中,集中表達對女性的反思。“長詩:女性獨白”組詩可謂是顧艷個人女性觀念的全方位表達。全詩一共分為三章,第一章中的五首詩歌《祈禱》《遐想》《閃電》《古堡》《火焰》充滿著對女性力量的謳歌,從對“坐在椅子上的褐衣女人”的描述到對“所有的墻壁都是路”的堅持和無畏,再到敢于忍受“蒼涼而且寒冷”的孤獨,詩歌提供了直率和勇氣,這種勇氣賦予女性以大無畏的果敢和對生命的擔當。如果說女性在傳統視域中常被視為如水樣的存在,是溫柔的、脆弱的、馴服的、沉默的大多數,那么我們于此則看到的是“火中鳳凰”般的敢于展翅翱翔的女性,女性的倔強、頑強、堅毅展露無遺。“古堡啊,多少白晝痛苦的光/從你身上流過”,古堡作為一種時光流逝的見證物,見證著女性的堅持和不拔。而《遐想》一詩則在一種想象空間中表現了詩人勇敢的氣質。這種勇敢開始以宏闊的意象和場景來呈現,并在意象組合中表現女性情感的堅韌不拔和氣魄。諸如:
“我,一個遐想的年輕女性
骨骼結構著完整的精神
所有的墻壁都是路
世界充滿我的眼睛”
詩句顯示出一種無畏的骨氣,這種骨氣給予人的力量是無窮的。于是,連構成障礙和阻隔的“墻壁”在這里竟然變成了“路”,顯然,詩歌結構上的這種悖論與矛盾構成了一種反邏輯,這就更加呈現出在無路中尋找出路的勇氣,一種不懼風雨與凌厲的氣勢也使得抒情主體像一位久經戰場的女俠。而事實上,詩歌中也時常呈現出女性滿身皆“英氣”,“我抽出一柄煌煌巨劍/馬蹄嗒嗒/巾幗不讓須眉”。由此出發,甚至聯想到花木蘭替父從軍、鐵骨錚錚的風范。而在意象的組建上,詩人巧妙地將中國山水和人文歷史符號編織到對女性情感的組建上,將女性個體情感和山水人文進行了粘連,構成一組宏闊的意象群落。在天與地、古與今之間游走的是一個新時代女性,這位女性接續古老中國的文脈符號,告別女性被壓抑的歷史,代之以個體的清醒姿態回應著歷史的詰問,顯示出深沉、開闊,廣博的韻味。如《遐想》中這樣描述:
“我將怎樣瞭望蒼茫大地
黃河母親無盡的傾訴
絲絲縷縷 繞指繞心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一代天驕,氣連霄漢
無數英雄像砂礫像星辰”
在這里,詩人巧妙化用毛澤東1936年2月創作的《沁園春·雪》中的名句,體現出個人對歷史和英雄人物的接納和重新認識。它打開了更為宏闊和浩淼的遐想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歷史英雄人物像“星辰”一樣凝視著大地,抒情主體也因此被灌注了生氣和活力,女性的遐想空間也因此變得陽剛而豪邁,而非婉約詩詞中的幽怨與憂思。
詩歌注重塑造勇敢的女性形象,強調做一個孤勇者所需要的強大意志力,這里的孤膽英雄不僅敢于忍受現實的摧殘,更具備超凡的耐力。《閃電》一詩突出表現詩人的這種情感:
“我披散長發站在這里
與啼血的夕陽融為一體
死亡一樣耐心地等待
宛如大海遺棄的巖石”
抒情主體是孤注一擲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并具有一種忘我的精神。“歲月的鞭打比金屬更冰冷/我將自己撕得遍體鱗傷”,時間給個體帶來的除了無情的鞭打之外,還有讓主體領悟的事物,而主體也具備一種將自己“撕毀”的勇氣。在這里,主體不懼重頭再來,坦然面對著生命的重啟和再生。這組詩呈現出特有的冷峻和孤傲的氣質。
顧艷的詩歌也不斷回溯女性的的前世今生,深入到歷史的場景中探尋女性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古堡》《火焰》十分典型地體現出對女性生命源頭的追溯,并且在這個追溯的過程中。“我從傳說中來到這里/以女性沉思的姿態”,古堡見證了多少女性的故事,當詩人作為女性中的“一個”遇到古堡時,便似乎遇到了無數個和自己有著共同性別的姐妹們。因此,古堡恰似親切的可以聆聽我傾訴的長者,女性悲凄的憂傷的故事都一一被古堡撞見。輪到“我”出現時候,那是“我繞過九曲十八彎”才得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新女性”的時刻,歷史中的女性的悲傷的故事皆已成為過去,而這位新女性則有著自己堅定的決心和步伐,詩歌以女性中的“這一個”與眾多女性展開一種對話,消逝在歷史云煙中的眾多女性身影剎那間似乎紛至沓來。一幅女性沉默而又凄美的命運圖譜呼之欲出。《雕塑》《歌唱》等詩也呈現出對不屈女性的贊頌。
二、隱秘情感的燭照與精神世界的發掘
顧艷詩歌充滿著對個體隱秘情感的燭照和對靈魂奧秘的洞悉。和瑣屑的雜亂的日常生活題材比較而言,顧艷更注重對精神生活的投注,注重精神上的自我世界的構建。在系列散文中,顧艷都表達了她對自身精神蛻變的焦渴和希冀,并在實際行動上呈現著自身對現實物質化世界的超越。顧艷喜歡舞劍,她注重對古典歷史文化和藝術美的捕捉。從個人的志趣上說,對古典藝術美的追求,是顧艷詩歌創作的一種動力,也影響著詩歌題材的選擇。這種力量也是支撐顧艷現實生活的重要依賴。但這種徹底和純粹的追求,并不一定與周圍的聲音合拍。在上世紀90年代乃至新世紀初,中國大陸文壇事實上充滿著一種市場化的喧鬧、炫技,乃至對金錢和性的媚俗。正如羅振亞所述:“因國情與現實限制,大多詩人不深掘人性和靈魂究竟,進入形而上境界,同時民族的實踐理性精神使詩人難以滋生非理性的虛無荒誕和自我擴張”。可是,外部世界的這一切喧鬧,對顧艷來說,似乎都不存在一般,她只管投身于自己所熱衷的精神試煉和文字經營之中。這種追求帶有著宗教般的虔誠,也昭示著顧艷面對藝術的最大真誠,這是“向傳統的召喚和回歸”。對精神之豐盈與健美的倚重,使其接近老莊哲學對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呵護。
顧艷詩歌的另一主題在于表達她對生活與世界的愛與熱望。在手法上,詩人有意識與靈魂展開一場場對話。借助于不斷回訪和反思的能力,她不斷對自我進行反芻式思考,鮮明的主體意識不被現實蠶食和吞沒。在對話之中,詩人嘗試洞悉靈魂的繾倦多姿,也即透析靈魂本身的復雜癥候,進而為靈魂尋找更好的安頓居所。詩人渴望將獨立的精神化為個體活著的支撐和底座,于是即便身處于焦灼和局促的現實生活中,她仍能對鏡自照,從諸多頓悟的時刻和瞬間中,自覺捕獲對生命的寬宥和同情、謙卑和包容。詩歌充滿著她對人類的基本情感諸如愛、恨、孤獨、心靈的存在狀態等主題的系列思考和探析。在一些哲思性的詩篇中,顧艷善于從現實入手,尋找捕獲哲理的碎片,構成對形而上思想的探訪和質詢。在顧艷的詩集之中,《廣場》《思索》兩首詩歌顯然與本章其它詩歌不太一樣,它更具有理性的思辨和哲思的氣韻,詩人巧妙地將這種思辨落實在對思考習慣的自覺遵守上。詩歌語言也干凈整飭,顯示出哲思的深沉和凌厲。《廣場》描述了矗立在廣場中的一個玻璃鋼女神的塑像,她始終“保持锃亮 保持觀察視角”,廣場經歷著時間的沖刷,而“時間偶爾也有裂縫/就像一群野孩子追趕麻雀/唱著失傳的歌謠”,由廣場——時間——歌謠展開的想象的鏈條,自然生發出形而上的深度,對廣場這一空間的凝視遂構成對時間這一無法把握事物的探討。由于這一想象鏈條的引發,玻璃鋼女神的塑像便成為蒼茫時間的見證者。塑像便不僅僅只是一尊塑像,而是具有神一般的威力。她似乎既昭示著遠古的歷史,又掌控著未來,無法把握的時間在她的形象中,獲得了一種物質化的聚焦和凸顯。詩歌最后寫道:“唯有玻璃鋼女神如水晶浴罩里的美人/使人們回憶起廣場/掠過歷史和傳奇的聲音”。由此,玻璃鋼女神塑像便成了抵抗歲月流逝的一種可視化物件。看到她,似乎便看到了時間的不舍晝夜的無情流逝,也似乎看到了時間本身的樣貌。而《思索》一詩則呈現出詩人對思考的親近,思考可以抵達和靠近本質,思考因此構成一種智慧,詩人篤信不能放棄對思考的追逐。“任何力量都來自思索后的眼前一亮/任何事物都通向辯證的上帝”,詩句體現出思考的意義。思考也是對常規習慣的打破,因此,“我愿意在一場透明的雨中演講/在時間面前我慶幸是一個思索的人”,思索賦予詩人再生的可能,對習慣的默認固然是對現實秩序的一種遵守,但是打破常規習慣則意味著一種新的意義元素的植入。由此,詩人在思索中聽到內心在呼喊:“救救虛無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正是對思索的敬畏和追求,才促使詩人發出此類吶喊,這是對鐵板一塊的刻板化生存的一種抵抗,也是向流俗和虛無展開決戰的心聲吐露。
女性的情感伴隨著一部女性歷史的發展呈現出復雜的曲線,女性天然具備對世界的感知和對秩序的質疑的超能力,這使得女性比男性要更能夠體味和蠡測情感的隱秘和靈魂的悸動。詩人翟永明在《女人》中描述過女人的強大:“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創造黑暗使人類幸免于難。”[5]女性身體具備孕育生命的能力,像地母蓋亞一樣先天具備觸摸宇宙空間變化的能力。故而,女性情感的質地豐富多彩。在顧艷這里,對靈魂的深思和不懈的追求,體現在她對具有書卷氣、思考力的女性形象的構建上。這是一個不甘于平凡的女子,同時也是一個喜歡思考的女性。
顧艷關注到女性情感世界中一片隱秘的晦暗未明的區域,這片區域除了布滿憂傷、疼痛的質地和色彩之外,也表征著女性的力量和存在的真相。詩句“我的思想錚錚作響/像一只鳥銜著自己羽毛飛翔”,表現出的是主體深陷孤絕境地之中的一種力量。最讓人吃驚的地方在于,詩歌在悲愴情調中表達對人類孤獨處境的發現,這是對人類普遍性處境的發現。《秋季》組詩表現了對人類孤絕處境的深刻理解:
“我們因孤獨而相依
又因孤獨而獨處
這是我們的存在方式
命中之弦
一種無法改變的狀態”
詩歌呈現出了詩人對孤獨的透徹的理解。兩個相愛的人,即便心靈相通,卻也不一定能夠在一起,只因每個個體的孤獨是恒常的,長相廝守終究是暫時性策略。對個體而言,孤獨才是最真實的存在方式和狀態。這種對人生的帶有濃郁的宿命式的透徹體驗,顯然是顧艷對個體生命窘境的深刻體察,是對人的普遍性處境的一種發現,這種發現與叔本華對人生本質的認識具有相似性:“只有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才可以完全成為自己”。顧艷詩歌中充滿著傷痛、孤獨,也充滿了堅韌不拔和對生活的毅力。在《紅鳥》一組詩中,詩人表達了對至高無上的靈魂的追逐。紅鳥是靈魂之鳥,“無人能夠對話的局面/是靈魂掉入深潭的境界/一根救命稻草/支撐我全部重量”,這些詩歌形象地體現出紅鳥對靈魂的執著 追求。顧艷在詩歌中說:
“詩歌是我血液中的血液
晦澀時節
它是撕裂白晝的鷹”
可以看出,與靈魂的對話不僅實現了詩人對精神身份的確認,還使其在現實世界之中找到了一種生存的力量。它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靈魂被燭照,顯然是最寶貴也最為難得的存在。這一點在顧艷的生命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詩歌則成為表達此種心志的工具和載體。
組詩《熱愛生活》呈現出了生活的多種樣態和面貌,這組詩歌共15首,都是短詩,從主題上可以分為哲理詩、愛情詩。哲理詩表現了詩人渴望理解事物和生活本身的強烈沖動。諸如《八月》中聯想到詩人馬拉美,表達詩人渴望與后者一樣回到事物本身的情感沖動;《保衛愛情》《西窗》《隔海相望》《與自己交談》《老街》表達的是詩人對愛情的細密審視。
三、異域抒懷與風景再現
顧艷生在杭州,之后又旅居美國,在熟悉西方現代性與異域文明之后,她更具備一種“文化間性”思維,自覺地運用對照視域和對比思維,不斷省思中西方歷史和文化景觀的復雜關系。于是,詩歌中的風景和情感結構不再單一,而是充滿了多元、互滲、互補的效果。對于顧艷這樣的新華人來說,故鄉概念不再是鄉愁的凝聚和濃縮,相反,故鄉作為一種雄厚的支撐力量和關鍵背景,在其詩歌中呈現著故鄉對新華人的吸引作用。這也反映了政治實體對個體意義和價值的成全和完善。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跨國開放程度的加大,國人在地理空間上的“去—留—回”容易而便捷,遷徙和移動的頻次增加,故鄉和異鄉的情感聯結也變得日常化。這種情感結構上的嬗變及其現實,使得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文作家在情感空間的構建上,也呈現出新的轉向。日籍華文作家黑孩便在短篇小說《萬有引力》中呈現情感經由互聯網微信的傳播,使得故鄉中國和東京的距離感消失了。這極大地改寫了華人華僑的空間想象。回想早期北美華人華僑筆下無不充斥著流浪的痛苦,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查建英的《到美國去,到美國去》無不彌漫著美國的現代化奇觀給中國留學生帶來的震撼和休克。而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人,顯然有了更多的余裕和自信去關注精神空間的成長和變化。于是,書寫題材領域取而代之的是華人對在地性的適應和融入,并以更加主動的姿態自覺去審視中國和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纏繞。這一點正如張福貴所言:“華文文學的全部時空存在,是以中華民族和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域和族群文化的融匯為基礎的。”同在美國的新華人盧新華就將筆觸聚焦了,曾曉文則將書寫的中心對準了華人的在地化情感,而陳謙則在華人故事中窺視一種全人類的共在性和共融性命題。
在這些詩歌的周邊體裁中,可以看到華人書寫的一個巨大的轉向,而顧艷顯然對這個變化有著更為清醒的認知。其詩歌中不僅布滿海洋、飛翔、遷徙等標識空間流動性詞匯和意象,更是充滿著情感的隱喻系統中識別。這些詞匯構成的意象群落源自于中國和美國兩個空間。詩人有意識地挖掘不同空間所裹挾的涵義。以藝術的統覺,挖掘繪畫、音樂、舞蹈、劍術等不同藝術之間的互通雜糅關系;有時將植物景觀也寫進詩歌之中,來寄托愁思別緒,諸如紅玫瑰、白樺林、空藤椅、無名花、水稻等。
在第三輯“旅途”、第四輯“風景”篇中,也可以看到她對中國不同地區風景和事物的關注和留戀,對不同地區故事的發掘和梳理,更有對海外其他國家景觀以及旅行途中的獨特發現。在“旅途”篇中,詩人深入中國的大西北和大西南,對青藏高原、樓蘭、喜馬拉雅、克拉瑪依、巴顏喀拉、絲綢之路、陰山下、敦煌、楚雄等這些常見于地理場域進行了游歷,并將這些地理空間與今天進行一種記憶拼接和串聯,進而呈現古老的中國記憶和精神在大地上的流轉和銘刻。
在詩歌中,詩人懷揣對中國古典文明和神圣土地的敬畏和新奇,用心打量這片神奇的土地,“我的眼里淌出淚水/說不清淚為誰而流/一汩一汩/泛濫成雅魯藏布江”(《喜馬拉雅》),可以說這是詩人內心情感涌動的自覺表達。在詩歌中,詩人又關注到當地的民俗和故事,諸如走過絲綢之路的商旅、手骨舞、駝鈴、草原奶酒、青稞酒、賽馬號子、佛教經文、石窟、刺繡等密集的西部文化符號。
《代友人書——回故鄉》主要書寫的是內蒙古草原風景,抒發詩人對祖國西北大草原的熱愛,并將這種熱愛融匯在對歷史的思考之中。《巴彥呼碩》中嵌入了“敖包相會”這一流傳久遠的典故;在《孤獨的騎手》中,一種自由奔騰的情感宣泄出來:“我縱馬揚鞭 塵世遠去/與漲潮的瀚海靈犀相通 靈魂飄入宇宙”。在詩歌中,顧艷隨時都能夠照顧到個體的靈魂,詩歌充滿了對靈魂自由飛翔姿態的贊頌。這組詩是源自于詩人在欣賞友人興安的攝影圖片之后寫出來的,如果不是在題記中知道這是源自于繪畫,讀者會有一種親臨蒙古草原的感覺。
《賽馬》寫出了一種朝氣蓬勃的氣勢,將草原人的陽剛與速度之美呈現出來。巴彥呼碩、那大慕、蒙古包、蒙古大草原等宏闊的意象組構成北方中國一幅粗獷而又原始美麗的風景畫。顯示出詩人從圖像藝術到文字藝術的強大的轉換生成能力。
顧艷的旅游類詩篇注重對歷史和人文價值的挖掘,并在對地理景觀的書寫中凸顯個體的情感。《組詩:我在莫干山上》表達詩人對浙江湖州德清縣莫干山美的贊頌和對歷史的深思,這種深思使得莫干山有了歷史的重量感和人文含量。莫干山、蘆花蕩、別墅、劍池瀑布、蔭山街、美人茶、塔山等地理媒介都在詩歌中得到了傳神精細的描繪,而其本身也是一種文化記憶符號,傳遞著歷史的回聲和身份認同。“通過共同的符號,個人分享一個共同的記憶和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
在組詩《歲月之河》中,《致李白》《杜甫草堂》等詩篇書寫詩人與古代詩人的相遇和對話,呈現詩人與古代文人的心靈相通,表達對古人高潔情操和志趣的承襲。此外,詩人也不斷穿越中外歷史之中,對19世紀以來經典作家進行對話與憑吊。在《獵人筆記》一詩中,詩人描述自己閱讀屠格涅夫同名散文集《獵人筆記》的感受,“今夜你依舊是獵人/我入迷地翻閱/宛如束手就擒”,詩人沉浸在對屠格涅夫筆記的閱讀之中,宛如束手就擒的動物;在《死屋手記》中,詩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遇,贊美這位“解剖黑暗世紀的內臟”的作家。《古戰場》中有一種悠久的歷史之音在回蕩,“我”與先人展開了對話,對古代的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進行了剖析;《中原之原》抒發對秦漢之際出現的民族間的殺戮事件的感慨,《碑林》中的絲綢、青銅、古箏,都充滿了西北古長安的風貌。《組詩:在香港》則著重描繪對香港歷史的追思,其間交織著對女作家蕭紅的懷念,從香港碼頭集裝箱、溫泉、大海、高山滑草場等地理景觀中發掘出一種歷史感和滄桑感。《組詩:梅關古驛道》中主要對南華寺、丹霞山、梅關古驛道、牡丹亭、郴州蘇仙嶺展開了一種詩意的書寫,詩人的足跡深入到這些區域,思維與文字也開始撬開歷史的閘門,讓原本的歷史人物和故事開始生動鮮活起來。
詩集中也不乏對域外旅行題材的關注,這一類詩歌也可以被稱之為“旅行文學”,域外旅行文學本身包含著文化的碰撞和交匯。黃麗娟便指出:“旅行的形式和意義除了指實際的遠足,還賦有抽象形式,甚至隱喻為想象的各種生命活動,如生命的旅程、知識的歷程、頭腦的旅行等。”這類詩歌顯示著詩人審美視野向異域的延伸和鋪展,呈現著詩人對他者文化的感受和態度。
《組詩:某個秋天》是對日本旅行的游記匯總,詩人用詩歌形式記錄了日本東京、奈良、大阪、京都、箱根等地的風景和民俗。《組詩:火奴魯魯》則將筆觸對準了美國的夏威夷、珍珠港等地。《組詩:面對新現實》這一組詩歌,主要表現了詩人對“自我囚禁”式生活的思考。在這期間,詩人經受了與家人、朋友的分離,見證了生命的死亡,甚至眼睜睜看著友人被瘟疫所吞噬,詩歌表現了瘟疫大流行帶來的創傷記憶,并引發了詩人對文明的更深刻的思辯。
詩集《風和裙裾穿過蒼穹》在主題上,愛情、哲理、旅游、漂泊等主題比較明晰,題材雖然龐雜,但是主題按照五輯做出了一定的統籌,比較容易辨認。在在詩歌語言上,這些詩句因使用了反邏輯等手法,使得詩歌主題比較明晰。一些詩句甚至在詩境的創構方面,顯示出奇特的稟賦。尤為珍貴的是,詩人特別注重捕捉靈魂頓悟的時刻。在《獻給父親的詩》等詩歌中,時有類似于警句的詩句出現:“從前的磨難 是怎樣撕裂著我們的平靜?”將一個趟過歲月之河的年邁的父親形象成功塑造出來。
顧艷比較注重意象的使用,在情感表現和哲思的醞釀萃取中重視獨特意象的生成,進而將這種意象運用在詩歌創作中。吳曉曾經指出:“一般語言只需要呈現邏輯的有序性,而意象則相反,可以或者說需要打破語言邏輯及理性邏輯的規范,追蹤‘情感邏輯’與‘想象力邏輯’的發展而不斷推進。”龐德也說:“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語言的道”,《瓢羹》中寫父母用過的瓢羹,“宛如風雨飄搖的古宅 質地堅韌有力”,比喻恰如其分,代表著詩人對父母一代人的情感經驗的熟稔和懷念,而對瓢羹這類舊事物的追思和懷念也表明詩人具備將現實事物進行“情感邏輯”提煉的審美能力。《生命》中的意象十分別致:“我輕抵冰冷石壁/宛如閃著磷光的魚/靈魂遠游,疼痛像一輛救護車/呼嘯駛過人群”, 這里的修辭賦予疼痛以具象,短小精悍,在視覺上可觀可見,是很成功的意象運用。這些都是詩人將經驗、才學、天賦融為一體進而生成藝術能力的體現。
顧艷的詩歌對現實進行了強烈關注,這種現實感使得詩歌總是輝映著主體的精神氣質,呈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詩歌將個體生命感知視域和家國歷史視域進行了融合,于是,她的詩歌具有少見的氣勢和力度。無論是在敘事詩還是在抒情詩中,她的詩歌強調及物性,在關注現實、勾勒現實事件的基礎之上,讓詩歌言之有物,拒絕做無意義的抒情。由此,我們看到《組詩:面對新現實》等對現實問題的關懷關切,對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所持有的寬容開放的態度。因此,這部詩集是顧艷詩歌走向成熟的標志。

作者簡介:張益偉(1980- )男,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