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誰意匠慘淡經營中
——王曉波詩讀后
作者:劉荒田
我在青春和中年,狂熱地寫詩20余年,后來厭膩于自己無詩思時的焦慮,改寫散文隨筆,但讀詩已成習慣。從去年起,微信上王曉波的詩,多次引起我的興趣。開始于這樣的美妙偶遇——一首短章,篇名《菩薩》,無意間“刷到”,咦,有意思!不動神色,卻內勁逼人,不曾注意作者,因為那不重要。瞬息間的審美愉悅,一如漫步林間,悠然回頭,一輪明月剪影般貼在柳條之上。從此,我喜歡上了這位有韌勁,有才氣,有根底的詩人。
讀王曉波詩多了,遂琢磨:為什么喜歡?答案是現(xiàn)成的——感人。當今詩叢蕪雜,有讀了惡心的詩,如矯飾的,如得意洋洋地拍馬屁的;有干巴巴的詩,讀了替作者著急的。但王曉波的詩,閱讀的反應常常是這樣的:先是“正中下懷”的“知心”之感,須稍加沉吟,體味,接下來,方是后勁綿長的感動,有時候,要賠上幾滴不怎么體面的老淚。
王曉波的詩歌以“深情”著。或問,詩必以情感人,現(xiàn)代詩難道有例外嗎?答曰,有是有的,如著重于諷喻的詩,宣揚哲理的詩。王曉波詩歌的精彩篇什,乃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所擎的一顆渾圓露珠,是以被擬物化、擬人化的意象浸泡的醇酒,是回甘綿延不絕的上好橄欖。
大略而言,王曉波的詩歌的“情”,具有以下特點。
一曰:飽滿
“情”之為詩的血液,飽滿才具震撼人心的力度。情感干癟,疲軟,蒼白,詩境難以推進,詩眼難以呈現(xiàn)。
且看《愛回來過》:
再美的鮮花也會凋零
再美的青春也會老去
再美的影劇也會結局
可是愛說
在你累了 在時光停滯
神思空白 無言的時刻
風說
愛跑得比飄浮的葉子快
愛回來過
愛說 你如她一般年輕
愛說 她回來過
愛說 你如信仰一般年輕
在黃昏 在黃葉
倦意飄蕩的一刻
在人們感到
生命如白開水
一般 涼時
愛說 她回來過
有緣的人 總會遇見
愛回來過
我想
你定如她一般美好
具體而言,這是對一場早已消逝的戀愛的憑吊;普泛地說,是對世間一切必然被時間消解的愛戀的挽歌。復調的詠嘆,一路散發(fā)滄桑感。人間有眾多的“必然”——鮮花凋零,青春老去,影劇落幕,好在總歸有不復存活的“愛”的撫慰——它“回來過”。其實,愛不曾老去,它“跑得比漂浮的葉子快”,依然如“她”,如“信仰”“一般年輕”。它在你厭倦了“白開水”般的生命時歸來,告訴你:有緣的人,總會遇見。我設想,以磁性的嗓子,向失戀者低聲朗誦這一首圓潤的詩篇時,對方是會靠著“愛”的肩膀,喃喃道:是啊,有過就是永恒,“你定如她一般美好”的。
再看《新月》,場景是兩個“分別”,第一個:外出打工八、九年的中年人,即將離開山村。詩里的祖父或祖母沒有叨念,“只有一滴渾濁的老淚/落入我的行囊”。正是這一滴淚,激勵打工者,“再苦再累也撐挺過去”。第二個:老人家來城里看望兒子和孫女,明天就要離開,“抱著才滿周歲的孫兒/你用粗拙的手/撫愛著她幼嫩的臉/望著我/心疼的一句/‘在外奔忙,別耽擱了孫兒!’”“上有老,下有小”的打工者這般感慨:“望著你漸彎的腰背/真害怕孫兒的體重/把它壓成半彎的新月”。讀到這里,誰不被這“新月”感動?厚如土地一般的親情,并不劍拔弩張,卻足以激發(fā)你心弦強烈的共鳴。可見,情的飽滿,并非外在的張揚,而是內斂的詩質。
二曰:別致
且看《菩薩》:
鄉(xiāng)間千年傳說,到禪城祖廟祈福
能給五行缺水的人添福消災
返鄉(xiāng)前,母親誠心去了一趟祖廟
添了香油請了開光佛珠
念珠至今在我手腕,已近十年
穿連念珠的繩子斷了數(shù)次
每次我將這念珠串起佩戴手腕
總覺自己被一尊菩薩攙扶
這是匠心獨運的妙品。母親聽說“開光佛珠”能夠給五行缺水的兒子添福消災,就去佛山祖廟“添了香油””“請了一串”。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詩人每天戴著,“穿連念珠的繩子斷了數(shù)次”。前面的平鋪直敘,是為感情的洪水“筑壩”,最后兩句才是肆意的奔瀉:“每次我將這念珠串起佩戴手腕/總覺自己被一尊菩薩攙扶”。念珠在手腕,菩薩在心。“攙扶”詩人的豈止是慈悲的菩薩?難道不是永恒的母愛?
“具體”的詩固然別出心裁,概括性較強的詩,因被人寫了千萬遍,出新更難,詩人也舉重若輕。《傳說》是歌頌普遍的愛情的佳作。
首先列舉古典的愛情傳說:“哪年哪月/那個桂子飄香的牽手晨曦/那個荷香渺渺油桐傘下的午后/那個花燈中煙火里的元宵 /那個石頭記里的西廂往事/那個死與生又生與死/那個打不成又解不開的結”。眾多感動了一代代人的不朽之愛,化作石頭,“在江邊守望千年的一個傳說”,傳說望不到頭,盼不了,望不見,因其太古老,太縹緲,也太豐富。好在,詩人終于頓悟:“望得見/盼不了/化蝶雙飛的前塵往事”,相遇只在“無心”之間,毋論有緣與否,均須“千里尋覓”。愛若不艱難,不遙遠,怎么配得起詩人的至情詠嘆?最后收官:“剎那的思緒如電閃/現(xiàn)世的我/驚疑前世/一個個遙遠的愛情傳說。”沒有判斷,沒有點題,全詩所道,是尋覓的過程。我被它牽引著,進入對亙古的愛情的思考,完成一次祭奠。
三曰:余韻
情感的筆酣墨飽,不等于一覽無余。好詩必須經得起咀嚼肌。讀者的回味,是作者殫精竭慮的勞作之后的接力,而“橄欖”的提供者,是詩人。
王曉波的詩,重節(jié)制,點到即止,所以有后勁。 這方面,意象密集,張力彌滿,為環(huán)保而吶喊的長詩《雨殤》可算代表作。
慘淡經營的短章亦然,且隨手舉《江南》:
江南,多荷多蓮
荷葉田田倚天碧
總是錯把每朵紅蓮
看成伊,羞紅的笑臉
又把隨風的那朵白蓮
看成伊,盈盈的背影
多蜻蜓,多蝴蝶
又多燕子的江南
再仔細也分不清哪只是伊
好想,問一問
那飄逸的風箏
伊卻纏著那根繩線不放手
有古詩《江南可采蓮》和余光中名作《蓮的聯(lián)想》的影子,然而并非陳陳相因,它是詩人的創(chuàng)造。伊人出現(xiàn)在蓮的江南,教詩人犯了糊涂,把每朵紅蓮,認作她的笑臉;把每朵白蓮,看作她的背影。那么多的蜻蜓,燕子和蝴蝶,到底哪一只是伊?詩人欲發(fā)問之際,只見她在放“飄逸的風箏”,“纏著那根繩線不放手”。詩到這里,戛然而止。“線”指向什么?她對任何人好奇的凝視不在乎嗎?她的心另有所向,她別有寄托嗎?隨你發(fā)揮。詩人只表現(xiàn)美麗女孩在江南的姿態(tài)。
至此,想起木心詩《失去的氛圍》的結尾:
“失去了許多人
失去了許多物
失去了一個又一個氛圍”
遂以為,詩人王曉波,可以效放達而自由的魏晉名士,對失去了眾多真摯情感的人間宣告:
情之所鐘,正在我輩!

(作者簡介:劉荒田,美籍華人,著名散文家、詩人,美國華文文藝界協(xié)會第四屆會長,1948年出生于廣東省臺山水步,1980年移居美國舊金山,現(xiàn)已出版數(shù)十部散文隨筆集和詩集。曾先后在大陸、臺灣獲得4次詩歌獎;2009年以《劉荒田美國筆記》一書獲首屆“中山杯”全球華僑文學獎散文類“最佳作品獎”。他為海內外報紙寫專欄,成文三四千篇。他的藝術觸角所伸進的地方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及,遍及美華社會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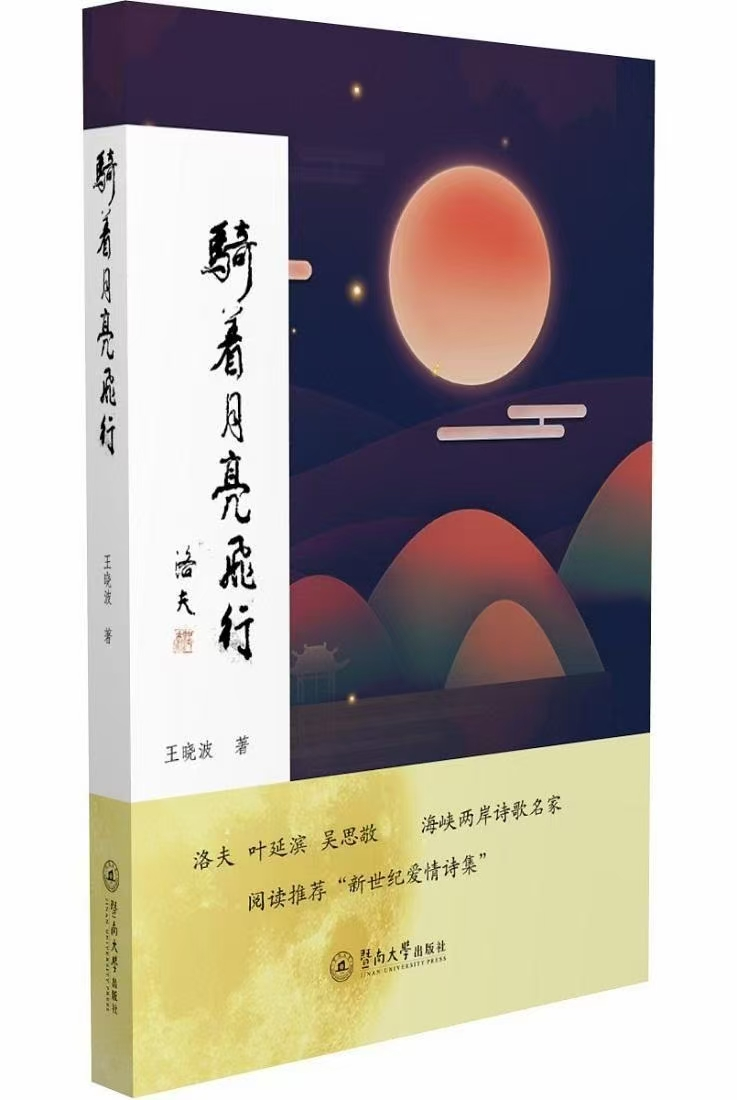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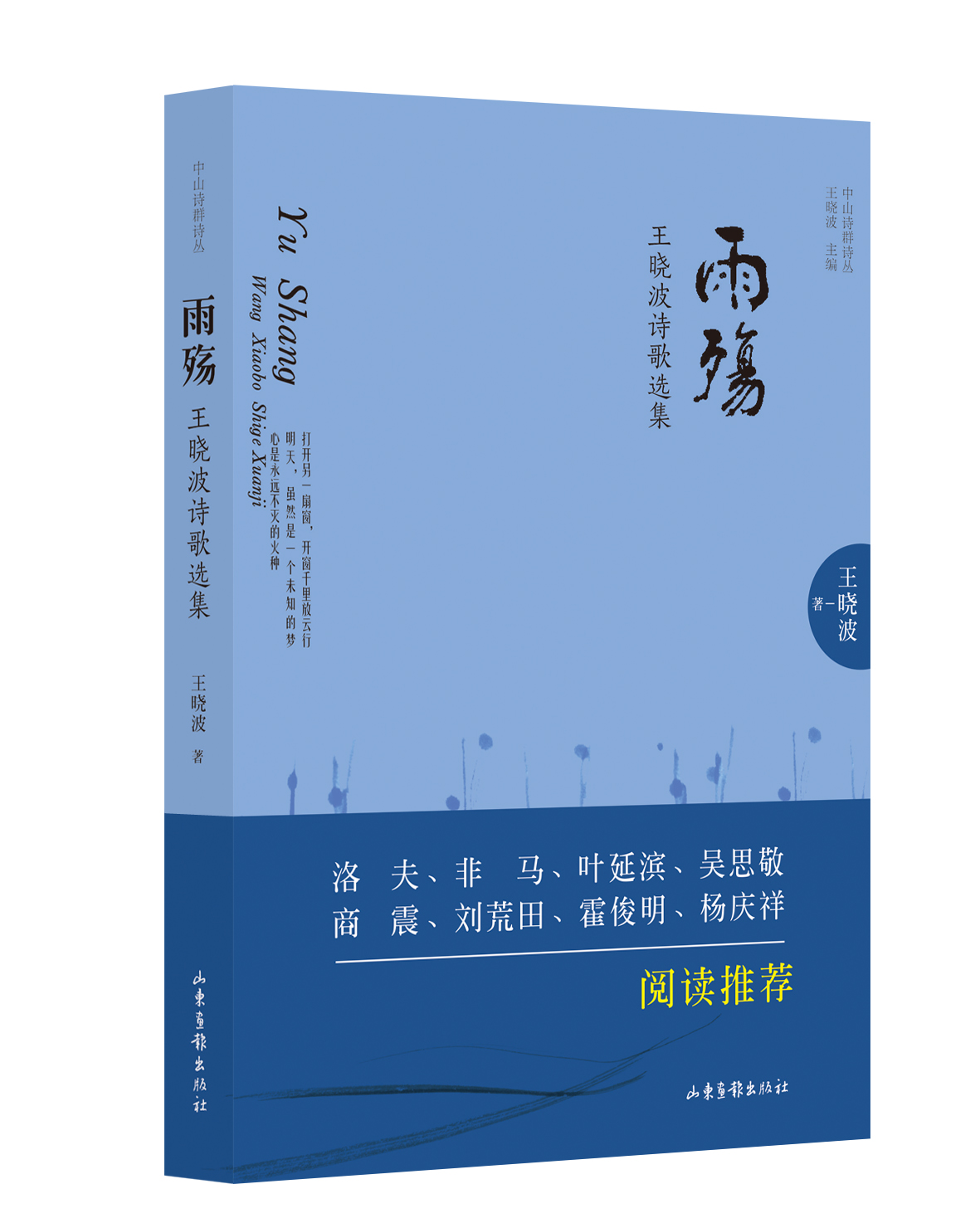
(王曉波,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山市詩歌學會主席、中山市文聯(lián)主席團成員、《香山詩刊》主編。著有《山河壯闊》《騎著月亮飛行》《雨殤》等5部;主編《那一樹花開》《詩“歌”中山》《中山現(xiàn)代詩選》等13部;曾獲人民日報作品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中山市優(yōu)秀精神文明產品獎、中山文藝獎、香山文學獎一等獎等獎項。其詩學評論《吹掉泡沫還詩歌以亮麗》(載《人民日報》2002年6月11日)和《不敢茍同的錯誤詩學》(載《作品與爭鳴》2003年7月)曾受到廣泛關注;詩歌作品載《人民文學》《詩刊》《中國作家》《青年文摘》《詩選刊》等刊物;入選《中國詩歌選》《中國詩歌年度選》《中國新詩日歷》《中國愛情詩精選》等選本。)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