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science Practi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ce Dimensions of Natural Ecological Poetry——Review of Selected New Ecological Geoscience Poems by Hu Hongshuan / Zhai Meirong
地學(xué)實(shí)踐:自然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維度的重構(gòu)
——評(píng)胡紅拴《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新作選》
◎翟美榮
摘 要: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人文交流的國際化進(jìn)程及生產(chǎn)發(fā)展理念的轉(zhuǎn)變,越來越多的人關(guān)注生態(tài)地學(xué)與自然生態(tài)詩歌創(chuàng)作的在場(chǎng)表達(dá)。以胡紅拴《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新作選》為例,以“在場(chǎng)”理論為核心,觀察和分析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的哲理意味、生態(tài)地學(xué)的覺醒與轉(zhuǎn)向,以及生態(tài)地學(xué)實(shí)踐三個(gè)維度的重構(gòu)。
關(guān)鍵詞:胡紅拴;地學(xué)實(shí)踐;詩歌在場(chǎng);生態(tài)詩歌;天人合一
作者簡(jiǎn)介:翟美榮,女,1980年出生,河南周口人,博士,佛山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教師,研究方向?yàn)樯鷳B(tài)文明與中國生態(tài)文化。
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是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胡紅拴是國內(nèi)最早開始倡導(dǎo)與創(chuàng)作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的詩人之一,現(xiàn)任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詩歌委主任,中國林業(yè)生態(tài)作家協(xié)會(huì)學(xué)術(shù)指導(dǎo),《新華文學(xué)》主編,《中國詩界》副主編,作品散見于《人民日?qǐng)?bào)》《光明日?qǐng)?bào)》《解放軍報(bào)》《文藝報(bào)》《詩刊》《中國作家》《小說選刊》《人民政協(xié)報(bào)》《北京文學(xué)》《花城》《南方日?qǐng)?bào)》《羊城晚報(bào)》《新民晚報(bào)》等,出版《山道》《地球語匯》等各類書籍 76部,主編各類文化叢書百余冊(cè),曾獲中國新詩百年百名最具影響力詩人獎(jiǎng)、中國長(zhǎng)詩獎(jiǎng)最佳成就獎(jiǎng)、寶石文學(xué)獎(jiǎng)等,作品譯成英、法、德、日、西班牙、尼泊爾等文字在海內(nèi)外出版發(fā)行。近期,筆者拜讀了《中文學(xué)刊》2024年第3期“詩歌評(píng)論”專欄之《從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談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在場(chǎng)寫作》和《胡紅拴詩歌近作》,激發(fā)筆者嘗試對(duì)胡紅拴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創(chuàng)作在場(chǎng)觀及其作品進(jìn)行分析,以助了解胡紅拴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的創(chuàng)作風(fēng)貌與境界,同時(shí)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種路徑。
一、“在場(chǎng)性”: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創(chuàng)作的哲理分析
胡紅拴指出:中國自然資源作家應(yīng)該將自然生態(tài)詩歌研究與創(chuàng)作的重點(diǎn)放在自然資源與人們對(duì)自然生態(tài)的“在場(chǎng)感知”上來①,這正是新時(shí)代構(gòu)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核心要義。安德魯·薩克也主張世界文學(xué)和全球化研究要建立在新批判文學(xué)地理學(xué)融合基礎(chǔ)上的新理論視野,深入反思對(duì)話文本、空間時(shí)間、哲學(xué)反思等各維度的關(guān)系,呼吁“在地”思考。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在場(chǎng)”性是生態(tài)地學(xué)表達(dá)的哲學(xué)根基,自然生態(tài)詩歌以其自然生態(tài)詩意和生態(tài)歸屬的特性反思人類中心主義視域下的生態(tài)危機(jī),抒發(fā)大地和人文千絲萬縷的情結(jié),為重建人與大自然融合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觀、為現(xiàn)代人探尋生態(tài)文明的新方向新境界提供實(shí)踐的信念和力量。如《于昆明圓通寺》:千二百年,因果/亦是因緣/螺峰山下,素花/染香光明的山原/也有滇池的蓮花為伴/翠湖的碧波,漣漪/洗心,無限循環(huán)/空齋閑語/心空,頓悟/身心的眼識(shí),也許是/心海駐定的禪/面湖而立/欲讀懂水石的文字/驚鴻飛鳥,一瞬間/說透人間。②這首詩通過“螺峰”“蓮花”“碧波”“頓悟”“身心的眼識(shí)”等一個(gè)個(gè)意象的描寫或想象,展現(xiàn)了詩人對(duì)自然與心靈和諧的追求,“一瞬間,說透人間”表達(dá)了對(duì)個(gè)體生命與自然規(guī)律的深刻思考,通過自然與心靈的融合實(shí)現(xiàn)情感與哲理的完美統(tǒng)一,使詩歌具有一種深邃的哲學(xué)內(nèi)涵。
新時(shí)代生態(tài)地學(xué)實(shí)踐主要體現(xiàn)在感官體驗(yàn)、實(shí)踐在場(chǎng)、哲學(xué)反思三重維度重構(gòu)的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寫作,分別從自然物質(zhì)與情感意志、現(xiàn)實(shí)存在與思維模式、人類實(shí)踐與新生態(tài)觀等維度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從人類實(shí)踐與自然生態(tài)良性循環(huán)等視角進(jìn)行生態(tài)詩歌的創(chuàng)作,傳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jià)值理念,如《星云湖上》:一路向南,鐵流/春風(fēng),花,寫著夢(mèng)幻/七甸,江城,孤山,窗鏡中一閃而過/玉溪的琴弦/我也可用楹花的素指撥彈/星云湖上,遙思亙古大地的賽場(chǎng)/高原斷層,河/畫出了湖的模樣/深閨,哪會(huì)掩沒俏麗/灣湖深深/我的釣線,今晚/一定能/釣來月亮③。詩歌題目“星云湖上”本身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達(dá),“春風(fēng)”“花”“江城”“琴弦”自然具象與“夢(mèng)幻”“撥彈”“遙思”“亙古大地”的深情意志彼此融合的詩歌表達(dá),使“我的釣線”在地學(xué)實(shí)踐中“一定能釣來月亮”的理想或抱負(fù)。詩歌在這里不僅令人體驗(yàn)到自然的壯麗與神秘,更在潤(rùn)心無聲中產(chǎn)生對(duì)自然的敬畏和追求美好自然生態(tài)的意愿。自然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寫作使情感、意境、能量不再孤立,而是彼此賦能、相互融合、渾然天成。
二、地學(xué)批判:自然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的覺醒與轉(zhuǎn)向
胡紅拴自然生態(tài)詩詩歌,通過與自然生態(tài)及個(gè)體心靈在場(chǎng)互動(dòng)的寫作方式,實(shí)現(xiàn)在場(chǎng)者心靈上的覺醒,乃至生態(tài)詩歌天人融合的在場(chǎng)轉(zhuǎn)向,其本身就是一種打破機(jī)械自然觀童話般泡沫的獨(dú)特的地學(xué)批判。
其一,自然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的心靈覺醒。面對(duì)生態(tài)危機(jī)、地質(zhì)問題及精神棲息貧瘠等現(xiàn)象,不是提出尖銳的批判,而是通過生態(tài)的感官體驗(yàn)、美的表達(dá)或人文關(guān)聯(lián)進(jìn)行一次次生態(tài)詩歌的在場(chǎng)覺悟或心靈升華,這是胡紅拴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顯著特點(diǎn)和藝術(shù)魅力所在。如《姑蘇盤門》:千五百年,護(hù)城河寫透青天/吳門橋外,禪風(fēng)/也洗田園/二千多年,盤門鐘聲一次次響起/水陸的關(guān)門,字,裝滿了一艘艘河船/古運(yùn)河默默,清流/一曲曲舊事/瑞光塔下步,蓮香的節(jié)拍/何須/多余的意見④。詩中“護(hù)城河寫透青天”“字,裝滿了一艘艘河船”“一曲曲舊事”等意象都在提醒讀者自然景觀、歷史、在場(chǎng)感受是情景相連、身心融合的生態(tài)境界,“何須多余的意見”更是提醒在場(chǎng)者在欣賞古運(yùn)河美景的同時(shí),思考?xì)v史人文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再塑的意義何在,喚醒人們保護(hù)生態(tài)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16世紀(jì)以來的機(jī)械主義自然觀認(rèn)為只要人類認(rèn)識(shí)了大自然的規(guī)律就能控制和征服大自然,從而利用科學(xué)技術(shù)加速推進(jìn)了近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而大自然逐漸演變?yōu)閱适?nèi)在的生命靈性僅供人類利用的客體。中國詩歌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楊克強(qiáng)調(diào),詩歌是靈魂的慰藉,生態(tài)詩歌更要不斷尋求技術(shù)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讓每一個(gè)生命體都能在科學(xué)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中找到心靈的歸宿。
蒂莫西·莫頓的“生態(tài)思維”思想打破自然、行為、科學(xué)、藝術(shù)和文化之間的傳統(tǒng)界限,敦促人類重塑面對(duì)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挑戰(zhàn)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全球變暖”“氣候變化”“生態(tài)危機(jī)”等也引發(fā)生態(tài)詩歌須“以生態(tài)的方式思考”和以生態(tài)在場(chǎng)的表達(dá)方式創(chuàng)作,如《稻田聽秋》:秋分之后/嶺南的晨,總有涼的心雨/驕陽秋瑰/流溪河翻開的書卷,竹影里/竟然寫滿云的詩句/紅蜓與蝴蝶/哪會(huì)錯(cuò)過這難得的熱鬧/一群山雀/也融入風(fēng)家歡聚著的山居/我也來湊湊秋召喚的周末雅集/稻田的香/香過那壇陳釀窖藏的創(chuàng)意/臨河漫步/田埂上呼叫對(duì)歌中的魚蛙/那幅神怡的油畫/青山相酬,一江碧水⑤。這首嶺南秋日頌歌整體而言是意境、心境、哲思覺醒等在場(chǎng)的統(tǒng)一,由“涼的心雨”到“驕陽”“熱鬧”“歡聚”“雅集”,詩人以哲人的形象表述聽秋的感受變化,這變化不是對(duì)秋天碩果的貪戀,而是“青山相酬”、天人彼此賦予“創(chuàng)意”的“心”境升華,令人神往,把美好的青春付諸于這“一江碧水”,達(dá)到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境界。沒有卡遜《寂靜的春天》生態(tài)危機(jī)的吶喊,沒有一字一句的批判和數(shù)據(jù)論證,而是以美好生態(tài)的深情體驗(yàn)與身心感悟來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的偉大覺醒,并賦予生態(tài)地學(xué)新的價(jià)值引領(lǐng),這種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的心靈覺醒,正是生態(tài)地學(xué)批評(píng)給予當(dāng)代人及自然生態(tài)詩歌創(chuàng)作最珍貴的啟示。
其二,自然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天人融合的轉(zhuǎn)向。生態(tài)地學(xué)批判的目的是在自然生態(tài)覺醒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寫作的轉(zhuǎn)向,以解構(gòu)機(jī)械主義自然觀視域下的生態(tài)認(rèn)知、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對(duì)大自然造成的生態(tài)危機(jī)及生態(tài)環(huán)境賦能個(gè)體價(jià)值差距越來越大的危害。阿萊霍·卡彭鐵爾提出見證文學(xué)的生態(tài)擴(kuò)展觀,引發(fā)人們對(duì)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深層反思,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寫作正是見證文學(xué)最為有力的表現(xiàn)形式,它架起了人類與地質(zhì)“因子”之間溝通的橋梁,如《在山塘評(píng)彈昆曲館聽昆曲》更能體現(xiàn)這種生態(tài)在場(chǎng)寫作的轉(zhuǎn)向:七里山塘,路/史海上繁華的工商/通天一理,責(zé)任把民生放在心上/想起了千多年前的醉吟先生/那些記憶,那些詩外的風(fēng)采/也可唱誦,融入/億萬蒼生的血漿/運(yùn)河之外,山塘街樓/蘭芽曲苑/游園,牡丹亭秀/戲文的記敘/不僅僅只是停步在那優(yōu)美的唱腔/遙觀虎丘塔影/劍池的風(fēng),清洗的何止是七里朗朗乾坤/我看到/一個(gè)個(gè),挺拔/偉岸的脊梁⑥。這里的“工商”“民生”“億萬蒼生”“朗朗乾坤”“偉岸的脊梁”等意象,把現(xiàn)代人對(duì)自然寧靜賦能的憂思凝結(jié)成自然生態(tài)的時(shí)代心聲,“一個(gè)個(gè),挺拔偉岸的脊梁”是人民獲得美好生活最堅(jiān)強(qiáng)的依靠,這難道不正是良好生態(tài)環(huán)境最公平最普惠價(jià)值的賦能嗎?
大自然和人類一樣,同樣具備吸引力、向心力和包容力,海德格爾提出“棲居”概念即人作為“存在的守護(hù)者”,人類詩歌語言與自然世界的本真相遇、情感表達(dá)、熱切向往也同樣在證明大自然也是人類心靈的守護(hù)者和最后歸宿,“在場(chǎng)寫作”觀揭露了生態(tài)地學(xué)“在場(chǎng)”的人與自然命運(yùn)休戚的哲學(xué)理念,如《那烏古橋》:地下三分/鐫刻著明清步履足痕的符號(hào)/橋下清流/歲月年輪沉默纏繞/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奔流不息,墨跡/史海長(zhǎng)長(zhǎng)的驛道/古石橋的老石/如佝僂老翁背負(fù)著日月/村頭的老牛/眸光的火把迎接過一個(gè)個(gè)拂曉/榕蔭下翻開舊年的志書/粗瓷里的茶湯/意念里,元公先賢,也曾/這樣品過⑦。詩歌中的“明清”“符號(hào)”“清流”“歲月”“志書”“意念”等一系列文字符號(hào)似乎孤立地串聯(lián)在一起,但詩人通過一個(gè)“品”字,便把歷史與未來、自然與人文、現(xiàn)實(shí)物質(zhì)與意志精神融匯在一起,人物、自然風(fēng)光、歷史、文化、思想等“奔流不息”,在“史海長(zhǎng)長(zhǎng)的驛道”里組成一個(gè)系統(tǒng)的動(dòng)態(tài)的生態(tài)鏈條,為守護(hù)好這個(gè)鏈條,元公先賢有責(zé)任,我們當(dāng)代人更要有擔(dān)當(dāng)。
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寫作不僅隱喻自然環(huán)境問題,更要引發(fā)人類實(shí)踐活動(dòng)對(duì)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關(guān)切,生態(tài)詩歌在場(chǎng)觀認(rèn)為地學(xué)批判的在場(chǎng)轉(zhuǎn)向在于使“環(huán)境的在場(chǎng)”本身成為解決生態(tài)美好之道,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作品要起到賦能心靈感悟、喚醒社會(huì)責(zé)任的作用,讓讀者領(lǐng)悟到天人協(xié)同效應(yīng)更加賦能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和大自然生態(tài)修復(fù)的自予力。如《寫春》:用杏香四兩/掛在枝頭,寫春/也寫我的心情/寫下春綠滿目,當(dāng)然/也不會(huì)忘卻舊年的碩果,以及秋冬積存在腦海的風(fēng)韻/我還是喜歡春的樣子/那氤氳春雨洗過的美態(tài)/常常讓醉的砝碼位移/微醺里發(fā)呆的眸子/成為春的陳釀塑定的作品,有時(shí)/也會(huì)突發(fā)奇想,思想著/如能作一回春的雕像那該多好/那樣,骨骼外的體表就會(huì)開出花來/桃、梨、櫻、杏/海棠,迎春/這樣,醉著的我,也會(huì)成為/春的時(shí)間,和/春,新長(zhǎng)出的文字圖騰⑧。是詩人在寫春天?還是春天在賦能詩人?詩人說“喜歡春的樣子”“雨洗禮過的美態(tài)”,而詩人“微醺”的“眸子”也是春“陳釀塑定的作品”,并期待和“春”一起長(zhǎng)成新的“文字圖騰”,這種詩歌語言的張力和在場(chǎng)體悟似乎汲取了大自然神奇的能量,從而使整個(gè)詩意得到脫胎換骨的升華,在美妙的天人對(duì)話中實(shí)現(xiàn)“作一回春的雕像”的夢(mèng)想,擁抱整個(gè)春天,永遠(yuǎn)充滿生機(jī)和力量。
三、地學(xué)實(shí)踐: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維度的重構(gòu)
胡紅拴生態(tài)詩歌作品以地學(xué)實(shí)踐在場(chǎng)寫作的方式,實(shí)現(xiàn)感官、實(shí)踐和哲學(xué)三個(gè)維度的重構(gòu),從而在生態(tài)文化圣壇上建立一個(gè)人與自然萬物互聯(lián)、彼此感應(yīng)、相互修復(fù)賦能的強(qiáng)大能量場(chǎng),這應(yīng)該是當(dāng)代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創(chuàng)作賦予的時(shí)代使命。
一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感官維度的重構(gòu)。北島說,中國詩歌早就遠(yuǎn)離了大地母親,因無根而貧乏,無緣而虛妄。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感官體驗(yàn)維度的重構(gòu)是通過直接的觀察、體驗(yàn)、感受等方式,撲進(jìn)大自然的懷抱,建立起人的身體和山水草沙、宇宙萬物之間的親密聯(lián)系,在大自然多姿多彩的調(diào)色盤中捕捉人類內(nèi)心世界對(duì)外界變化的認(rèn)知和求索,如《白沙山,白沙湖》:3100 的海拔,天/將云徐徐種下/種下珠翠,也種/仙家的白沙,瑤臺(tái)很近/湖水,成為綠云/埡口的段子/早已醉倒了山的姻親/我也是大山的兒子,心/早已醉了/白沙湖的微醺/我知道了醉入江湖的味道/幾個(gè)醉山的人⑨。詩歌把美麗的自然景觀和人類的視覺、聽覺、感覺和想象糅合在一起,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倍感親密,大自然學(xué)著詩人的樣子“種下云”“種珠翠”“種白沙”,而詩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中心靈得以釋放,喊出“我也是大山的兒子”,非常具有親和力和感染力,令人向往和追求。再如《雙王城林海之夜》:我想借夜鷹的路/在竹林穿行/燈卻了無影蹤/其實(shí),一盞心燈足矣/比如夜月,比如/繁星里那顆眨眼的星蟲/誰能知曉,一把海風(fēng)/也能催熟曙紅/海有浪,林間有月/有踏梯的步子/我的眼前,有一只提著燈盞的螢火蟲⑩。這首生態(tài)詩歌最顯著的特點(diǎn)就是以第一人稱“我”表達(dá)身臨林海之夜的感受,詩人“借夜鷹的路”,懷著好奇心,發(fā)現(xiàn)“踏梯的步子”,最終抵達(dá)“螢火蟲提燈”的頓悟時(shí)刻:“一盞心燈足矣”!這盞燈既來自于大自然又照亮了大自然,同時(shí)還賦予人類一盞心燈而照亮人與自然的希望。這種自然生態(tài)地學(xué)的詩性覺醒,恰如海德格爾所言,是“在世界的黑夜中走向黎明”的林中路。
富有感官體驗(yàn)的生態(tài)詩歌在一定程度上解構(gòu)了現(xiàn)代性發(fā)展造成的人與自然隔離后的孤獨(dú)、焦慮、荒誕、虛無的空缺狀態(tài)和負(fù)面生存體驗(yàn),激發(fā)人們深度走向自然萬物的能動(dòng)性,從而獲得感官體驗(yàn)的幸福感和心靈的歸屬感,如《昨夜我睡在仙云之上》:昨夜醉氧/身心,睡在仙云之上/祥云的腳步聲/意識(shí)外仙家的更聲梆梆/仙峰,原本是仙子的修煉之地/昨夜的我/竟然會(huì)步入瑤臺(tái)的道場(chǎng)/幾顆星,云間里眨眼嬉戲/酣聲里的夢(mèng)/也可信馬由韁/竹海穿梭,星月/當(dāng)然不會(huì)寂寞/何況還有,我這位/對(duì)坐執(zhí)碗的酒客/海飲歡暢?。詩歌直抒胸臆,富氧賦予我“我”超能量,可以安睡在“仙云之上”,還能聽到“祥云的腳步聲”,這里有悅耳的“更聲”和修煉的“瑤臺(tái)”,還可以同“竹海”“星云”“歡暢海飲”,喜悅和自在充滿心間,哪里還會(huì)有“寂寞”呢?華海說,生態(tài)詩歌創(chuàng)作要以真實(shí)、深刻的生態(tài)體驗(yàn)為基礎(chǔ),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寫作觀便實(shí)現(xiàn)了感官體驗(yàn)維度的重構(gòu),實(shí)現(xiàn)了生態(tài)性能量場(chǎng)和詩性心量場(chǎng)的深度交互與融合。
二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實(shí)踐維度的重構(gòu)。詩刊社編輯符力提出,詩歌創(chuàng)作者不能把自己關(guān)在樓房里隨意組織語言,而要切實(shí)地走到社會(huì)生活或自然界中去準(zhǔn)確、精妙地記錄自己的發(fā)現(xiàn)、感受與思想,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實(shí)踐維度的創(chuàng)作就提供一個(gè)在實(shí)踐中追求天然自然與生態(tài)人文和諧統(tǒng)一的全新視角。如《耦園秋記》:再讀耦園/將春的景移到了秋天/天很藍(lán),玉蘭已結(jié)出紅紅的果子/平江運(yùn)河,秋景簇?fù)碇娫瓢愕挠未?我還是喜歡載酒堂的寧靜/也許是血液里還留著昨夜的酒風(fēng)/無俗韻軒,窗外/老石上隱現(xiàn)的條條蒼龍/白墻黛瓦/且蓋上歷史的印鑒/詩家的云朵/就應(yīng)該/云淡風(fēng)輕?。這首詩把“耦園”和“秋景”時(shí)空的流轉(zhuǎn)和詩人“血液”里的“酒風(fēng)”、“詩家的云朵”意象的轉(zhuǎn)換在自然美景和精神家園融合中達(dá)到完美統(tǒng)一,詩人將“春的景移到了秋天”,既表達(dá)了時(shí)光流轉(zhuǎn)的感慨,也賦予了秋天以春天的生機(jī)與希望,這種詩歌在場(chǎng)的實(shí)踐方式使得詩歌表達(dá)更具有溫情、厚度和深意。
尊重自然并回歸自然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實(shí)踐維度重構(gòu)的意義所在,生態(tài)詩歌不再是脫離現(xiàn)實(shí)的虛構(gòu),而是成為人們反思生產(chǎn)、生活方式及觀念轉(zhuǎn)變的現(xiàn)實(shí)力量,并賦能人與自然高質(zhì)量存在的新質(zhì)生產(chǎn)能量,如《古勞水鄉(xiāng)秋行》:一步跨越,秋/還在翻閱著夏的辭典/七百年的行程/一路走來,澤國/已成為嶺南的經(jīng)典/西江右岸,江門/笑擁南海風(fēng)雨的頌詞/古勞水鄉(xiāng),水網(wǎng)的墨/也可演繹醉人的清樂江山/將家安置在圍墩之上/我也用鄉(xiāng)土的畫講述威尼斯的西洋/五邑之地,這里/本就是名滿天下的僑鄉(xiāng)/思想的河流當(dāng)然可以馳騁縱橫/落地生根,客鄉(xiāng)故鄉(xiāng)/四書五經(jīng),自然,也可以越洋/眼前的圍堤似聽到先人勞動(dòng)的號(hào)子/那首鄉(xiāng)音濃重的歌,此刻好像就掛在/太陽之上?。詩人通過“一步跨越”的切身實(shí)踐和“古勞水鄉(xiāng)”“七百年的行程”特殊的地理坐標(biāo)與歷史演進(jìn)賦予生態(tài)地學(xué)強(qiáng)大的能量;“先人勞動(dòng)的號(hào)子”“掛在太陽之上”等意境“演繹醉人的清樂江山”,令人敬仰和效仿。再如《在平江路上》:走一段石板路/陪河水流淌漫游/沿河小路,腳步/丈量著那張發(fā)黃的平江古圖/老橋上的唐宋/傳芳巷外的風(fēng)流/東華橋巷的文字/刻進(jìn)了史海千秋堅(jiān)硬的骨頭/十泉里,一口口古井裝滿滄桑/獅子寺巷,衛(wèi)道觀前/清風(fēng)中分明還可暢讀《蘇州府志》,我來無非是想近聞《姑蘇圖》的蓮香/河街相鄰的古畫/讓浪漫的酒令/拔得了頭籌?。詩歌中的“走”“漫游”“丈量”“暢讀”和“文字”“史海”“清風(fēng)”等元素融合在一起,把生態(tài)演變的動(dòng)態(tài)、歷史文化的能量和人類實(shí)踐印記的變化融合在一起生成一個(gè)“浪漫的酒令”在“平江路上”“拔得了頭籌”,寓意自然與人類命運(yùn)不僅息息相通,還可以彼此影響和相互作用,共同達(dá)到美好的境界。
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表達(dá)通過實(shí)踐維度的連續(xù)性和變化性方式不僅激發(fā)詩人本人的空間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更是賦能任何一個(gè)在場(chǎng)者靈感的頓悟,從而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共處的復(fù)雜關(guān)系,如《山塘街紀(jì)事》:在山塘風(fēng)味店前,心身/體悟著千年前的姑蘇江南樂天的意思/老街石巷,厚重的一部部書卷/繡娘的身影/似乎就在昨夜的夢(mèng)里/素指纖纖/汗雨里的綾羅玉緞/古樟樹外,讀懂了老鋪煙雨的調(diào)子/通貴橋頭,倔犟的琴音/沖出了,那座/古老的戲園?。這首詩通過“老街石巷”“繡娘的身影”“古樟樹”“通貴橋”等連續(xù)性意象勾勒出一幅充滿歷史感的江南畫卷。而“樂天的意思”“讀懂了老鋪煙雨的調(diào)子”等句子意境深遠(yuǎn),將個(gè)人的情感、歷史的厚重和大自然的規(guī)律融匯起來,不僅具有文學(xué)藝術(shù)的沖擊力,更頓生對(duì)自然遺風(fēng)的熱愛和敬畏。再如《漫游沙灣古鎮(zhèn)》江水亦有心境,這奔流不息的沙灣水道/滔聲,一把古琴的獨(dú)奏/擱淺在古鎮(zhèn)夜的曲里/市橋河的夜走出孤獨(dú)八百年了/亦如日月的時(shí)鐘/放肆地走出了自己的韻律/從行舟夜泊到商賈的夜酒/鱗次櫛比的作坊酒樓/宗祠的檀煙,朝著天空的方向/灌醉夜風(fēng)/星辰也顯得格外溫柔/古巷,總愛聽那棵老榕樹的嘮叨/電波拉近的距離/將縮短的歷史書頁輕輕合上/就像大洋彼岸,那個(gè)月下靜聽蟲鳴的老者/借夜月的 wifi,將鄉(xiāng)愁的微信/嵌入往事朦朧的城郭?。“江水亦有心境,這奔流不息的沙灣水道”和“滔聲,一把古琴的獨(dú)奏”等詩句以細(xì)膩的描寫和變化性的意象、擬人化的手法,將江水與滔聲賦予了生命與情感,“古巷,總愛聽那棵老榕樹的嘮叨”和“借夜月的 wifi,將鄉(xiāng)愁的微信嵌入往事朦朧的城郭”等詩句通過對(duì)自然景觀、人文歷史、詩人大膽的想象等各類意象的融匯與新時(shí)代的文明和鄉(xiāng)愁形成強(qiáng)烈的在場(chǎng)情感共鳴,使讀者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時(shí),主動(dòng)打通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彼此賦能的渠道。
三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寫作哲學(xué)維度的重構(gòu)。生態(tài)學(xué)家馬世駿在20世紀(jì)70年代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論點(diǎn),把“整體、協(xié)調(diào)、循環(huán)、再生”看作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整體,這無疑為生態(tài)地學(xué)哲學(xué)維度的重構(gòu)提供一個(gè)全新的思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創(chuàng)作追求人與自然的理想狀態(tài)、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愿景和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如《仙峰的云》:仙峰,當(dāng)然有云/仙家的事兒,何時(shí)/缺過素琴,一座山/琴臺(tái)已拉開幕幔/晨光的畫面,葉露/一串串晨的心魂/夢(mèng)麻的芽/今晨才剛學(xué)會(huì)說話/柳杉的詩句/竟然撩動(dòng)了靄的春心/躬身,向云天深施一禮/也學(xué)學(xué)云的步子,作一個(gè)灑脫之人?。詩人的大膽想象與細(xì)膩表達(dá)形成對(duì)比,加上“仙峰”“瑤臺(tái)”“心魂”“柳杉的詩句”“春心”等充滿詩意的意象,令人情不自禁走進(jìn)這美麗寧靜的仙界,也“作一個(gè)灑脫的人”,在大自然美麗的進(jìn)程中永葆浪漫與自由。再如《桂峰讀溪》:中秋之后/老梅,憋足了勁頭/桂峰山下,清溪/詩寫春秋/觀珠江的一域/看流溪河的源頭/舊年的梅香/舞溪,歲月風(fēng)流/清澈,通透的眸光接過峰巒的太陽/老柿樹下/秋影里的斑駁/朗誦著/山巖深沉的詩句?。“老梅憋足勁頭”“清溪詩寫春秋”“歲月風(fēng)流”“朗誦”等詩句的哲理覺醒時(shí)刻在于覺悟: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當(dāng)“山巖”吟誦出“深沉的詩句”,人與自然便自然而然產(chǎn)生“思想”上的共鳴。
生態(tài)系統(tǒng)學(xué)先驅(qū)?E.P. Odum把“能流”作為生態(tài)學(xué)的哲學(xué)原理是基于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的生態(tài)地學(xué)研究,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在場(chǎng)寫作哲學(xué)維度的重構(gòu)是新時(shí)代地學(xué)覺醒的標(biāo)志。中國生態(tài)地學(xué)詩派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態(tài)哲學(xué)為指導(dǎo),將人與自然看作一個(gè)相互依存的整體,通過詩歌的力量喚醒人們的生態(tài)意識(shí),促使人們采取行動(dòng)修復(fù)生態(tài),如《大運(yùn)河上》:乘一艘畫舫,泛舟/大運(yùn)河上/伍公的護(hù)城河,金戈/早已掛上了太陽的西墻/想起了煙花三月/翠柳也有思緒/思想的野馬/似已連起了浩瀚的海江/鑄劍江南/不僅僅是鑄就一把利刃/試劍石外的風(fēng)景/寫滿了/古道上的一塊塊石板/醉著的斜陽?。這首詩通過“泛舟”“翠柳”“斜陽”與“金戈“思想的野馬”海江”等現(xiàn)實(shí)刻畫與想象意象之間的流轉(zhuǎn),在自然的美麗與脆弱性的鮮明對(duì)比下,更加催人反思權(quán)力意志、資本、市場(chǎng)、歷史等帶給自然生態(tài)的印記或傷痕,引發(fā)讀者對(duì)生態(tài)問題的關(guān)注與反思,積極投入到建設(shè)美麗地球的行列。
吉蓮·克拉克主張生態(tài)詩歌把“深時(shí)”具象化與“人類世”密切聯(lián)系起來,為人們反思人與自然互賴共生的生態(tài)倫理提供有益的啟發(fā),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哲學(xué)維度的在場(chǎng)表達(dá)更多表現(xiàn)在引發(fā)在場(chǎng)者關(guān)注人與自然生態(tài)如何產(chǎn)生良性互動(dòng),從而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如《盤龍古道風(fēng)歌》:午后,驕陽熱烈/海拔 4210米,高原/再畫個(gè)新景詩月/浪漫,不一定都是花前月下/三十余公里,彎道,寫滿六百/冰山上的雪水,流溪里全是詩步/拐的家譜,此書,更是令人拍案叫絕/有道是走完此彎道人生盡是坦途?。詩歌中“熱烈”“新景”“浪漫”“詩步”等以擬人手法來寫景,本身就給人一種天人相依的啟迪,“此書”何以令人“拍案叫絕”?因?yàn)榻璐耍白咄甏藦澋馈保叭松M是坦途”。大自然的“無字書”和人類的“有字書”只有彼此助力,才能相互成就,這是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的哲理性寓意。
結(jié)語
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在場(chǎng)寫作,是積極投身美麗中國建設(shè)的生動(dòng)實(shí)踐。生態(tài)地學(xué)在場(chǎng)維度重構(gòu)的歷史使命,既是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jī)的哲學(xué)反思,更是一場(chǎng)重塑認(rèn)知范式的自然生態(tài)詩歌革命,清遠(yuǎn)生態(tài)詩歌現(xiàn)象和自然生態(tài)詩歌興起,都得益于這種生態(tài)命運(yùn)共同體系統(tǒng)觀的詩學(xué)實(shí)踐活動(dòng)。
注釋:
① 胡紅拴:《從生態(tài)地學(xué)詩歌談自然生態(tài)詩歌的在場(chǎng)寫作》,《中文學(xué)刊》2024年3期。
②③ 胡紅拴:《于昆明圓通寺》《星云湖上》,《延河》2024年2期上半月刊。
④⑥???? 胡紅拴:《姑蘇盤門》《在山塘評(píng)彈昆曲館聽昆曲》《耦園秋記》《在平江路上》《山塘街紀(jì)事》《大運(yùn)河上》,《北方文學(xué)》2024年第1期。
⑤⑧ 胡紅拴:《稻田聽秋》《寫春》,《北方文學(xué)》2023年2期。
⑦ 胡紅拴:《那烏古橋》,《揚(yáng)子江詩刊》2023 年第6期。
⑨? 胡紅拴:《白沙山,白沙湖》《盤龍古道風(fēng)歌》,《詩刊》2023年第21期。
⑩ 胡紅拴:《雙王城林海之夜》,《青島文學(xué)》2023年7期。
?? 胡紅拴:《昨夜我睡在仙云之上》《仙峰的云》,《生態(tài)文化》2023 年2期。
?? 胡紅拴:《古勞水鄉(xiāng)秋行》《桂峰讀溪》,《青海湖》2023年7期。
? 胡紅拴:《漫游沙灣古鎮(zhèn)》,《星星》詩刊2024年4期。
(原載于《中文學(xué)刊》2025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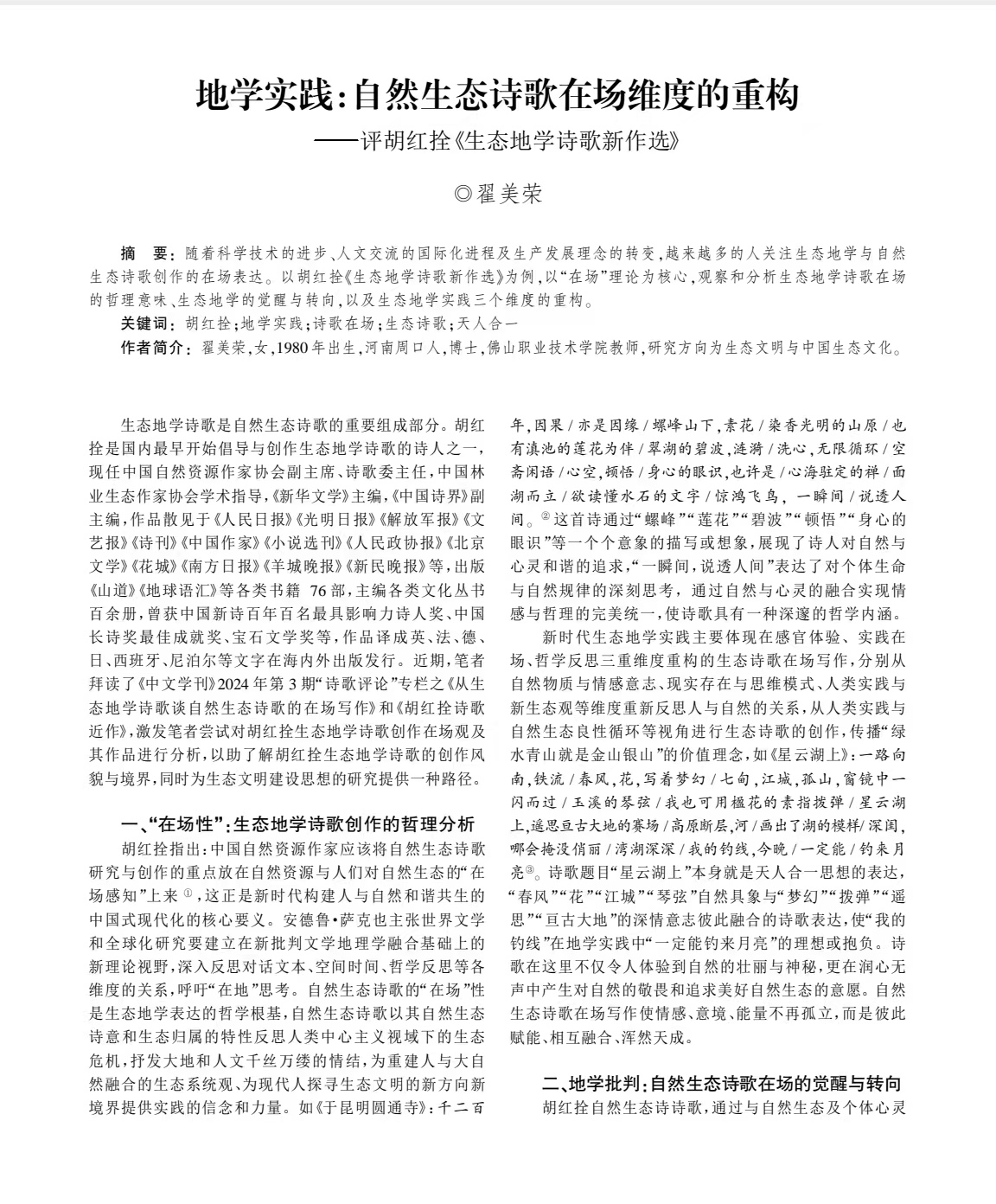
注:本文由路漫推薦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