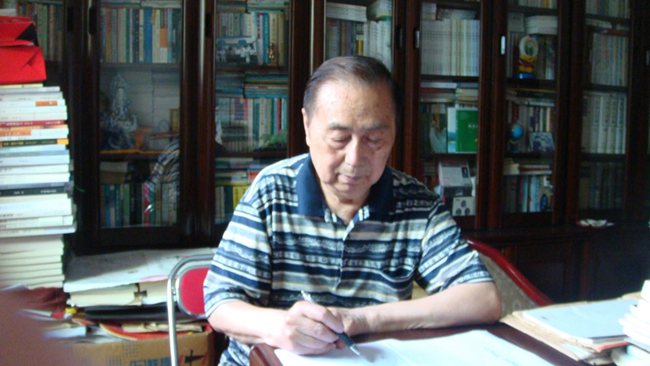
羅繼仁《中國詩人》工作照
何鷹:他堅守詩壇六十年
——我心目中的《中國詩人》主編羅繼仁
我與羅繼仁相識,是在上世紀60年前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天。那時我住在吉林市江北火電三公司的臨時職工家屬宿舍住宅區(qū),屬于簡陋的平房。當(dāng)時我父親在火電三公司起重隊從事吉林熱電廠的擴建工程。我離開黑龍江省化學(xué)工業(yè)學(xué)校之后正等著安排工作,所以便和全家住在這里。
我由于在1954年到1955年分別在《人民文學(xué)》《文學(xué)叢刊》(《鴨綠江》前身)《吉林文藝》《黑龍江文藝》《齊齊哈爾日報》上發(fā)表了一些反響較好的詩作,因此被推選為全國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會議代表,有幸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詩人歡聚一堂,受到了老一輩詩人和作家的教誨,特別是有幸親耳聆聽到了敬愛的周總理的報告。會議結(jié)束歸來后,我立刻把參加會議的情況向吉林市文聯(lián)的王璟石老師作了匯報。因為當(dāng)時我是屬于吉林市的與會作者。
王璟石老師聽了我介紹會議的情況后,高興地說:“這太好了,我們吉林市出現(xiàn)了兩名比較出色的青年詩人!”我迫不及待地問:“那一位是誰?”他告訴我:“他叫羅繼仁,年齡跟你差不多,是吉林熱電廠的工人,1955年就開始發(fā)表作品,很有才氣!”
聽了王老師的這一簡短地介紹,我立刻對這位從未謀面的詩友產(chǎn)生了一種“惺惺相惜”之情,心底對他的敬佩油然而生。以前,我一直認為自己發(fā)表作品時年齡很小,在1954年發(fā)表在當(dāng)年12月的《黑龍江文藝》上的《短詩五首》時,年僅17歲。沒想到羅繼仁和我同時間也開始發(fā)表作品了。于是,我產(chǎn)生了想見一見這位“少年才俊”的愿望,并請王老師幫忙,想盡快與他見見面。
但是,由于我隨后便接到了東北作家協(xié)會的通知,要我在3月15日之前務(wù)必去沈陽參加?xùn)|北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大會。我才方知我已被吸收為東北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了。當(dāng)時各省都還沒有組建省一級的作家協(xié)會。
參加完會議回來后,我又接到長春市文聯(lián)副秘書長王蒲英的通知,要我在同年5月15日之前去長春市文聯(lián)報到,任詩歌編輯。
于是,我便急急忙忙地趕回在臨行之前,在王老師的協(xié)助下與羅繼仁第一次見了面。
乍一相見,我立刻對他產(chǎn)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好感,他中等個頭,長相端正而又面善,眉宇間透著堅毅和忠厚。他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人很聰穎,一臉虔誠,值得信賴。”這一年的6月,吉林省召開全省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會議,傳達貫徹全國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會議精神。羅繼仁作為吉林代表來長春與會,我們又一次見面,相談甚歡,便成知已。
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沒有錯,果然是一位信守承諾,忠于友誼的人。在交談中還得知,他跟我竟是同齡人,都是十九歲,只是比我大幾個月,但是卻顯得比我成熟多了。他高興地說:“其實我早就認識你了,準確一點說,我通過你在報刋上發(fā)表的詩認識你的,讀你寫工業(yè)題材的詩感到非常親切!”
他只說他是一個普通工人,只字不提他十七歲就開始發(fā)表作品的事,我感到這個同齡人非常謙虛而又內(nèi)斂,這種素質(zhì)奠定了后來他事業(yè)的成功。
我們各自介紹了彼此的一些近況之后,他鼓勵我:“你到了新的崗位,就好好干吧,當(dāng)編輯也可以從閱讀作者的詩稿中學(xué)到一些東西。服務(wù)于他人,也是一種幸福。”
沒想到他也許是在無意間說出來的話,竟變成了他自己的踐行了一生的頇言。在1960年1月,他也踏上了編輯崗位,在吉林一家公開發(fā)行的刊物《江城文藝》做詩歌編輯。此后,雖然工作有幾次變動,但都沒有離開與文字打交到行當(dāng)。

羅繼仁80年代照
接下來我想還是從我和羅繼仁相識時談起,披露我和他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從這些一件件平凡的小事上看來,可以折射出一個人的人格魅力。
我到長春市文聯(lián)報到后,當(dāng)時,市文聯(lián)創(chuàng)辦了一個《布谷周刊》,每周編輯一期,發(fā)表在《長春日報》上。內(nèi)容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還有曲藝作品。我任詩歌編輯。盡管工作繁忙,要審閱的來稿很多,但我還是抽暇常與羅繼仁通信,在書信來往中,我們互相交流近況,互相鼓勵,一晃兒就來到了1957年,我和羅繼仁都邁入了20歲的門檻。我寫出了一首400行的長詩《青春之歌》,發(fā)表在吉林省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長春》文學(xué)月刊社上,羅繼仁來信熱烈祝賀,字里行間,洋溢著道不盡的欣喜,顯得比他自己發(fā)表作品都高興。接著我又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勞動者之歌》,也算是我步入20歲的一個紀念。
正當(dāng)我滿懷憧憬,準備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時,眾所周知的那場政治運動開始了。
我一夜之間,就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為了怕因為我入了另冊而株連到他,我便主動切斷了和他的聯(lián)系。不久,我的處理決定下來了,撤銷編輯職務(wù),取消工資待遇,每月只發(fā)20元的生活費,被下放到長春市郊區(qū)的“新立城水庫”接受監(jiān)督勞動改造。
于是,我當(dāng)上了一名開山工,每天開山采石,提供大壩護坡所需要的石料。工期很緊,勞動量很大,每天勞動時間長迏10個小時,所消耗的能量自然也多。每月給我的20元生活費,除了剛夠吃飯,就沒有分文剩余了。當(dāng)時,我家不算我還有六口人,全靠當(dāng)工人的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維持生活,我自然不能再增加家里的負擔(dān)。

羅繼仁發(fā)言照
我這一困難處境不知怎么被羅繼仁知道了,竟然從他每月30元的工資里,拿出5元資助我,解決我的燃眉之急。我不能為了緩解自己的困境而株連到他,于是我慌稱:因為我勞動出色,表現(xiàn)好,工資恢復(fù)了,要他不要再寄錢了。他信以為真,因為他認為我不會騙他。
之后我便把發(fā)給我的每月20元生活費,全用在吃飯上、穿一身襤褸沒關(guān)系,食物鏈不能斷裂。否則就不能維持每天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了。也是由于我表現(xiàn)突出,勞動拼命,1959年成為全國第一批為數(shù)不多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的人。但是羅繼仁在我最困難時資助我的義舉,卻讓我終生難忘。從那以后,又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我深怕自己這個有“前科”“污點”的人,“污染”了羅繼仁,怕他因為我這個“摘帽右派”的社會關(guān)系而影響了前途。因此,我毅然切斷了跟他的一切聯(lián)系。這一斷,就是20年。

羅繼仁2010年10月照
到了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獲得了徹底改正,從勞動了22年的長春市新立城水庫調(diào)回到長春市文聯(lián)重新當(dāng)了詩歌編輯。突然有一天,相別20年的羅繼仁從沈陽風(fēng)塵仆仆而來,找到了我。他帶著兄長般地關(guān)切神情問我:“這些年來,你是怎么過來的?我一直惦記著!”
我只輕描淡寫地說:“挺好的,一帆風(fēng)順。”接著,羅繼仁告訴了我說他這次來長春的目的。
原來,沈陽市文聯(lián)辦的《芒種》文學(xué)月刊復(fù)刊了。他擔(dān)任詩歌組長兼編輯部主任。這本刊物在1957年創(chuàng)刊時,曾引起過很大的反響,因為這是市一級文聯(lián)第一個辦起的文學(xué)月刊。隨著“反右斗爭”的開展,由于刊物提倡“干預(yù)生活”,很快就被停刊了,編輯隊伍也被整肅拆散了。22年以后,終于又復(fù)刊了。羅繼仁此行是來約稿的。于是,我把剛完成的一首比較長的詩歌《電柱之歌》給了他。他拿回去以后,很快就在《芒種》的復(fù)刊號上發(fā)表了,這首詩在讀者中引起了不錯的反響。后來我又在《長春》(《作家》前身)《江城》《黑龍江文藝》《吉林日報》等報刊陸續(xù)發(fā)表作品。為此,我心中默默地感激他。
后來我知道他一直在編輯崗位上,他當(dāng)年發(fā)表的抗聯(lián)詩抄及描寫北方大森林的作品,我始終念念不忘。尤其是發(fā)表在《吉林日報》上一組詩《大青山短歌》,被許多詩友稱贊不絕。
到了80年代,他編輯之余,還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xué)》《上海文學(xué)》《長春》《鴨綠江》《文學(xué)報》等刊發(fā)表了許多作品,并前后出版了《大森林之戀》《愛之路》《羅繼仁短詩選》及《詩潮耕耘錄》等著作。我記得《芒種》復(fù)刊后.他還發(fā)表過一首小長詩《安源山,我心中的大山》,印象尤為深刻。他的《詩潮耕耘錄》一書,還曾獲沈陽“五個一工程”獎。他的詩人條目,先后被收入《世界名人錄》《世界華人文化藝術(shù)名人》《中國作家大辭典》《中國詩人大辭典》。他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詩歌學(xué)會創(chuàng)會理事。2017年11月,當(dāng)中國新詩百年時,他還被授予“全球華語詩人百位最具影響詩人”稱號。
而時至今日,他已到耋耄之年,但還一直堅守在編輯崗位為他人做嫁衣。他晚年甚至放棄自已的寫作,有時為了改好作者的一首詩,甚至不惜將自已生發(fā)出來的好的詩句放在別人的作品里,他樂此不彼。他就是憑著這種忘我的工作熱情,贏得了許許多多詩友的贊譽。六十年來,他先后在《江城》《芒種》《詩潮》《中國詩人》的崗位上堅守著這片心靈的沃土,培養(yǎng)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詩人;他當(dāng)年在《芒種》辦的“青年與詩”專欄,許多當(dāng)下已有成就的詩人,最初也都在這里留下他們踏入詩壇的足跡。
1998年10月,他從《詩潮》主編崗位上退休以后,就著手接辦原在上海出版的《中國詩人》,一幌兒在遼寧沈陽又辦了22年。這些年的《中國詩人》可說是風(fēng)聲水起,在那里發(fā)表的一些作品,有的獲得魯獎、省部級獎,并有多篇被多家報刊、出版社選載。
在他的堅守下,《中國詩人》已經(jīng)是當(dāng)下詩壇一部不可或缺的詩歌讀本。這些年,他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已的寫作,全身心地撲到這本刊物上,一心想把《中國詩人》辦成國內(nèi)外知名詩刊。功夫不負有心人,2012年被國際詩歌翻譯研究中心和《世界詩人》(混語版)雜志社聯(lián)合推舉,被評為世界4家最佳詩刊之一。這些年,在朋友和有識之仕的支持下,刊物從季刊改出雙月刊,從郵局發(fā)行到書店及自辦發(fā)行,始終堅持出刊。在他的親力親為下,《中國詩人》于2015年成功舉辦了創(chuàng)刊25周年紀念活動,褒獎了25位頗有創(chuàng)作成就的詩人和評論家。2019年當(dāng)《中國詩人》創(chuàng)刊30周年之際,又一次舉辦了大型紀念活動,全國數(shù)十家媒體、電視、網(wǎng)站、公眾號都做了大篇幅的報道,《中國詩人》的影響日漸擴大。為了鼓勵創(chuàng)作,刊物還前后舉辦過五屆年度詩歌獎,重獎了20余位詩人和評論家。近年來,又與世界華語詩盟屬下《詩》季刊簽訂了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在河北館陶著名詩人雁翼故鄉(xiāng)建立了“中國詩人創(chuàng)作基地”,與秦皇島思仁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組建了“中國詩人角”,為下一步開展全國性的詩歌創(chuàng)作及詩人休閑活動,提供了可利用的場所。
從1960年的《江城文藝》,到2020年的《中國詩人》,羅繼仁從23歲的年輕才俊,到83歲的年邁老者,他在編輯崗位上整整工作了60年。我常常想,他這一份的執(zhí)著,這一份的堅守,這一份的奉獻,到底是為了什么?《文藝報》曾發(fā)表一篇署名文章《北方詩壇的拓荒犁》寫的是他,詩壇泰斗賀敬之在接受一次采訪中說,“羅繼仁,他不為名、不為利,為中國詩歌發(fā)展辦詩刊,默默無聞作貢獻,是個好同志啊!”
也汻,能從這些評價中誤出一些端倪吧!
2020年11月1日改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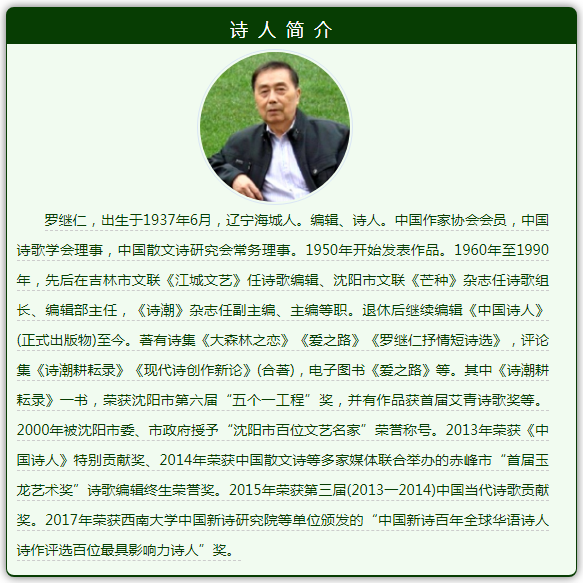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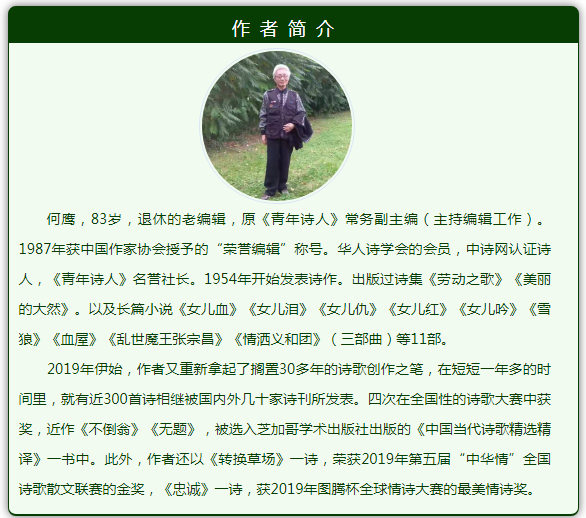
作者:何鷹
來源:中詩網(wǎng)
http://www.yzs.com/zswshowinfo-1-8328-0.html
來源:中詩網(wǎng)
http://www.yzs.com/zswshowinfo-1-8328-0.html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