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有病
作者:贠靖
丁四元半夜里被蚊子叮醒,穿條大短褲在房間里來回走動著打蚊子。媳婦兒夏麗花面朝墻壁摟著五歲的兒子睡得正酣,毛巾被蹬到了地板上,露出兩條雪白的細長腿。
丁四元用手在空中撲打著,突然聽到客廳里有隱隱約約的響動聲。他驚岀了一身冷汗,停下手來側(cè)耳傾聽,又沒了聲音。
過一會,又有聲音從客廳那邊傳了過來,好像是椅子被撞了一下,又像是桌上的花瓶什么的被撞倒了,發(fā)出噼哩哐啷的聲音。他的汗毛一下豎了起來,驚恐地朝后退縮著,伸出手去捅了捅媳婦兒。夏麗花將臉貼在兒子后腦上輕聲地囈語著,翻個身又沉沉地睡去。
丁四元貓著腰伸出手去,抓起床頭上的枕頭舉在手里,腳卻像生了根,站在那挪不動。他將半個身子探出臥室,壯著膽子顫悠悠喂了一聲。
客廳里一點回音都沒有,媳婦兒在床上發(fā)岀細微的鼾聲。
誰?丁四元開了燈,舉著枕頭一驚一乍地低頭尋找著,客廳里什么也沒有。夏麗花嗔怪道:大半夜的不睡覺,你發(fā)什么神經(jīng)啊?
噓——有人進來了!他一邊說一邊朝桌子下面瞅著。媳婦兒打著哈欠擰過臉去看了一眼窗戶,窗戶關(guān)得嚴嚴實實的。
哪有什么人進來呀,快睡吧,明天還要上班呢!媳婦兒坐起來抻個懶腰又一頭栽倒在床上。
丁四元還站在客廳里一臉疑惑地嘀咕著:真是活見鬼了,門窗關(guān)得好好的,不會是院子里的野貓白天闖了進來吧,就躲在什么地方?他過去推上窗戶玻璃,擰上鎖扣,又左右推了推,然后彎腰在桌子底下仔細地尋找著。
早上起來,丁四元從桌上拿起一塊面包,拉著兒子的手準備出門。媳婦兒夏麗花在衛(wèi)生間里刷牙,一嘴的白沬子,偏著臉問:哎,昨晚你不睡覺,在客廳里找尋啥呢?
沒有啊!丁四元眨著眼說,他低頭看了看兒子,兒子一臉的茫然。
丁四元在單位一直干審計。上了班,他又從財務室抱來一大堆憑證,一整天都埋頭在憑證里一遍遍地翻找著,似乎想要從中找出什么蛛絲馬跡來,結(jié)果什么也沒找到。單位里的人都說他心態(tài)出了問題,老是疑神疑鬼的,覺得賬有問題。但又沒人敢阻止他查賬,那是他的職責所在。
吃午飯的時候夏麗花打來電話說,我下了班要和同事去一趟四方城里,前些天在東大街的百貨商場相中一條滌絲裙子,想再去看看。她說,好好的一個東大街修地鐵給挖得稀巴爛!又叮囑丁四元,你接上兒子就帶他在外邊吃東西點吧。別老帶他吃快餐,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吃多了對孩子身體不好。他說,這我還不知道呀,你不用叮囑,偶爾吃一兩次沒事的。什么就偶爾吃一兩次沒事的?她厲聲道:不許帶孩子亂吃東西!他只好地點頭稱諾。
夏麗花在研究所干會計,她和丁四元是財經(jīng)學院一個班的同學。那時的夏麗花沒現(xiàn)在這么瘦,臉上屁股上都肉嘟嘟的。
在談戀愛這件事情上夏麗花比丁四元要主動一些。她老說他是個呆瓜、提線木偶,除了算賬查賬來勁,連談戀愛都沒勁,打不起精神來。一次他們?nèi)W校旁邊的影院看電影,黑暗中夏麗花在丁四元的臉上親了一口,他嚇得低了頭,半晌不敢抬起來。夏麗花逗得仰面大笑,池子里的人都扭過臉看著她,她這才止了笑,拽了拽丁四元,將頭枕在他肩上。
多少年后,夏麗花仍清楚地記得,新婚之夜,竟然是她把丁四元拿下的,現(xiàn)在想起來她還有些臉紅心跳。
那晚鬧洞房的人都走后,她插上門坐在床沿上,閉上眼,想像著他會迫不及待地過來挨著她,輕輕地擁抱她,然后……可等了半天,卻沒見動靜。她忍不住窺了一眼,他似乎比她還沉得住氣,坐在那一下一下絞著手指。她又窺了他一眼,說,我肩膀酸,你過來給我揉一揉,他這才往她跟前挪了挪。最終還是她放下矜持,捶了他一下,小聲罵了一句呆瓜,將臉貼在他懷里,伸手解開了他的扣子。
有一次,夏麗花和幾個閨蜜聚會,喝了點紅酒,臉紅撲撲的,瞇著眼說,這輩子嫁給丁四元這樣的男人,雖然不指望他能給她一個浪漫的擁抱和親吻,但卻讓她一百個放心,她從來不用擔心他會做岀對不起她的事情來。有一個低了頭一直不說話,挨著夏麗花坐了,懷里抱著一個十幾萬的包包,看上去小鳥依人的閨蜜聽了半晌沒言語。過了一會,她將包包丟到一邊,捂著臉,抽抽嗒嗒哭了起來,夏麗花勸了半天也沒勸住。
當然,夏麗花和丁四元的夫妻生活也是有缺憾的。在那件事上,多數(shù)時候都是她主動。但懷上兒子后,慢慢地她也就沒了多少激情和興致。
吃晚飯時丁四元和往常一樣,沒看出什么異樣。他坐在餐桌前一口氣吃了三個煎餅卷土豆絲,一個勁地說好吃。剩下一個,他看了看兒子,兒子搖搖頭說不吃了。他又看了看媳婦兒夏麗花,夏麗花也搖搖頭說,老公——人家減肥,不能再吃了,再吃要長肉肉的!他就抓起來瞅了瞅,一口塞進嘴里,臉噎得像個紅冠公雞,脖子一抻一抻的,嗓子眼里發(fā)出絲絲的咕嚕聲。夏麗花忙端起水杯遞給他,他喝了一口,打了個嗝,這才緩過氣來。
凌晨兩三點的時候,夏麗花迷迷糊糊睜開眼,發(fā)現(xiàn)客廳燈亮著,丁四元不在床上。夏麗花嘴里自言自語著,下床趿拉上拖鞋,探頭探腦地邁岀臥室。丁四元光膀子穿條短褲,低頭在客廳里尋找著什么,說是有人進來了,就躲在屋里什么地方。夏麗花聽了嘴角抽了抽,有些毛骨悚然。
一連折騰了幾個晚上,夏麗花就覺得丁四元有些不正常。她說,你請個假,一會把兒子送到幼兒園咱去醫(yī)院瞧瞧吧。丁四元說,我沒病,我才不去醫(yī)院哩,上午去單位還要接著查賬呢。
巷子里的風不緊不慢地刮著。丁四元躡手躡腳地往前走著,噏噏鼻子說,誰家的鐵鍋燒干了,有一股子難聞的焦糊味。夏麗花聞了聞說沒有啊,他把丁四元硬塞進車里,一踩油門拉到了醫(yī)院。
往常沒病的話夏麗花是不會進醫(yī)院的,因為她一聞到福爾馬林的刺鼻味兒就忍不住捂著嘴想吐,一看到白大褂就暈。
大夫聽夏麗花皺著眉頭描述后,示意丁四元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他問了幾句無關(guān)緊要的話,讓丁四元看著他,用拇指和食指翻開他的眼皮,拿電筒照著瞅了瞅說,沒什么大礙。說著站起來擦擦手,走進里邊的檢查室。夏麗花忙跟了進去。大夫?qū)⑹持笁涸谏舷麓介g,噓了一聲,小聲道:輕度抑郁癥!夏麗花問,您要不要再給做做檢查,大夫說不用,這種病我見多了,一眼就能瞧出來。夏麗花說,好好的咋能得上這種病呢?大夫問:他是不是老疑神疑鬼的,還有情緒低落,干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來,包括那方面?夏麗花聽了臉刷一下就紅了,難為情地低了頭。大夫說,這就對了嘛。又問:他平時有沒有受過什么刺激?夏麗花還是搖頭。結(jié)婚這么多年,他們連一句嘴也沒拌過。
那可就不好說了,也許是工作壓力大吧,又裝在心里不愿和別人說。大夫說,這種病人很可憐,其實他心里是很孤獨的,沒有人能夠理解他。這樣,我先給開點藥吧,回去調(diào)理調(diào)理,過段時間再來復查一下。對了,要多關(guān)心他,千萬不能讓他再受任何刺激。不然,病情只會加重。夏麗花又試探著小聲問了一句:大夫,你說這種病嚴重的話會怎么樣?跳樓!大夫面無表情地說了一句,夏麗花嚇岀了一身冷汗。如果她沒記錯的話,她姥爺就是得了啥“夜游癥”,癥狀一模一樣,大半夜不睡覺,起來光著屁股在院子里亂跑,結(jié)果一不留神從一口枯井口栽了下去,不知這兩種病是不是一回事。
從醫(yī)院回來,夏麗花便得了失眠癥。整宿整宿睡不著。她一閉上眼,就感覺像走在一條漆黑的長得沒有盡頭的巷道里。丁四元不聲不響地跟在她身后,她能聽得到他喘息的聲音,卻看不清他的樣貌。
一會她又聽到轟隆轟隆火車穿過漫長的黑洞的聲音,她和躺在身邊的丁四元就像兩列相向而行的列車,只是眨眼的工夫她和他就擦肩而過,漸行漸遠,直至互相看不清對方。
一會她又像坐在易俗社的戲樓里看戲,偌大的臺下就她一個人。臺上一男一女在唱秦腔折子戲,唱來唱去就一句臺詞:戲開了,落幕了,各回各家睡覺了!讓她感到奇怪的是,臺上的人就是她和丁四元。她有點弄不清楚,臺上臺下,哪一個夏麗花才是真實的自己。
天快亮的時候,夏麗花又做了個噩夢,這回她夢見丁四元一絲不掛從樓上一躍而下,悄無聲無息地在空中飄著飄著,像一張皮影一樣墜落下去,一動不動地扒在地上的草叢里。她驀地坐起來,喘著粗氣,見丁四元卷曲著身子側(cè)臥在床榻上,她揪著頭發(fā)咦了一聲又重重地躺下了。
奇怪,丁四元最近一直睡得很好,他彎著腰,背對背躺在她旁邊,像個聽話的孩子一樣。她突然覺得躺在身邊的這個男人很陌生,像從來就不認識一樣。她已不記得他們有多長時間沒有肌膚之親了。
夏麗花懷疑自己得了焦慮癥,夜里一有半點風吹草動,就嚇得坐起來,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沒了一絲睡意。在研究所上班她也心不在焉,做賬老是岀錯,已被領(lǐng)導叫去批評了好幾回。
后來夏麗花慢慢地恢復了平靜,卻發(fā)現(xiàn)丁四元又有些不正常了。他半夜里從床上跳起來,惶恐萬狀地在客廳里跑來跑去,說是有人要加害他,還大聲地嚷嚷著要打電話報警。經(jīng)他這一通叫喊,樓上樓下的住戶就都被噪醒了,他們?nèi)嘀殊斓乃蹟D在樓道里敲著門問咋會事,大半夜的嘈嘈嚷嚷還讓不讓人睡了。夏麗花在門里說著道歉話,死死地抱住丁四元,捂上他的嘴,說是鬧著玩呢。她想不明白,自己當初怎么就稀里糊涂嫁給了這么一個男人。
單位的人還是知道了丁四元患抑郁癥的事,他上班后埋頭在屋子里一遍遍查看賬本的時候,辦公室的人就在外邊嘀嘀咕咕地小聲議論著。丁四元在里邊呆煩悶了,便岀來走到窗戶那里,推開玻璃窗扇,將半個身子探出去透著氣。辦公室的人嚇得趕緊打電話把保安喊了上來。幾個人哈著腰悄沒聲地合圍過去,將丁四元攔腰抱住,拖拽進屋子里,反鎖上屋門。丁四元突然受到驚嚇,在里邊手舞足蹈大喊大叫。
夏麗花肩上挎只包驚慌失措地趕過來,耳朵貼在門板上聽了半晌,里邊竟一丁點動靜都沒有,她心里便有些慌張,讓人打開門,丁四元伏在桌子上,頭埋進一堆半人高的賬本里,嘴里嘟嘟囔囔翻看著賬本。見夏麗花進來,他眨著眼問:你咋來了?
夏麗花白天受了驚嚇,晚上心慌得不行。
她摟著兒子,就像躺在空無一人的荒野里,一會渾身冰冷,一會又熱得不行,像泡在水里,不停地岀汗,渾身上下濕漉漉的,像剛從水里撈岀來。
漸漸地她有些眼皮發(fā)沉,朦朦朧朧中剛閉上眼,丁四元倏然大喊大叫著坐起來將她一腳踹到床下。他從床上蹦下來,在客廳里揮舞著手臂,邊跑邊喊:站住,好一對狗男女,瞧你往哪里跑?看老子不打死你!
夏麗花站在臥室里,靜靜地看著他,問他在干嘛呢,丁四元說他在抓流氓。他怪模怪樣地盯著夏麗花問,你咋會和那個人在一起?剛才我看到你一絲不掛躺在床上,他就爬在你的身上,在和你干那事!
你胡吣啥呢!夏麗花站在那胸脯一起一伏,臉蛋兒紅紅的。
都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搞不明白,丁四元咋會做這樣的夢?難道是他察覺到了她和那個人的隱情,故意裝瘋賣傻,想看看她的反應?更叫她意外的是,他竟把她和那個人說成是一對狗男女,并且破天荒用了“老子”這個詞語。要知道,他平日在她面前總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唯唯諾諾的,還從來沒這么大聲和她嚷嚷過。
夏麗花已被丁四元折騰得神經(jīng)衰弱了。那天她在辦公室里低頭核對憑證,聽到有人走動的聲音,一抬頭看到不知誰在她面前的桌上放了一束黃玫瑰,就是她喜歡的那種帶著淡綠色的玫瑰,插在瓶子里,上頭閃爍著晶瑩的露珠。她閉上眼嗅了嗅,一股淡淡的清香立刻撲進鼻孔里。她睜開眼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觸摸,摸到的卻是一只冰冷的保溫壺。那壺也是綠色的。本來她是要去開水房打水的,不知誰打了個岔,說要查一下上個月的賬目,有一筆數(shù)字對不上。結(jié)果她放下壺,就把打開水的事給忘了。
為人莫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她抬手拍了拍額頭,有點搞不清楚她和那個人之間的事情到底是夢還是真實的存在。有時覺得真實得連對方急促的呼吸都能夠感覺得到,有時又覺得是那么的遙遠,或者說虛無縹緲,壓根就沒發(fā)生過。
夏麗花鎮(zhèn)靜了一下,沉著臉道,你要再敢胡吣我就和兒子搬出去住!她說話的語氣明顯有些底氣不足。但這句話還是起了作用,丁四元聽后便垂了頭,乖乖地到床上去躺下。很快,他又發(fā)岀沉沉的鼾聲。夏麗花卻沒一點睡意。
城里的夜晚不似鄉(xiāng)村那般寂靜,偶爾有一輛兩輛貨車踩著剎車從什字路口開過去,發(fā)出刺耳的尖叫聲。
那個人也是夏麗花大學的同學,在校時交往似乎不多,畢業(yè)后他就出國了。據(jù)說在國外和一個金發(fā)碧眼的洋妞如膠似漆地好過一陣子。半年前他突然回來,不知從哪打聽到夏麗花的聯(lián)系方式,打電話說想請老同學聚一聚,希望她能夠賞光。本來夏麗花是不想去的,但他都那樣說了,她就有點不好意思拒絕。思來想去,她竟鬼使神差地答應了他。到了那里才發(fā)現(xiàn)他就請了她一個人。
他還跟以前一樣,一副風流倜儻的樣子,穿一身白色的西裝,系一條紅色領(lǐng)帶。就是看上去很有質(zhì)感,價格不菲的那種。見了面他微笑著張開手臂,上前輕輕地和她擁抱了一下。這正是她內(nèi)心里一直渴望的那種浪漫的感覺,她居然沒有任何抗拒就欣然接受了。
那天他們倆人喝了一瓶法國波爾多紅酒,到后來倆人都有些站立不穩(wěn),說話舌頭僵硬,前言不搭后語。
但他們還是有一句沒一句地聊了很多,還聊到了《紅樓夢》。他說她很像《紅樓夢》里的薛寶釵,容貌豐美,舉止嫻雅,又博學多才,正是他喜歡的那種類型。她心里明明知道他是沒話找話,在想著法子討好她。但她還是感到很受用。盡管她有點不喜歡薛寶釵。她喜歡的是林黛玉,喜歡那種弱不經(jīng)風的,被人寵愛的感覺。
或許是借著酒勁,他醉眼迷離地瞅著她,有些動情道:你知道嗎麗花,我一直喜歡你的……說著緊緊地抓住她的手。她緊張地將手抽了回來,抬手攏了攏零亂的鬢發(fā),神色慌張道,那,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上大學那會,他的確追過她,但被她拒絕了。雖然她是個骨子里渴望浪漫的人,但卻覺得她和他不是一路人。他就是一個多情的公子哥兒,給不了她想要的安全感,不是那個她要托付終身的人。
他隔著餐桌目光灼灼地瞅著她,瞅著瞅著眼里就有了些許沖動,過來挨著她坐了,伸出手輕輕地摟住她。她掙扎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股男性荷爾蒙氣息讓她渾身不由自主地顫栗,她感到身子有些發(fā)軟。
記得后來他拉著她的手踉踉蹌蹌跑下樓梯,在昏暗的地庫里,他拉開車門,疾風驟雨般裹攜著她上了車。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們瘋狂地擁吻著。
一番激情過后,她拎上不整的衣衫,拉開車門,想要下去,但渾身無力,腿腳軟綿綿地邁不開步子。他輕輕一拽,她就倒在了車座上。他俯過身去,給她系上安全帶,輕輕地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下說:我送你回去吧,親愛的,太晚了。她沒再掙扎。
到小區(qū)門口看著她下了車,他搖下車窗玻璃,抬手沖她送了一個飛吻,才一打方向開走了。她突然覺得很惡心,覺得自己很齷齪,胃里頓時翻江倒海,蹲在地上哇哇地嘔吐起來。
她曾經(jīng)想要刪掉他的號碼,從此不再跟這個人有任何瓜葛。但拿起手機猶豫良久又放下了。此后他們又有過幾次激情的幽會。雖然她一再在心里發(fā)誓這是最后一次了,但又抗拒不了他那令人神魂顛倒的誘惑。她覺得自己很下流,很可恥。
她至今仍不知道他和那個洋女人有沒有結(jié)過婚,在國外有沒有妻兒。他沒說過,她也沒問。她覺得那個黃頭發(fā)藍眼睛,人高馬大的女人和她沒半點關(guān)系。
她和他充其量就是一時沖動,她并沒想過要和他在一起。
除了男女間的那點事,讓她對他產(chǎn)生幾分好感,甚至依賴的是,他很懂得女人的心,會討女人的歡喜。比如時不時地噓寒問暖,送一些化妝品什么的給她,還有一只很貴的包包,正是她喜歡的款式。她一直想買,但猶豫很長時間還是沒舍得買。
有一陣子,她為兒子小升初的事兒愁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他得知后撫著她的手說:麗,你放心,這事交給我來辦吧。他說話的時候含情脈脈地注視著她,眼里充滿了令人無法抗拒的柔情。這讓她蒼白的內(nèi)心感到無比的溫暖和踏實!更讓她感動的是,他為此托了不少的關(guān)系,還花了二十多萬,提前給兒子爭取到了一個市級重點中學的名額。
令夏麗花感到十分糾結(jié)和懊惱的是,小升初統(tǒng)考成績岀來,平時看似學習不用功成績一般般的兒子竟然超常發(fā)揮,自己考上了那所市里排名前三的重點中學。
月光水一祥從窗外潑灑進來。窗戶半開著,臥室里沒一絲風。夏麗花覺得周身濕冷,就像躺在冰窖里,手腳冰涼。她渴望丁四元能從后面輕輕地擁著她,他卻睡得很死。
她懷疑他一定是察覺到了什么。否則,他為什么會說自己做了那樣的夢?
夏麗花的心情很復雜,她低頭看了一眼在懷里熟睡的兒子,決心和那個人做個了斷,不再見面。
現(xiàn)在丁四元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踏實,夏麗花卻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她老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夢,夢見她一個人在小時住的巷子里低頭往前走,走得很快,面前的路很長很長沒有盡頭。一會又像走在沒有人煙的荒漠上,口渴得厲害。
她還夢見自己站在大學圖書館前的梧桐樹下,手里拿著一本錢鐘書的《圍城》。頭頂上巴掌大的梧桐樹葉下雨般輕飄飄無聲地掉落下來,落到地上就變成無數(shù)雨點濺起來。她淡漠的目光穿過飛舞的梧桐葉,漫無目的地在空中游蕩著,找尋著,卻看不到丁四元的身影。
冥冥之中那個人好像遠遠地跟在她身后,穿一身白色西裝,系著鮮艷的紅領(lǐng)帶,任她怎么奔跑也甩不掉他。
后來她又夢見曾是工程師的姥爺不說話,光著身子在院子里跑,頭頂上有無數(shù)只紅嘴烏鴉在飛來飛去,最后風卷殘云一樣掠過樓頂飛走了。
夏麗花陷入了痛苦的旋渦之中。
她懷疑丁四元沒病,是裝的,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患上了抑郁癥。
如果他沒病,那可就太可怕了,她想一想就有些脊椎發(fā)涼,頭皮發(fā)麻。
有時她又想,或許她和那個人之間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只不過是一些零零星星破碎的夢而已。這樣一想,她心里便有些釋然。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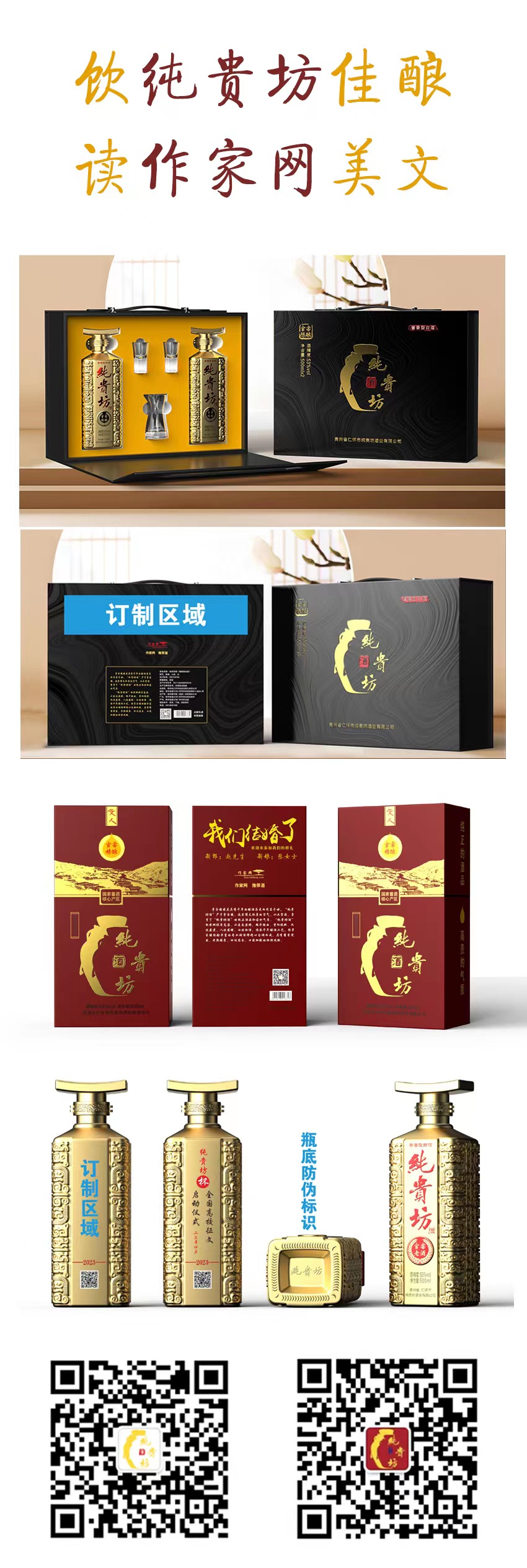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