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華楠的詩魔方與思維蒙太奇
——華楠詩學的玄奧密碼
作者:余文
?
華楠的詩我評過很多次,部分詩評在他的公眾號《有人寫詩》上發布過,與諸多評論不同,我注重從現象學角度欣賞華楠的詩。他的詩吸引過很多人,但我以為只有具備現象學思維方能洞察華楠詩學的玄奧密碼。不少詩人都能寫出個體存在,但只有華楠能寫出理解存在的存在,即此在(Dasein),只有他真正做到以詩的方式詮釋存在本身,這個過程說來簡單、其實很難,這類詩作看似平常、實則高妙。
有說詩不能講道理,實際上是講道理的詩很難寫好。真正的道理并不在那些宏大的意向和超拔的想象中,而是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現象里,一個人的真正革命是生活革命,只有當日常生活發生變化的時候,才是有可能獲得真知灼見的時候。華楠的詩是對日常生活中人和事物存在狀態的直觀揭示,要對其中任何一首詩進行解讀就勢必要面對如何揭示事物存在本身的現象學描述問題,而這又需要讀者具備‘理解’直觀的能力。作為詩人,也許華楠并‘不知道’直觀的哲理,但他的詩寫卻天然就處在這種直觀當中,他在一種不自覺的天賦下進行直觀并通過語言(符號)將這個過程展露出來,這種因‘不知而智’的詩寫狀態令人羨慕。下面是對華楠三首詩所作的現象學解讀,三首詩作均選自公眾號《口紅文學》華楠專輯。
1.想摸沒摸到
作者/華楠
黑暗中
那種真正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見
我覺得旁邊有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伸手去摸
但什么都沒摸到
我覺得不是因為什么都沒有
只是我什么都沒摸到
那個我感覺到的東西
還是在那里
每個人都生活在直接物理環境中,我們能夠意識到許多實在的空間性對象,但實際上,這些對象只是我能意識到的東西的很小一部分,它們并沒有窮盡(人的)意識。也就是說意識本身的結構,意識的意向性行為,還存在著多種可能。如當我端坐于此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不僅能夠思考火星的地形結構,也能想象圓的方、飛馬、天使,以及=±2等,我所意向的這些東西(對象)可以是不在場的、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顯然,在我的意識活動中,這些對象并未因果性地直接影響或作用于我,但是,我依然能夠經由意識行為清晰地指向它們。
華楠這首詩,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見的前提下,我覺得旁邊有什么”。這正是一種意識的可能性,是一種有別于常規的看、聽和觸摸的意向行為,它除了體現一個詩人對生活的特別感知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蘊涵著對這個世界可能性的追問與思索。在探索過程中,詩人伸手去確認,這實際上是一種明證,并且基于我目前的局限,這個明證只可能是俗常的,它只能明證空間性物理對象。但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明證失敗后,詩人并未就此判斷旁邊“空無一物”,卻反而更加確信:雖然我沒有摸到,但是一定有某個我感覺(意向)到的東西在那里。正是這種超乎尋常的感受或經驗(這里指經歷),呈現出一種有別于常規的高級詩意,為我們展現出一種可能性的永恒存在。
除了探索意識行為的可能性之外,這首詩還能引發我們對語言性意義的思考,即它可用于質疑語言哲學中“所有東西都是語言性的”表達,追問或溯源人類前語言和前述謂的經歷。詩中那種想摸沒摸到的經驗,正如一種在語言性意義產生之前,我們與世界在勾連中打交道時的知覺性熟悉狀態,一種前述謂的“朦朧”。我相信一定有人在不經意間也有過類似的經歷(近似于無法用語言表達),但問題在于他們很難或不會留意到這樣一種實際上是鐫刻在人類進化本能中的古老“熟悉”。顯然,華楠不僅留意到了,還經由詩意的方式為我們呈現出來。
2.螺紋和葉脈
作者/華楠
有知識向我傳授過
螺紋和葉脈的形成原理
但后來我忘了
類似的還有大理石的紋路
毛巾的織法
水龍頭的進化
凳子的工藝
我知道了然后又忘掉
事物浮現又退回
保持著神秘的美感
田螺來了又走了
留下螺殼
事物的存在通過事物由以顯現的多樣性的豐富性而增加,事物顯現是其存在方式的展露,我們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感覺對事物形成經驗和認知的。而由于事物顯現的多樣性,顯現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在場與缺席的混合:某些事物在此時此地以某種角度或方式向我們顯現,我們通過種種方式把事物帶到對我們在場,使我們得于了解事物形成的原理,但與此同時,這個過程也伴隨著另一些事物以及事物的某些方面對我們缺席,從曾經的在場退入缺席。因此,事物總是浮現又退回,退回又浮現,保持著永恒的神秘,其實這就是事物存在的本性,一點也不神秘。
有人問我:‘為什么華楠寫這種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物叫詩,而我寫的卻不是?’我的答案:沒錯,日常事物誰都可以寫,但為什么華楠寫的日常是詩,而‘你’寫的日常只是日常?很簡單:因為華楠的語言(即寫出句子的方式)是現象學態度下的描述,而你的語言只是自然態度下的單純記錄。說得再通俗一點:華楠不僅寫出他看見的,還寫出了他究竟是怎么看見的,而你只寫了看見,卻寫不出你怎么看見你的看見。
3.我看不見自己的后腦勺
作者/華楠
但看見不是我們確認事物的唯一方式
我摸了摸后腦勺
硬硬的
上面覆蓋著頭發
有個道理常被人們忽略:即世間學問種種看似紛繁復雜,其實大多數都有憑空想象和捏造的成分,特別是在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的領域,因為它們早已脫離乃至遺忘了它們賴于產生的現象之源。這就好比你永遠看到的只是這把椅子,卻看不到你自己到底是如何看到這把椅子的。
當人們在形而上里忘乎所以地覺得自己很哲學時,其實他們恰好離真理越來越遠(No truth is a fact)。真正有智慧的東西就藏在我們每天習以為常的對象中,但是(但是后面通常都很重要):只有真正具備現象學反思能力的人,才能洞察到這種把對象立起來的過程,才能在回溯意識構造功能的過程中導向并看到先驗自我(本我)。
華楠是一個極富智性的詩人,且恕我斗膽斷言,不具有現象學思維的人,即使宣稱‘讀懂’他的詩,也僅僅只是驚奇于他對日常生活事物的意外描述或隨意堆砌一些模糊性的詞語而已,講不清楚這些句子究竟怎么寫來的過程(按照胡塞爾的觀點:除現象學之外其他所有哲學在‘邏輯上’都是不嚴格的)。下面就以《我看不見自己的后腦勺》一詩為例,做一個簡單的現象學分析。
首先要說,這首詩很短,但‘完成過程’非常復雜:因為它涉及現象學的身體性敞開、明證性、視域、存在乃至先驗自我等一系列問題(真理隱藏在看似平常的事物里,如果你能真正‘看’到一件,就能體會到一次智慧的感覺),因此我只做個淺讀。題目‘我看不見自己的后腦勺’,這是一個視覺經驗的表達,雖然沒看到,但我在說的時候,即用語言(符號是一種范疇意向)說出這句話的同時,我實際上已經在意向著‘自己的后腦勺’了。但顯然,后腦勺現在對我是缺席的,我沒有形成對它的直觀充實,因此我想去確證(我當然想要直觀它)。
在無法直觀的前提下,詩人馬上反思到‘看見不是我們確認事物的唯一方式’,并由此轉向另一種意向行為即觸摸,‘我摸了摸后腦勺’這其實是我第二次意向我的后腦勺了。但這次意向與第一次不同,因為這次我摸到了,也就是后腦勺在觸覺中自身被給予(這里還涉及交互主體性,我不僅經由頭感受到頭被手摸,還同時經由手感受到了手在摸頭),是一種直觀的被充實,這就是現象學所說的存在,這種存在以它(也即被我的觸覺意識‘立’了起來),即我的后腦勺是這樣(被)存在著的,它‘硬硬的,上面覆蓋著頭發’。
需要注意的是:兩次意向行為雖然不同(它們的質性不同,但質料相同),但它們意向的依然是同一個對象即‘我的后腦勺’,假如你來看我的后腦勺,那么我的后腦勺不僅僅只是你看到的那個后腦勺,它同時也是你告訴我你看到的那個后腦勺,以及我想看到的那個后腦勺,以及我伸手摸到的那個后腦勺。這些所有的后腦勺同屬于一個先驗的同一性的后腦勺,而所有這些多樣性的后腦勺,又都是我的后腦勺存在之展露的某種方式。(作者/余文 編輯/劉不偉)
附:
華楠:素未謀面的朋友余文先生寫過多篇關于我的評論,這是最新的一篇,我很榮幸得到這樣的評價,這篇文章是真正的智力游戲,簡單直接、干凈利落。最后一段把玄奧的經驗說得像繞口令一樣輕松有趣。我的詩總是被評價為平易日常,也的確是這樣,但它們同時又艱深玄奧。余文中提到的“前語言”、“前述謂”是我思考得比較多的概念,當我說凳子的時候凳子包含了人類直立行走以后遇到的第一個石墩,并在此發現了“坐”這個姿勢。“我坐在凳子上”,就是“我坐在凳子上”,簡單、日常。世界的秘密永遠是敞開的,所有被隱藏的秘密都是故弄玄虛。當我寫下“我坐在凳子上”這個句子的時候,我其實是在寫幾十萬年來所有坐過凳子或石墩的人坐在凳子或石墩上,既有幾十萬年來的習俗與習以為常以及由此繁衍生息的儀式及意義,也有第一次坐上石墩的怪誕和驚喜。這就是我說的作為智人這個物種的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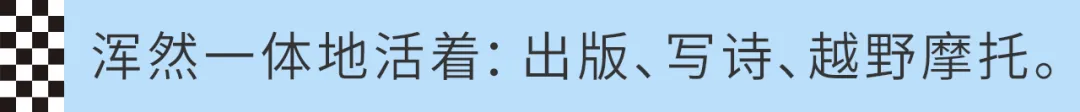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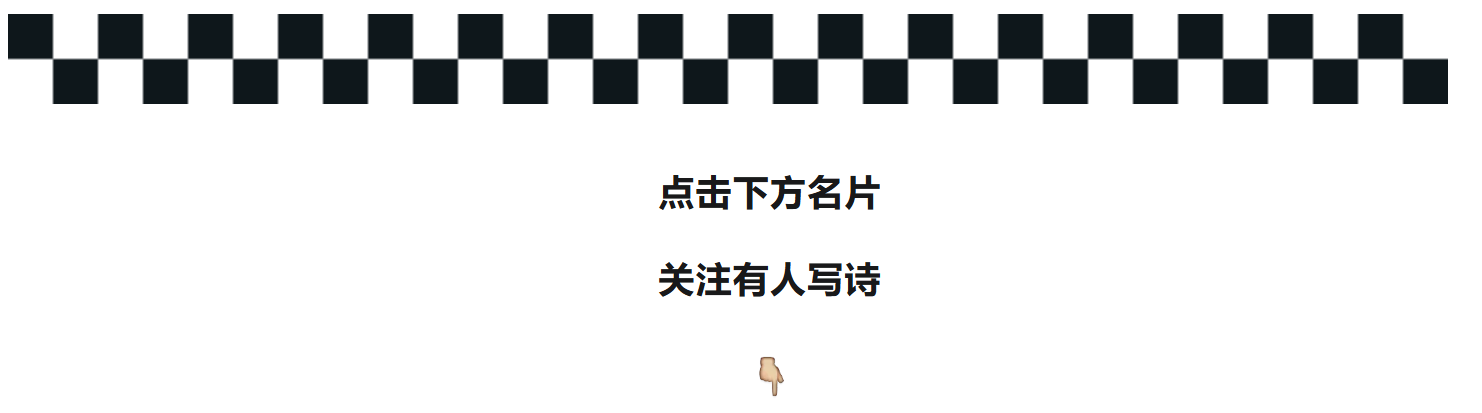

來源:有人寫詩
作者:余文
https://mp.weixin.qq.com/s/aNAHjq-GzDOJGSfofFOerQ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