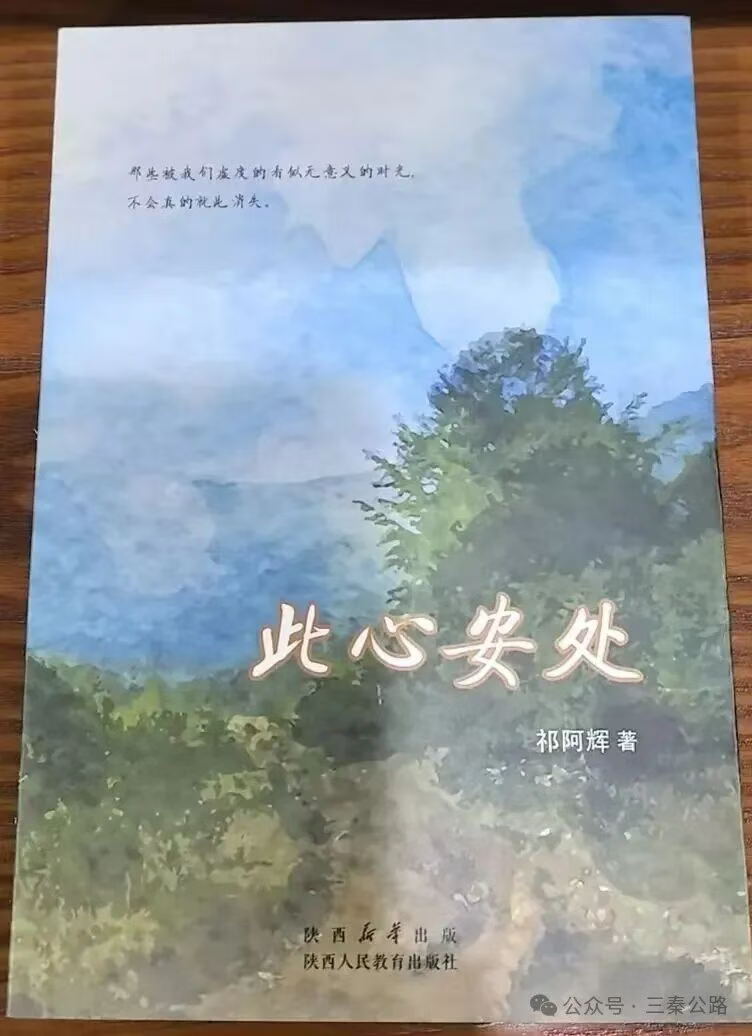
時光的云朵記憶的藤蔓
——祁阿輝散文集《此心安處》讀記
作者:張念貽
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和文學(xué)復(fù)興浪潮共同奔涌,那時的大學(xué)中文系女生,無疑都是天選的文字織女,是文山的攀登者,是文心的守護(hù)者、是文海的擺渡者。我所認(rèn)識的女性寫作者中,無不閃耀著黃金時代中文才女的光芒。九十年代初,從西北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的祁阿輝便是如此,散文集《此心安處》是她踩踏時光的織機(jī),繡出的一段文字的云錦;是她彈撥記憶的琴弦,奏出的一段如歌的行板。深情不負(fù)往事,如她所言:“那些被我們虛度的看似無意義的時光,不會真的消失。”
“此心安處”,固然出自蘇軾的名句,在祁阿輝卻不是信手拈來,她在自況里說:“曾渴慕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終不得不委身生活,困居古城鬧市。遂心安此處,浮生偷閑,游走街巷,邂逅煙火悠然,撿拾細(xì)小感動,絲絲溫暖……”這段文字讓我想起數(shù)年前,同是西大中文系出身的才女秋鄉(xiāng)寫我的文字“就像兩只師從一個師傅的靈獸,在人流里晃蕩,不經(jīng)意間一回身,竟然發(fā)現(xiàn)一個自己的同門,只一個眼神,時間和空間瞬間就坍塌了。”
《此心安處》是祁阿輝歸來的綻放,所折射的又何嘗不是王陽明“我心光明”的光芒。在“風(fēng)物隨想”“記憶告白”“行走筆記”三個錦盒里,分別裝著的十八到二十不等的錦囊,我想這些文字之于她,一定是敝帚自珍,歲月深深處,心有千千結(jié)。
她的“風(fēng)物隨想”,是一場隨風(fēng)奔跑的輕舞飛揚(yáng),風(fēng)的足跡天馬行空。開篇就淪陷在春深似海的季節(jié)里。她為觸目驚懷的一句”彎曲的時光“做注,篤信彎曲的時光,“一定是沉重的,有質(zhì)感的時光”;她對《風(fēng)》的定義,起句孤絕:“這世上最難以琢磨除了人心,就是風(fēng)”,風(fēng)的故事呼嘯而來,從鄉(xiāng)村少女的叛逆,到城市少婦的恬淡,切換到塞上大漠正午陽光下,一片風(fēng)沙中茁壯生長的向日葵,她像是在鋼琴上彈奏出風(fēng)的旋律:“我們所能感受到的風(fēng),總是連著云、連著月、連著土、連著沙、連著萬物,千姿百態(tài)、氣象萬千,神奇莫測,風(fēng)能去它想去的任何一個角落,誰也擋不住風(fēng)的翅膀”,她用她的文字刻刀,雕刻出風(fēng)的形象與風(fēng)的個性。倘若靈魂高蹈,生活便是芭蕾舞鞋的水晶腳尖,婀娜多姿又亭亭玉立于日常的瑣細(xì)。她所感悟的《微涼》,是在溫暖的年夜飯后,一陣夜風(fēng)微涼輕襲,敏感推己及人,在酒店電梯上、在地鐵上、在微信朋友圈里,像八爪魚一樣,伸出悲憫的觸角。她的《委身生活》,是一場靈魂的“下嫁”,對于一個《沒有故鄉(xiāng)的人》,《生活圈》似乎只是巴掌大的三點(diǎn)一線,但歲月的故事隨物賦形,《一些草木》中苦難的回甘,《年上,塬上》的悵惘,曾經(jīng)對紅色高跟鞋的渴慕生發(fā)出《奔跑的平底鞋》,這種對極致的取反,是云泥的參照,如《城也是村》《春天的落葉》《淺山的愜意》,風(fēng)中的隨想,可謂“星河欲轉(zhuǎn)千帆舞”,隨心、隨性,并不隨意,并不沉溺、拘泥,取而代之的是她抖出相聲和脫口秀的《包袱和梗》,她歸來依舊是少年的《江湖俠客》,快意恩仇。
她的“記憶告白”,是一場揮手往事的深情重逢,流年似水光陰如鏡。她與《七歲的帳篷》里的自己重逢,她與那個曾經(jīng)獨(dú)自一人走路的小女孩重逢,她的外婆、她的老爹、她的家人們、親人們一一登場。她與少女時代的偶像“千金大小姐”、她與曾經(jīng)熟識的街巷里炸油條的攤主“許大馬棒”重逢,她與同班外號“右邊的弧光”的女同學(xué)重逢,她與拾麥穗的女人重逢,她與花的主人重逢,不僅故人,還有故地,她與老屋的澇池重逢、與那些年的胭脂河重逢、與大學(xué)南路重逢,與曾經(jīng)的遇見,并肩戰(zhàn)斗的報社同事重逢,勾連出昔年的年歷、手表、遠(yuǎn)去的干煸豆角酸豆角、陜南深山的包谷酒,縱是似水流年,并非鏡花水月,當(dāng)歲月的鏡頭在文字里歷歷在目,也許記憶逐漸模糊,但情感的著色分外鮮亮, 故鄉(xiāng)與故事,在記憶里,盤根錯節(jié)又牽牽絆絆,終有一天,化作筆下最長情的告白。
她的“行走筆記”,是一場浪跡天涯的芬芳抵達(dá),繁花似錦俯拾皆是。從《早市風(fēng)云》到《在城邊閑逛》,再到《小館子》《街角的歡樂》《甑糕愛馬仕及涼粉三吃》,從《誰為阿房覓新賦》《西山邂逅楊二郎》,到《陜南背簍》《陜北行記》,再到《南京的秋》《淺嘗蘇州生活》《湘西小記》,從一個中年女子蝸居城市的煙火日常,到心馳神往無往不至的靈魂徜徉,她唱出藍(lán)田杏花谷的《三月芳菲》,她唱陜南秦巴的《只此青綠》,她能讀取《黃昏的語言》同樣能夠讀懂《塞上西風(fēng)》。當(dāng)然,她的邊走邊唱,帶著她作為公路人對“世間的路”的深沉的探問,不惜筆墨講述穿越秦嶺的寶雞244國道上的雪山洞道班的平凡夫妻的暖心故事,講述橫貫沙漠的靖邊210國道上曾經(jīng)的“柴草路”和“信天游”。
時光的腳步,如云朵的聚散,那么輕、那么重;記憶的脈絡(luò),似藤蔓的纏繞,那么柔、那么韌。祁阿輝說:“每一個無聲的日子看似庸常,仔細(xì)端詳,卻充斥著滴水穿石的堅(jiān)韌和巖漿炸裂的洶涌。”這是一種和光同塵,吹灰為羽的力量。我相信時光的云朵歷經(jīng)風(fēng)雨,終會照進(jìn)陽光,我也相信記憶的藤蔓蓬勃生長,終會開出繁花。
2025年11月29日北京魏公街
作者簡介:張念貽,作家、評論家、資深媒體人陜西省作協(xié)、美協(xié)會員,陜西省散文協(xié)會副秘書長。

 來源:石榴花文藝
來源:石榴花文藝
作者:張念貽
https://mp.weixin.qq.com/s/HNufTRhaj0BnF3Elj2VaFg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