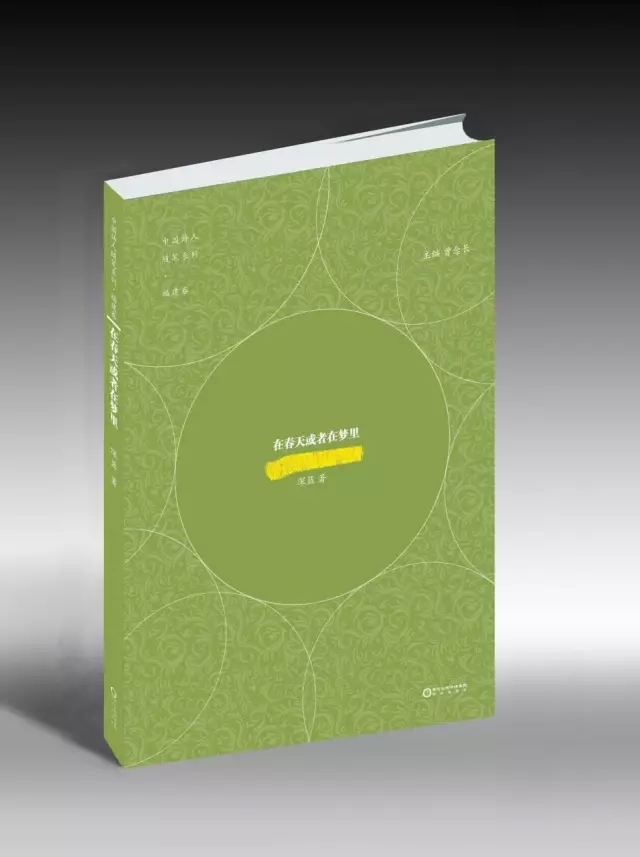
詩人深藍隨筆集《在春天或者在夢里》出版
詩人深藍隨筆集《在春天或者在夢里》2015年12月由陽光出版社出版。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的散文隨筆作品集。十年來,她是“小鎮上的單相思者”,也是“五里橋畔的夢囈者”。她從情感、生活、行走中的點滴感悟出發,自在隨意地書寫涂鴉。她的文字里有悲喜,有冷暖,有失落,也有希望。她向往遠方和彼岸,熱愛不羈與自由。她用感性溫暖的筆觸抒寫塵世里最最瑣碎的心情故事,以獨到開闊的視角思考生命的沉重與輕盈。她的文字,清新不失成熟,成熟不失純真。本書和安琪《女性主義者筆記》、魯亢《被骨頭知道》、老皮《知天命》、何奕敏《去遠方尋找自己》一起,構成“中國詩人隨筆系列•福建卷”書系,書系由福建省文學院曾念長博士作序。
目錄
時間的尖叫
以荷的氣質生活
回不去的故鄉
春天的禮物
明媚的憂傷
你也在這里
是否你已將我遺忘
讓我抱抱你
夢中的向日葵
我們的愛情
豆豆十歲
生活如舊
想念母親的粽子
畫出心中的美好
又見風的那端
落到一朵云上
開滿蘭花的峽谷
策馬歸來
純手工活
整個八月
人生如戲
此刻已然過去
翅膀隱隱還在
南方
雨季漫想
橋上的光陰
等愛的狐貍
你真正想要的
煙雨韶光
這個茶香彌漫的秋天
山城記憶
觸不到的戀人
如果塵世將你遺忘
現在還和相愛的人在一起嗎
在水上書寫
巴掌大的愛
親親,我的寶貝
花事
細微的存在
夢見一條會走路的魚
那個叫揚的情人
秋日清源
你的名字
清晨從橋上回來
是誰推開黑夜的門
似有暗香盈袖
通往春天的地鐵
突然很想你
從山中歸來
褪色的抒情
有時會突然忘了我還在愛著你
握緊回程的車票
行走江南
有誰是你
又見薔薇花開
這有點暗淡的人生隧道
云中誰寄錦書來
那場下了千年的雨
一個令人不解的偶然
空岸
塵世很遠,幸福很近
余生
我在這里活著
你永遠看不見最初的那個人
我始終堅持的
黯淡也是明亮的
彼岸咖啡
不舍
塵世的塵
匆匆
仿佛有所等待
孤獨的網
忽逢桃花林
像所有的天經地義
窗臺上的那只鳥
也寂寥也安謐
有座島嶼在那里
贈你一朵
像石頭陷入河流
就這樣走啊走
永不再來的夢
藍不是抽象的事物
老街轉角
彼岸花
每篇字都是一個殘局
你會不會像正午的鳳凰木
誰正灼灼盛開
“每一次分手都無可挽留”
那樣的兩棵樹
周漁的火車
夢里走過的路
恰似一朵煙花
山水有相逢
三峽行
深灰夜空,以及晚風
四月初的襯裙
突然間的自我
我在
小紙條
絢爛也許一時
“一直飛到你悲傷的心所在的地方”
銀色的光芒
遺失的一頁
挽歌
聽到春天逝去
自己的書房
當我老了
如塵如寄
原來不是那么寂寞
曾見一人
一個人走著
“我總是意猶未盡地想起你”
寂靜,也是喜悅
——————————
【書摘】
策馬歸來
深藍
傍晚天色黯然,似乎醞釀著一場雨。這樣的天氣,特別適合一個人到橋上走走。拎一把傘走下樓,沒走幾步,細雨迷蒙。好一場及時雨啊。
這個傍晚,一定是上天有意安排,讓我得以一個人安靜地行走。靜靜地走,聽著林木間追逐的風聲,細細的雨聲,聽著斑駁的歲月里心頭的蛩音。是的,我聽見了。
那一面湖,宛然恩慈的母親,敞開懷抱,迎接它遠行歸來的孩子,一個個頑皮的小雨點。那滴答滴答的聲音,是擁抱的聲音,還是輕輕的耳語?岸邊的廣玉蘭,美人蕉,在雨里怒放。有一種特別的寧靜與嬌羞。輕輕地拾起地上的一朵白色花朵,花瓣柔美,仍有余溫。讓我想起青春里的那一樹油桐,一地不忍踏過的芬芳。青春終是遠了,留下我們在未知的路上踟躇。此時的我,終于可以輕輕捧起一朵花,沒有憂傷,輕輕放下。那一樹鮮活的桃紅深紅,和著身后夏天蔥郁的深綠粉綠,徐徐展開一個雨后的夏日黃昏。
是不是會有一天,我可以站在春天的湖邊,用最溫柔的聲音告訴春天、湖水,告訴那只多少回游進我夢里的藍色水鳥,告訴這肅穆而活潑的自然萬物,我終于老了。用了很多很多的掙扎,很多很多的迷惘,很多很多的張望,終于抵達,安詳地老去。那時,會不會有清澈的雨水從眼睛里漫溢出來,上蒼恩賜的眼睛依然眷顧著我和我的世界?
又突然想起一首歌,試著哼出一兩句:讓我們紅塵作伴活得瀟瀟灑灑,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喜歡一個詞,策馬奔騰。人生的路千萬條,我們極少佇立凝望,只是策馬奔騰。很多人被路過,很多事來不及完成。然后有一天,站在歲月的盡頭,回望那蒼茫的來時路,會有一些遺憾和悵然吧。
打個電話,給誰?告訴他,這里只有一個人和一場雨,一面湖和一座橋,天然去雕琢的樹木花朵,灰色的天空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明凈柔和。或者發個簡訊給誰。告訴他,我在湖邊在橋畔,一把格子傘,撐開一小片晴空,其實不打傘亦無妨,雨下得未免溫柔,一點兒也沒有往常凌厲的撒潑。
終于還是沒有,如果此刻無人將我想起,也請讓我忘記塵世。一個人的漫步,天馬行空,以夢為馬。然后,在意念里系好我的那匹馬。我回來了。
2012.6.14

深藍:原名黃美瑜, 1974年生。小鎮上的女教師。書寫文字,作品散見于報刊。系福建省作協會員,泉州市作協會員。出版過詩集《等待一朵蕾》,散文集《靜寂的角落》。曾獲泉州青年文學獎等。現居福建泉州。
————————————
【總序】
走向“文學廣場”的詩人們
——《中國詩人隨筆叢書•福建卷》序
文/曾念長
就文學體式而言,散文與隨筆可并成一大類。若要一言以蔽之這類體式之特性,我斗膽說:公共性。它是眾多文學體式的公約數,也是無數社會性言說的公約數。所以,詩人、小說家往往要附帶寫寫散文或隨筆,學者、醫生、演員、商人和官員,數不盡的各行各業的人,都會跑到散文或隨筆這塊領地上卡遛一番。它是文學的“公共廣場”,無論你是專業的文學寫作者,還是其他社會領域的各路神仙,只要來到這個廣場,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學身份”,就可以以文學的名義說話,甚至聊聊文學本身的問題。
作為社會物理空間的廣場,天然具有兩種功能屬性:抒情性和議論性。在農村,村廟就是廣場。每逢佳節,村民在此狂歡;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論。在城市,廣場的雙重屬性在聚合,在放大,還變幻莫測地相互轉化著。君不見,三十年前廣場批斗小兵橫行,三十年后廣場歌舞大媽擾民。而我想說的是,散文和隨筆,作為純粹精神空間的“文學廣場”,也有這雙重屬性,并且它們在這個時代發生著復雜的轉換關系。
一般而言,散文親抒情,而隨筆親議論。這種天然分化與中國古代的文章學傳統并不相符,而是現代文學體式發生流變的結果。這里面不得不提魯迅的特殊貢獻。通過他的海量寫作,雜文從廣義的散文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以純議論為要義的文學體式。顯然,在這個體式茁壯成長的背后,隱含著特定的訴求:對社會公共問題的介入。其結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議論性分道揚鑣了。不過,自1990年代末以來,情況又有了新的變化。雜文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快速衰變為兩個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刪除了雜文的文學性,發展為大眾媒體時評;一支則向文學性回歸,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統,發展為隨筆寫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與隨筆的議論性在慢慢靠攏,“文學廣場”上的兩種聲調正在匯合。讓議論變得更加柔軟,讓抒情變得更加有力,這是世紀之交發生在“文學廣場”上的交響曲。
這套叢書名為“中國詩人隨筆叢書•福建卷”,其中對隨筆這一文體的界定,必須放在這個時代的“文學廣場”中給予具體的考察。隨筆不僅僅是一事一議,而是在與散文大統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學廣場”,走向遼闊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說過,21世紀的寫作是隨筆的寫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證癖的人能夠考證出這句話出自何人。如果“查無此人”,那就當是我說的好了。就文體的普適性而言,我以為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隨筆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章”,可長可短,可記事可議論可抒情,可寫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體不可比擬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從各種狹窄、僵硬的言說空間中溢出的話語。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種言說體式,唯獨如此,它才能夠呈現言說者的真誠品質和精神形狀。詩人于堅認為存在一種“散文化的寫作”,它是“各種最基本的寫作的一種集合”,其“出發點可以是詩的,也可以是小說的、戲劇的,等等”。我理解于堅所說的“散文化的寫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們的文體觀念接受了的隨筆。它是一種最公共的寫作,也是一種最自由的寫作。這種寫作本身,就是個體言說與公共言說的有效結合。
有一種傳說試圖指出,福建是一個“詩歌大省”。如果僅僅是指詩人的數量和影響力,我以為這種傳說言過其實。哪個省域不是詩人成群?又有哪幾個省域舉不出若干有影響力的詩人?但我以為,如果是指詩人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詩人及其寫作是極具典型性的。從歷史上看,閩人文學長于詩文,而對小說幾乎沒有什么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這種宿命的循環。其中的原因,很難給出一個實證性的定論。一個較具有說服力的觀點認為,閩地方言制約了閩人的大眾化寫作,因而也就失去了進入白話小說領地的優勢。這一說法或許不假,但我以為還有一個因素是需要認真對待的,那就是閩人精神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內排遣”傳統。閩人是習慣于自我言說的。他們往往向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尋找人生問題的答案。在依然保留著傳統生活氣息的鄉村地區,拜神依然是許多福建人極具日常化的行為。他們習慣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語,實則是在與自己的心像一問一答。這種向內延伸排遣路徑的精神構造,也正是詩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說指向社會的豐富性,詩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個人內心的細密紋理。閩人對詩歌、散文以及散文詩的偏愛,或許正是緣于此。他們的天然節奏不是東北人的嘮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為外部表征的內心絮語。這種精神特征也讓閩人背負了一項無端的罪名,那種通往內心的訴說與自救,往往被假想為深不見底的心計。我以為這實在是一種誤解。人們對自我言說的恐懼與排斥,在“早請示、晚匯報”的時代一度達到極致。如果我們不理解自我言說是人類話語結構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們為什么要反駁那場極端化的話語運動。正是在這一點上,以蔡其矯、舒婷為代表的福建詩人,憑著對自我言說的時代性覺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詩潮中成為一面旗幟,也為福建詩歌贏得了至高的榮譽。
作為一種帶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詩人(也包括批評家)依然保持著如隱士般構建自己的內心世界的精神傳統。如廈門的舒婷、陳仲義,福州的呂德安、魯亢等等,他們對這個時代的公共話語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詩人一樣甚囂塵上。與其說這是詩人的一種刻意姿態,不如說這是詩人的一種心靈隱喻。詩人就是這個時代的隱士。他們是一種逃遁式的存在,真實地輻射著一個時代的精神氣場,卻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陽來到了隱士的家/隱士卻不在家”。這是江蘇詩人胡弦的詩句,在此我愿意借它來闡明這個時代的詩人的心靈志。但我還想說的是,現代詩人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絕于世。他們往往還借助詩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與外部世界進行對話。在此意義上,我們這個時代不乏有令我們素然起敬的國內同行。比如于堅,這位自稱“在散文寫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詩人,實際上是通過隨筆這條言說通道重新抵達時代現場,將文學的態度和立場帶入大地與環境、建筑與城市、本土化與全球化等一系列社會性問題。再說王小波,他不是詩人,卻在小說中前所未有地開辟了自我言說的路徑,因而比許多詩人更早抵達詩性的精神國度。即便如此,他還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時代議論的隨筆寫作,并稱這是知識分子在承擔應有的道義和責任。我想詩人寫作隨筆的意義也許就在于此。詩人不僅僅是詩人。他首先是個人,具有每個人通常都有的兩面性,以及由兩面性拓展開來的多面性。當詩歌在表達一個人的多面性時變得言不及物,詩人就會借助另外一種表達形式,以探求詩人與世界之關系的多種可能性。寫隨筆就是詩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間的一種有益嘗試。正如前文所言,隨筆是“文學廣場”,是個體言說與公共言說的交匯地帶,也是詩人出來卡遛的絕佳場所。
我想這套叢書的多數作者是以詩人為身份自覺的,因此才有“詩人隨筆”一說。這么說來,我們似乎可以將這些隨筆作品看作是詩人的“副產品”。一個成熟的詩人對自己的作品是極為苛刻的,我想他們對自己的“副產品”也應抱有同樣的態度。至于這些隨筆寫得如何,實無由我評說的必要。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費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這個機會,談談對寫作的兩種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現在我眼前的這些隨筆作品,更多是延續了福建詩人的自我言說的精神傳統。這種“路徑依賴”是一種常見現象,也符合詩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數人的閱讀期待。一位學者來到廣場,未必就能拋棄書齋里的習慣,遇見新鮮事恐怕要尋根究底一番,甚至與自己“死磕”。這在許多人看來是合乎常理的。依此類推,詩人出現在廣場,也有自己的習慣性方式。他們左顧右盼,略帶神經質,卻不愿參與任何“群眾聚會”,就像傳說中的“打醬油”者,一溜煙又飄走了。我作此類比,僅僅是想說明,詩人自有詩人的專注精神。詩人最關心的,終究還是自己的內心世界。即便是寫隨筆,他們還是習慣于將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靈空間。這本無可厚非,但又何嘗不是一種遺憾!時代的聲音牽扯著人心,我們又豈能充耳不聞?但我并非是要主張詩人們去做單刀直入的社會時評家。詩人自有表達時代經驗的獨特方式。像安琪一樣立誓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將詩人與時代的緊張關系和左沖右突毫無保留地呈現在字面上。或像魯亢一樣寫留學往事,寫對疾病與死亡的深度凝視,并將它們與讀萬卷書的知性體驗融為一體,再和盤托出。凡此種種,都是詩人介入公共言說并借以重構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嘗試。
我之于這套叢書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讀者了。這里我指的是他們的詩歌。對于他們的隨筆作品,我卻讀得較少。我愿意將這一次的集中閱讀,當作一次發現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識的詩人,其實還有著不為人知的更為豐富的一面。
2014年12月

曾念長:文學博士,現供職于福建省文學院。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