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劉秉政中短篇小說(shuō)集《對(duì)稱(chēng)軸》出版發(fā)行
近日,作家劉秉政中短篇小說(shuō)集《對(duì)稱(chēng)軸》由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小說(shuō)集收錄不同時(shí)期作品13篇,題材涉及人生價(jià)值、青春、愛(ài)情、婚戀以及對(duì)人生意義的追問(wèn)和思考。每一篇都呈現(xiàn)著嚴(yán)肅與堅(jiān)硬的文學(xué)質(zhì)地。古典意象和現(xiàn)代主義元素的有機(jī)融合,神話(huà)、科幻、寓言、象征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介入,同時(shí)以豐富的想象力作為文學(xué)探索的有力觸角,是作品的鮮明特色。
本部小說(shuō)集亦可看作是作者致敬青春之作,是作者前半生的一個(gè)文學(xué)小結(jié)。作者立足于自己和當(dāng)代青年的心路歷程,完成了對(duì)愛(ài)情精神的崇高解讀,兩性關(guān)系的另類(lèi)探索以及存在意義的深度靜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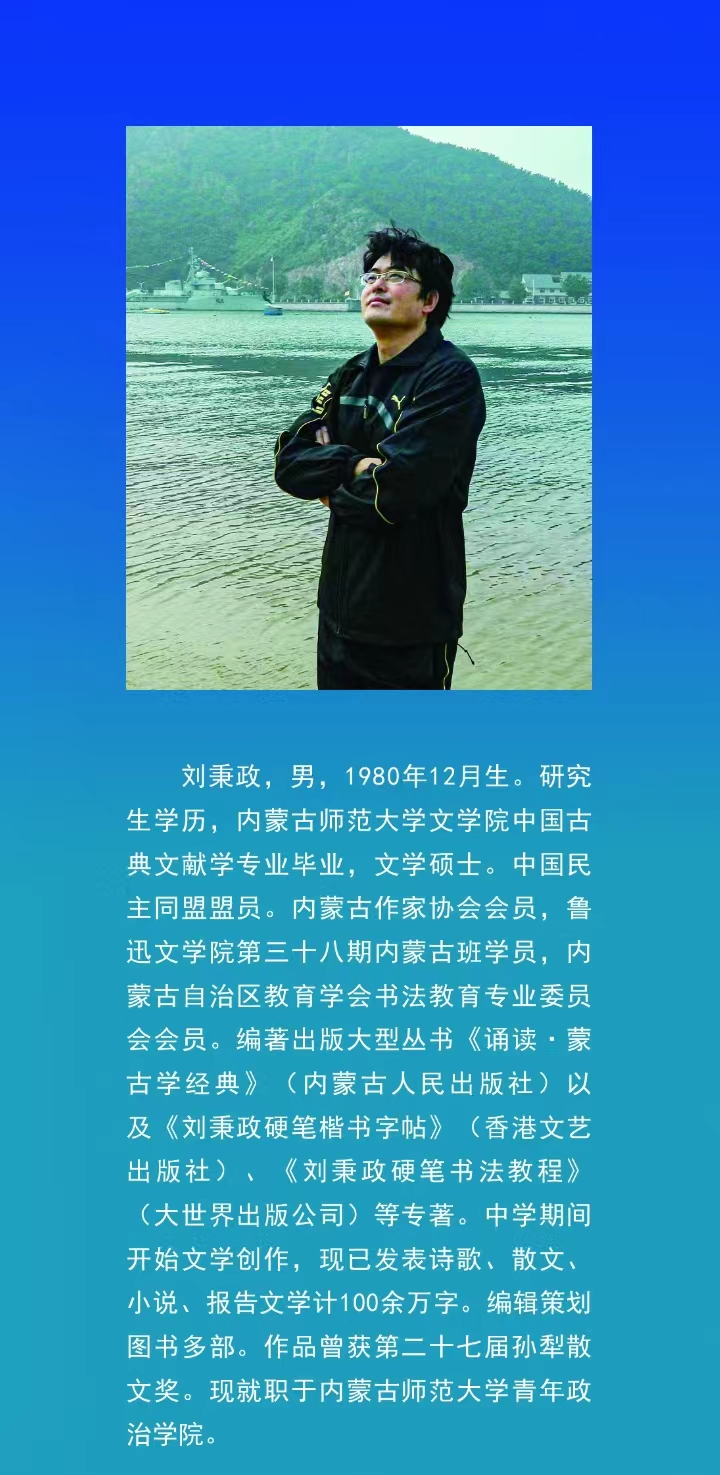
附:創(chuàng)作談
踽步在對(duì)稱(chēng)軸
——小說(shuō)集《對(duì)稱(chēng)軸》創(chuàng)作談
作者:劉秉政
這部小說(shuō)集里收錄了十三篇小說(shuō),有短篇,有中篇。從創(chuàng)作時(shí)間來(lái)看,最早的一篇《一個(gè)幽靈的日記》創(chuàng)作于 1999 年,最晚的一篇《對(duì)稱(chēng)軸》完成于 2022 年。
《一個(gè)幽靈的日記》中兩個(gè)同樣找不到出路的年輕者,一個(gè)是人,一個(gè)是鬼,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交集。然后就是愛(ài)情主題了。說(shuō)愛(ài)情也不是很確切,這里只有失敗的男女關(guān)系。是關(guān)系失敗后身體的割裂感和不完整感,乃至整個(gè)宇宙秩序的傾斜感。《桃之夭夭》是這個(gè)系列的第一篇,完成于 2002 年初。當(dāng)時(shí)我兼具劇中人和觀察者雙重身份,想讓全世界和我“共情”。這個(gè)作品差不多是一種平移,一種從人生舞臺(tái)到戲劇舞臺(tái)或藝術(shù)舞臺(tái)的平移。這個(gè)故事像一個(gè)夢(mèng)一樣,不知是從什么地方忽然一下子注入我腦子里的。題記中所提及的“儀式”指的就是婚姻。我用一種寓言的方式詮釋了婚姻的價(jià)值指向。父母(文中花母就是待嫁女兒母親的化身)大多希望女兒嫁給有錢(qián)有勢(shì)之人,以為這是最好的歸宿。這篇作品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還是在探討“不擇手段式的自我完成與恪守善良式的自我完成”這一亙古話(huà)題。婚姻,在這里只是作為一種外在的價(jià)值考量。毫無(wú)疑問(wèn),世俗的婚姻只會(huì)選擇前者。因?yàn)榍罢吒欣谌〉蒙媾c發(fā)展資源。只是為了生存。悲劇一直在完全重合般輪回著。
《后園》是我好幾年沒(méi)動(dòng)筆寫(xiě)作之后的一個(gè)大動(dòng)作,是經(jīng)歷身心飄蕩,安全上岸后一次時(shí)間、空間、思想、情感的大梳理。寫(xiě)作的那段日子里,我長(zhǎng)時(shí)間地徘徊在那些留下印記的漂泊之所,一遍遍傾聽(tīng)并記憶著那教父般和我對(duì)話(huà)的聲音。那聲音不知來(lái)自何處,卻使我欣慰、寧?kù)o,一步步地靠近崇高。后來(lái)我才發(fā)現(xiàn),那個(gè)聲音的節(jié)奏,就是《后園》里不折不扣的感情基調(diào)與思想脈絡(luò):“后園真正的主人是一群野鴿子,我其實(shí)不知道它們的真實(shí)稱(chēng)謂,似鴿又比鴿稍小,全身深灰色,不見(jiàn)作長(zhǎng)途飛越,只是悠閑地滑翔而過(guò),從一個(gè)枝頭落到另一個(gè)枝頭,讓人眼睛里布滿(mǎn)了眨不去的灰影……”自此,有一個(gè)地方永遠(yuǎn)為我荒蕪著,平淡著。直至“在一個(gè)有限的空間里靜靜地感受著無(wú)限的時(shí)間……而這個(gè)空間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又將是一個(gè)大雪飄落、野鴿紛飛的后園。”如此完成了我自己。
《潮白河邊的女人》嚴(yán)格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是寫(xiě)家鄉(xiāng)性格的,或者說(shuō)是寫(xiě)地區(qū)性格的。這種性格是設(shè)定在“存在主義苦難” 抑或稱(chēng)為“原苦難”的背景下展開(kāi)的。潮白河是流經(jīng)我故鄉(xiāng)的一條河流,評(píng)劇是我們那里的地方劇。我在故鄉(xiāng)一共生活了十二三年,我熟知的那些長(zhǎng)我一輩的女人們都已老去,甚至死去,像我的母親一樣。但是她們的言語(yǔ),她們的神態(tài),她們的性格,我至今難忘,就像評(píng)劇女主人公唱腔里的吞言吐字的一板一眼,鏗鏘有力中表現(xiàn)著一個(gè)女人的不屈不撓、有理有據(jù),構(gòu)成家鄉(xiāng)性格中非常典型的東西。
《愛(ài)情實(shí)驗(yàn)》是思念成疾之后痛苦的私生子。美是深情。當(dāng)思念以回憶和想象的方式形成了與現(xiàn)實(shí)生活并列的一條平行時(shí)空后無(wú)法再進(jìn)行下去,或者達(dá)不到預(yù)期的結(jié)果時(shí),科幻再次登場(chǎng)了,它的作用和神話(huà)別無(wú)二致,是一個(gè)飽受離別之苦的癡情人能想到的,以最樸素的方式,完成生命中最鄭重的自我救贖。思念是我經(jīng)常所處的情感狀態(tài)。前幾年的一個(gè)深冬,我走進(jìn)一條雜亂的街道去上課(就和故事開(kāi)頭男主人公所經(jīng)歷的一樣),那些關(guān)于愛(ài)情的理論忽然在腦子里成型了:肉體和精神高度契合的有情人分開(kāi)后,其“情熵值”會(huì)很低,并且會(huì)遺傳下去,現(xiàn)代人的情感純度和質(zhì)量,相比古人,有較大幅度下降……于是,拯救者也是自救者來(lái)了。
《對(duì)稱(chēng)軸》是這部集子的最后一篇。有些終極意義,也有些終結(jié)意義。這個(gè)作品其實(shí)源于一個(gè)老命題:前世修好修善,來(lái)世就會(huì)有一個(gè)好的歸宿。沒(méi)錯(cuò),這是對(duì)彼岸的一個(gè)探索。我相信這是很多人都想過(guò)甚至終其一生都在想的問(wèn)題。二十年前,我因?yàn)榭佳腥ヒ凰髮W(xué)的學(xué)生宿舍見(jiàn)一位大學(xué)生,他那里有我需要的復(fù)習(xí)材料。他比我小好幾歲,卻顯得異常穩(wěn)重和冷靜。當(dāng)時(shí)不知為什么談到了那個(gè)問(wèn)題。他搖搖頭說(shuō):“我看不會(huì),來(lái)世會(huì)和此生一樣,會(huì)照搬此生的命運(yùn)狀態(tài)。”這讓我心頭一震。明知我們的問(wèn)答可能都屬于無(wú)稽之談,但他的回答還是給了我很大的不安。從此,對(duì)稱(chēng)觀念,即此岸與彼岸的對(duì)稱(chēng)性夢(mèng)魘般籠罩著我。
我沒(méi)搬家前的那個(gè)住所旁有條廢棄了幾十年的鐵路,是一條運(yùn)輸內(nèi)線(xiàn)。我每次上下班都會(huì)沿著這條鐵路走一段時(shí)間。望著長(zhǎng)長(zhǎng)的鐵路線(xiàn),便形成了“對(duì)稱(chēng)軸”這一意象。我們每天走在“對(duì)稱(chēng)軸”上。《對(duì)稱(chēng)軸》中,貫穿一個(gè)個(gè)透明格子間的那條長(zhǎng)長(zhǎng)的金屬線(xiàn)是對(duì)稱(chēng)軸,那個(gè)“中轉(zhuǎn)站”是此岸和彼岸的對(duì)稱(chēng)軸,活著或者說(shuō)有意識(shí)的任何一個(gè)瞬間,都在對(duì)稱(chēng)軸上。這部集子每一個(gè)故事中的人物何嘗不是孤獨(dú)地行走在對(duì)稱(chēng)軸上?也正如現(xiàn)在,我活著,我有意識(shí),我正在對(duì)稱(chēng)軸上寫(xiě)著文字,所以不妨以此篇的名字命名整部書(shū)——《對(duì)稱(chēng)軸》。

附:評(píng)論
人與命運(yùn)的對(duì)稱(chēng)
——簡(jiǎn)評(píng)劉秉政小說(shuō)集《對(duì)稱(chēng)軸》
作者:趙卡
在這本小說(shuō)集正式出版之前,我已提前讀完了。應(yīng)該說(shuō),讀完后我有點(diǎn)無(wú)話(huà)可說(shuō)的感覺(jué),因?yàn)樽髡邉⒈谛≌f(shuō)集的自序中把他這十三篇中短篇小說(shuō)基本說(shuō)明白了,核心意思只有一點(diǎn),人與命運(yùn)的對(duì)稱(chēng)。所以,我認(rèn)為拿“對(duì)稱(chēng)軸”這三個(gè)字做書(shū)名再恰當(dāng)不過(guò)了。
《一個(gè)幽靈的日記》最后一句把我震驚了——“我又把自己殺死了一次。”這篇小說(shuō)據(jù)作者說(shuō)寫(xiě)于1999年,那時(shí)他剛20歲,就寫(xiě)出了意識(shí)和技法如此老練的作品,有點(diǎn)胡安?魯爾福在他的傳世之作《佩德羅?巴拉莫》里的那種恍惚感。《桃之夭夭》是一個(gè)以花言志的架空題材的小說(shuō),有點(diǎn)像現(xiàn)在流行的古言網(wǎng)文,其意思作者在自序中已經(jīng)說(shuō)清楚了。《玉生煙》篇幅短,行文凄美甚至絕望,寫(xiě)了一種對(duì)命運(yùn)控制的象征物,有審判意味。《白日》的篇幅也很短,白日熠熠卻調(diào)子陰冷,寫(xiě)一個(gè)人為了愛(ài)而悲壯赴死,像神話(huà)故事一樣具有神秘感。《天鵝之死》寫(xiě)得太凄涼了,完全是童話(huà)和神話(huà)的路子。《化異》完全是網(wǎng)文的寫(xiě)法,不是神話(huà),是神幻類(lèi)的小說(shuō),講的是一個(gè)拒絕被同化也拒絕被異化的故事,主題好,語(yǔ)言也非常精致,我有一種設(shè)想,如果作者能將這個(gè)故事拉長(zhǎng)5倍,應(yīng)該是一個(gè)不錯(cuò)的中篇網(wǎng)文小說(shuō)。《斷碑》很短,寫(xiě)由人到馬的輪回,還是神話(huà)式的,標(biāo)題給人一種山崩地裂的感覺(jué)。《釀蜜》更短,但故事讓人有點(diǎn)匪夷所思。
一口氣讀完以上這8篇寓言式的小說(shuō),除了《一個(gè)幽靈的日記》《釀蜜》,其余6篇的內(nèi)容都和愛(ài)情有關(guān),都寫(xiě)到了死亡。可以看得出來(lái),作者很在意文本的形式感和對(duì)語(yǔ)言的考究,而故事本身,似乎處理得有點(diǎn)簡(jiǎn)單了。還有一點(diǎn)我不得不說(shuō),作者雖然寫(xiě)得短,但不克制,因?yàn)橐宫F(xiàn)人格化或神格化的靈魂,就難免要煽情,卻又無(wú)不彰顯著堅(jiān)硬的文學(xué)質(zhì)地。作者曾在私下里跟我講過(guò)——他應(yīng)該是自謙——這本書(shū)的前半部分展示出來(lái)的作品略顯不成熟,我為這是作者對(duì)自己的略顯粗糲堅(jiān)硬的指控和審判,他在憋著一股不服的氣。
小說(shuō)《后園》其實(shí)不是一個(gè)小說(shuō),準(zhǔn)確說(shuō)是一篇令人動(dòng)容的散文,在氣質(zhì)上有點(diǎn)像史鐵生那篇不朽的《我與地壇》,情景思合一,作者思考了貧困、疾病 、厄運(yùn)、愛(ài)情、死亡等問(wèn)題。我之所以說(shuō)《后園》不是一個(gè)小說(shuō),在于作者對(duì)敘事保持了一種非常克制態(tài)度;我覺(jué)得《后園》的整體敘述還是很不錯(cuò)的,作者努力在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記憶片斷上建立了一種重現(xiàn)的表述,使我們能適應(yīng)這種文字的細(xì)膩。《潮白河邊的女人》是一篇呈現(xiàn)地方性風(fēng)俗又飽含深厚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作品,白描了中國(guó)農(nóng)村普遍存在的諸如人際、婚嫁和不斷貶值的日常經(jīng)驗(yàn)等社會(huì)問(wèn)題,付諸于作者筆下的故事悲傷而陰森,尤其是女人們艱難而悲慘的命運(yùn)令人心有戚戚然;我中意作者極其老辣地道的具象化敘事語(yǔ)言,顯然十分契合這種題材的小說(shuō)。
不可否認(rèn),或者說(shuō)我完全沒(méi)有料到,《愛(ài)情實(shí)驗(yàn)》是一篇帶有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元素的先鋒性小說(shuō),主人公的愛(ài)情記憶在一個(gè)神秘機(jī)構(gòu)的物理、醫(yī)學(xué)和心理學(xué)實(shí)驗(yàn)的加持下,交纏于現(xiàn)實(shí)和夢(mèng)幻之中;作者啟用并結(jié)合了賽博朋克的形式,虛實(shí)的角色在虛實(shí)的空間中出入,這種介入時(shí)間的結(jié)構(gòu)方式令人感到非常驚艷。《青春期》是一篇探討家庭倫理的小說(shuō),展現(xiàn)了偷窺、性欲和背叛的人類(lèi)通病;一個(gè)美麗的少女長(zhǎng)著一個(gè)尾巴似的的尾椎骨,醫(yī)生從生理生殖學(xué)角度分析后斷定,這是一種返祖現(xiàn)象——不由讓人想到馬爾克斯在他《百年孤獨(dú)》里的那個(gè)豬尾巴梗,但女孩出于對(duì)家庭的不信任而拒絕手術(shù)。這篇小說(shuō)大膽而獨(dú)特,作者似乎有意放任語(yǔ)言的泛濫,給人一種饒舌式炫技的感覺(jué)。
《對(duì)稱(chēng)軸》這篇小說(shuō)放在這本小說(shuō)集的最后,的確起著壓軸作用。這是一篇充滿(mǎn)了隱喻卻又怪異的亡靈敘事之作,通讀下來(lái)給人一種強(qiáng)烈的卡夫卡式小說(shuō)的感覺(jué),既荒涼又荒誕,荒涼的是命運(yùn),荒誕的是意識(shí)。作者在故事里為自己精心設(shè)置了一個(gè)對(duì)稱(chēng)面,生與死的二元對(duì)立意義在細(xì)節(jié)中不動(dòng)聲色地展開(kāi);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shuō),作者僅以此一篇就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敘事性風(fēng)格。
就劉秉政目前的小說(shuō)看,他絕大多數(shù)作品是青春期似的抒情寫(xiě)作,據(jù)我私下了解,源于多年前的一個(gè)女人給他生命留下的深深刻痕甚至死穴,他努力去消解,用時(shí)間,用文字。《潮白河邊的女兒》《青春期》《對(duì)稱(chēng)軸》這三篇是敘事的,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的是,劉秉政在初始寫(xiě)作時(shí)就試圖不落入他人的窠臼,但也造成了他自己的風(fēng)格困境,所以到了2022年的《對(duì)稱(chēng)軸》這篇小說(shuō),他的風(fēng)格上的一致性才算中斷。這種中斷,我不認(rèn)為他是在做自我糾正的努力,而是他要檢驗(yàn)他在小說(shuō)上一種信念,就是小說(shuō)里作者和文本的互文性,就是要在小里發(fā)現(xiàn)人的命運(yùn)。
劉秉政還年輕,未來(lái)可期,我真心祝愿他今后的小說(shuō)越寫(xiě)越好。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